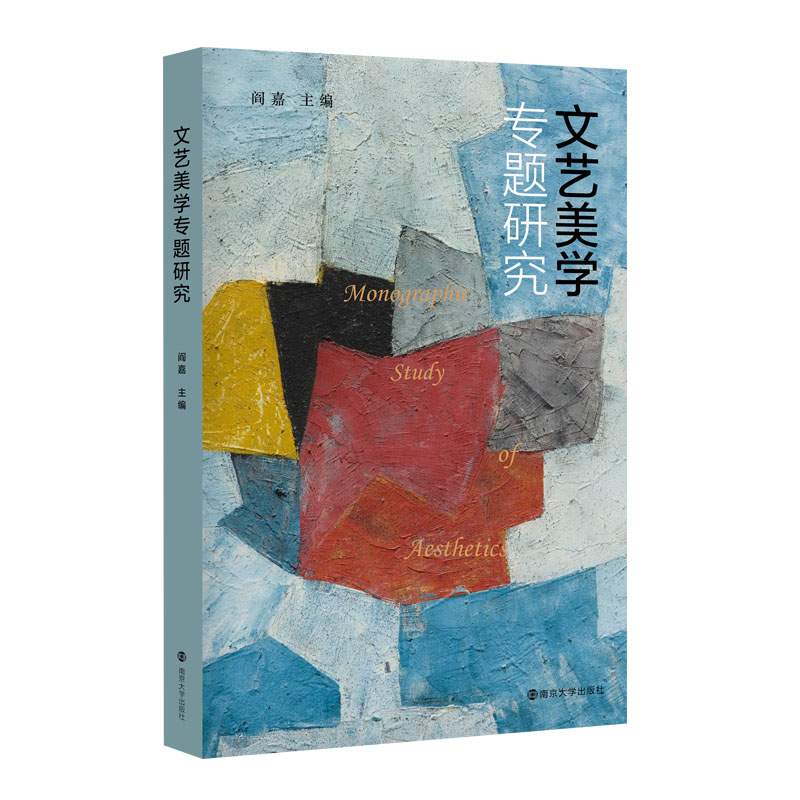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75.00
折扣价: 46.80
折扣购买: 文艺美学专题研究
ISBN: 9787305243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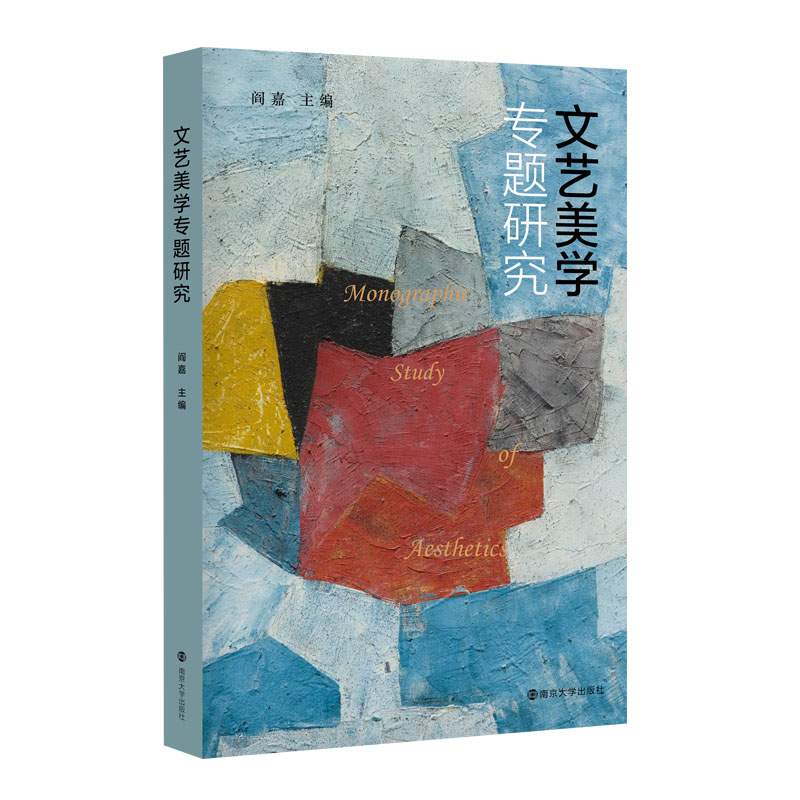
阎嘉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美学学会会长。著有《马赛克主义》等多部作品,译著有《后现代的状况》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美学思想的诞生与发展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随着生存能力的提升、思维水平的发展,以及关键的文字的出现,原始社会时期那些直观的、感性的、朦胧的审美意识逐渐演变成相对明确的观点、概念和范畴。人类希图揭示出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中某些带有本质性和规律性的内容,审美活动开始具备初步的理论形态,并通过书面文本的形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当然,在18世纪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的美学思想基本上还是混杂在历史文献或哲学典籍中,美学未能从哲学、伦理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没有出现依据自觉的学科意识来系统建构的美学著作。全面地、详尽地对这一历程进行总结和论述,是多卷本的美学发展史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只能做一简要的、粗线条的勾勒。 西方美学思想源远流长。早在《荷马史诗》中,就零星地表现出了对美的感知,诗中对阿喀琉斯盾牌的赞美,对海伦美貌的惊叹,都包含着诗人对美的意象的青睐。但那时文艺作品中出现的对于美的描写,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书写,并不具有概念性。真正从哲学意义上来讨论美学问题,一般认为是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由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的团体,他们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世界的本质为数,而数的和谐构成了整个宇宙的和谐,而美就孕育在这一和谐中。他们从探求音乐节奏的和谐出发,将音乐视作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将杂多导向统一,将不协调导向协调,并将这一原理推广至建筑、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试图找出数量、比例与美之间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的和谐的观点使得造型性成为希腊美学的重要特征,这也促成后来美学中形式主义思想的萌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35—前475)在他的《论自然》中提出,和谐产生于对立和斗争之美,具有相对性等特点,初步具有了哲学思辨的色彩。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约前460—前370)在《著作残篇》中将人比作“禽兽的小学生”,人从蜘蛛那里学会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造房,从天鹅和黄莺等鸟类那里学会唱歌。这种朴素的“模仿说”,连同其“灵感论”以及对美和艺术的思考,给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以直接的思想启迪。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著述,只有他的学生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前355)的回忆和柏拉图的记录。然而,在色诺芬和柏拉图的笔下,呈现的却是两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苏格拉底形象。在色诺芬的《会饮篇》中,相貌丑陋的苏格拉底和美男子克里托布鲁有一段关于“比美”的对话,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美于克里托布鲁,理由是克里托布鲁的“眼睛只能朝正前方直接看过去,而我双眼凸起,目光旁射,所以能够朝两边看”;而且“你的鼻子朝下,直冲着大地;我的鼻子宽大,敞开着,就好像从各个角度迎接芬芳的气息”。这则对话通常被认为是苏格拉底 “美是效用”的观点的例证。然而,在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中,在经过和希庇阿斯的一番讨论之后,苏格拉底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说道:“那么,我恐怕我们的美就是有用的,有益的,有能力产生善的那一套理论实在都是很错误的。”他无法给美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无法为美设定一个明确的范围,只能得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美是难的”。虽然在色诺芬的回忆和柏拉图的记录中,苏格拉底关于美的见解有些摇摆而且不甚明了,但依然可以看出,苏格拉底逐渐摆脱了前人从自然科学角度思考美学问题的路径,转而从哲学抽象思辨的角度来探讨美学问题,这是西方美学史在思维和方法上的一次重要转变。 经由上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推动,西方美学思想在柏拉图手里形成了第一次大综合,而亚里士多德通过第二次大综合基本奠定了西方美学思想的哲学传统。在他们师徒二人的许多著作中,虽然美学问题只在讨论政治、伦理、教育等其他问题时被附带提出,但毫无疑问,今天西方美学中依旧被学者们激烈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他们那里早已经被涉及。比如,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中讨论了“美是什么”的问题,从个别事物的美到美之所以为美的“美本身”,尽管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得出的结论是“美是难的”,但他的讨论至今仍然富有启示性,即便到了当下,学者们依然很难准确明晰地说清楚“美”到底是什么。另外,柏拉图的讨论还涉及艺术的本质与特征、人类的创作才能、审美经验和审美教育等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依然居于时下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作为柏拉图继承者和推进者的亚里士多德,“既批判师说而又继承师说”,将柏拉图“影子的影子”发展为“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的”,肯定了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将艺术上升到可以表现真理的高度。同时,亚里士多德关于美的“整一”性,艺术的功用以及悲剧心理学说的观点,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应该说,之后西方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是沿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他们关于美和艺术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分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他们两人的观点交错地影响着西方美学史和艺术史的发展进程。 概括地说,柏拉图创造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美学体系,提出了“美是理念”(idea)的命题。他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源,万事万物都是“理念”的“分有”,是“理念”的影子。理念高高盘踞在上,无始无终,无增无减,是永恒的,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分享了美的理念才变成了美的事物,他著名的“三张床”理论即源发于此。柏拉图认为,人们在制作一张床之前,一定先有一个床的理式存在于脑海中,然后人们按照这个床的理式造出现实的床,而艺术家又按照现实的床模仿出作为艺术品的床。按照今天的美学眼光来看,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具有典型的“本体论”色彩,他试图从众多美的现象中寻找美的普遍性,追问“美本身”到底是什么。后世的诸多美学家沿着柏拉图的道路寻找美的本质,提出了“美在关系”(狄德罗)、“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等观点,形成了一条本质主义的美学研究路径。另外,在“理念”论基础上探讨艺术的社会功用时,柏拉图认为一些艺术作品(主要指诗歌和悲剧)伤风败俗、亵渎神灵、迎合人性中的低劣部分,对城邦正常的健康生活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是有害的。他的“灵感”说和“迷狂”说,都建立在此哲学思想之上,这也是西方美学发展史上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在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