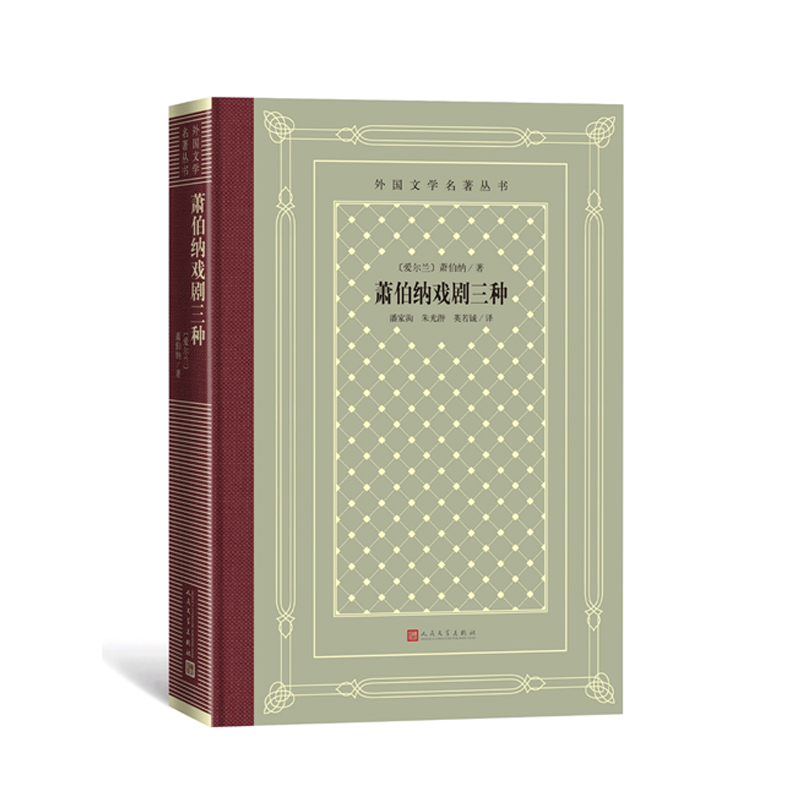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85.00
折扣价: 46.80
折扣购买: 萧伯纳戏剧三种/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020170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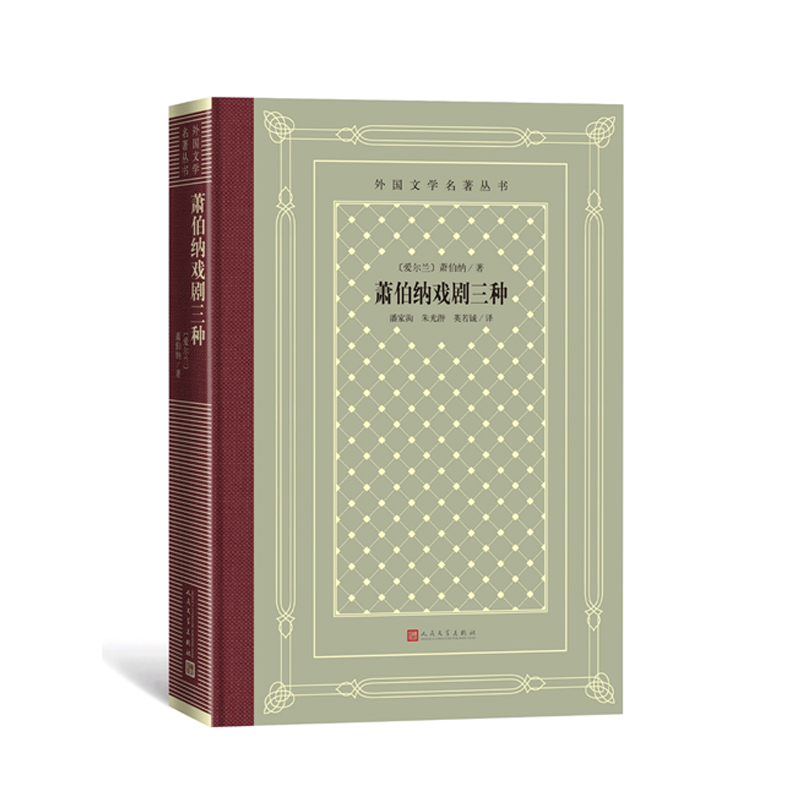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 爱尔兰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共写了大小五十一个剧本,数量之大,英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代表作有《华伦夫人的职业》《芭巴拉少校》《匹克梅梁》《圣女贞德》等。192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将伦敦的剧坛同当时欧洲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也与以阿里斯多芬和莫里哀为代表的欧洲古典喜剧传统相结合。 译者简介: 潘家洵(1896—1989) 江苏苏州人。翻译家。代表译作有《易卜生戏剧集》(四卷本)、《萧伯纳剧作选》、《扇误》等。 朱光潜(1897—1986) 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著有《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译有《歌德谈话录》《文艺对话集》《拉奥孔》等。 英若诚(1929—2003) 北京人。翻译家、演员。著有《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译有《推销员之死》《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等,主演或参演《推销员之死》《茶馆》《龙须沟》《末代皇帝》《围城》等戏剧、影视作品。 王佐良(1916—1995) 浙江上虞人。翻译家。著有《英国诗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英国文学史》等,所译诗人数十位,远可至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廉·邓巴,近可达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菲力浦·拉金,译作还包括《雷雨》(与巴恩斯合译)及大家耳熟能详的散文名篇《论读书》(培根著)。此外,在翻译理论上亦多建树。
译本序(节选)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是世界闻名的戏剧家,但是他却不是从小就立志要写剧本的。在少年时代,他爱好绘画和音乐,一度想做一个像米开兰琪罗那样的画家;而在音乐方面,由于他母亲的熏陶,从小练钢琴,学唱歌,熟悉歌剧犹如普通孩子熟悉冒险故事。后来他到伦敦,失业达九年之久,忙于参加群众活动,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兴趣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使他注意起戏剧来的,是易卜生。一八八八年左右,马克思的女儿伊林诺拉他参加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业余演出,扮演柯洛克斯泰一角,虽然据萧自己回忆,这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当时是莫名其妙的”。接着,有一次,剧评家威廉·亚秋口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一剧给他听,他感到“一刹那间这位伟大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叫我同时领悟到他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的重要性”。萧的小说《无理之结》序。于是他对易卜生的剧本进行了研究。一八九○年他做了有关这位挪威戏剧家的公开演讲,次年将讲稿整理出版,便成为有名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书。 这本书是近代欧洲戏剧史上的重要论著;一个大戏剧家受到了另一个大戏剧家的阐释,前者已经震惊全欧,后者即将崛起。通过易卜生,通过易卜生的《群鬼》一剧在伦敦公演时所遭遇的英国绅士们的恶毒攻击,萧看清新戏剧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宣传工具——用他后来的话说,它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它的重要性“只有中古的教会可比”。 然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伦敦的舞台情况却只能引起萧的嘲笑。英国戏剧有过几个兴盛的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十六、十七世纪,以康格利夫(Congreve)等为代表的复辟朝喜剧时期,其后在十八世纪又有费尔丁、利洛(George Lillo)、盖伊(John Gay)、谢立丹等人的建树,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却一蹶不振了,戏院里很少见到有生命力的好剧本,而无数文人所写的诗剧又因缺乏戏剧性而上不了舞台。六十年代中,罗伯逊(T.W.Robertson)的《门阀》(1867)一剧获得了舞台上的成功,但是它也为家庭琐事剧开了先河。等到法国沙杜(Victorien Sardou)、斯克里布(Eugene Scribe)成为巴黎剧坛红人,伦敦的剧作家又竞以仿效他们写“结构谨严剧”(la piece bien faite)为时髦。这种剧本讲究章法、线索、伏笔等等,而主题则是家庭纠纷、三角关系、不尽的通奸案件、无数的“有着一段过去伤心史的美妇人”。影响所及,王尔德在九十年代写社会剧时,虽然加入了讽刺成分,也仍然脱不出这个格局,只在《认真的重要》(1895)一剧里他才写下了较好的喜剧。八十年代英国剧坛上的唯一光彩来自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地方,即吉尔勃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合作写成的通俗的、善于挖苦的、纯然英国风的喜歌剧,但它却又充满了小市民气味。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时英国的剧坛不但不是“庙堂”,连正经的艺术场所也算不上,它只是迎合低级趣味的“糖果店”。 现在却来了易卜生。萧在他身上看出了生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戏剧已在席卷欧洲——易卜生之外,还有瑞典的斯特林堡,还有契诃夫和其他俄国巨匠,还有被萧推崇过分了的法国人白里欧(Eugene Brieux)。这种戏剧之新不只在技巧,更在它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它对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揭露和讽刺,它的破坏力,它的愤怒和憧憬,在某些情形下还有它的诗情。新戏剧的重要与有力既如此,伦敦剧坛的不振又如彼,萧本是一个有志之士,如今看到了易卜生的榜样,于是油然而生夺取伦敦旧舞台、创造英国新戏剧之心了。 他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方面,他用凌厉无前的戏剧评论从旧舞台内部进行爆破,为此不惜向被旧势力捧为护身符的莎士比亚猛烈开火;另一方面,他正面阐释欧洲新戏剧,竭力主张戏剧不应依赖离奇的情节而应依赖理想的冲突和意见的辩论,介绍易卜生和白里欧之外,又在一八九二年自己动笔写起剧本来。 从一八九二年的《鳏夫的房产》到一九五○年的《为什么她不肯》,萧总共写了大小五十一个剧本,数量之大,英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就时间而论,萧的条件特别优越。他活了九十四个年头,直到最后智力依然活跃;其中从事戏剧创作共达五十八年(1892—1950),时间超过莎士比亚整个一生;这一点已经十分不凡,但却还有一个因素,使他更能充分地利用这漫长的五十八年,那就是:别人在创作生涯之始,往往要有一个摸索试验的学徒时期,而萧则在一八九二年动手写《鳏夫的房产》之时,就已显得处处成熟,一切宛如老手了。 《鳏夫的房产》开英国戏剧史上新页,然而这部新人新作却几乎没有幼稚或粗糙的地方。从头起,萧的特点就大部分出现了:论主题,这里所处理的就是以后萧要不断处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论人物,干练的房东老板是后来军火商安德谢夫、罗马大将凯撒、《苹果车》里的国王等人的先驱,而能言善辩的狗腿子李克奇斯又是《康蒂妲》里的柏格斯和《匹克梅梁》中的杜立特尔的祖宗;论对话,萧一开始就写得十分生动、机智;论情节,在第一个剧里犹如在后来许多剧里,出现了一个典型的“颠倒”场面:一个医生原来义愤填膺地责备房东不该压榨贫民区住户,等到他发现自己的收入也来自贫民区的房租,就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他的同伙。作者的手法是老练的,态度是自信的,几乎是傲慢的,没有半点吞吐或迟疑,一种新的戏剧从头就以战斗的、毫不畏缩的姿态出现了,它的艺术特点也几乎从头就具备无遗了。 这当然不是说,萧没有经过学徒时期。区别只在这里:别的剧作家往往在剧院里或书斋里尝试着写他们的第一行台词,而萧则在伦敦的失业日子里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街头煽动和会场争论里练出了辩才,加上从小就有音乐和歌剧修养,在一八七九到一八八三年间写作五本长篇小说又给了他以描写人物、安排情节的能力,再加上易卜生的启示和自己作为剧评家在戏院里的见闻感触,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他那杆又犀利又典雅的文笔,那个在莎士比亚和斯威夫特的影响之下形成,在千百篇政论和艺术、音乐、戏剧评论里得到锻炼,在无数次的辩难争议里变得锋利无比的散文风格。 这样,在一八九二年之前,他具备了写作他那一类戏剧的必要条件。 这样,他赢得了时间,从一八九二年起就放手写起适合自己天才的剧本来。长达五十八年的创作生涯,就在这样充满了自信、具备了坚实的艺术基础的有利情况下开始了。 结果是:他获得了比文学史上见过的任何剧作家更多的充裕时间来完善自己的戏剧艺术。为了看出萧的变化发展,我们不妨将他的剧作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大概的分界线是:一九○○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九年。 远在二十世纪之前,萧就已经写出了他若干最出名的剧作。《不快意的戏剧集》之中,《鳏夫的房产》(1892)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至今盛名不衰,只有《荡子》(1893)已经无人注意。《快意的戏剧集》之中,《武器与人》(1894)是英国戏剧史上最好的喜剧之一,《康蒂妲》(1894)在戏院里一直叫座,《风云人物》(1895)有其独特的吸引力,《难以预料》(1896)同样是出色之作,其中出现的老茶房威廉承继了欧洲喜剧中仆人一角的某些传统特点,但又加上了萧所独有的智慧与成熟。《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里包括了两个成功的历史剧:一个是以美国革命为题材的《魔鬼的门徒》(1897),其中有新颖的人物处理;另一个是有名的《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1898),后来到了四十年代还被摄成电影,可见其戏剧吸引力之巨大。以上总共十个剧本是任何剧作家都可以感到无愧的作品,足以替任何剧作家赢得文学史上的一席地。 然而它们却只是一个开始。在二十世纪初年,又出现了一系列在观众和读者之间造成了更加深刻印象的成功剧作:利用唐璜传说写成的《人与超人》(1903),根据爱尔兰问题来剖析英帝国主义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以军火商为主角的动人心魄的《芭巴拉少校》(1905),描写艺术家的命运的《医生的困境》(1906),处理宗教问题的《安乔克里斯与狮子》(1913),以及情节有趣,发人深思,至今显得十分新鲜的《匹克梅梁》(旧译《卖花女》,1913)。在这个阶段当中,萧写的剧本远不止这一些,然而仅仅这一些——仅仅将它们的名字回顾一下——就足以确立一个事实: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之内,萧写下了不少成功的剧本,他的视野广阔了,他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见解深入了,而且才思敏捷,新意泉涌,在戏剧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为常人之所不敢为,将唐璜打入地狱,将大军火商的资本主义世界端上舞台,令狮子随使徒跳舞,叫蚱蜢向老人诉苦,让一个贫苦的卖花女在学习了六个月的标准发音之后变成了大使馆游园会上的绝色公主——凡此种种,都显示萧在戏剧创新上的成就,显示英国戏剧在他的指引之下,确实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了。 然而这新天地里却没有真正的欢乐。黑云笼罩着;眼看战争就要像暴风雨般袭来。在这种预感之下,萧进入他创作的第三时期,开始写《伤心之家》(1913—1916),未到完稿,欧洲的不少精华地区已经变成了废墟。这部以契诃夫式的阴郁气氛见长的剧本反映了那样的现实,被不少行家(例如也是写剧能手的奥凯西)评为萧的真正的杰作旭恩·奥凯西:《夕照与晚星》,第230页。。而萧本人,却认为他的杰作不是这个,而是接着出现的、合起来称作《回到麦修色拉》的庞大的一组剧本。在这组剧本里,他上天入地,透视古今,想要穷究长生之道,花了不少气力来宣扬他的唯心的、反达尔文的“创造进化论”,但是剧本并未在舞台上获得成功。论舞台上的成功得数写作于这个时期之末的历史剧《圣女贞德》(1923)。萧通过贞德的生平表现了西欧近代历史上的两种力量,即基督教新教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出现。演出之后,获得空前热烈的赞誉,不少演员以扮演贞德为本人演技的一个考验,就像他们看待莎士比亚的某些著名角色一样。商业舞台上的成功常常不是剧本本身价值的可靠衡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通过这些剧本看到:萧在连续创作剧本三十年之后,仍然精力饱满,创新不绝。 经过了这样活动频繁、收获丰富的三个时期,也许在一九二九年以后的最后时期里没有多少新东西了吧?不然。萧是难于预料的。一九二九年写成的《苹果车》一剧依然令人吃惊。这时候他将眼光从经济和社会问题移到了实际政治,不仅在《苹果车》里揭发了工党政客麦克唐纳等人的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剖析了资产阶级民主为金融寡头操纵的真相,而且接着在《搁浅》(1933)里写失业群众的示威,在《日内瓦》(1938)里对法西斯头子巴特勒和庞巴董尼(影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审判。这一类的剧本,萧自己有时称之为“政治狂想剧”,它们的特点在于作者将真人真事同幻想的情节糅在一起,用来暴露经济大危机里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孔千疮。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虽然未必所有的人都欢迎它,然而《苹果车》的成就却是观众和批评家所公认的,其中对话的机智达到新的高度,与十年后出版的《在贤君查理士的盛世里》(1939)一剧成为这个阶段里对峙的双峰。后者显示了萧怎样让自己的历史想象力自由驰骋:原来他在这个剧本里将风流国王查理士、查理士的情妇名演员耐尔·格文、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画家耐勒,和大科学家牛顿一同放在牛顿的书房之内,各逞雄辩,大谈人生。这是第一幕里的精彩场面,第二幕却显得平淡乏味,难以为继了。 到了四十年代,萧的剧作显著减少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中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少人能在英国的战时空气里写出大部头的作品来;而战争结束之后不过三年,萧的新剧《波扬家的亿万财产》(1948)就出现在欧洲的舞台上了。九十二岁的老翁而能完成一个多幕剧,毅力着实惊人。无怪萧感到自豪,一九四九年他在整理自传材料之时,这样写道:我甚至不想就此告别,因为我身上还有足够的劲儿,还可以大干一气呢!自然,一年之后,他终于离开人世了,然而逝去的只是他的肉体。他的剧本传了下来。它们不断在舞台、银幕和广播上重新出现,原来以为过了时的萧的人物和场面还是十分新鲜,原来以为听腻了的萧的对话依然耐人寻味。时间——向来是无情的时间——终于在这个最不屑于追求不朽的戏剧家身上,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无从轻易摧毁的对手。 ………… 华伦夫人的职业(节选) (1894年) 潘家洵 译 薇薇 你是不是我母亲? 华伦夫人 (大惊)我是不是你母亲!哦,薇薇,你怎么问得出这句话! 薇薇 你说你是我母亲,那么,咱们家里的人在哪儿?我父亲在哪儿?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在哪儿?你说,你是我母亲,有权利管教我:有权利骂我是胡闹的孩子,有权利用大学女训导员不敢用的态度对我说话,有权利硬支配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权利硬逼我认识一个谁都知道是伦敦最下贱的高等游民、流氓畜生。在我拒绝你这些要求之前,我倒不妨打听打听,你究竟凭着什么身份对我提这些要求。 华伦夫人 (神志错乱,身子一软,跪倒在地)哦,别说了,别说了。我是你母亲,我敢赌咒。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过不去——你是我亲生女儿!你太没良心了。你得相信我。你说,你信我的话。 薇薇 我父亲是谁? 华伦夫人 你不知道自己嘴里问的是什么话。我不能告诉你。 薇薇 (坚决)你能,只要你肯。我有权利知道,你心里也很明白我有这利。要是你不肯说,那也由你。可是要是你不说,明天早晨我就走,从此以后不再见你。 华伦夫人 你说这种话,我实在受不了。你不会离开我——也不能离开我。 薇薇 (毫不留情)要是你不把实话告诉我,我一定离开你,一点儿都不踌躇。(心里一阵厌恶,身子抖起来)我怎么拿得稳,我的身体里一定没有那个废物畜生的肮脏血? 华伦夫人 喔,没有,没有。我敢赌咒,不是他,也不是你见过的那批人。这一点我至少还拿得稳。 薇薇心里一亮,猛然间辨出了母亲这句话的滋味,马上用眼睛狠狠盯住她。 薇薇 (慢吞吞)这一点你至少还拿得稳。哦!你意思是,只有这一点你拿得稳。(沉思)唔,我明白了。(华伦夫人两手捂着脸)别装腔作势,妈妈,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一点儿都不在乎。(华伦夫人把手放下,抬起头来苦苦地瞧着薇薇。薇薇掏出表来一看,说道)好,今儿晚上不必再谈了。明天你什么时候吃早餐?八点半你是不是嫌太早? 华伦夫人 (气极了)天啊,你是个什么女人? 薇薇 (平心静气)我想,我是世界上数目最多的那种女人。要不然,世界上的事儿谁去办。起来(抓住她母亲的手腕,一把把她拖起来):定定神。这才对了。 华伦夫人 (抱怨)你对我太粗野了,薇薇。 薇薇 胡说。该睡觉了吧?十点都过了。 华伦夫人 (气愤愤地)睡什么觉?我睡得着吗? 薇薇 为什么睡不着?我就睡得着。 华伦夫人 你!你这人没心肝。(说到这儿她露出了本来的语调——一个平常女人的方言——母亲的威势和架子全没有了,心里充满了一股强烈自信心和瞧不起人的劲儿)喔,我不能忍受,我不能这么受屈。你凭什么自以为身份比我高?你在我面前夸耀自己怎么有出息——可是你也不想想当初给你机会让你有今儿这么一天的人就是我。我小时候有什么机会?像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女儿,这么个自命不凡的假正经女人,别不害臊了! 薇薇 (把肩膀一抬,坐下来,自己没有信心了,因为她答复母亲的那段话刚才自己听着很有理,现在她母亲把声调一变、换了新口气,她觉得自己那一番话有点书呆气,甚至于有点道学气)你别以为我欺负你。刚才你用做母亲的传统权威向我进攻,我就用正经女人的传统优越身份防卫自己。老实告诉你,我不能忍受你那一套。可是只要你不拿出你那一套来,我也不在你面前拿出我这一套。我绝不侵犯你保持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华伦夫人 我自己的意见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听听她的话!你以为我小时候能像你似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吗?你以为我干那种事是因为喜欢干,或是觉得干得对才干的吗?你以为我要是有机会,我不愿意上大学做上流女人吗? 薇薇 谁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妈妈。一个顶苦的女孩子虽然未必能随意选择做英国女王还是做牛纳学院的院长,可是她总可以凭自己爱好,在捡烂布和卖花儿两个行当里挑一个。世界上的人老爱抱怨自己境遇不好。我不信什么境遇不境遇。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能放开眼光找他们所需要的境遇的人,要是找不着,就自己创造。 华伦夫人 嗯,说说挺容易,一点儿不费劲,是不是?哼!你要不要听听我从前的境遇? 薇薇 好,说给我听听。你坐下好不好? 华伦夫人 嗯,我坐下:你别害怕。(她拿过椅子使劲往地下一蹾,坐下。薇薇不由自主提了提神)你知道不知道你外婆是干什么的? 薇薇 不知道。 华伦夫人 不错,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外婆自己说是寡妇,在造币厂附近开个小铺子卖炸鱼,带着四个女儿靠那小买卖过日子。四姐妹里头,我跟利慈是亲的。我们亲姐儿俩都长得挺好看,身材也不错。我们的父亲大概是个吃得肥头胖耳、日子挺好过的人,母亲说他是个上等人,谁知道是不是。其余那两姐妹跟我们不是一个父亲生的。她们长得又矮又丑,黄瘦脸儿,是一对规规矩矩、肯做事肯吃苦的可怜虫。要不是母亲常把利慈和我打个半死、不许我们欺负她们,我们准会把她们给打个半死。她们俩是一对正经人。可是做正经人有什么好处?让我告诉你。她们俩有一个在铅粉工厂做女工,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活,一星期只挣九个先令,干到后来中了铅毒,把命送掉。最初她以为至多不过得个两手麻痹症,没想到后来命都保不住。另外那一个,母亲常说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因为她嫁了一个代福海军军需厂的工人,她丈夫一星期挣十八个先令,她倒也把他的家和三个孩子安顿得整整齐齐的,可是后来她丈夫喝上了酒,一切全完了。你说做那么个正经人上算不上算? 薇薇 (现在凝神屏息起来)你和你姐姐觉得做正经人上算吗? 华伦夫人 利慈觉得不上算,她比我有志气。我们俩一同进了个教会学校——这件事也是我们看见了那些什么都不懂、哪儿都没去过的女孩子就摆架子的一个原因——在学校待了一阵子,有天晚上利慈出去了从此没回来。我知道,女校长担心我不久也要学姐姐的榜样,因为学校的牧师时常提醒我,说利慈的结局一定是在滑铁卢桥跳河自杀。可怜的蠢牧师,他只懂得那么点儿事!可是我觉得进铅粉厂比跳河更可怕,要是你是我,你的想法也会跟我一样。后来那牧师在一家名目上不卖酒其实什么都卖的饭馆里给我找了个厨房打杂儿的活。后来我又当了女茶房,又进了滑铁卢车站的酒吧间——端端酒,洗洗杯子,一天十四个钟头,吃他们的饭,一星期挣四个先令。在我说,这就算是往上爬了一大步。有天晚上,天气冷得好难受,我在柜台里累得都快睡着了。那当儿有个客人进来要半品脱威士忌。你猜那是谁?不是别人,是利慈。她穿着一件长的皮大衣,又雅致,又舒服,钱袋里还装着好些金洋钱。 薇薇 (冷冷地)是利慈阿姨! 华伦夫人 正是,并且还是个很不丢人的阿姨。现在,她住在温切斯特,靠近大教堂,算得上当地一个上流女人。你能信吗,阔人开跳舞会的时候,她还负责照管人家的小姐呢。谢谢老天爷,利慈没跳河!我看你有点儿像利慈:她是个头等能干人——一开头就攒钱——从来不大肯露自己的真面目——从来不慌张,也不错过一个机会。那晚上她看见我长得挺好看,就隔着柜台冲我说:“小傻瓜,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消磨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己的脸子,给别人挣钱!”那时候利慈正在攒钱打算在布鲁塞尔自己弄一所房子。她想,我们两个人攒钱总比一个人攒得快。因此,她就借给我一笔钱,给我做本钱。慢慢儿我也攒了钱,先还清了她的账,后来就跟她合伙做买卖。凭什么我不该那么做?我们在布鲁塞尔搞的买卖是个真正高级的:女人在那儿过日子比在安·简恩中毒的工厂里福气得多。我们养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受过我在饭馆里,或是滑铁卢酒吧间,或是自己家里受的那份儿罪。难道你愿意我在那些地方待下去,不到四十岁就变成一个苦老婆子吗? 薇薇 (这时候听得有滋有味了)不愿意。可是你为什么单挑那么个行当呢?只要能攒钱,会经营,什么行当都干得成。 华伦夫人 不错,只要能攒钱。可是请问,一个女人干别的行当,攒得起什么钱?一星期挣四先令,还要自己做衣服,请问能不能攒钱?干脆办不到。不用说,要是你脸子不好看,只能挣那么点儿钱,再不就是你会音乐,会唱戏,会给报馆写文章,那情形当然不同了。可是利慈和我在这些事儿上头都不行,我们的本钱只是一张好脸子和一副奉承男人的本事。人家拿我们的脸子做本钱,雇我们当女店员、女茶房、女招待,你说我们难道是傻子,为什么要死守着吃不饱肚子的那几个死工钱,自己不去发这笔财。这道理说不通。 薇薇 你这话很有理——要是用做买卖的眼光看。 华伦夫人 不论用什么眼光看都有理。把一个正经女孩子带大了干什么?还不是去勾引有钱的男人、跟他结婚、从他的钱财上沾点实惠?好像事情做得对不对只在乎有没有结婚仪式!哼,这种假仁假义的把戏真叫人恶心!利慈和我还不是跟别人一样也得工作,也得攒钱,也得算计,要不然,我们也会穷得像那帮醉生梦死、自以为可以一辈子走红运的糊涂女人。(使劲)我最瞧不起那等女人,她们没骨头。要是女人有什么毛病让我瞧不起的话,那就是这种没骨头的毛病。 薇薇 妈妈,老实告诉我:难道你不认为女人有骨头就应该痛恨你那种挣钱的方式? 华伦夫人 那还用说。谁都不喜欢让人逼着干活挣钱,可是不喜欢也得干。当然,我也时常可怜那些苦命女孩子,身体疲乏了,兴致懒散了,可是还得勉强敷衍一个看不上眼的男人——一个喝得半醉的混蛋——他跟女人纠缠的时候自以为很讨人喜欢,其实讨厌透顶,女人随便能到手多少钱心里都不愿意。可是那些女孩子不能不敷衍这种臭男人,她们不能不忍气吞声,像医院护士对待病人那么耐心地对待他们。天知道,那个行当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喜欢干的,尽管一些正人君子谈起来,好像那是一件顶快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