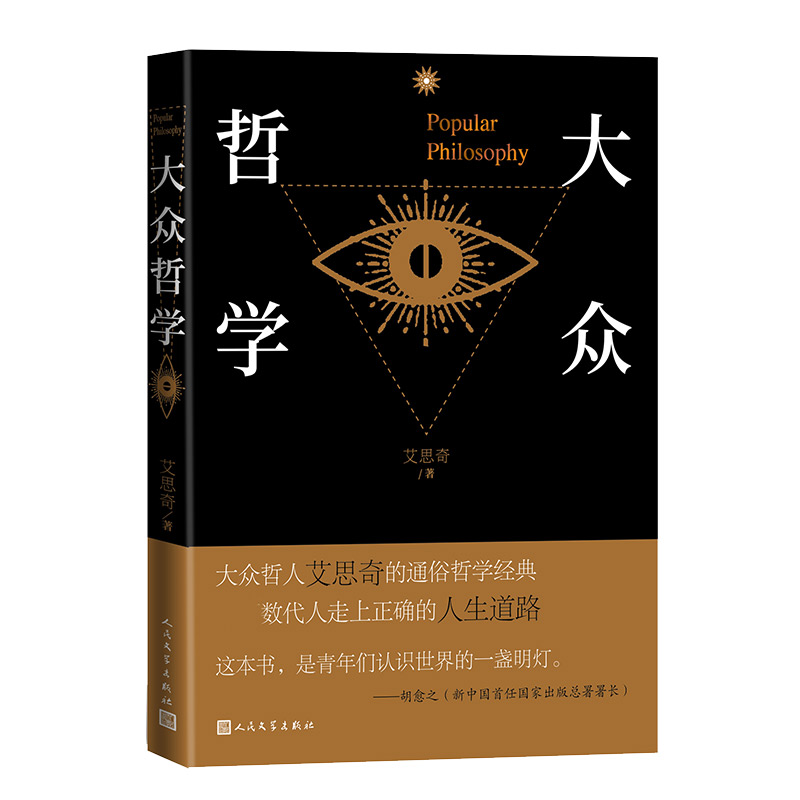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7.80
折扣购买: 大众哲学
ISBN: 9787020164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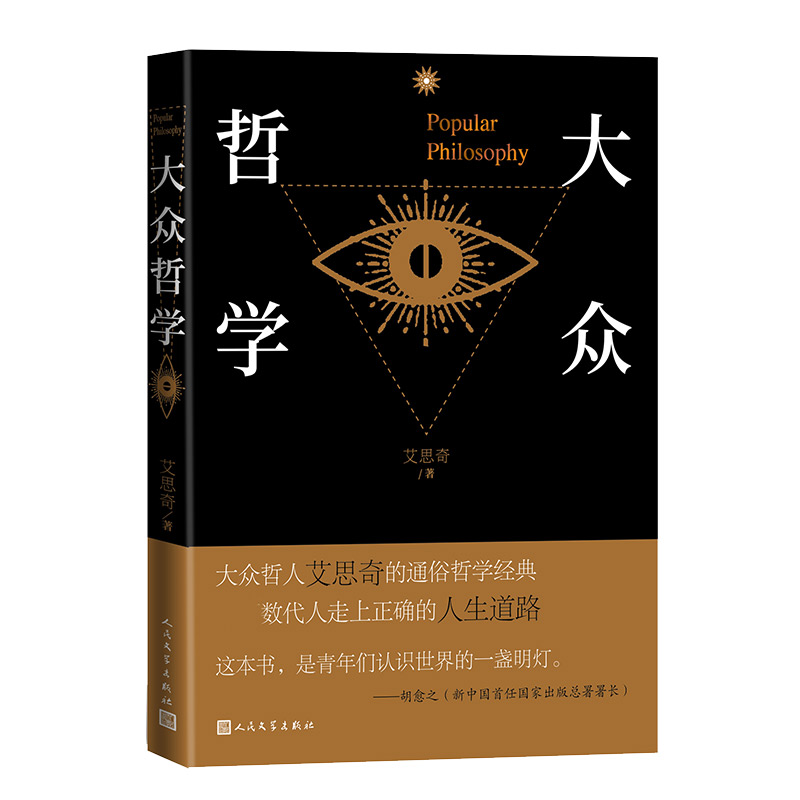
艾思奇(1910—1966) 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并与李公朴、黄洛峰等创办读书出版社。1937年赴延安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实践与理论》《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并主编全国高校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①的(代序) 我写成了一本通俗的《大众哲学》,并且获得了不为不多的读者,在我自己,实在是一件意外的事。 理论的通俗化,现在是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它所关涉到的一切问题,也有很多人热烈地讨论过了。但在两三年前,在《读书生活》中《大众哲学》以及柳湜先生的《街头讲话》等没有出世以前,就很少人注意到通俗化的问题,甚至于对于通俗化的工作轻视的人也是有的。老实说,我自己就多少有点偏见,把理论的深化看得比通俗化更重要。就是到了现在,虽然读者们接受《大众哲学》的热情教训了我,使我深深地领悟到通俗化工作的意义了,但就我个人的兴趣来说,仍是想尽量偷空做些专门的研究。我的这一种兴趣上的偏好使我成为一个爱读死书的人。如果不是为着做了《读书生活》的一个编者,不能不服从编者的义务的逼迫;如果不是朋友们的鼓励和督促,《大众哲学》也许就永远不会开始写,而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使这么多的读者们认识了。 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读者。因为读者诸君对于这本书虽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的代价,而我在写作的时候,却没有投下了同样的热情的资本。我对于这件工作是时时刻刻抱着踌躇的心情,并不是勇猛地做下来的。我对于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实在认识得不够了。 但也得要声明,我只是没有用很大的热心来写,这并不是说写的时候没有用力。热心不热心是一回事,用力不用力又是一回事。是的,《大众哲学》实在花费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吧。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前后竟经过了一年才写完。虽然这一年中我还做了其他的事情,但至少四分之一的时光是用在《大众哲学》上的。这就是说,我至少写了三个月的工夫,而写出来的东西又是这么幼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做到完善的地步。 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方面要归罪于我的不大敏活的头脑,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件工作的本身有着许多的困难。 第一,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即使用了艰涩的文字和抽象的把握,也不是十分要紧的。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术是第一要义,同时理论也切不可以有丝毫的歪曲,这就是一个困难。这困难在哲学这一门最一般的学问上更是显著,而把这一个困难的重担担负到了我的肩上,就尤其是更大的困难。我掮着这个担子是极不胜任愉快的,因为真能当这重担的人,应该对于生活有充分的经验,而我缺少的却正是这一个东西。我的生性不大活泼,向来就是在学校生活中过去了大半的时光,生活经验尝得极少。朋友们当我的面时,常常称我做“学者”,背地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换上一个“书呆子”的称呼。是的,叫一个“书呆子”来把生活和理论打成一片,不是妄想吗?不客气地说,我自己还不至于这样完全不能自信。近几年来,我也在不断地向生活学习;但我所懂得的生活毕竟很少,不能够运用自如地把材料装进作品里去。这是我在写作《大众哲学》时最感困难的一点。 第二,是环境的困难,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不但是写作通俗文章感觉到,就是一切其他愿意存着良心来著作的人都很明白的。当《大众哲学》在《读书生活》上逐期连载的时候,言论界还存在着检查委员会的统制。一篇文章写成之后,要经过“删去”、盖章,然后才能够和读者见面。碰得不好的时候,就根本无法出版。《大众哲学》所要讲的全是新唯物论方面的东西,这根本就已经不大妙了。如果再把说明例子举得更现实、更明了、更刺激,那么,这个发育不全的小孩也许就会根本流产。为着这样的缘故,就是有了实际生活的材料,也因为碍于环境,没有办法拿出来。慢说我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即使有了,也会感觉到运用困难的苦楚。我有时不能不把很实际的例子丢开,而用上了很不现实的例子,譬如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说明本质和现象就是一个好例。这些地方,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指摘。我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我写作时的困难。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势,就像乱岩中间的流水一样,本来应该一条直线流下去的,但中途遇到许多阻碍,只能不断地溅着飞沫,打着许多弯转,然后才能够达到目的。《大众哲学》的写成,就是这样辛辛苦苦地绕了许多弯路的。 在这样的困难情形下诞生出来的《大众哲学》,自然要感到极大的难产的痛苦,而所生下来的婴孩又一定是不很健全的了。我在这本书第4版改名《大众哲学》(本书原名《哲学讲话》)时,说写作《大众哲学》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就是指这样的意思。 在这样的困难之下是怎样写作的呢? 因为不能充分地把实生活的事例应用到所写的东西里去,于是我就不能不另外再找许多接近一般读者的路径。首先我要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一个专门家是常常爱单刀直入地把握到理论的核心,对于事例的引证倒反放在附属的地位。我以为如果每一句理论的说话都要随伴着一句事例的解释,在专门家看起来是浅薄幼稚,通俗读物所要求的却正是那样的东西。通俗读物要求从头到尾都有明白具体的解释,因此每一篇都把一件具体的事例做中心,而每一篇所定的题目也就不用哲学的题目。这样的写法,和一般哲学文字的写作原则自然是违反了的。也就因为这样,使得有些专门研究的朋友认为《大众哲学》的体裁是“喧宾夺主”,把事例遮盖了理论了。是的,我自己在写作的当初也觉得这有点喧宾夺主的样子,但这样的写法是不是不对呢?这是要由我们的读者来评判的,因此就不顾一切地这样尝试了。在这里,我所选择的接近读者的第一条路径就是:故意写得幼稚。 我选择的第二条路径,是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复。一个例子在这一节用了以后,在另外一节仍然不怕再拿来应用;一件事情在前一节做了详细的解释以后,在第二节仍不惮烦地再略说一遍。在一册小书里用这样的方法来写,在文字上自然是很不经济的。但我们如果顾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和理解力,就觉得这样写也是很必要,因为在专门学者或有较高修养的人,有些事是可以不必多讲就明白的,而对于初学者,你却最好给他多解释。我是抱着这一个宗旨去写的。因此,如果一个对于文字美有嗜好的人来读我的《大众哲学》,他一定会感到不简练、啰唆、重复的毛病。 自然,使我不能不采取这种重复而啰唆的形式的原因,另外也还有一个,这就是因为《大众哲学》是需要按期发表的东西。每期杂志的出版要隔半个月的工夫,而《大众哲学》又是有系统的读物,中间时期隔得太多,就难免会感到兴趣的减少。因此不能不把每篇写成有独立性的东西,使读者按期看下去也可以,而单独看一期也不至于一无所得。为了这缘故,一篇文章的内容如果和另外的一篇有密切关系时,就不能不把另外一篇所说过的在这一篇略复一遍,这也就造成重复现象。 以上就是我努力接近读者所取的路径。这样的路径自然不很正确的。论理说,我们应该有更直接的路径,但为着自己的缺点和环境的困难,我只好把更直接的路径回避了。这是消极地从形式上接近读者,而不是积极地使内容和读者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联。 像这样写出来的《大众哲学》,自然不能算是一本很好的读物了。我同意有一个刊物所批评的话说:“现在不是没有人能写出更好的同类的书,而是没有人来努力。”是的,我承认中国应该有更好的书出来。我把这不大好的一本投到读者的面前,是很惶愧的。但这一部书竟写成了,而且竟意外地获得了不少的读者。这又使我的心里感到了一些安慰,感觉到一年的功夫也并没有白花。但这样的现象,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勿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知识饥荒是太可怕了。读者对于我们的期望的热烈,实在是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才能和努力之上,因此才使这样一本蹩脚的书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的欢迎。我所感到安慰的是,因为《大众哲学》的出现,因为读者诸君对于这本书的热烈的爱好,研究专门学问的许多人(连我自己也在内)也许会因此深 切地明白了中国大众在知识上需要些什么,因此也才知道自己为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我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才把当初写作时的那种踌躇的心情抛弃了,更有勇气地来做一些我认为应该做的工作。我相信另外的许多朋友也会有这种同感。要是这样,那么目前中国哲学上的同道者也许有人会起来努力做一件更好的工作的。《大众哲学》如果能产生这样一种“抛砖引玉”的效果,那就更是我私心所要引为慰藉的了。 艾思奇 1936年 二 果树林里找桃树 ——哲学是什么 我们已经了解哲学并不神秘,已经知道哲学的踪迹在日常的思想里到处都可以找到了。但是,究竟什么是哲学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哪些思想是属于哲学一类的,哪些不能算是哲学思想呢?假使有一个人走在各种各样的果树林中,想要找寻桃树,如果我们仅仅向他说,你到处都可以找到桃树,那他是不能满足的。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样的树是桃树,什么样的树不是桃树,这样他才能够容易找到桃树。 我们还是从生活的问题讲起吧。试就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来说,那时人民的生活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处在生活困难的情形之下的人,会发生一些什么思想呢?首先他们自然要对于自己的目前境遇表示不满,对于社会现状表示不满,这是一切生活困难的人大致共同的思想。但是事情是不是就这样简单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对于现状的不满是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的;而这些不同的想法是由于各种人的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有的人会由不满而变为绝望,会感到人生没有意味,会以为世界无可留恋,个别的人甚至于会进行自杀。有的人相信命运的观念,遇到困难的时候,只埋怨自己的命苦,认为现状无法改变,即使是牛马的生活,也只能默默的忍受,而不敢希望翻身抬头。又有的人却相反地认为生活困难不是生前命中注定,而是由社会上的许多事实原因所造成。由此相信这令我们不满的社会生活现状一定有方法可以改变,只要能看清楚这些原因,并且努力从事实上打破这些原因。例如说看清楚了旧中国人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腐败统治;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不够团结不够觉悟,没有动员起足够的力量来彻底打退侵略和推翻这种统治。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以工农为主的全国人民,把他们的觉悟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成为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主要的方法。好了,我们看,同是处在生活困难境遇中,而各种人的想法是那么不同!我们再看,在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上,除了生活困难的广大人民以外,还有少数生活优越的人,他们是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资本家,他们专门依靠剥削广大人民,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对于他们,生活困难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除了剥削和压迫人民之外,说不上什么职业。他们以为自己生来就是社会上的统治者,广大人民应该受他们的压迫剥削,他们命定的应该征服别人,而别人也命定的应该被他们征服。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属于他们少数人的,而不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例如日本投降之后,他们宣传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接收主权”,而不准广大人民接收,广大人民要去接收,要在抗日胜利之后起来做主人,他们就不答应,就要用武力、用内战来禁止这种接收。这是他们中间的主要思想。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坐食游荡、无所事事,每天所追逐的只是消遣作乐,这些人的思想又稍不同,他们用游戏作乐的眼光来看一切,说:“人生不过是寻乐而已,不过是美梦而已!” 我们举了以上各种人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正是旧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里很容易可以碰到的,而同时也是包含着各种哲学的萌芽的。这是些什么哲学的萌芽呢?让我们加以说明吧:第一种人感到人生无聊,世界值不得留恋,这里面就有“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第二种人以为生活困难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主张消极忍受,这里就有“宿命论”的哲学思想。第三种人认为我们只要能够把生活困难的现实原因研究清楚,就可以找出克服困难的方法,这里面就有着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第四种人坚持认为少数人是天生的优越人物,反对广大的人民有自由生存权利,这就包含着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所宣传的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也是带宿命论的性质,它把少数人看做是天生的或命定的应该来压迫和统治大多数人的。最后一种人把人生看做游戏,以追逐乐趣为能事,这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哲学思想。 这种种思想,我们都加上了什么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字,是不是有人要说太大胆了呢?那些惯于在书斋里和大学教室里推敲词句的教授学者们,是不是会笑我们浅薄呢?也许会如此!但是,让他们去说笑吧!我们不需要在他们的书本里找是非的标准,而主要应该在人类生活事实中去找真理。我们做的并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因为我们所举出来的这些思想,的确可以叫做哲学思想,这些“主义”,和那些砖一样厚的专门哲学书里所谈的“主义”并没有根本的分别。 为什么说这些就是哲学思想呢?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这些思想,和那些专门的哲学书上所讲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们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根本的认识或根本的看法。悲观主义的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根本都是没有希望的,宿命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根本决定于鬼神上帝,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变化都有它现实的原因和规律,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认为全社会的广大人民需要向少数统治者或独裁领袖屈服,享乐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游戏场,人生在世界上就是要来享乐的,值不得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不同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用哲学上的专门名词来说,就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但很多都不是对于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而只是对于世界一部分事物的部分认识。例如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对于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有国民党的一些军事将领们以阵地战为主的思想,有另外一些人以运动战为主的思想,还有中国共产党以发动广泛的游击战,辅之以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思想;关于抗战的前途,有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速胜论”思想,也有国民党中另外一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亡国论”的思想,也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全国人民及进步人士所接受的“持久战”的思想。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对于抵抗日本这一个具体事件的认识或看法,而不是对于全世界一切事物的总的认识或根本看法,所以都不能叫做“世界观”,而只能叫做“抗战观”,都不是属于哲学思想的范围,而是属于军事政治思想的范围。 现在我们可以完全弄清楚了,不论在我们的日常思想中,或是专门书本所研究的问题中,都可以同样找到哲学思想。只要这种思想所涉及到的,主要是关于我们对整个世界如何看法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思想包括到哲学的范围内;如果这些思想所涉及到的,主要是关于我们对某一件事或某一类物如何看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说它不是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是哲学思想和一切其他思想的分别。 但是,在我们认识清楚了哲学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区别以后,我们还不要忽视它们中间的关系。哲学既然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因此它也就必然要涉及到我们对于世界的一部分事物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事物的看法中,同时必然包含着某一种哲学思想。以前我们说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思想里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其原因就在此。就把刚才抗战问题的例子拿来说吧:例如“亡国论”思想,一方面它是某一些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件事的不正确的认识或看法,在这种认识和看法中,虽没有直接提到整个世界是如何如何的问题,但它仍然和某一种世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对于事情悲观失望,认为世界上事情的困难是无法改变的。这在根底里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又例如那持久战的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国抗战的实际历史事实中证明的确是真理。这种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关于中国抗战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是按照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各种主要的事实条件,加以深刻研究而得到的结果,因此,这种科学思想的根底里,就包括着唯物论的哲学思想。这两个例子,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思想,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或每一类物的认识和看法,都在根底里包括着一种哲学思想,或者照专门哲学的说法,都有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哲学思想所涉及到的,都不仅仅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如何看法的问题,它同时也贯串在我们对于任何一种事物的看法里。 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一切思想,既是世界观的基础,因此就有着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方法的作用或研究指导的作用。亡国论的思想,在思想方法上是受了悲观主义的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指导,把日本的强和中国的弱看作不能改变的,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做绝望的。如果他肯虚心学习,接受唯物论的思想,抛弃悲观主义的思想,按照唯物论的方法,把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和各种最主要的事实条件认真研究一番,那么,只要他不是汪精卫的死党,或昧着民族良心要跟反动派和敌人讲妥协,他就应该承认亡国论的不对,就应该接受持久战的真理。这一种情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了不正确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看事情和认识问题的时候,就会受到不正确的方法的引导,而这种方法就会把我们带到错误思想里面去;反之,如果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看事情和认识问题的时候,也就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能使我们对于每一件事和每一类物找到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因此,哲学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思想方法。我们研究哲学,目的就在于学习掌握一种正确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在于要学到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我们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力的武器。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犯错误,就要使革命队伍和革命人民遭受损失。 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什么叫做哲学了。但是,我们就此能算完全找到桃树了吗?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番解答。我们不仅要求懂得什么叫做哲学,而且还希望懂得什么是正确的哲学,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先一般地解释一下:什么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和看法。还是用抗日战争的例子来说,对于抗战的三种看法——亡国论、速胜论和持久战,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抗战八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看法都不对,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才是正确的。这种正确的思想,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它和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呢?它的特点和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持久战的思想,和抗战的事实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它不只是我们头脑里的思想,而且是把事实的发展规律正确的反映在这一个思想里。至于那不正确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想,它的内容却和抗战的事实发展规律全不符合,它之所以叫做错误思想,就在于这种思想不能正确地把事实发展规律反映出来。什么是这里所谓的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变化发展中一定不移的关系和过程。由于敌强我弱以及其他许多事实条件,抗战必定要经过长期的战争而不能速胜,必定要通过防御、相持和反攻的三阶段的道路,必定要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到处打击敌人,才能渐渐削弱敌人以至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由于我们是进步的,敌人是倒退的,我们多助,敌人寡助,我们是大国,敌人是小国这些事实条件,因此只要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定归于我们,而事情的发展决不会如亡国论者的悲观想法那样。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关于中国抗战发展的规律,抗战中一定不移的各种关系和过程,都在持久战的思想里正确地反映了出来,而速胜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却完全违反了这些规律,因此持久战是正确的思想,其他两种思想就是错误的思想。 现在我们就可以谈到什么是正确的哲学思想了。各种正确的思想,都是反映了一定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正确的哲学思想,则是正确地反映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规律,以及我们对于世界应如何认识的总规律。这样的正确的哲学思想,就是辩证法唯物论,我们学懂了它,那我们对于世界就有了正确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就可以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就能够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掌握到有力的方法武器。研究各种事物规律,是科学的任务。我们如果要想对于一定事物,获得正确的思想,避免错误的认识和看法,就必须对这一类事物作科学的研究。但要对于任何事物能作正确的科学研究,就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作为基础,就要研究整个世界变化发展的总规律,以及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认识的总规律,而这就是哲学的任务。因此,我们如果想获得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避免受到错误的反动哲学思想的影响,就必须很好的研究一下哲学。 还要重复说一下:哲学是世界观又是思想方法,正确的哲学就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科学的研究,找出它们的真实的发展规律,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我们在革命行动中和斗争中就不至于摸错道路,就有胜利和成功的希望,否则就要受到挫折或失败。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应用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就为我们指示了持久战的科学真理。中国人民所以能够以一个弱国而在八年抗战中挡住一个强大敌人的侵略铁蹄的前进,给它以有力的打击,最后把它打败,并且发展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作为走向全国解放的基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我们依照了持久战的科学思想进行抗战,而不是依照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来指导行动。正确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有这样的重大作用,它就是我们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思想方法的武器,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哲学,学习掌握那正确的思想武器——辩证法唯物论。 学习哲学既然是为着掌握革命斗争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武器,因此,我们研究哲学的时候,就也必须时时刻刻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一个解决实际问题和指导行动的目的,在研究中经常联系工作和斗争中的问题,切不要缠绕在与当前实际毫无关系的空洞议论和名词的纠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