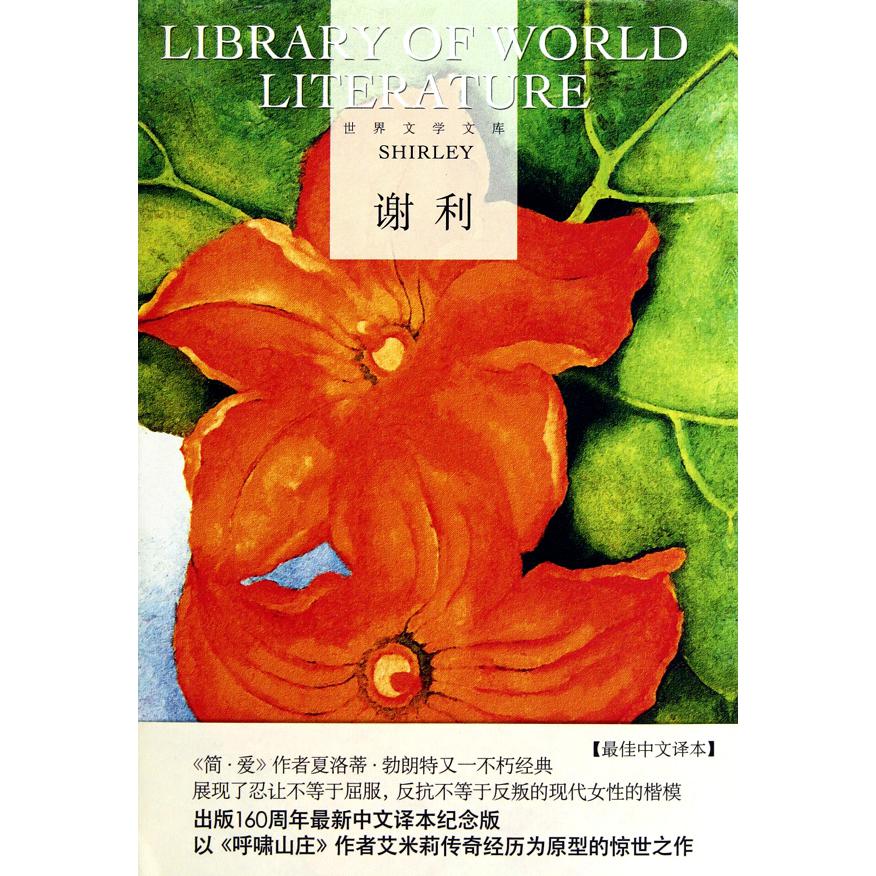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燕山
原售价: 2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谢利(精)/世界文学文库
ISBN: 97875402234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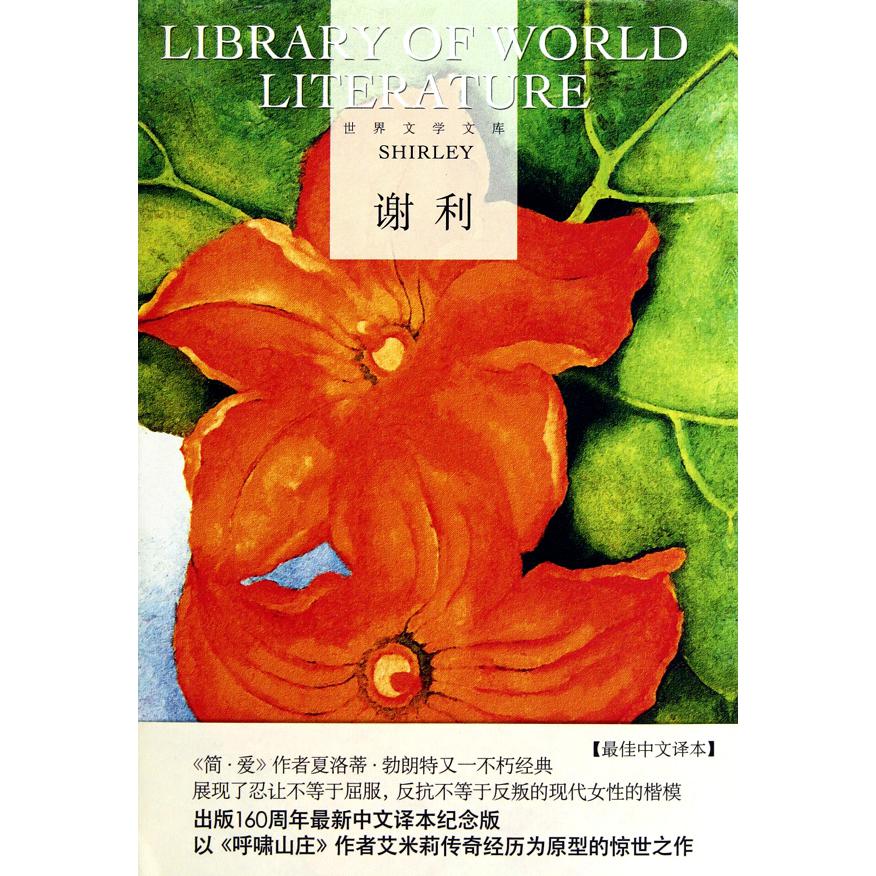
勃朗特,本名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与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妹妹安妮·勃朗特称为勃朗特三姐妹,她的祖先是凯尔特人和摩尔人的后代,所以从情感上更亲近苏格兰人。 艾米莉出生于贫苦的牧师之家,曾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求学,也曾随姐姐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学习法语、德语和法国文学,准备将来自办学校,但未如愿。 艾米莉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30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中22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 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艾米莉的写作,从诗开始,她在着手创作《呼啸山庄》之前十六七年间,陆续写出习作诗文《贡代尔传奇》和短诗,如今所见,近200首诗。 姑且不论它们本身的艺术价值,这些文字起码也是创作《呼啸山庄》这部不朽之作的有益准备。换言之,她写《呼啸山庄》,是她写诗的继续。她的诗,真挚、雄劲、粗犷、深沉、高朗,这也是《呼啸山庄》的格调。 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写过一首诗叫做《豪渥斯墓园》,其中凭吊她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她心灵中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是自从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第一章 利未人 这些年来,副牧师好像雨后春笋似的在英格兰北部涌现。他 们密密麻麻,遍布穷乡僻壤,每个教区无不冒出一个两个,他们年 轻有为,充满活力,想必正在四处奔走,广济众生。但是,我这里要 讲的不是近几年的情况,而要回到本世纪的初始年代。眼下这 些年头简直是尘埃滚滚,赤日炎炎,犹如酷热焦躁的夏天中午。让 我们避开它吧,在迷迷糊糊的午睡中忘却它,在昏昏沉沉的瞌睡中 消磨它,去梦想那丝丝凉意的黎明。 读罢这段开场白,如果你以为即将上演的是一出传奇浪漫戏,亲爱 的读者,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想看看多愁善感的角色、诗情画意的场 景、虚无缥缈的境界吗?你要尝尝情欲冲动、兴奋刺激、大事渲染的滋味 吗?读者,请不要有过高的奢望,我可不打算吊你的胃口。在你面前展 现的只是一些真切感人、冷静达观、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星期 一早晨工薪族一觉醒来意识到必须马上起床赶紧上班一样普普通通,平 淡无奇。当然,我也不是一言以蔽之日:本书毫无惊人之处。也许在中 途和接近尾声的地方你可领略一二。然而,端上餐桌的第一道菜无疑是 一个天主教徒——唉,甚至是安立甘公教派教徒③——在蒙难周的耶 稣受难日所吃的东西:一盘只加醋不搁油的冷扁豆,几块未经发酵的面 包,还有苦野菜,绝无烤羊肉的踪影。 开头我说过,这些年来,副牧师好像雨后春笋似的在英格兰北 部涌现。但在一八一一、一八一二年间,那滋润万物的甘霖还不曾 普降,副牧师如凤毛麟角稀罕得很。当时,既无“牧师补助金”,也 没有“增设的副牧师协会”对日见衰老的教区长和任职牧师助一臂 之力,向他们提供一笔钱去雇个牛津或剑桥出身的精力旺盛的年 轻同行。目前这批年轻的传道士、皮由兹博士的门徒以及罗马 传道总会的奴仆在那个时候都还躺在襁褓中吃奶,或者正在托 儿所的洗手盆里受洗以求开化启蒙呢。目睹着他们,你怎么也不 会想到那戴着一顶意大利熨法的双花边网眼帽的小萝卜头,日后 竟鬼使神差般地被封为圣保罗、圣彼得或圣约翰的继承人;从那穿 着长睡衣的孩子身上,你怎么也不曾预见到,他后来竟披上宽大的 白色法_衣对教区居民无情地发号施令,还在布道坛上将一件衬衫 似的东西当空挥舞,令老派的国教牧师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从前 这东西决不可以飘得比读经台还高。 但即使在副牧师甚为罕见的年代,干这一行的人还是有迹可 寻的,恰如灵芝草虽稀少,依然可以找到。在约克郡西区某个得天 独厚的地方有三位亚伦嫡传弟子,他们如花吐艳,蜚声方圆二十 英里。亲爱的读者,他们就在眼前,请你走进位于温伯雷城郊的一 座整洁的花园住宅,迈进那间小客厅——三位正在吃饭呢。让我 介绍一下:这位是邓恩先生,温伯雷的副牧师;这位是马隆先生,布 赖菲尔德的副牧师;这位是斯威廷先生,南尼利的副牧师。这房子 是一位叫约翰·盖尔的小布商的住宅,眼下邓恩先生在此租住。今 天他做东,款待两位同行。你我不妨也来凑凑热闹,趁此机会必能 大开眼界,饱享耳福。不过,此刻他们正默默地吃着,我们先在旁 边聊上几句吧。 这三位有身份的先生正值青春焕发的年岁,浑身洋溢着那种年 龄所特有的一股活力——对此青春活力,那些老气横秋的牧师们一 心想把它纳入恪守神职的轨道,他们总是希望看到这股活力能倾注 在对学校的辛勤督导,对各自教区内老弱病残的频频探望等公益事 情上。然而这班风华正茂的利未人颇感这类公干纯属乏味之举,他 们宁愿把精力毫不吝惜地耗费在另一种活动形式上。在旁人的眼 中,这种活动简直比织布机旁织工的劳作还要繁琐厌人和沉闷单 调,却似乎给这几位利未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消遣与乐趣。 我这里是指他们相互之间来来去去的串门:一个家门出,另一 个家门进;虽非一长串的社交聚会,却可谓三角模式的轮流拜访; 从冬到春,从夏到秋,一年四季永无休止。天寒地冻也好,骄阳似 火也好,他们全不在乎;怀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倦倦之忱,他们顶飞 雪冒冰雹,风雨无阻;他们踏泥泞踩尘土,来到一处;吃餐饭,喝杯 茶,或是夜宵共坐。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谁也说不清楚。 并非他们之间情同手足,因为只要他们聚到一块,总免不了唇枪舌 剑一番。也不是宗教信仰,信仰这东西他们从来不屑一顾;尽管谈 话中偶尔也涉及神学,但从来不提虔诚之类的词儿。更不是贪恋 吃喝,因为每位客人各自家里有的是同东道主餐桌上一样可口的 大排与布丁,一样香浓的茶,一样新鲜的烤面包。盖尔太太、霍格 太太和惠普太太——三位先生的房东——一致断定:“他们这样做 不为别的,只是给人家添麻烦。”善良的女房东们这里所说的“人 家”,当然是指她们自己;因为,说真的,只要这种互相串门儿的习 惯无休止地坚持下去,女房东们就得天天围着锅台忙个没完。 刚才说过,邓恩先生和两位客人正在吃饭。盖尔太太在旁侍 候,但见厨房里灼热火花的余晖依然在她的眼中闪烁。她觉得,近 年来房客们偶尔邀朋友到住处吃餐饭而不必另外付钱的特权已经 得到相当充分的行使(这一特权也包括在她那租房合同的条款之 中)。可眼下这一周才到礼拜四,客人像走马灯似的:礼拜一是马 隆先生——布赖菲尔德的副牧师,来吃早饭,还呆卞来吃中饭;礼 拜二是马隆先生和南尼利的斯威廷先生,来喝午茶,留下来吃晚 饭,占据了那张空床过夜,次日礼拜三早晨又赏光与她共进早餐; 今天礼拜四,这两位老兄又来吃中饭,她几乎可以肯定今晚他们会 赖着不走的。“这太过分了。”要是会讲法语,她非这样说不可。 斯威廷先生一边在盘中切着烤牛肉,一边嘀咕这牛肉太老嚼不 动;而邓恩先生又说啤酒走气了。唉!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要 是他们能客气一点,盖尔太太辛苦一些倒也不大在意;只要他们吃 得满意喝得开心,她个人劳累一点倒也不必计较,可是“这班年轻的 牧师眼界很高,挑挑剔剔,什么人都够不上他们的‘尺寸,;他们有点 儿瞧不起她,只是因为她没有雇佣人,而像早先她母亲那样屋里屋 外一人全包,所以他们老在说约克郡的风俗和约克郡老乡的坏话”。 单凭这一点,盖尔太太就不相信他们当中有谁是真正的君子,或者 属于名门弟子。“老一辈的教区牧师抵得上整个儿大学里的小伙 子;他们懂得怎样待人接物,他们对上上下下都一样友善。” “再来点面包!”马隆先生嚷道,他的喊话虽短,但那拖长的嗓 音让人一听便知他是来自那块长满白花酢浆草和马铃薯的土 地。三个人当中盖尔太太最讨厌马隆先生,但也有点怕他,因为 他个子高大,身强力壮,生就地道爱尔兰人的四肢,正宗爱尔兰民 族的脸孔。并非普通爱尔兰人的面孔,也不是丹尼尔·奥康内尔 那种脸型,而是面部轮廓突出的北美印第安人一类的相貌。这类 容貌属于爱尔兰士绅的某一阶层,常常伴有一种呆滞僵硬的高傲 自负的神情,在雇佣农民的地主中间尚不多见,在使唤奴隶的庄园 主身上却屡见不鲜。马隆的父亲自称为英国绅士,他穷困潦倒,债 台高筑,却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其子也跟老子一个模样。 盖尔太太端上了面包。 “切一切,婆娘。”这位客人说。“婆娘”便遵命将面包切开。若 能遵从自己的意愿,她真想同时也将这位牧师一劈为二,她那约克 郡人的心灵对马隆如此发号施令感到深恶痛绝。 这几位副牧师胃口真好,嘴上虽说牛肉太“老”,吃起来却没完 没了,就连“走气啤酒”也按法定容许量灌了个饱,一盘约克布丁和 两大碗蔬菜如遭受蝗灾般在他们面前消失。干乳酪也受到特别青 睐,一大块“香酥饼”以及其后上桌的甜点心转眼间被一扫而光。 厨房里盖尔太太的儿子兼继承人——六岁的亚伯拉罕为此而大号 哀歌,因为他原指望能享用部分的继承权,当看到母亲捧回的大浅 盘竟然空空如也,不禁扯高嗓门,痛不欲生地大哭起来。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