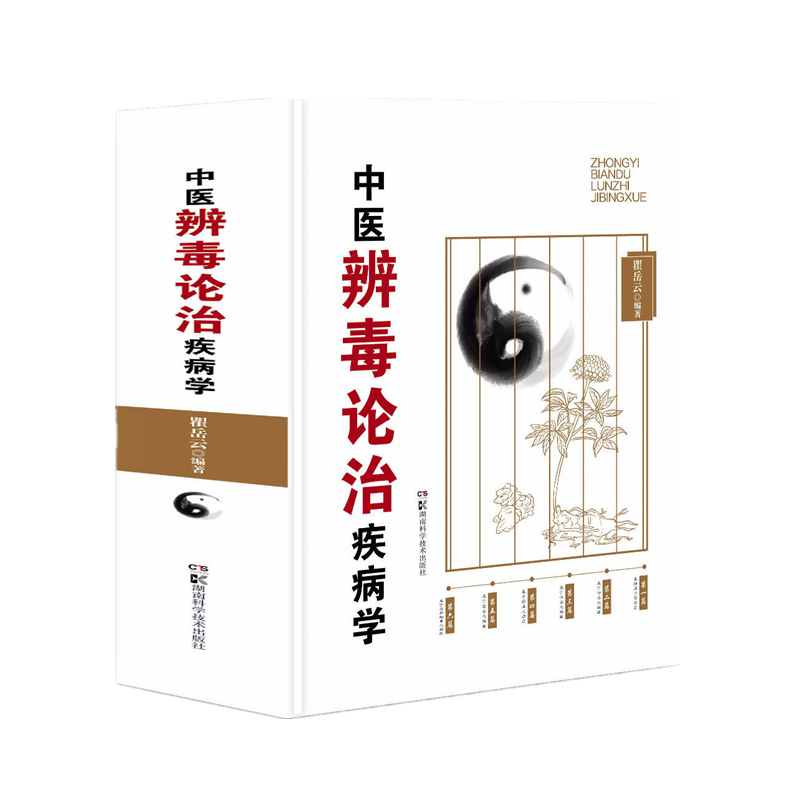
出版社: 湖南科技
原售价: 398.00
折扣价: 258.70
折扣购买: 中西医论治疾病学系列:中医辨毒论治疾病学
ISBN: 9787571016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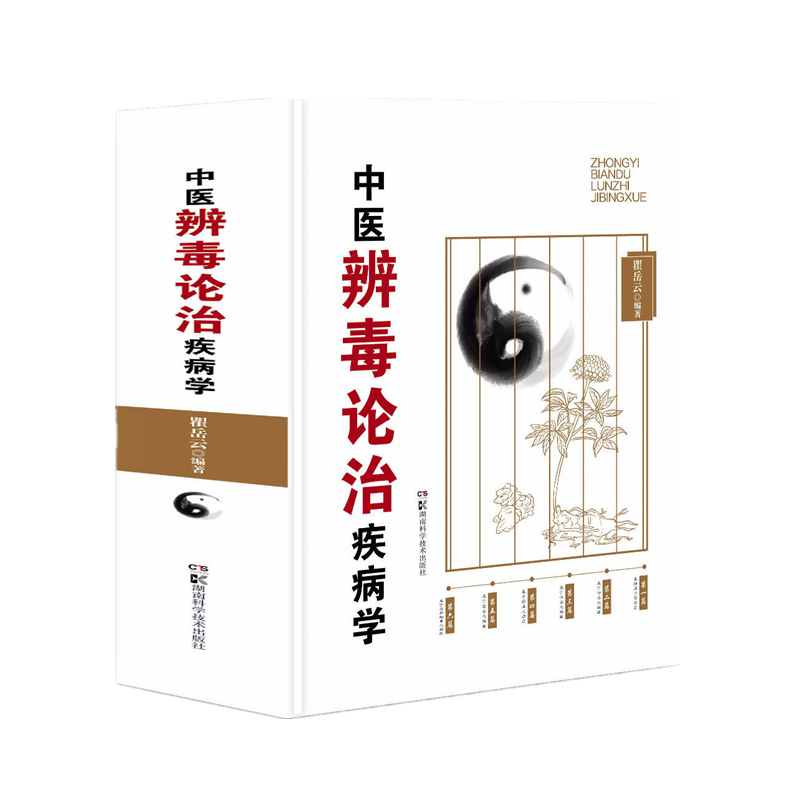
瞿岳云,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原病证研究室主任,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诊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专业委员会常委。编著学术著作、教材30余本,代表著作有《悟变中医——瞿岳云教授别具一格的中医学理论解读》《中医经方全书》《中医诊断历代医论》《沉疴取痰瘀显奇效——瞿岳云教授解读中医学从痰瘀论治疑难病症》等。
第一篇基于毒邪之病症 1《黄帝内经》毒论 毒邪是一类重要的致病因素,既可由外侵入,也可由内产生,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密切相关。深入研究毒的概念、内涵,从源头上剖析其致病特点,对一些重大疑难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尤其是清代重视毒的研究,曾对深化认识外感温病,提高温病的防治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随着社会的演变、环境污染的影响和饮食结构的改变等,使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如何深入研究目前一些重大疑难疾病,搞清其发病机制并提高其临床疗效,成为医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为此,学者常富业等对于现代疑难性疾病和增龄衰老性疾病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毒于其中的作用。相继提出了毒邪入络、损络等系列学说,掀起了国内毒邪研究的高潮。为深入研究毒,诠释毒的概念和内涵,剖析毒的致病特点和临床表征,弄清其致病靶位和易损环节,进而确定相应的干预方案,在此其就《黄帝内经》中关于毒的经典论述进行了初步梳理、诠释。 《黄帝内经》毒论回顾 《黄帝内经》中对毒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素问》部分,出现于12篇共34处。大致对毒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病因之毒:此所称的病因之毒,主要指六淫之毒或外毒,但也暗示有内涵更深邃的“毒”。如在《素问·生气通天论》论之毒当属于六淫之毒或外毒,“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于《素问·五常政大论》的前半部分所论之毒,既属于药物之毒的范畴,也属于病因学的范畴之毒,且有更多的内涵。 指出“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 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治。”文中提出了“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等名词,这些毒,显然指病因,为外邪所演化而来,提示毒不是独立的一种致病因素,而是邪气演变的产物。按照天人相应的观点,人之五脏六腑犹如天地之五运六气,天地运化能生外寒湿热燥,人之变化亦能生内寒湿热燥。外寒湿热燥能演变为“寒毒”“湿毒”“热毒”“燥毒”,内寒湿热燥亦能演变为“寒毒”“湿毒”“热毒”“燥毒”。以上对毒的提纲论述,为后人认识毒指明了方向。 2药物之毒:《素问·异法方宜论》、《素问·移精变气论》、《素问·汤液醪醴论》、《素问·藏气法时论》、《素问·宝命全形论》、《素问·示从容论》《素问·疏五过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素问·徵四失论》和《素问·五常政大论》的后半部分共10篇所论之毒属于药物之毒。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素问·移精变气论》云“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 此云药物之毒,从内涵来说,并非单一。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此毒,显然既是药物之毒,也含有干预或治疗方面的含义。《黄帝内经》首次将毒赋予药物和治疗学含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黄帝内经》提倡治未病的思想,认为治未病,胜于治已病。既是未病,显然不需用“毒药”,一旦已病,则非“毒药”不可胜任。 只有“毒之”,方能直达病所,切合病机,驱除病邪,达到疾病症愈。当然在这里所说的“毒药”,既包括现代所说的毒药,也指药力峻猛,或说药力大,治疗作用明显的药物。不能一概认为单指“毒药”。 《黄帝内经》首次提出的药物之毒和毒药的含义,可以这样来理解。大致药物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药有毒也。机体之所以为病,大致病因于毒也。以药物之毒去攻疾病之毒,所谓以毒攻毒,可能是《黄帝内经》作者的初衷。遗憾的是,《黄帝内经》中对此论述得过于简略,未能详细介绍毒药的属性和所攻之毒的种类,对毒的内涵也未加界定。但也不难看出,疾病之所以为病,盖体内有毒在作祟,为后人认识和深入研究毒奠定了基础。 循着《黄帝内经》思路认识毒 1毒是一类致病因素: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确立了毒是一类致病因素,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由于社会的落后,缘于自然环境即天地因素的疾病较多,因而,对毒的认识只能限于天地方面的成因。由于天地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毒,当然是外毒。初步指出了外毒有“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等。虽然未能介绍上述毒的致病特点和临床属性,但也不难看出,大抵“寒毒”为病当具有伤阳、寒邪的属性;“湿毒”为病当具有遏气、黏滞的属性;“热毒”为病当具有耗阴、酷烈的属性;“清毒”为病当具有侵犯肝胆和心包、影响神志和决断的属性;“燥毒”为病,当具有津少液涸干燥的属性,甚至临床上可以出现金水不降,水金不相生,阴虚火旺的证候。 2毒的从化性和非孤立性:《黄帝内经》中所言的毒作为一类致病因素,具有明显的邪气从化性。意谓毒非孤立而为之,乃邪气从化于机体和周围环境的状态而成。结合现代的认识,大抵“寒毒”从化于外界的寒邪峻猛或机体的阳虚寒盛;“湿毒”从化于外界的湿气太盛或机体的胃虚阳弱、脾不运化;“热毒”从化于外界的暑热酷烈或机体的阳亢有余;“清毒”从化于外界的木气不柔、木火不合或机体的心肝火旺;“燥毒”从化于外界的燥气太盛或机体的金水不布和肺肾阴虚。 毒的从化性,决定了毒的非孤立性。这种非孤立性的内涵,意指毒不是一种单独存在的致病因素,而是原致病因素蕴积的结果。换句话说,毒的形成必须有成毒的母基因素或说是潜在的、持久的其他致病因素。 可以说,《黄帝内经》所提出的毒的从化性和非孤立性,当算是毒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毒的从化性,是说毒乃邪气从化而成,但并非任何邪气或疾病的任何阶段都可从化为毒。只有当致病邪气峻猛酷烈或非峻猛酷烈,但于体内长期滞留时,才可从化为毒。在此,既要强调认识毒于疾病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要避免陷入万病唯一毒的泛毒论。 既然是从化之毒或说是从化致毒,而又有非孤立性的特点,那么,启示医者在寻找或认识毒时,就应当按照从化之前的病邪性质及机体的整体状态,来考察从化的可能性。同时按照这个思维,来认识毒的属性和临床表征。 目前在临床上,言毒、论毒和治毒的意识在进一步强化,然而如何辨识毒,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即使目前,也无法总结出毒的特有的临床表征。结合毒的从化性和非孤立性的特点,可以认为,毒的临床表征,可以表达为原致病邪气数量猛增、致病性质骤变、致病力量骤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又可以由于邪气所在部位的不同,而表现为相应靶位的损伤过程,而这个过程,从即刻属性来说,呈现出机体的正气与邪气相互作用后,正邪交争剧烈的某种状态。 3药物之毒有大小等的区分:药物之毒有大毒、常毒、小毒、无毒之分,以药物之毒测病因之毒,病因之毒也应有大毒、常毒、小毒、无毒之异。《素问·五常政大论》明确将药物之毒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按照以药测病的方法,作为病因之毒,也可以分为大毒、常毒、小毒。结合上述的邪气从化致毒原则,大致原致病邪气峻猛者,可以从化为大毒;原致病性质不甚峻猛者,可以从化为常毒;原致病性质相对柔弱者,可以从化为小毒。 如果原致病性质一般,且在一定时期内,对正气的损伤不剧,或呈慢性病程者,则标志者尚未从化致毒,即无毒。在这里提出毒的分类方法,有助于在临床上把握病情,确定干预方案,以进行恰当的治疗。 4治毒必须用毒药:《黄帝内经》关于治毒的论述,可以说比较具体。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明确将毒药分成了大毒、常毒、小毒、无毒、有毒等,意味着对于疾病来说,可能也有大毒、常毒、小毒、无毒、有毒的疾病阶段和状态。同时可以推测,疾病进入了毒的阶段,就必须用毒药,即毒病就要用毒药。 进一步是否可以认为,对于大毒阶段或说大毒为病,在用毒药治疗时,是否也可遵守“十去其六”的原则,其他依次类推,常毒阶段或常毒为病,当“十去其七”,小毒阶段或小毒为病,当“十去其八”,无毒阶段或无毒为病,才可“十去其九”。总以不过为度,以免正气受伤,于事无补。 需要说明的是,何为上述治毒之药,即平常所说的解毒药?毒药既然是药性峻猛之药,那么,反之亦可以说,药性峻猛的药物就是治毒之药。 目前在临床上,说起毒的治疗,动辄就要用清热解毒药。认为只有清热解毒药才是解毒治毒之药。显然是把毒的概念和内涵简约了。对于热毒,选择清热解毒药是正确的,而对于寒毒为病,或五邪必然会积累蕴结,日久邪气从化,酿变为毒。若因于内风所蕴变之毒,多称为风毒,因于寒所蕴变者为寒毒,因于湿蕴变者为湿毒,因于瘀蕴变者为瘀毒,因于痰蕴变者为痰毒。这种蕴变为毒的过程,实际上是由于气血相乱,邪气从化所导致的。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黔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黔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治。”《慈幼新书·胎病》云:“小儿胎病凡二端,在胎时母失爱护,或劳动气血相干,或坐卧饥饱相役,饮酒食肉,冷热相制,恐怖惊悸,血脉相乱,蕴毒于内,损伤胎气,此胎热胎寒,胎肥胎怯,胎惊胎黄诸症,所由作也。”《保婴撮要·伤食发丹》云:“一小儿停食便秘,四肢赤色,此饮食蕴毒于内,用枳实、黄连、厚朴、山楂、神曲,而便通赤解。” 从毒的形成来看,邪气蕴结是成毒的重要环节。诸邪蕴结的内涵,并非单指蕴结成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而是包括通过邪气的蕴结,诸邪的交互为害,形成疾病过程中的一些新的病理机制,当然也同时伴生出一些新的致病因素。 总之,总结古今对毒的认识,毒是有害于机体的、引起机体功能破坏、丧失和/或败坏形质、导致病情突然加重或呈沉疴状态并难以干预的、隶属于病因和病机学范畴的一类特殊的致病因素。这种致病因素无论是渐生抑或骤至,也无论来源于外界或体内,统称为毒。说疾病进入了寒毒阶段,择用清热解毒之药就是药不对证了。鉴于此,从《黄帝内经》所说的“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来看,对于“寒毒”的治疗,可选择药性峻猛的散寒药物;“湿毒”就可选择药性峻猛的辛散芳香药物,其他依此类推。 总之,《黄帝内经》中有关毒的论述,对嗣后历代医家认识“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领会《黄帝内经》毒论思想,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毒的概念及其致病性质,加深对毒的理解,为当前进一步认识“毒”和研究“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毒的含义 “毒”是中医学重要的概念之一,历代医学典籍对“毒”这一概念均有论述,涉及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诸多方面,理论纷繁复杂。然而每种观点、学说,甚或流派的产生都受其所处的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受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影响的中医学更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理论特性。“毒”这一概念历经千年,围绕“毒”所形成的理论不胜枚举。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所处的环境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意味着疾病会变化,患者会变化,治法方药亦会随之变化,中医学的理论亦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学者赵帆等论述了“毒”这一概念的观点,旨在为中医学理论创新提供新思路。 毒的原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毒,厚也,害人之草”。三国魏时张揖所著的《广雅》记载“毒,犹恶也”。清代光绪34年间编撰的《辞源》中“毒”的释义有三:①恶也,寒也;②痛也,苦也;③物之能害人者皆曰毒。1978年首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毒”的解释扩大到6种:①进入机体后能与有机体起化学变化,破坏体内组织和生理机能的物质。②对思想意识有害的事物。③毒品。④有毒的。⑤用毒物害死。⑥毒辣,猛烈。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各个学科的发展,“毒”的概念也逐渐扩大。通过总结我国现存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字典、词典,可以对“毒”的解释归纳为以下3点。首先,“毒”是一类植物,具有名词属性,其作用是损害人体,而后其损害从生理方面扩大到精神方面、生理精神方面(毒品);第二,“毒”具有“甚”、“猛烈”等意思,具有形容词属性,是对程度的描写;第三,“毒”亦有动词属性,指用“毒”伤害人体的过程。 中药学中的毒 1“毒”与“药”:“是药三分毒”将“药”和“毒”的关系描写得淋漓尽致,使这2 个概念难分难解。《黄帝内经》中有大量内容论述药物的毒性。如《素问·五常政大论》载“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其详细地论述了药物毒性,并对其程度有明确划分。又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此处的“毒”亦是“药”的意思,古人甚至将“毒”与“药”等同看待,药即为毒,用之宜慎。“毒”若指代“药”,则作名词意。古人对用药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药”用之不当,亦可以损伤身体,药气太盛即为“毒”,“药”亦会转化成“毒”变成病因。 2“毒”指药性:“以毒攻毒”是个耳熟能详的词语,指用有毒性的药物来治疗因毒而起的疾病,引申义是指利用某一种有坏处的事物来抵制另一种有坏处的事物。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使得大家对这个词的意思产生了一定的误解,片面地理解了该词的含义。另外,《素问·五常政大论》云:“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此处之“毒”具有形容词属性,是指气猛味厚作用峻猛的药物。由此可见,“以毒攻毒”也有用性味猛烈的药物治疗严重疾病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毒”损机体的现象普遍存在,那么对应的治疗原则就应该是“解毒”。但回顾中药学的相关内容,只有“清热解毒药”这一类药物是明确写出其具有解毒功能。这里我们要澄清2个问题,第一,不是所有的清热类中药都具有解毒功效;第二,“清热解毒药”所解之“毒”应为“热毒”。 中医学中的毒 1“毒”与“邪”:“毒”的原意之一是指代一类植物,这类植物是人体受害的原因, 同时这类植物也具有使人受到伤害的能力。《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早把“毒”作为医学概念提出的典籍,在“毒”原意的基础上,赋予了“毒”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意义。将“毒”引申为病因、致病因子。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载“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又如《素问·刺法论》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毒”究竟是何种病因?具有何种致病特点?临床各家亦有诸多论述。王黎等通过分析《黄帝内经》和其他中医典籍的相关论述,认为“人体之毒”的本质是指人体气血阴阳的失衡状态,亦为病因。姜良铎教授从病因病机层面总结出“毒”的概念——凡是对机体有不利影响的因素,无论来源于外界或体内,统称为“毒”。从“毒”的角度来认识病因病机,是根据病因作用于人体后所产生的影响——无论这种病因对整个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都经高度概括后抽象出一个概念——毒。周仲瑛教授的“伏毒”理论指出毒邪具有潜藏于人体、待时而发的病理特质。感邪之后并未立即发病,邪气伏藏,遇感而发,且发病迟早不一,一旦发病,既可以表现为猛烈急骤,亦可以表现为病势缠绵、迁延难愈。伏毒最主要的特点是隐伏。“毒邪”伏而待发,未发之时即受体质、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且往往发病之时病情复杂。伏毒之“毒”可为风、寒、暑、湿、燥、火任意一端,亦可为痰、为瘀,其毒既可以是外感病因,又可以成为病理产物。 中医学中的“邪气”,泛指各种致病因素,简称“邪”。人体是否发病,取决于“正邪斗争”的结果。如将“毒”作为“失衡状态”或者“不利因素”,那么“毒”与“邪”这2个概念则有部分重合,临床上“毒邪”的描述亦不罕见。如果简单地将“毒”和“邪”等同观之,那么周仲瑛教授提出的“伏毒”理论似乎也可以称为“伏邪”理论。分析“伏毒”理论,其重点并不在“毒”上,而是在“伏”上,强调的是动态的过程。根据上文对“毒”的分析,“毒”亦有“毒害人体的过程”的意义,而“邪”则 不具该含义。那么“毒”是否能替代“邪”?“毒”和“邪”这2个概念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呢?《黄帝内经》中对“邪”的描述共441处,其中425处均为“不正”之义,并成为各种致病因素的代称。因此用“邪”指代一切致病因素已是一种习惯的、并且被接受的、被承认的说法。与此相较,“毒”的概念则略显狭窄,因此赵帆等认为,“邪”包含了“毒”,“毒”是一种病因,也就是“致病之邪”的一种。 2“邪盛谓之毒”:《金匮要略》指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 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宋代陈无择在《金匮要略》的基础上引申出“三因学说”,即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 “毒”作为病因的一种,究竟何为“毒”呢?有研究者认为“邪盛谓之毒”。“毒”作为病因而言,亦有内外之分。“六气”是自然界 6种不同的气候变化,是无害于人体的。然而“六气”异常则变生“六淫”,“淫”为太过,太过则引起疾病,有害于人体。而“六淫”太过则成毒。《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治。”此段论述出现了大量以“毒”为名称的病因,目前临床亦认同“寒毒”“湿毒”等是由“邪气”衍生而来,同时比“邪气”所引起的疾病更为复杂,更为难治。可见“毒”作为病因亦可看作是对“毒”的第二种意义(现代字典、词典)的引申,即“甚者为毒”。 “七情”是7种情志变化,是机体的精神状态,也是人体对客观事物的不同反应,正常情况下不会使人致病,而异常的情志刺激,其变化超过了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范围,则就会导致疾病发生,成为“内伤七情”。饮食、劳逸亦是如此。七情不遂,五志过极化毒,饮食不节,脾胃功能受损生毒,均是在原有内伤基础上程度加重,由“内伤”质变为“内毒”。 “痰饮”“瘀血”等病理产物亦为致病内因,甚者则为“痰毒”“瘀毒”。现代关于“毒”的理论也十分丰富。浊毒既是一种对人体脏腑经络及气血阴阳均能造成严重损害的致病因素,同时也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脏腑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致使机体内产生的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正常排出,蓄积于体内而化的病理产物。“浊”性黏滞、重浊,易结滞脉络、伤气浊血、阻塞气机。结合上文对“毒”的分析,拆分“浊毒”的概念,可知“浊”是“毒”的定语,是对“毒”特点的描述。 3“毒邪”的标准:根据“毒”的原意,结合对现有病因理论的分析,我们将“毒”作为一种独立的致病因素,归入内外因中则为“六气六淫六毒”“七情、饮食、劳逸内伤内毒”“痰饮痰毒”“瘀血瘀毒”等等。众所周知,从六气到六淫,情志、饮食、劳逸到内伤,水液到痰饮等的变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以是否引起疾病作为判断标准的。而从六淫到六毒,内伤到内毒,痰饮到痰毒,或者从六气、七情直接变化到毒,亦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毒”为病更甚。 遗憾的是目前普通病邪发展到何种程度则成为“毒”, 临床各家尚无明确的判断标准。临床上对“毒邪”的判断也是莫衷一是。赵帆等认为“六淫”“七情”“饮食劳逸”等普通病邪致病,无论轻重缓急,痊愈后不遗留器质性损伤;而“毒邪”致病,无论“风毒”“热毒”等,治愈后会遗留器质性损伤。 以是否存在器质性损伤来区分“普通病邪”与“毒邪”具有以下优势。其一,通过西医学方法评价,有统一的标准和指标,更具客观性。其二,随着医学的发展,评价手段的进步, 区分“普通病邪”和“毒邪”的标准也随之变动。 通过对“毒”的分析,对于“毒”这一概念,首先,“毒”的本意泛指有毒的植物。其次,“毒”的引申意义在于,“毒”是一种致病因素,外来如寒毒、风毒等,内生如火毒、湿毒等,亦包含病理产物如瘀毒、浊毒等。第三,“毒”是对致病因素、病情、药物性味等方面程度的描述,有“甚”“加重”“进一步”的意思。“毒”和“药”的概念有重复的部分,性味猛烈的药物可称为“毒药”,使用性味猛烈的药物治疗疾病均可以称为“解毒”,不仅仅局限“清热解毒”一项。“毒”是“邪”的一种,“邪之甚者谓之毒”。致病不遗留器质性损伤的为“普通病邪”,而“毒邪”猛烈,致病后预后差,遗留器质性损伤。 目前中医学对“毒”的研究逐渐深入,建立和完善“辨毒”(识别“毒”)——“确毒”(诊断“毒”)——“解毒”(治疗“毒”)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3毒的多义性 中医理论之中的“毒”是如何形成的,有过怎样的理论意义。学者曹东义等认为其借鉴了化毒、解毒学说,并为此作了全面而颇有见解的论述。严格的说,什么是毒?古人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这并未妨碍他们使用“毒”来说明临床问题。 远古时药就是毒 在先秦的时候,古人用“毒”来说明药性,《周礼·天官冢宰下》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文中将“毒”与“药”并称,把二者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关系。按照常人的理解,毒与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毒是对于人体有危害,药是对于人体有帮助,不应该相提并论。 希波克拉底在《医生誓言》中,虔诚地向众神宣誓说:“余愿尽己之能力与判断力之所及,恪守为病家谋福之信条,并避免一切堕落害人之败行,余必不以毒物药品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之术。”在希氏看来,毒品与药物是截然对立、不容混淆的,所以他说:“余必不以毒物药品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希氏的这种观点与中医主张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是完全不同的看问题方法,中医能够化毒为药,毒与药没有截然的界限。希氏所谓“至于手术,另待高明, 余不施之,遇结石患者亦然,惟使专匠为之”的主张,是不屑于做手术。西方几千年的手术、放血,基本都是请剃头匠完成的事情。至今理发馆红白相间的招牌,就是血液和止血带的象征。几乎与希氏同时代的扁鹊秦越人,高举反对巫术的医学旗帜,经常从事“聚毒药”的医疗活动。中医受古代辩证法的指导,认为一种物质,它既可以是危害人体的毒物,也可以是治疗疾病的药物,二者没有截然的界限,并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可以组合成方,药物之间互相制约,或者通过加工炮制,达到“减毒增效”,或者“有毒无害”的用药目的。因此, 才能有医师“聚毒药”的事情,否则,就无法区别“投毒害人”与“解毒行医”的行为,医生的职业也将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欧洲的辩证法成熟于黑格尔(1770~1831)时代,此前辩证地看待毒与药的转化问题,应该是不现实的。中医学历史上却是一直辩证地看待毒与药的问题的,而且善于“化毒为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云:“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 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这段经文中,也是“毒药”并称。联系上下文来看, 东方治病用砭石,南方治病施九针,北方治病常用艾灸,中原治疗多用导引按摩。这样说来, 西方治病尽管经常使用“毒药”,也是毒与药不分,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如果有区别的话, 勉强可以解释为毒是猛烈的意思,“毒药”也就是药性猛烈的药物。 《素问·移精变气论》有一段讨论“毒药”起源的论述,可以为上述“毒药不分”的观点作注解。“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文中说,上古的时候治病不需要毒药。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神农还没有尝百草,古人对于药物还没有研究,治病也就没有“毒药”可供选用, 只有用自我保健锻炼、心理调整的治疗方法,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后来,这些措施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要了,就通过不断摸索,甚至是神农尝百草的探险,才逐渐发明了“毒药”治病的方法。在这个早期用药物治疗的阶段,由于服药经常中毒,所以“毒药”并称,这也是毒与药难以分别的早期用药现象。古人这样“毒药并称”,既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习惯,也暗含着慎用药物的思想,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使用药物。《黄帝内经》中“毒药不分”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毒药攻邪,五谷为食,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毒药无治,短针无取”,“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刺灸砭石,毒药所主”,“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其于毒药何如”等等, 都是不加区别地把“毒”与“药”等同看待,说明了中医对于药物的慎重态度。 《论语》记载了孔夫子对于服用药物的慎重态度,他收到季康子赠送的“保健药”时, 真诚而慎重地说“丘未达,不敢尝”。因为那时,尽管人们服用某些药物也许会有《神农本草经》所说的“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的作用,但是用不好就会适得其反,会造成“服药不成反成毒”,伤害身体,有碍生命。 药气太盛可成毒 药有利与害的两面性,勇于探索的医生,代不乏人;敢于服药的患者,也越来越多。随着实践的深入,用药的经验和理论逐渐丰富起来。绝大多数人服药之后,不仅祛除了疾病的痛苦,而且达到了健壮体魄,安定神志,愉悦精神,美颜色,益气力的美好境地。因此,“毒药并称”的局面逐渐发生了改变,“毒性”在淡化,“药性”在强化。因为人们在实践之中, 掌握了规律,可以控制药物的毒副作用,“化毒为药”、“化害为利”成了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独特贡献。《左传·僖公三十年》曾经记载,晋候让医衍为卫侯诊治,并嘱咐他借用药的机会“下毒”,以便谋害“罪不至死”的卫侯。医衍不敢违抗命令,又不忍心以救人之名杀人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所以就“薄其鸩”,让卫侯上吐下泻而免于一死,从而在史书里留下了一段感人的事迹。这也充分说明了远在春秋时期,医生对于药和毒的把握,或者二者之间互相转化的“关键技术”,已经达到了很精深的程度,不是盲目摸索的阶段了。 当然,中医学在奉献的过程之中,积极地吸收了大量前人、民间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人体试验”总结之后的“科研成果”。毫无疑问,这种实验风险极大,代价很高,因此也就更加可贵。很多人“密不外传”,或者“传男不传女”,或者“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得到了这种宝贵的用药经验,就要“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素问·示从容论》云:“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这是黄帝君臣谦虚地求教过程,“投毒药”就是用药治病。《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把药物划分成有毒与无毒、大毒与小毒是一种进步。《神农本草经》积极吸收这个成果,把365种药物按照这个思想进行归类,分成上中下三品,此后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法则,一直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几千年。 化毒为药,是古人不懈的追求,也是今人创新的一个途径。砒霜有毒,尽人皆知。然而, 在今天医学家的手里,借鉴古人经验,已经把砒霜的有毒成分砷用于治疗白血病,这是古为今用的一大成果,与古人“化毒为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毒与药的关系里,其相互转化的关键,是对于人体的利与害。对人体有害的,就是毒;对于人体有利的,就是药。当药物的有利作用转化为有害的时候,药就变成了毒;当毒物被人们利用而有利的时候,毒就变成了药。维生素、氧气、水、盐、食品,这些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一旦过了量,对人体造成危害的时候,也就变成了毒。细菌、病毒、有害的重金属等等,它们也不是绝对有害的东西,一旦它们成为疫苗,或成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的时候,它们也就由毒变成了药。中医在古代发明的人痘疫苗,就是在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哺育出来的药,是人类战胜传染病的伟大原始创新。假如没有毒可以转化为药的思想,就不可理解古人把天花患者的脓疱痂皮, 接种在健康人身上的行为动机。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攻击中医不人道。 六淫太过则成毒 毒是一种危害人体的因素,因此凡是危害人体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毒。根据危害的程度不同,可以划分为大毒、小毒、常毒、苛毒等不同的毒性,也可以根据其不同性质,划分为寒毒、热毒、湿毒、浊毒、秽毒等。风是自然界里最为普遍的客观存在,《易经》里就用巽来代表风,代表春天,也就是代表万物的生机。张仲景说:“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害万物的风,肯定是太过分的风;太过分的风,就是属于六淫的风。“淫”就是太过分;太过分,就是邪,就是害。《左传》中,医和所说的“天生六气,淫生六疾”,就说明了自然界的阴阳、风雨、晦明都可以因为太过分,而变成致病的六淫。《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风气是古人很早就观察到的自然力,因此对于风的研究和认识,也就形成得早,看得深刻。善于养生的人,不会受风气的伤害,无论冬天里的寒风,还是夏天里的热风,都不会伤害健康人。甲骨文里,“祸风有疾”的记载很多见,写上日期的“祸风有疾”,都在冬春季节。甲骨文里,把“杞侯热病”的病因,归结为风邪引起的,可见其认识甚早。 《素问·征四失论》云:“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 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文中把“或伤于毒”当作致病的四大因素之一,可见毒邪的致病作用,已经引起了古人的高度重视。颈部、腋下产生了一串一串的结节,古人称之为瘰疬。当瘰疬引起恶寒发热的时候,他们追索这种疾病的原因,就归结为毒气留结于脉而引发本病。所以《灵枢·寒热》云:“黄帝问于岐伯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通过脉象的判断,也可以诊察出来体内有无毒气。《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脉“微滑, 为虫毒、蛕蝎、腹热”。对于六气太甚产生的毒气,《素问·五常政大论》论述得最系统:“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 其治淡咸,其谷黅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 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知。”文中提出来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的概念,不仅是“五毒俱全”,而且指明了“五毒”都是从寒热燥湿转化而来。对于六气转化而来的“五毒”的治疗方法,文中提出“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故云: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由此不难看出,治疗“五毒”,不仅可以使用针刺,在经脉上下内外取穴治疗,而且可以用药物调治。调治的原则,是用气味比较足的药物治疗五毒较甚的病情;而气味比较淡薄的药物,只能用来治疗五毒比较轻浅的病证。 毒延伸出预防思想 既然五毒是由六淫转化而来,那么,避免毒气的伤害,也就是避免过分暴露于六气、六淫之中。《灵枢·九宫八风》云:“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曰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这是一般的避免六淫的伤害。同样的道理,传染病的传播,也是由邪气引起来的,也需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论语》里记载“伯牛有疾”,孔夫子作为伯牛的老师,希望前去探望患病的弟子,又怕被他的疾病所传染,就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窗户里看看。事到临头,孔夫子不仅看见了他的学生伯牛,而且还“执其手”,感慨地说“斯人也, 而有斯疾!斯人也,而有斯疾!”古人为了预防疾病,因此建立了“疫室”,进行隔离,以防传染。《素问·刺法论》云:“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黄帝问的问题是“不施救疗”时,如何预防被传染?岐伯用他所积累的医学理论和医疗经验,回答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古人要“避其毒气”,自然不会主动地接近患者,不是“无知者无畏”地蛮干,而是要积极预防。一方面要“正气存内”,一方面要“避其毒气”。为了做到这两点,一是要练气功,从心理上不怕邪气,二是服用药物进行预防, 三是制作疫苗抗击毒气。这种靠疫苗接种战胜传染病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是中医学贡献给人类极为宝贵的财富,是人类战胜传染病的原始创新,是一个伟大创举。 在古代,疫病来临之际,中医要进入病患之家进行治疗,有什么措施可以预防吗?《素问·刺法论》云:“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显然这种思想上的准备动作,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准备, 也是与气功导引一样的一种做法。在临床上,患者精神的力量是不能低估的,中医一贯主张精神驾驭形体。中医治病的过程,不是要“排除心理因素影响”,而是要充分调动患者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中医“形神一体”的特色所在,也是中医主张五神脏的科学性所在,更是不能用“脑主神明”代替“心主神明”的原因。 中医战胜传染病方法很多,国医大师邓铁涛说“有一个武器库”。《黄帝内经》在论述了“正气存内”、“避其毒气”、“五气护身”之后,又告诉后人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有了“五气护身”的思想准备,再加上一些呼吸吐纳的健身措施,一些服药预防的避毒方法,中医医生们、患者家属们,终于可以进入“疫室”了。整个的过程之中,尽管有一些措施,是那样原始,是那样有些欠妥当,但是他们都是积极应对传染病的挑战,都属于主动探索,因此是可贵的,是值得尊敬的。由他们积累出探索的成果,象发明人痘疫苗那样的世界奇迹,也不足为怪。 治疗过程也可以简称为毒 辩证地说,既然药物就是毒物,药物的治疗过程,可以称之为“以毒攻毒”。那么,“毒”也就可以代指“治疗”。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妇人重身”就是怀孕。对于孕妇,现在强调尽量不用药,以免药物引起对于胎儿的伤害。古人更是不把药物推荐给孕妇,《黄帝内经》把对孕妇的治疗说成是“毒之何如”,可见古人对于孕妇用药是格外小心的。 智慧的医师岐伯,并没有说孕妇绝对不能用药,而是说“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只要病情需要,就可以使用药物。精明的黄帝一定要刨根问底:“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不敢隐瞒不告,就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过者死。”治疗疾病,尤其是“大积大聚”的病,很有可能存在着浊毒,治疗的时候,必须攻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衰其大半即可,不仅“过度医疗”不可以,就是过了“大半”也会引起不良后果,甚至可以导致“死亡”,这个界限的把握需要精湛的医术。 《黄帝内经》对于毒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也是很深入的,因此,黄帝与岐伯对于这个“科学问题”讨论了很多次。《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帝曰:请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 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中医所使用的工具,针刺可以伤人,因此要讲求针道;药物有毒性的一面,所以要深入研究炮制、配伍,不断体验药物组合起来之后的效应。逐渐地,人们在实践之中发现,配伍起来的复方,其中有毒性的药物可以减缓毒性,避免副作用,增加治疗作用。也就是说,按照一定原则组合起来的“组合效应”,远远地胜过了使用单味药的“个体疗效”,为安全有效使用药物开辟了一条道路。无论是“制”之小与大,都有君与臣,是一个有序的组合,而不是随意的“鸡尾酒”疗法。有序的组合,就能“整体涌现”出来新的效应,不是“简单加合效应”。所以,中医学“有实无名”地最先运用了“复杂性科学”的原理,安全有效、复杂高效地解决了很多临床复杂问题。甚至到目前为止,现代科学还远望着中医学的背景,既看不明白其中道理,更无法把它作为一个普遍可行的技术方案加以推广。比如,中医对于(SARS)的良好疗效,中医对于艾滋病复杂病情的控制,都不是还原论方法能够研究明白的。 4毒的概念诠释 学者常富业等认为,毒不仅是一个具有物质属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病理学属性的概念。毒的概念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毒,乃为一类特殊的致病因素,如糖毒、脂毒、食毒、虫毒等。广义的毒,则是指寓于病因和病机双重属性的一个概念,该概念的实质,强调在病因的作用下,疾病发生和发展的骤然变化,出现功能破坏和形质受损。毒可分为外毒与内毒。 近年来,随着对中医病因研究的深化,对于毒的研究,逐渐引起同仁的关注。据初步的近1000部古文献检索发现,毒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名词,尤其是广泛地见于明清书籍中。 对毒的提法也有种种称谓,形成了众多的相关名词。毒的相关名词或称谓主要有:邪毒、毒邪、毒气、气毒、毒血、风毒、毒风、湿毒、火毒、毒火、痰毒、毒痰、毒涎、寒毒、热毒、郁毒、瘀毒、水毒、液毒、脏毒、胎毒、遗毒、痘毒、痧毒、温毒、瘟毒、疠毒、疫毒、毒疫、疳毒、痢毒、酒毒、食毒、肿毒、蛊毒、阴毒、阳毒、痈毒、疡毒、疮毒、恶毒、时毒、瘴毒、虫毒、宿毒、斑毒、疹毒、恶毒、便毒、秽毒、渚毒、百毒及毒聚、毒滞、毒结、毒壅、毒归、毒泛等。由此可以看出,古人论毒,有的指病因,如邪毒、毒邪、毒气、毒血、 风毒、湿毒、火毒、毒火、痰毒、毒痰、毒涎、寒毒、热毒、郁毒、瘀毒、水毒、液毒等;有的兼指病机或病理变化,如气毒、毒血、郁毒、瘀毒、毒聚、毒滞、毒结、毒壅、毒归、毒泛等;有的指病证名,如脏毒、胎毒、便毒等。虽然称谓众多,但对毒的系统论述尚属匮乏。可以说,古人对毒尚未有明确的概念,内涵不清,外延不明;对毒也未有明确的分类,可以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且详于外毒,而略于内毒。 关于毒的分类 从上述古人所提出的毒的相关名词上看,病因学上,可以将毒分为外毒与内毒;从毒的病理性质上,可以将毒分为阴毒与阳毒。前者分类方法,如同六淫和内生五邪的分类方法类似。所谓外毒,意为来源于体外,可单独害人,亦可杂六淫侵袭的一类致病因素。与此相反,内毒则是脏腑功能减退或障碍,机体代谢减退、紊乱或乖戾失常过程中而产生的一些新的致病因素和或新的病理变化。而后者的分类方法,则强调了毒邪为害的致病特性,或损阳生寒,或灼阴助热,表现出阳盛或阴盛的临床表征。 关于毒的内涵 毒为何物?毒的内涵是什么?目前,大都认为毒就是一种(类)或几种(类)致病物质,具有类似现代医学所言的毒素或毒物一样的物质性。按照如此的解释,那么,采用现代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的实体实验里,就有可能还原出或寻找出中医所说的毒的原形。以临床上被广泛认同的热毒来说,热毒是什么?热毒是一种或几种物质?热毒是一种或几种毒素亦或毒物?恐怕目前尚不能决断。不仅热毒不能断言,就是其他被广泛说起的诸如温毒、瘟毒、疫毒、 瘴毒、疟毒、虫毒、疳毒、暑毒等,也同样不能断言。虽然对清代温病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但导致一系列温病的各种温毒、瘟毒、疫毒等,也与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微生物如病毒、细菌等,也有不同的内涵。例如,导致西医伤寒病的伤寒沙门菌,侵袭机体发病后引起高热、皮疹和出汗的临床表现,据此辨证当属于温病范畴。因而现代临床多从热毒或温毒、疫毒来辨证。而病程阶段出现的畏寒、食欲不振、腹胀、便秘等,又可辨证为寒毒作祟。显然,将伤寒按中医辨证为温毒、热毒到寒毒,使毒具有不同的内涵。而西医从病因学上所说的致病菌,即伤寒沙门菌。由此可以看出,中医学所说的毒,不仅包括了西医所说的致病源或致病菌乃至毒素,具有物质性上的涵义,更主要的,将西医伤寒辨证审因为温毒、热毒和寒毒的变化,概括了伤寒疾病病程中的病理变化、病理机制,是疾病病理过程中的概括。 因此,常富业等认为,毒不仅是一个具有物质属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病理学属性的一个概念。犹如炎症或毒害一样。毒是隶属于发病学范畴的、具有病因病机双重属性的一个概念,该概念的内涵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毒之概念,乃为一类特殊的致病因素,如糖毒、脂毒、食毒、虫毒等。广义的毒,则是指寓于病因和病机双重属性的一个概念,该概念的实质,强调在病因的作用下,疾病发生和发展的骤然变化,出现功能破坏和形质受损。可以这样认为,内毒从其物质属性来说,其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机体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代谢废物,由于其在生命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因而它是内生之毒的主要来源,也是机体排毒系统功能紊乱时存留体内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二是指那些本为人体正常所需的生理物质,由于代谢障碍,超出其生理需要量,也可能转化为致病物质形成毒。三是指本为生理性物质,由于改变了它所存在的部位,也成为一种毒。可见内毒既是一种生理物质,又是一种病理产物,都是脏腑功能失调的反映,一旦产生,便又加剧脏腑功能失调,形成复杂的病证。 从内毒的病因病机属性来说,内毒的产生,往往提示着新病因的产生,在这种新病因的作用下,会产生出新的病机,介导新的病机变化,从而使病情发生新的变化,产生出新的证候。诸如中风病过程中的内风之邪,在中风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风邪的肆虐,扰乱气血,出现种种见证。持续的风邪肆虐,进一步的气血逆乱,往往会引起经络失调,气遏血瘀,络道受损,运毒排毒障碍,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致病因素风毒。风毒的产生,不可避免的引起原病情的加重,使病情步入难以干预的境地。 关于毒的产生 毒具有病因与病机的双重属性。无论是作为病因之毒或病机之毒,毒的产生都应当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1外毒的产生:外毒,顾名思义,是来源于机体外的一类毒,如温毒、瘟毒、疫毒、瘴毒、疟毒、虫毒、疳毒、暑毒、水毒等。这些毒邪,或生于异质之体,或成于运气乖戾之时。由于其致病能力强,当机体正气不足,或脏腑组织器官功能紊乱或防御屏障受损时,便得以侵袭机体而为病。外毒既然来源于体外,自外侵袭机体,必然也属于外邪的范畴。既然是外邪,其与六淫的关系和区别值得关注。外毒和六淫同属于外邪,二者可杂合为病,如风毒、湿毒之属。同时,六淫侵袭机体,在某种条件下,如邪气猛烈,正虚邪气恋滞,蕴结日久,亦可酿变化毒,如风毒、湿气、暑毒、寒毒等。由此可以看出,同是作为风毒,既可以为风邪与毒邪相合而成,亦可以为风邪久恋蕴结而为之。因而在临床上就可能具有相同的临床表现。当然也有其不同之所在,其最根本的不同,当随其起病的急骤、病程的长短和机体的正气之盛衰而异。 关于外邪侵袭蕴结为毒,所谓蕴毒或积毒说,自古以来就倍受重视。此所谓“毒者,邪气蕴结不解之谓”。其成毒的具体过程,大致如下:六淫之邪侵袭人体,在病程演变中,可因机体阴阳状态的失衡而衍生为毒,此所谓著者邪盛为毒,微者病因积累,日久反复外感,邪积为毒。无论邪盛为毒或邪积为毒,其致病作用都比原病邪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外邪所致的心痹,是由于“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素问·痹论》)所致,此时,内舍于心之邪除部分具有原病邪的性质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反复外感,病因积累,邪积成毒,形成一种有别于原病邪的更强的致病因素。 2内毒的产生:内毒,顾名思义就是内生之毒,其来源于体内,是正衰积损,脏腑功能减退或障碍,机体代谢减退、紊乱或失常,体内排毒系统功能发生障碍的标志。内毒的产生多是一种长期的慢性潜变过程,既可以单独产生,亦可夹杂其他内生之邪而现。尤其是当内生之邪气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因众邪蕴积,阴阳状态严重失衡,导致众邪的积化酿生毒,此即《金匮要略心典》云“毒者,邪气蕴结不解之谓。” 了解了内毒产生过程,就有必要探讨内毒与内生五邪的关系。一般认为,内生五邪一旦产生,如脏腑的功能失调不能恢复,或不能及时进行祛邪扶正等相应的干预,则内生 ★ 研究大成:本书对中医毒邪学说在几千年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经过历代医家不断探索、实践与总结所形成的理论建树、学术成果和现代研究进行了全面解读。 ★ 经验集成:本书对造成机体阴阳失调的浊毒、伏毒、瘀毒、癌毒古今诊治经验、方药运用规律、论治思路方法进行了系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