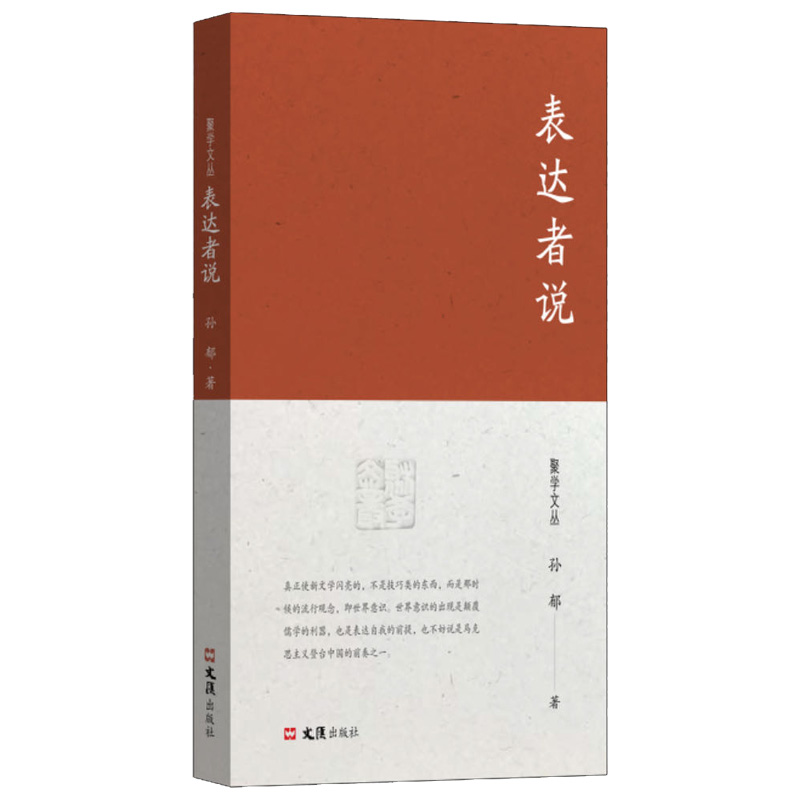
出版社: 文汇
原售价: 56.00
折扣价: 32.00
折扣购买: 表达者说
ISBN: 97875496428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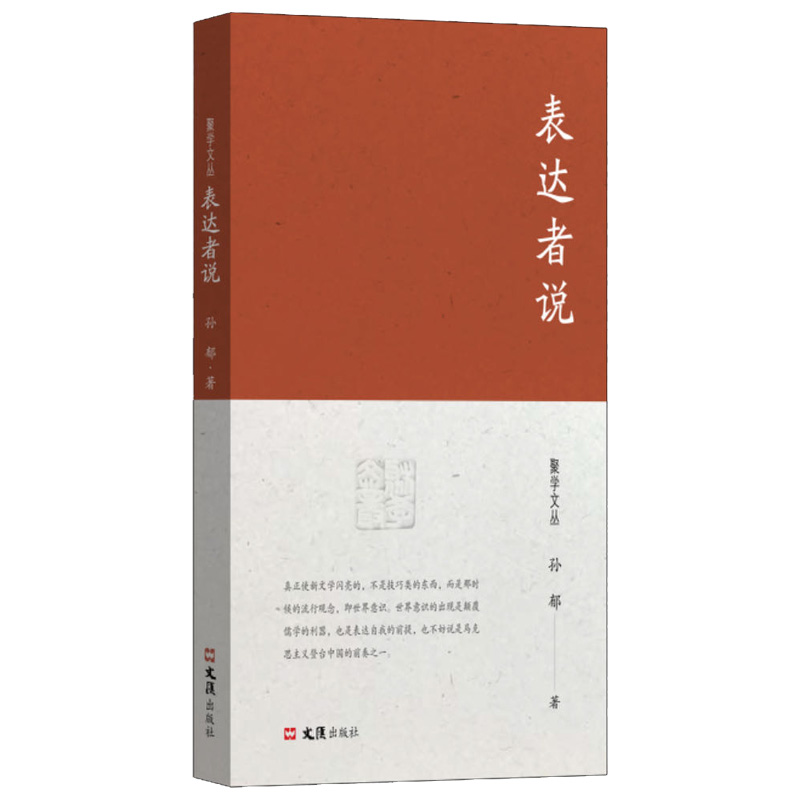
孙郁,本名孙毅,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等,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忧思录》《民国文学课》《思于他处》《苦雨斋旧事》《张中行别传》《孙郁散文》等。
表达者说 1 在《新青年》的文章里,陈独秀的表达逻辑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最不满意的是“伪饰虚文”、憎恶“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文字,于是提倡写实主义,力主睁着眼睛看世界。优婉明洁之情智,才是应当提倡的,不可落入陈陈相因的迂腐之地。新文化讲的自由,其实就是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载体如果不能进入自由的言说的领域,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的。 初期白话文的讨论颇为有趣,胡适与陈独秀商谈白话文走向时,重点强调不用典,要口语入文,还应当拒绝对古人的模仿。在胡适看来,模仿古人和乱用典故,易华而不实,滥而不精,乃文章之大忌。好的作品都非无病呻吟之作,艺术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而非造出来的。这是《新青年》当初要解决的问题。陈独秀在与友人讨论此话题时,延伸了其内涵。他以为胡适的观点还有些温和,要建立真正的白话文,不能不有峻急的文风。他自己就喜欢用此类笔法为文的。 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文字,流出对旧文人习气的厌恶。他们远离官场,揶揄神灵,但他们最想做的是对士大夫文化的颠覆。那时候陈独秀的文字就一反士大夫的正襟危坐气,不中庸,非暧昧,将儒家的虚假的东西踢出去。一时应者如云。比如,说极端话,讲极端句,旨在从四方步式的摇曳里出来,精神的躯体被换了血。而鲁迅的《狂人日记》,简直就是天人之语,读书人的自恋语气全然没有了。鲁迅和陈独秀相似的地方是,都对自己的本阶层的人以嘲笑和绝望的目光视之,意识到连自己也充满着罪过。重新开始,远离着无病呻吟之徒的文字,是那时候的新文化人特有的特征。 解决书写的旧病,一是输进学理,引来新观念和思想。另外呢,是个性主义的展示。在那一代人看来,中国文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人的自我意识,人不过还是奴隶。向人的内心世界开掘,直面世界才是重要的。所以,那时候文章好的,都是有过留学经历的人。他们的文字是从个性文化那里沐浴过的,说的是自己的话,而非别人的意识。 但那时候大家的思想也不尽一致,胡适还是把白话文看成工具,注重表达的自然和平易。而陈独秀则认为艺术之文与工具理性略微不同,有创造性的一面在里面,是不能忽视的。鲁迅和周作人则一开始就呈现着语言的神异性,他们在白话里多了精神的舞蹈,不断冒犯旧的词语搭配习惯。表达在他们看来不仅是思想的演示,也是创造快感的呈现。而后者,那时候没有人重视的,大家其实还不能立即意识到这些。只是在《呐喊》问世后,人们才意识到,智慧对审美的意义大于观念形态的东西。不过,后来的艺术发展,还是观念在主导着审美的思维,能做到鲁迅这一点的人毕竟是有限的。 2 毫无疑问,《新青年》的面孔所以诱人,乃是多了世界性的眼光。同人们讨论问题,已不再是“天下”“华夏”一类的民族主义心态,精神是开阔的。这里主要的功绩是翻译。如果没有现代翻译,就没有新生的白话文。或者说,翻译对陈独秀那代人来说,是建立新文学的基础。他在杂志上不仅翻译了美国国歌、法国散文,还编译了科学思想史方面的文章。他最初的译文,也是文言的,后来自己也不满意这些,当看到胡适所译的契诃夫、莫泊桑的作品时,才感到白话翻译的可能性。后来他推出的易卜生话剧、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已经感到新文学的书写是具有一种可能性的。 一九一六年,陈独秀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希望其多介绍美国的出版物:“美洲出版书报,乞足下选择若干种,详其作者,购处及价目登之《青年》,介绍于学生、社会,此为输入文明之要策。”(水如编: 《陈独秀书信集》,页四六,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胡适应邀在《新青年》发表了多篇译文。像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完全是白话文。所以说白话译文在前,白话创作在后,那是不错的。正是翻译的白话文的成功,才刺激了鲁迅的写作。先前人们不提这些。实际上,陈独秀对此是心以为然的。他的催促之功,胡适与鲁迅都颇为感激。 用翻译来刺激创作,是陈独秀的梦想。但他深知自己没有这样的才华,于是在翻译之余,喜欢编译。他的许多文字,都留有这样的痕迹。《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近代西洋教育》,都显示了他阅读外文的功力。他一方面借用了洋人的思想,反观国人命运;另一方面,从对比里思考超越自我的内力。他在组稿时,有相当的选择性。其实最欣赏的是思想性的文章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作品。这两点,在中国最为难得。中国文人不经历西洋文明的沐浴,难以再造自己的文明。 陈独秀在译介中形成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观在那时候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对这个差异的概括一直在影响着后来的人们。比如,“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重新出现文化热的时候,学人们似乎还没有超出陈氏的眼光。他的穿射力是内在的,学人们很长一段时间直面的是相似的问题。这也是他的启蒙的基本思路,而对文章与艺术变革的思考,也是缘于此点的吧。 不过陈独秀的表达,在那时候还显得急促,似乎没有完全消化人文主义的思想。他自己的文字内美,未必就比梁启超高明多少,只是见解高于对方罢了。主要的问题还是立言、立志,而非精神的盘诘与深省,自然没有哲学层面的高妙和艺术的深情致远。他反对旧文人的“载道”,自己未尝不是在走这条路。他神往自我的个性表达,但在那时肩负着使命,只能把目光盯在传道上,心性的攀援只好置之一边。启蒙者的悲哀往往是这样的: 他们要唤起民众,推倒旧的逻辑,可是自己必须进入这个逻辑后才能出离旧路。而自己不幸也在这个逻辑中。既是启蒙,又是个人主义,在那时候殊为不易。所以,是否真的消化了洋人的思想,还是个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过是借着这些,来讲自己的意思呢。 ………… 二〇〇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真正使新文学闪亮的,不是技巧类的东西,而是那时候的流行观念,即世界意识。世界意识的出现是颠覆儒学的利器,也是表达自我的前提,也不妨说是马克思主义登台中国的前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