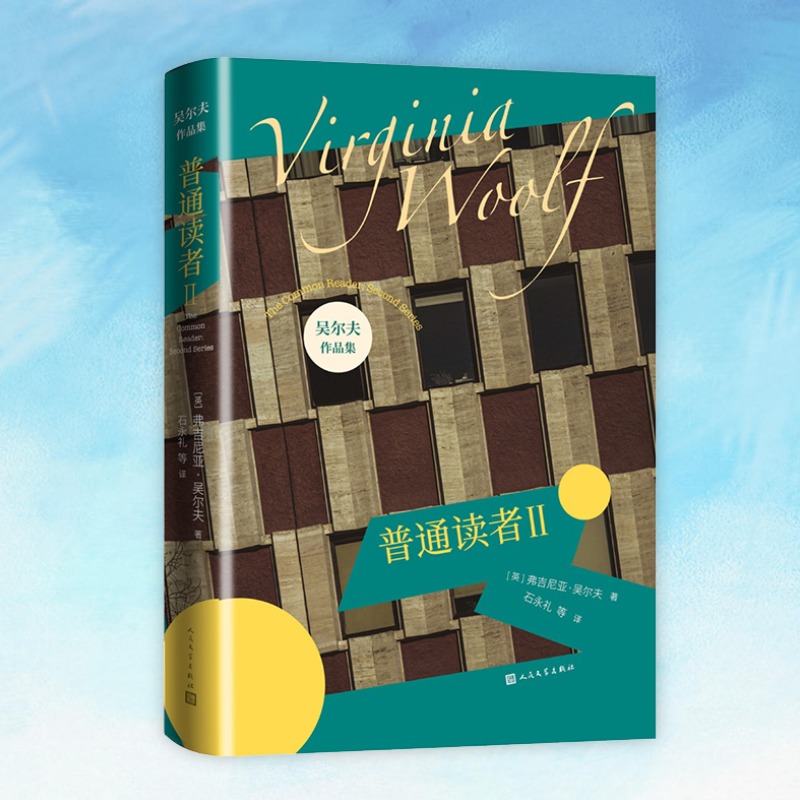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普通读者Ⅱ/吴尔夫作品集
ISBN: 9787020151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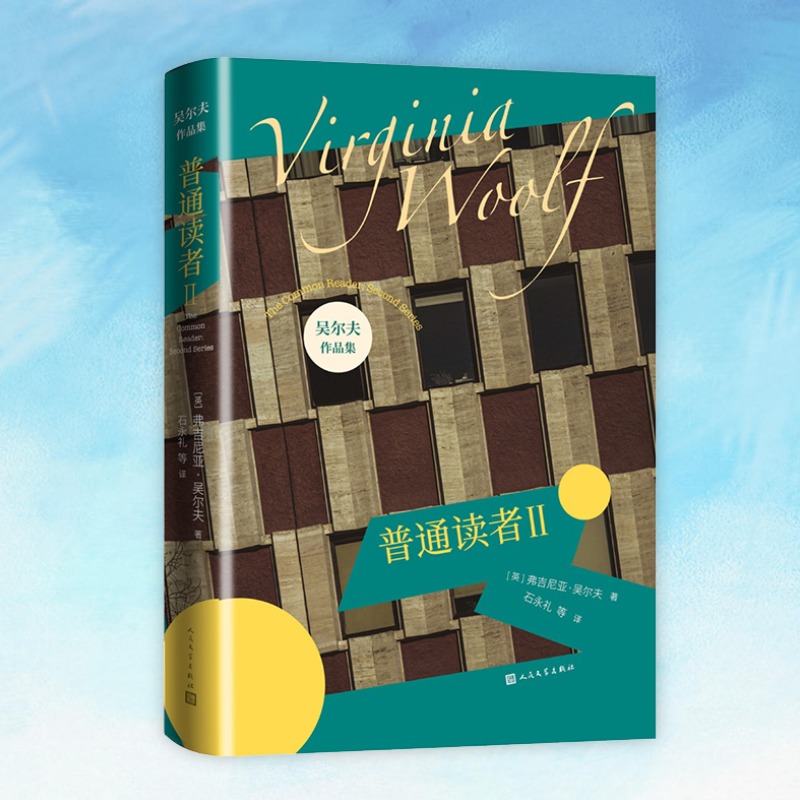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 英国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其作品摒弃传统的小说结构,运用“意识流”手法,注重心理描写,对现代文学影响深远。 译者简介: 石永礼(1927—2005) 重庆人。一九四九年毕业于重庆相辉学院外文系,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科科长、鲁迅著作编辑室编辑、外国文学编辑部编辑、副编审、编审。主要从事编辑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一九八四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译著有《威弗莱》《多情客游记》《双城记》等。 马爱新(1974— )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先后在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林出版社做翻译、编辑工作,曾参与翻译“哈利·波特”系列、《通灵侦探吉尔达》,单独翻译《男孩彭罗德的烦恼》《谎言城堡的秘密》《帝国瀑布》《普通读者Ⅰ》等。 刘春芳(1970— ) 教授,博士,现就职于上海海洋大学,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文学翻译。共出版专著译著十五部,主要译著包括《格列佛游记》《丧钟为谁而鸣》《奥威尔散文》《存在的瞬间》《大瑟尔》《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
前 言 本书是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第二本《普通读者》,让人不由想到她对“普通读者”为什么如此感兴趣。在第一本《普通读者》里,吴尔夫在代序里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这话讲得实在有见地,令人琢磨。一是要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二是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普通读者的判断来决定,这两点一下子把普通读者放到了很高的位置。这至少让人看出吴尔夫阅读文学作品的态度:出于本能,阅读再阅读,得到什么收获写出什么收获。 吴尔夫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这在许多传记里都是有定论的,但是在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却是没有什么规则可寻的。比如,她无数次提及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等英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家,却没有一篇专门文章是谈论他们及他们的作品的。这难免让我们有点遗憾;但是一篇接一篇读下去,我们却又会为吴尔夫为我们提供的文章感到由衷的喜欢。我们会由衷钦佩吴尔夫的读书感的切入点。她把英国文学反复掂量,全盘衡量,分出了各种级别,由此及彼地比较再比较,呈献给读者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有特色的文章。本书所收集的二十六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名家名著;文坛钩沉;书信日记和文人逸事。 想来意味深长,“名家名著”这类评论文章或曰读后评点式文章本应该是一个评论家或者读书人(哪怕是“普通读者”)的主要阅读板块,自然而然也是评说的主体,但在吴尔夫的这本集子里,点评一流“名家名著”的只有两篇:《〈鲁滨孙飘流记〉》和《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这当然不能说吴尔夫阅读的名家名著少。从她的小说和文章里我们知道,她对英国文学如数家珍,对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乔治·爱略特和特罗洛普这些大作家都有极为独特和准确的点评,但长篇大论和专著她却从来不作。这表明吴尔夫点评名家名著是很有选择的。她不止一次表示,但愿自己能写出如同笛福那样的叙述体的《鲁滨孙飘流记》。有了这样的情结,笛福的作品就会成为阅读重点,反复阅读。有了这样的背景,吴尔夫三言两语就说得出笛福的一生经历。关于《鲁滨孙飘流记》,虽写了四五千字评说,但是一个段落或几句话就能让我们大开眼界:“现实,事实,实质将支配以下整个故事。”“人必须贬为奋斗的自我保护的动物;上帝萎缩为行政长官,他那实在的,还有点硬的宝座,在仅仅稍高于天边的地方。”“如果你是笛福,的确,描写事实就够了;因事实是恰当的事实。凭借这种求实的天才,笛福取得的效果,除了伟大的小说大师,谁也达不到。”凡是文学评论如果都能挖掘到这样的深度,那是多好的光景? 因为大量阅读,吴尔夫能把英国文坛上被人忽略的作家从暗处拉到明处,让读者看到一些不凡的作家。《三百年后读多恩》《陌生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杰克·米顿》《乔治·吉辛》等多篇均属此类。他们大多数是没有被他们的同时代人所理解,时过境迁后便被人遗忘了。吴尔夫把他们拉出来评说,自然要写出理由,写出特点。例如,多恩这位英国文学史上难得的玄学派诗歌代表人物,吴尔夫不惜近两万字的篇幅来评述他。他的诗妙在哪里?“我渴望跟一个老情人的幽灵谈谈。”“像一束竖起的破红萝卜/你那害痛风的手的发肿的短指头。”“为探测海深,人们放下那么多绳索,/有理由认为,绳索的尽头处,/地球另一面,会有一片与此相对的地区。”看到吴尔夫能勾出这么精彩奥妙的诗句,她的评论自然会精当无比,读之有味。她用“你知道伦敦城有人走街串巷兜售煤油吗”开始写《乔治·吉辛》,让读者立刻感觉到吉辛是个表现自然的作家。因为急于揭露丑陋的现实,吉辛多了思考,少了艺术,成为“一个不完美的小说家,却堪称一个修养很高的人”。 不过,本书中最有看点的是她关于作家书信日记和文人逸事的文章。出版书信是现代事件,大概最数英国人做得好。说不清是不是因为英国人是世界上资本积累完成最早而最有休闲时间的人,要么是因为工业革命和科学发展最早而最早省下时间的人,反正他们写下的书信和日记是最多的国度之一。书信和日记是最具私密性的,因此也最接近真话和真实的东西。阅读这些材料确实有趣,有味,因为人是受好奇心驱使的动物。在这类材料上大做文章当然很有动力,却也很容易流于低俗。吴尔夫很智慧,把眼光定位于文学写作和文化事件。这样,她挖掘到的东西就特别和“普通读者”这个称谓接近了。文人通信也好,写日记也罢,评说文学作品和谈谈文学写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于是,我们在《多萝西·奥斯本的〈书信集〉》里看到:“写作书信没有什么不体面……我们在英国文学里第一次听到男人女人围炉聊天。”在《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家书》里,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在议会,或当牧师,或从事法律工作,不擅演说就不能崭露头角。”“上午用于学习,晚间参加良好的社交活动。要像最好的人那样穿着打扮,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举止,切勿显得古怪,或自高自大,或神不守舍。遵守比例的规律,每时每刻都要过得充分。”看着这些话,如果是在看小说,还会认为这是某个虚构人物在逢场作戏,而当我们看到这些话是出自书信的话,我们就和英国社会和社会的人拉得很近很近,会对这些话再三琢磨,把它们引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家书或信件的意义便显示出来了。日记又是另一种情形:“人的一生即使在其他方面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但日记往往是其中唯一秘密的事实。”信件的隐秘性与日记的隐秘性一下子就区别开了。日记成为某种身份特殊或性格特异的人宣泄自我平衡自我的一种工具。一个牧师会“天天坐下来记他星期一干了什么,星期二晚餐吃了什么,记了四十三年”。他看不惯人类的大吃大喝,就会写出来:“他们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这样大吃大嚼,直到他们之间一定吞下成群的牛羊,成群的家禽,一打左右的大小天鹅,成蒲式耳的苹果和梅子,同时,必然有一座座山,一座座金字塔,一座座宝塔似的馅饼和果冻被他们的餐匙捣碎压烂。”吴尔夫看到这些日记里这样的话,由不得总结说:没有哪部小说会像这样的作品塞满了食物。从日记与书信里看人,看得再真切不过了。 在这本集子里,吴尔夫评论书信和日记的文章占比很大,差不多是四分之三的篇幅。实际上,这些文章也是吴尔夫在写英国文坛上古往今来的文人逸事。不同职业的人交往方式必然不同,而文人因为有了文化而交往起来更有故事,加之他们能写会吟,一定要把他们的所想所说写出来,因此从书信和日记看文人交往,便是一个既便捷又真切的角度了。吴尔夫发现,一个作家或者学者,看他们的作品与看他们写的或别人写他的信和日记,差别真是太大了。他们在作品里可以板着面孔或者以某种身份描写人和事,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有时连日常生活都难以应付。《杰拉尔丁和简》堪称这类文章的代表。杰拉尔丁·朱斯伯里是一个三四流作家,但她的作品具有特色,她这个人就更有个性。她的这些性格是从简·韦尔什·卡莱尔书信里反映出来的,而卡莱尔就是鼎鼎有名的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吴尔夫像提葡萄,一提就是一串串。这里主要写杰拉尔丁和简的交往;文人气味相投时会互相来往,卡莱尔头脑一热,建议夫人把杰拉尔丁请到府上住一住。杰拉尔丁不客气,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一上午都写信。一下午都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大觉”。“她谄媚。她哄骗。她不真诚。她调情。她咒骂。”而卡莱尔夫人还“没法让她离开”,最终落得不欢而散。文人似乎无法相聚过久,但是她们却在帮助一家穷苦人家时又亲热起来。卡莱尔夫人简帮助米迪家的女儿们找事干,但她们“呆头呆脑”,总把差事丢了。无奈之下,简写信给杰拉尔丁,杰拉尔丁对这事热心得出人意料,竟超过了简,完全当成自己的事来做了。这让简很感动,很内疚,认识到宽容待人是多么重要,两个人于是成了终生朋友。吴尔夫写这样的文坛逸事绝不马虎,一定是有更深层的内容。她让我们通过文人的交往,看到了卡莱尔所谓的“英格兰现状”,十分难得。 另一些逸事是通过传记和宴会、聚会向读者披露的,重点是突出作家个性,反映当时文坛的风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写人写事,吴尔夫最擅长的仍是关于女性的。男性就事论事,而女性的文章就显得生动活泼。《“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一篇的篇名就是这位女诗人在一次宴会上自报身份的话:“一个身材娇小、身着黑色衣衫的女人猛然从座椅边站起来,快步走向客厅中央,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说完,又回到她的椅子。”吴尔夫总能从阅读中挑出这样凸现人物性格的故事,自己欣赏后又提供给读者。 总之,吴尔夫从阅读角度写评论,近乎自我欣赏,却给后人留下了如何写好文学评论的一篇篇范文。她的文章历经半个多世纪更为读者喜爱,专家学者看重,我看,在于她这种文章的亲和力。 苏福忠 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鲁滨孙飘流记》 探讨这部古典著作,有很多方法;但我们选择哪一种呢?我们用这句话开头如何:自从锡德尼未完成《阿卡迪亚》,在朱特芬去世以来,英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说已经选择了,或者说被迫选择了它的方向?中产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能读而且急切想读的书,不仅仅是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还有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平凡生活的细节的作品。散文依靠大批作家得到扩展,适应了这一需求;它使自己适于描述生活的真情实况,而诗则不情愿。这的确是探讨《鲁滨孙飘流记》的一种方法——通过小说的发展;但立即出现另一种方法——通过作者生平。我们在传记这一片片天堂般的牧场上消磨的时间,可能比通读原著的时间多得多。首先,笛福的出生日期就可疑——是一六六○年,还是一六六一年?再说,他拼写他的名字是用一个词,还是两个词?笛福,原姓福(Foe),不知什么原因加上法语词头笛(De)。他的祖先又是谁呢?据说,他做过袜商;但在十七世纪袜商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后来他成为小册子作者,获得威廉三世的信任;由于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受过上颈手枷示众的刑罚,又被关进新门监狱;1703年,笛福为之受颈手枷示众,并被关进监狱的小册子,是他那本著名的讽刺习作《对付非国教徒的最简便的办法》。他受雇于哈利,后来又受雇于戈多尔芬;他是第一个受雇用的新闻记者;他写了无数小册子和评论文章;还写了《摩尔·弗兰德斯》和《鲁滨孙飘流记》;他有妻子和六个孩子;身材瘦削,鹰钩鼻子,尖下巴,灰眼睛,嘴边有一颗大黑痣。即使对英国文学了解很少的人,也无须告诉他们,探索小说的发展,查看小说家们的下巴,可能花多少小时,又有多少人为此耗费了一生的精力。但是,当我们从理论转向传记,又从传记转向理论的时候,有时不由产生怀疑——即使我们知道笛福出生的确切时刻,他爱谁,为什么,即使我们记住英国小说从它在(姑且说)埃及孕育到它(也许)在巴拉圭的荒野里死亡这部兴盛衰亡史,我们能从《鲁滨孙飘流记》多得到一点快乐,或者阅读时多一分明智吗? 至于这部书本身,依然如故。我们在探讨作品的过程中,无论怎样扭动身子绕来绕去,悠悠闲闲随意赏玩,末了总有一场孤独的战斗在等待我们。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件事须先磋商,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在这次面谈的中途还要提醒一下,笛福卖过袜子,一头褐发,上过颈手枷示众这些事,会让人分心,让人烦恼。我们的头一项任务,而且往往很艰巨,是掌握这位小说家的透视法。在我们知道他是如何整顿他的世界之前,批评家硬要让我们接受的那个世界的装饰品,传记作家要我们注意的这位作家的冒险经历,都是我们不能利用的多余的东西。我们必须独自爬到这位小说家的肩上,通过他的眼睛观察,直到我们也了解他是按什么秩序安排那些庞大的普通的观察对象,这是小说家注定要观察的:个人,人们,他们后面的大自然;他们之上的那种力量,为了简便,我们不妨称之为上帝。于是,马上引起混乱,判断错误和困难。我们虽然觉得这些对象很简单,但是,由于小说家处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用的方式,可以把他们写得很怪异,当然认不出来了。即使朝夕相处,呼吸同样空气的人们,在比例感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这个人来说,人类是巨大的,树很渺小;对那个人来说,在背景的衬托下,树是巨大的,人类微不足道,看来的确如此。因此,作家们可以生活在同一时代,看见的东西却不一样大,且不管教科书如何说。这里以司各特为例,他的山在朦胧中显得很高大,因此他的人物都是按比例描绘的;简·奥斯丁挑出她茶杯上的玫瑰花与她的对话的机智相比;而皮科克却用一面奇异的扭曲的镜子看天下,在镜子里,茶杯也许是维苏威火山,或者维苏威火山也许是茶杯。然而司各特,简·奥斯丁和皮科克都生活在同一时代;瓦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简·奥斯丁(1775—1817);托马斯·洛夫·皮科克(1785—1866)。他们看见同样的世界;在教科书里,把他们列于文学史的同一时期论述。他们之所以不同,在于他们的透视法。那么,如果答应我们,只要各自牢牢抓住这一点,这场战斗就会以胜利结束;由于确信我们私下的谈话,我们就可以享受批评家和传记作者慷慨提供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乐趣了。 然而,还会出现不少困难。因为,我们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那是由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偏见形成的,因此,与我们自己的虚荣和爱好紧密相连。如果有人耍花招,搅乱了我们私人的和谐,而不感到受了伤害、侮辱,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无名的裘德》,或普鲁斯特的新书问世时,报上的抗议如潮水般涌来。如果生活真像哈代所描写的那样,明天切尔特南的吉布斯少校就会往他脑袋上开一枪;汉普斯特德的威格斯小姐一定要提出抗议,虽然普鲁斯特的艺术手法高妙,她感谢上帝,真实世界与那个反常的法国人扭曲的描写毫无共同之处。这位先生和这位女士都试图控制小说家的透视法,为了跟他们自己的透视法相似,从而得到声援。但是,伟大的作家——这位哈代,或这位普鲁斯特——不顾私人财产权,仍我行我素;他靠辛苦工作,使混乱状态秩序井然;他在那儿栽一棵树,在这儿安排一个人物;他按自己的意愿把他的神造成古代的或现代的形象。在杰作里——即幻象清楚,已建立秩序的书——他把自己的透视法那么猛烈地强加于我们,我们往往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我们的虚荣受到伤害,因为我们自己的秩序被推翻;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把支持我们的旧支柱强行拔掉;于是,我们感到厌烦——从一个崭新的思想能捞到什么愉快或娱乐呢?然而,有时一种罕有的持久的愉快即诞生于愤怒、恐惧和厌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