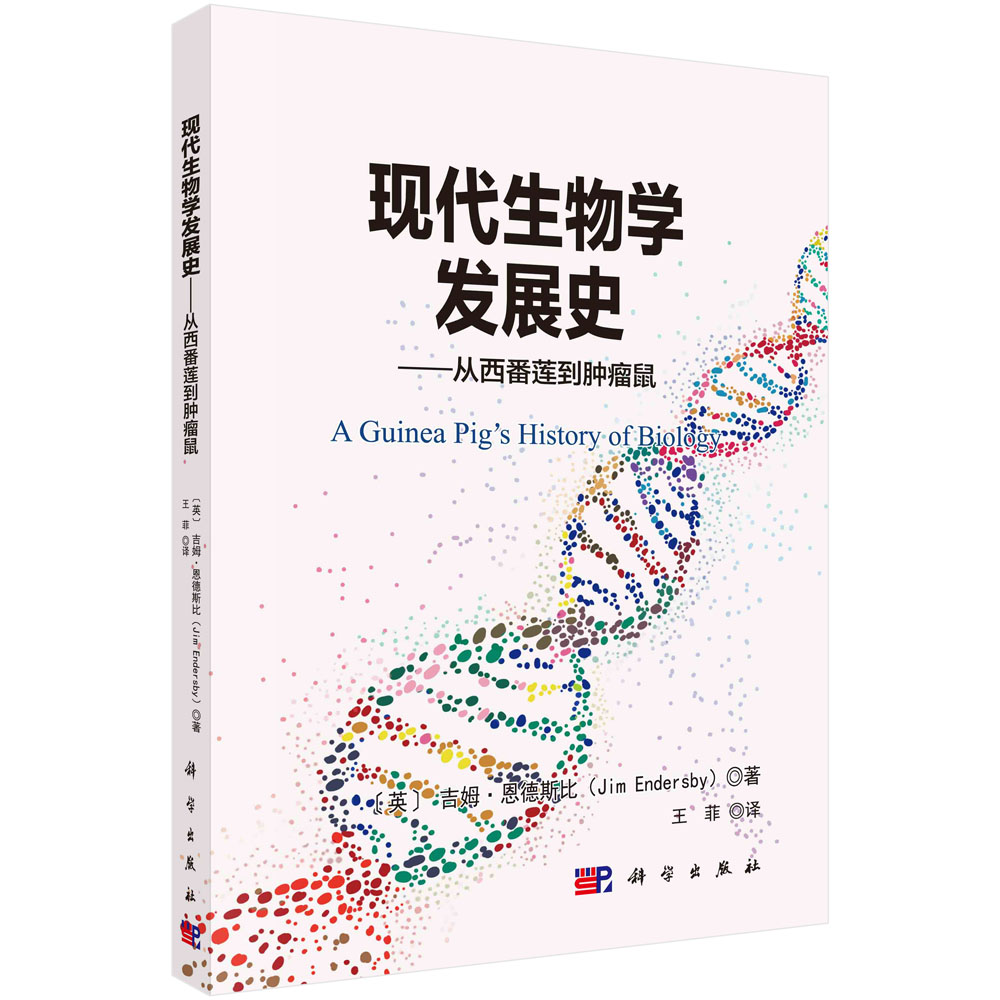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现代生物学发展史——从西番莲到肿瘤鼠
ISBN: 9787030685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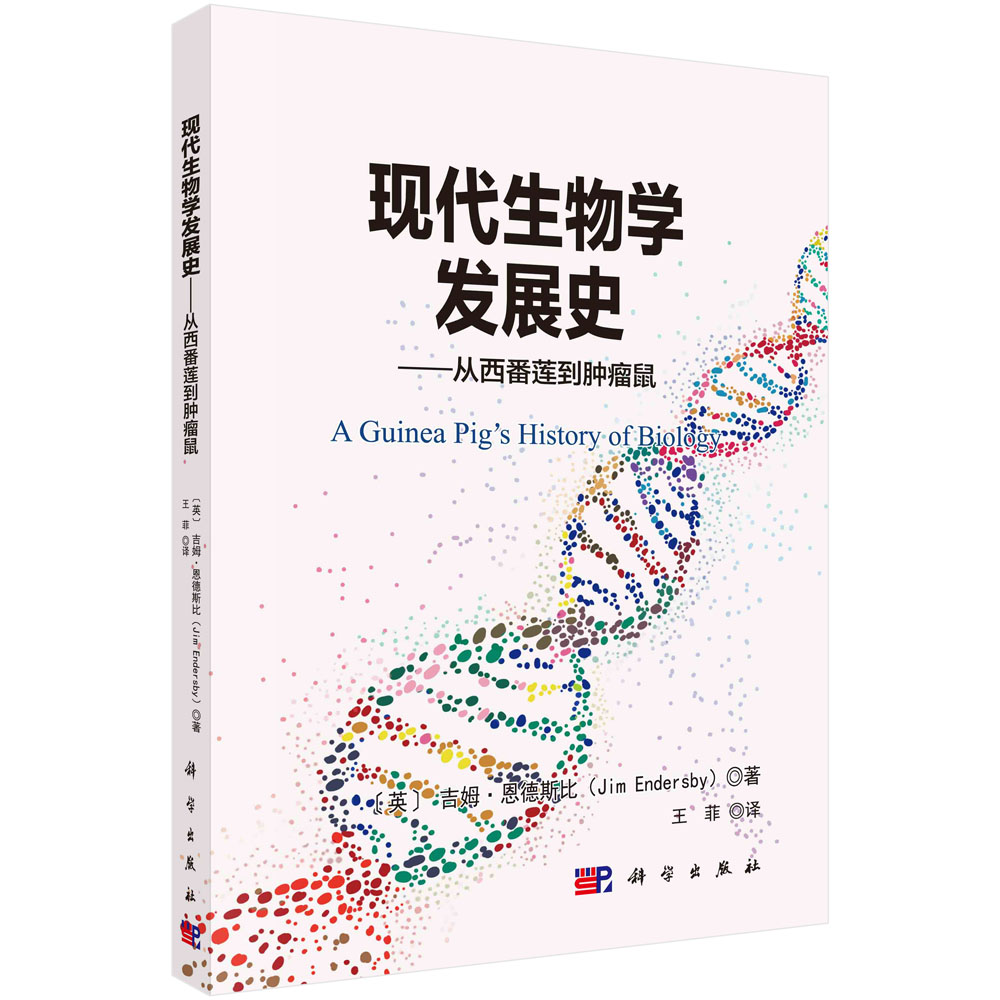
第一章 拟斑马和莫顿伯爵的母马
Chapter 1 Equus quagga and Lord Morton’s mare
乔治 道格拉斯(George Douglas),这位受人尊敬的十六世莫顿伯爵(16th Earl of Morton)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看着眼前的两匹小马驹,迷惑不解。事情是这样的,1820年他将一匹栗褐色母马卖给了朋友,戈尔 乌斯利爵士(Sir Gore Ouseley);乌斯利爵士将这匹母马和一匹纯黑的阿拉伯马交配,产下两匹小马驹。很显然,它们应该属于阿拉伯马,“可皮毛颜色和鬃毛却与拟斑马有相同的特征”。1
拟斑马,又称斑驴、半身斑马,是平原斑马的一个亚种,仅头肩部有条纹;与旅鸽和袋狼(别称塔斯马尼亚虎)一样,都属于已经灭绝的物种,并且灭绝的日期有明确记载——1883年8月12日,最后一匹拟斑马在阿姆斯特丹的阿蒂斯 马吉斯特拉(Artis Uagistra)动物园去世。可惜那个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这是最后一匹拟斑马,因此也无人哀悼。
既然双亲都是马,为什么乌斯利爵士的小马驹会长得像拟斑马?莫顿伯爵数年前饲养过一匹雄性拟斑马,本来他希望能驯服这匹拟斑马,但是与其他野生斑马一样,拟斑马基本上无法被驯服——它们脾气倔强,不仅喜欢乱咬,而且一旦咬上了就不松口。这也是为什么至今被斑马咬伤的动物饲养员人数比被狮子或老虎咬伤的人数要多的原因。南非当地人从来没有驾驭过它们,因此欧洲人发动对非洲的侵略时,没有受到任何非洲骑兵的阻挠。如果斑马像欧亚大陆的马一样容易被驾驭,那么非洲的历史恐怕就不一样了。
莫顿伯爵非常渴望能驯化拟斑马。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非洲的疾病。其中,昏睡病不仅感染欧洲人,还感染他们带来的马匹,但拟斑马和斑马基本上不患此病,因此一些欧洲人希望通过将拟斑马和家马杂交获得一个能更好地适应非洲当地环境的品种,莫顿伯爵也对此颇感兴趣。1788年,德国博物学家约翰 乔治 格梅林(Johann Georg Gmelin)发现,“拟斑马相较于斑马更壮实,更温和,被驯化后可以用来拉车”。而一位去过南非的旅行者则宣称,他在寄宿人家看到“一匹被驯服的拟斑马,被主人用来做改良马匹的实验”。可是在莫顿伯爵开展杂交实验的几年后,出现了关于拟斑马习性和可驯化性与先前相矛盾的报道: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宣称,他看到的拟斑马“并不温和,甚至比斑马更野性十足”。而另一位评论家则建议,尽管这样,仍然“有可能驯化它们并为人类所用”。2
莫顿伯爵买下一匹雄性拟斑马后,将其与一匹栗褐色母马交配。据他的描述,其杂交结果是,“一匹在外形和毛色上都具有明显双亲特征的小母马”。这匹小母马可能保留了其父亲的条纹特征或者习性——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伯爵没有再重复杂交实验。可是,正是这匹与拟斑马交配的母马,被伯爵出售给了乌斯利爵士,并且这匹母马产下具有拟斑马特征的后代——即使这是它与普通马匹交配后生产的。小马驹的腿部有条纹,鬃毛又短又硬,像斑马那样直立着,而不像普通马匹那样垂落下来。马匹之间交配产生的后代偶然也会出现条纹,但在阿拉伯马的后代中是很少见的,而且连莫顿伯爵和乌斯利爵士都从来没有见过哪匹马有这样的鬃毛。与拟斑马的交配似乎永远地改变了这匹母马,它被打上了无法磨灭的拟斑马的印迹,以至于影响了它后来产下的小马驹。
这件事对莫顿伯爵冲击很大,他将此事转告给他的朋友——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威廉 海德 沃拉斯顿(William Hyde Wollaston),并引起了他的注意。1821年,莫顿伯爵的来信发表在《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题为“对自然史中一个奇特现象的简报”(A Communication of a Singular Fact in Natural History)。雄性个体对雌性个体的后续子代具有影响这一观点并不新鲜,但一般都被当作民间神话。可是,现在这个观点被享有声望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提出,拟斑马效应虽然非常奇特,但被认定为一个科学事实。
在莫顿伯爵的来信发表大约五十年后,查尔斯 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仍然认为,“毫无疑问,是拟斑马影响了黑色阿拉伯马后代的特征”。3他把这个例子视为在设计一套生物遗传理论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和其他被莫顿伯爵的母马震惊到的人一样,达尔文相信这匹雄性拟斑马给与之交配的母马留下了永久的印迹;通过某些尚未知晓的方法,拟斑马的特征印迹留在了母马身体里,这种印迹是心理上的——母马在它头脑里保留了拟斑马特征,还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存在于雄性精液或血液中的粒子或液体被输送并保留在母马体内?雄性拟斑马会不会此后对雌性拟斑马失去兴趣转而去追求母马呢?
您现在阅读的正是一本关于如何揭开此类秘密的书。在达尔文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大多数生物和人类一样,只有雄性和雌性交配后才能产生后代。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究和猜想,仍然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或者说得清楚雌雄两性对其后代的影响。既然有些生物无须两性交配便能繁衍后代,那么有性生殖的目的是什么?遗传又是什么?为什么大多数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长得像?动物或者植物的特征是如何一代代传递和保留的?既然生物只能产生同种后代,那么新的物种从哪里来?既然物种一代代基本保持不变,那么为什么有些时候它们又会变异,它们又是如何变异的?
莫顿伯爵对小马驹为什么出现条纹的解释现在看起来很荒谬,后来许多人也都尝试去解决这个困惑。为了理解为什么他的观点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了解,在莫顿伯爵开展杂交实验之前,人们对生殖的思考。
莱斯博斯的码头
莱斯博斯岛的渔夫已经非常熟悉这位哲学家了。每天早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要走到码头去检查当晚的收获,搜寻不常见的或者奇怪的鱼,他和他的学生们会把这些鱼拿走做研究。大约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开始了对生命的系统研究:他观测海洋生物的生长和发育,所用的工具不过是他的一双眼睛而已。
对生物进行观测,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看——现在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难道还有别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吗?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Plato)来说,“赶海”这一行为无疑是异数。柏拉图教导学生,只有头脑才能指引人们认识世界,只有通过逻辑思考人们才能理解理念,即隐藏在令人迷惑的外表之下的抽象的真理。例如,学过几何学的每一位学生都知道,无论我们如何小心地画图,就算是画一个三角形,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线条具有可测量的宽度,转角不可能形成完美的三角。我们画出的每一个三角形不过是对三角形这一理念的描绘,其与理想三角形之间的差距,类似一个孩童为其父亲绘制的写生图与父亲真实长相之间的差距。柏拉图将他的这种观点扩展到每一件事物身上:在街上溜达的狗不过是对狗这一纯粹理念的不完美反映,甚至天空的蓝色不过是对蓝色这一纯粹理念的一种投射。对某只狗进行观察将永远不会揭示狗的理念,而将蓝色天空与蓝色眼睛相比也不会揭示蓝色的理念。只有推理才能洞悉理念的真谛。
所以,如果柏拉图看到他学生的行径,将会非常恐惧:一个中年人湿着脚划船并倾听渔夫们的粗言俗语——这一形象已经说不上体面了,而且他还要试图通过对似乎无穷无尽的各种鱼进行分类来揭示鱼的概念。但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尝试去做的。更糟糕的是,亚里士多德不仅仅在寻求鱼的概念,他还希望通过研究和比较不同的鱼,发现它们的本质属性:它们之所以成为鱼的共性是什么,而又是什么让我们能将每种鱼区分开?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对差异的分析是理解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的关键,而这些原因又是理解事物的关键。仅仅知道鱼能在水下呼吸而其他动物不能是不够的,亚里士多德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的哲学体系确立了四类原因:第一,形式上的原因——鉴定物体的结构;第二,质料上的原因——这一结构由何种材料构成;第三,动力上的原因——是什么力量将这一特定材料塑造成这一特定结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终极原因——形成这一结构的目的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将他的“四因说”用到各个方面,从政治到伦理,从天文学到宇宙学。他对生命体格外感兴趣,为了研究它们,他对生命体的繁殖尤其是它们的卵做了特别的关注。他在著作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他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低等的生物,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大自然的痴迷。他写道:“对于智者,自然的鬼斧神工为那些能理解事物原因的人提供了无穷快乐”。4海洋生物对他的研究非常有用:它们在海里产卵,相比卵在体内发育的哺乳动物,海洋生物的卵的发育更容易被观察;而且因为是在海里产的卵,也就意味着这些卵无需坚硬外壳的保护,所以,亚里士多德可以观察海洋生物在没有外壳的卵里的发育过程。并且亚里士多德还解剖了渔夫们带给他的生物,并做了细致的观察[在《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中,他记录了500多种生物,其中120种是鱼类]。他发现了许多特别的生物,其中一些生物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仍然没有得到确认。他也喜欢倾听老渔夫们讲述的传说,他记录并保存这些难以置信的故事但并不做深入的调研。
仔细观察鱼卵从胚胎发育到自由游动的幼体帮助亚里士多德将“四因说”运用到生命体上。他主张生殖是证实柏拉图观点错误的最根本的证据。没有物质,哪有理念:如果没有承载“蓝色”或“狗”这一属性的物质——真实的蓝天或狗,就没有“蓝色”或“狗”这一理念。两条狗交配能生出新的狗这一事实,说明自然具有赋形于物的能力。亚里士多德没有将狗的大小、身形和行为归结于难以触摸、抽象的狗的理想形式,而是归因于生殖:正是生殖使生物的形式得以保留下来,并一代一代自我更替。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随者们被他所研究的生物迷住了。他似乎出于好奇去观察它们,但同时也渴望从它们身上了解自己和人类。他这样记录道:“人体内部的样子几乎无人知晓,因此我们必须参考并研究那些与人内部组成具有相似性的其他动物的结构”。5研究动植物的一个原因是把人类生殖和人口质量弄清楚——包括我们如何将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一代代传承下去。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不是在古希腊世界传播的唯一思想。从莱斯博斯岛往南航行一天便能到达古希腊城邦米利都(现属土耳其)。这是个喧嚣的商埠,来自东地中海各地的人们会到这里从事香料、染料、木材和瓷器的贸易。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各自的语言和习俗,以及信奉的神灵和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传说。这种世界性的“交汇”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比亚里士多德还要早几个世纪的时代,这座城市就已经诞生了希腊哲学。面对这么多不同的关于世界是如何及为什么这样运行的解释,米利都人泰勒斯(Thales)成为第一个质疑“遵循传统而非独立思考是认识宇宙本原的最可靠方法”这一观点的希腊人。
泰勒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提出了许多对世界本原的不同解释:其中一个追随者申明,有生命的物体是由照射到水蒸气上的太阳热量所形成的,其他所有物体则都是由单一的物质所形成——否则无法解释一个物体如何能转变成另一个物体(例如,冰变成水再变成水蒸气)。一些追随者提出水正是这种基本的物质,而另一些追随者则认为是空气。后来这种由单一物质构成万物的观点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彼此冲突的思想被统一起来形成了“四元素说”,即万物是由土、气、火和水这四种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有各自不同的属性,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世间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