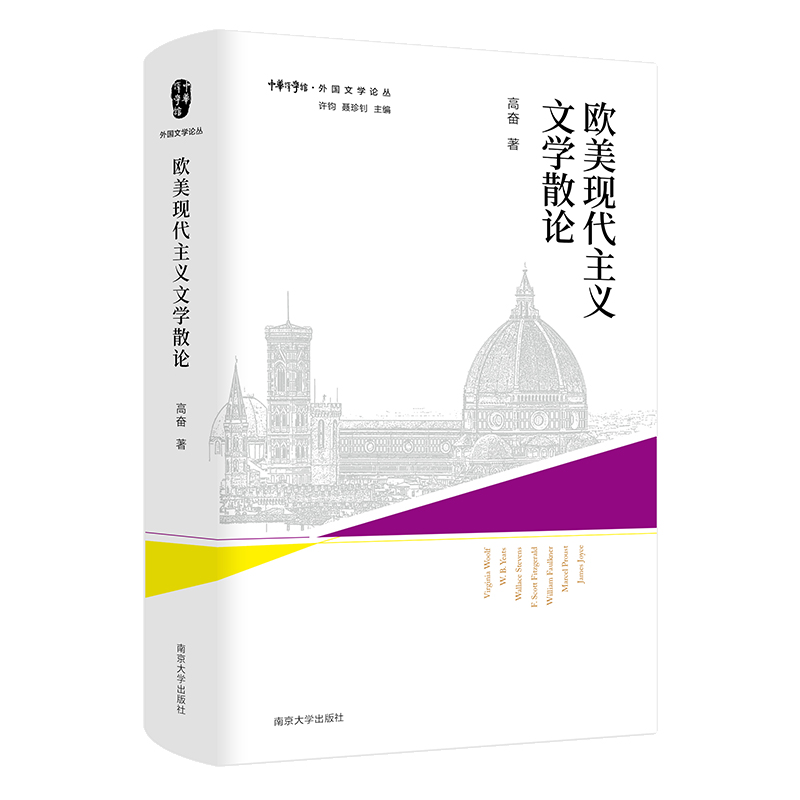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108.00
折扣价: 67.00
折扣购买: 外国文学论丛: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散论
ISBN: 9787305249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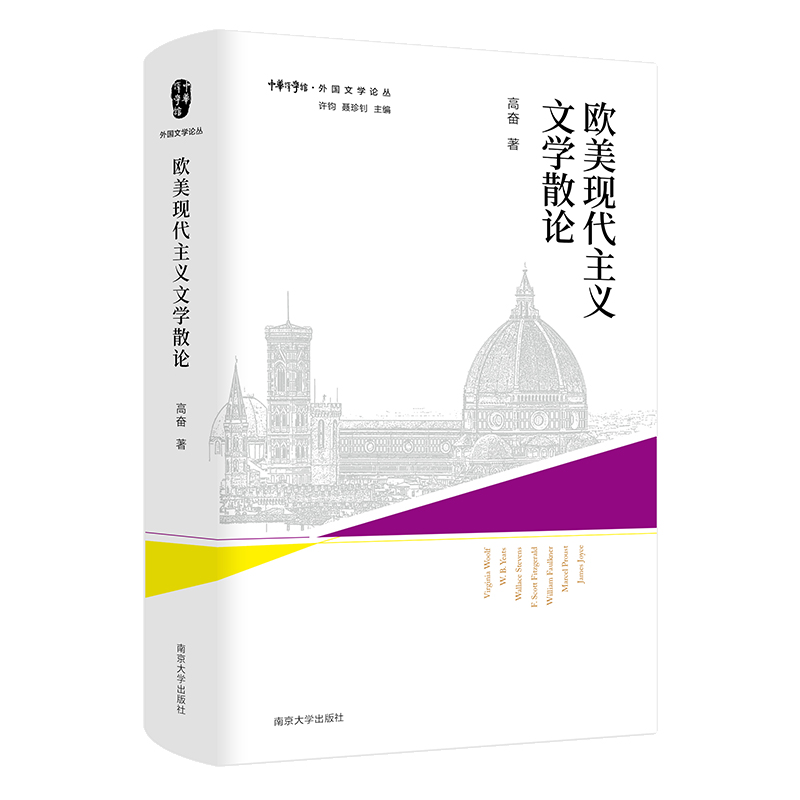
高奋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外文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作协会员。任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2006—2007)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1995—1996)。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对英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华莱士·史蒂文斯、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做深入研究。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主要包括:《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2021)、《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2016)、《小说、诗歌与戏剧探寻之旅:英语文学导读》(2013)、《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2012)、《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源与流》(2000)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2009)、“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2014)。 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9)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中国眼睛”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中国文化的表现与大多数欧美作家一样,主要有两种形式。首先,“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扇子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中国人散落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抒发想象中的中国意象和中国形象”;其次,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艺术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体现对中国思想的领悟,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隐在或显在地表现出基于中西方美学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出现在伍尔夫作品中的直观中国意象包括中国宝塔、千层盒、茶具、瓷器、瓦罐、旗袍、灯笼等,它们散落在她的小说和随笔之中,喻示着中国文化物品已成为英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伍尔夫的深层次理解基于她对有关东方文化的文学作品和视觉艺术的领悟和洞见,在创作中表现为全新的创作心境、人物性情和审美视野,其显著标志是她作品中三个人物的“中国眼睛”。他们分别是:随笔《轻率》(Indiscretions, 1924)中的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小说《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中的伊丽莎白·达洛维和小说《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中的丽莉·布里斯科。这三位典型欧洲人的脸上突兀地长出“中国眼睛”,这与其说是随意之笔,不如说是独具匠心。 英美学者已经关注到伍尔夫的“中国眼睛”,并尝试阐释其内涵。帕特丽莎·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曾撰写《伍尔夫与东方》(“Virginia Woolf and the East”, 1995)一文,指出伍尔夫赋予其人物以“中国眼睛”,旨在以“东方”元素突显人物的“新”意。此后劳伦斯在专著《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2003)中,通过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透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诗社之间的对话和交往,回顾和总结英国人认识、接受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历史、途径及表现形式。她指出丽莉的“中国眼睛”,“不仅喻示了英国艺术家对中国审美观的包容,而且暗示了欧洲现代主义者乃至当代学者对自己的文化和审美范畴或其普适性的质疑”,代表着英国现代主义的“新感知模式”。不过她的研究聚焦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重在提炼英国现代主义的普遍理念,并未深入探讨伍尔夫的“中国眼睛”的渊源和意蕴。另外厄米拉·塞沙吉瑞(Urmila Seshagiri)比较笼统地指出,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批判了20世纪初期英帝国独断式的叙述方式,用丽莉·布里斯科的眼睛所象征的东方视角担当战后贫瘠世界的意义仲裁者”。 那么,伍尔夫的“中国眼睛”缘何而来?其深层意蕴是什么?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 东方文化与“中国眼睛” 伍尔夫笔下的三双“中国眼睛”集中出现在她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即随笔《轻率》(1924)、《达洛维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这与她对中国文艺的感悟过程及中国风在英国的流行程度相关。像大多数欧美人一样,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最初是从东方文化中提炼的,不过当她最终在作品中启用“中国眼睛”一词时,它背后的中国诗学意蕴是明晰的。 她感知和了解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她的亲朋好友的旅游见闻、译介,以及她本人与中国朋友的通信交流。1905年她的闺密瓦厄莱特·迪金森去日本旅游,其间曾给她写信描述日本的异国风情,伍尔夫随后撰写随笔《友谊长廊》(Friendships Gallery,1907),以幽默奇幻的笔触虚构了迪金森在日本的游览经历。1910年和1913年,她的朋友、剑桥大学讲师高·洛·狄更生两次访问中国,他在出访中国之前已出版《中国人约翰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1903),讽刺英国人在中国的暴行。1912年,弗吉尼亚与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后者此前曾在锡兰工作6年,回国后撰写并出版了《东方的故事》(Stories of the East,1921)。1918年至1939年,她的朋友、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继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6)的七卷本《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和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之后,翻译和撰写了十余部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文史哲著作,包括《170首中国诗歌》(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更多中国诗歌》(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1919)、《中国绘画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 1923)等,韦利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 1925—1933)、《道德经研究及其重要性》(The Way of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 1934)、《孔子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38)、《中国古代三种思维》(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1939)等。伍尔夫曾在小说《奥兰多》前言中感谢韦利的“中国知识”对她的重要性。1920年伍尔夫的朋友、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回国后出版《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一书,论述他对中国文明的领悟和建议。1925年她的密友、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选编出版了《中国艺术:绘画、瓷器、纺织品、青铜器、雕塑、玉器导论》(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to Painting, Sculpture,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s & Minor Arts,1925),并撰写序言《论中国艺术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rt”),详述他对中国视觉艺术的理解。1928年她的另一位密友、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出版一部关于中国皇帝和皇太后慈禧的讽刺传奇剧《天子》(Son of Heaven,1928)。1935—1937年,伍尔夫的外甥朱利安·贝尔到国立武汉大学教书,不断写信给她,介绍中国文化和他喜爱的中国画家凌叔华。1938年,朱利安在西班牙战死后,伍尔夫与凌叔华直接通信,探讨文学、文化与生活,并在信中鼓励、指导和修改凌叔华的小说《古韵》。上述人员都是伍尔夫所在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成员,该文化圈坚持了30余年的定期活动,他们对中、日等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主动接纳对伍尔夫的影响深远。他们有关中国文化的作品基本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这与伍尔夫20年代作品中出现三双中国眼睛相应和。 伍尔夫对中国和东方文化的深层领悟源于她对相关文艺作品的阅读。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一方面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翻译的中国典籍和文艺作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出版;另一方面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于1916年成立,阅读英译中国作品或学习汉语变得便利。中国艺术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社会受到热捧,一位出版商曾在前言中概括这一态势:“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和领悟正在日益增强,近二三十年中,有关这一专题的著作大量出版便是明证。”他在该书中列出了20世纪头30年有关中国艺术的出版书目,其中以“中国艺术”为题目的专题论著多达40余本。伍尔夫的藏书中有阿瑟·韦利的《170首中国诗歌》、翟理斯的《佛国记》(The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1923)和《动荡的中国》(Chaos in China,1924)、奇蒂的《中国见闻》(Things Seen in China,1922)等书籍,同时伍尔夫夫妇共同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曾出版2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今日中国》(The China of Today, 1927)和《中国壁橱及其他诗歌》(The China Cupboard and Other Poems,1929)。伍尔夫究竟阅读过多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已很难考证,从她撰写的随笔看,她曾阅读一些英美作家撰写的东方小说,也阅读过中、日原著的英译本。她不仅积极领悟人与自然共感共通的东方思维模式,而且青睐东方人温和宁静的性情。 她对东方审美的领悟大致聚焦在人与自然共感共通的思维模式中。 她体验了以“心”感“物”的直觉感知。在随笔《东方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East”,1907)中,她评论英国作家夏洛特·罗利梅(Charlotte Lorrimer)的小说,赞同小说家的观点,“我们已经遗忘了东方人当前依然拥有的珍贵感知,虽然我们能够回忆并默默地渴望它。我们失去了‘享受简单的事物——享受中午时分树下的荫凉和夏日夜晚昆虫的鸣叫’的能力”。她认为“这是欧洲文化走近神秘的中国和日本时常有的精神状态;它赋予语词某种感伤;他们能欣赏,却不能理解”。虽然该小说仅描述了一位西方妇女目睹日本母亲平静地接受丧子之痛的困惑和费解,伍尔夫对它的评价却很高,认为“这些在别处看来极其细微的差异正是打开东方神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