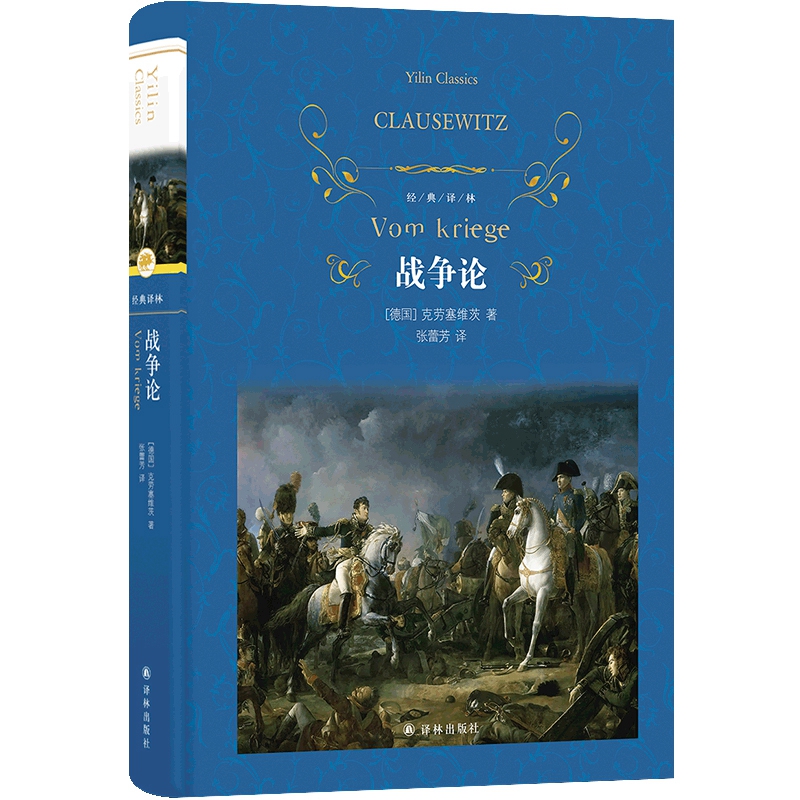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6.10
折扣购买: 经典译林:战争论
ISBN: 9787575302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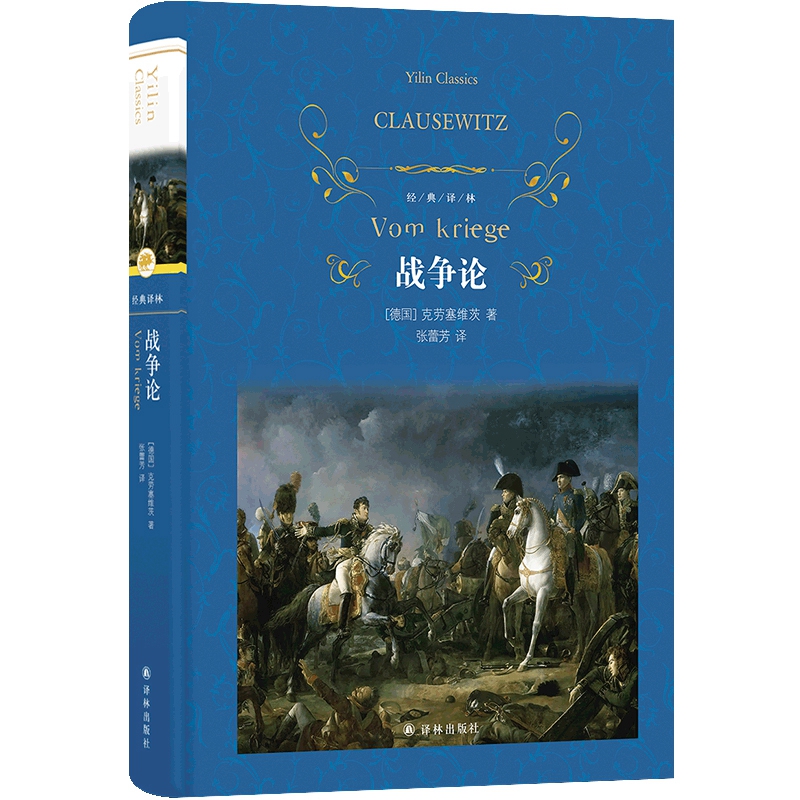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1792年参加普鲁士军队,1795年晋升为军官,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他主张联合俄国抗击拿破仑,1812年来到俄国军中参加抵抗拿破仑的战争,1818年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战争论》是他用辩证法系统总结战争经验的思想成果。
第一章 什么是战争 1. 前 言 我打算先考虑战争的各个基本要素,然后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或部件,最后是它内部结构的整体。换句话说,我将从简单谈到复杂。但战争相较于其他话题更必须先看整体,因为战争的整体和部分总是比别处更需要统一考虑。 2. 定 义 我不会用一个学究式的、文绉绉的战争定义来做开场白,而是直接抓住战争的核心要义,也就是对决。战争就是大规模的对决。无数的对决组成战争,但只要想象一下一对摔跤手,那就是战争的整体概念。每个摔跤手都试着通过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标就是掀翻对手,使其无法做进一步的抵抗。 因此,战争就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武力行为。 武力要用来反击对手的武力,就必须用艺术和科学的发明来装备自己。一些附着在武力上的限制,如众所周知的国际惯例,是自愿承担、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不会削弱武力。因为道德力量除了在国家 和法律中得以体现之外没有存在余地,所以武力,即物质力量就是战争的手段,逼敌人服从我方意志就是战争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让敌人失去力量,在理论上,这就是战争的真正目标。目标取代目的,把目的当作实际上不属于战争的一部分而摒弃它。 3. 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 好心人当然认为可能有更奇妙的办法,不流太多的血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击败敌人,并且还想象这是战争艺术的真正目的。听上去挺不错的,但这是必须指出的谬误;战争是高度危险的事,来自好心肠的错误是最糟糕的。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与同时运用智力并不相悖。如果一方毫无愧疚地使用武力,在流血牺牲前毫不退缩,而另一方却一味退让,那么前者定会占上风,他会迫使对方也采取流血行动,然后每一方都会把对方逼至极端,唯一能够限制行动的因素只有战争固 有的平衡力。 问题就必须这样来看待,纯粹为战争的残暴而愁苦,因而对战争的本来面目装作看不见,这是毫无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野蛮人之间的战争残酷,破坏性也没那么强,原因在于国家的社会条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引起战争的因素,也是限制和缓和战争的因素。这些影响力却不是战争的一部分,在战争爆发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把缓和原则纳入战争理论总是会导致逻辑上的悖论。 两种不同的动机让人互斗:敌对情绪和敌对意图。我们的定义就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因为后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要素。没有敌对意图,就连最野蛮的、几乎是本能的敌对情绪都难以想象会存在;但敌对意图并不经常伴有敌对情绪—至少不伴随有占主导地位的敌对情绪。野蛮人被情感所支配,文明人被智力所操控。然而,区别不在于野蛮和文明的本质特征,而在于随之产生的情况、制度习俗等等。这种区别并不是在每个军事事例中发挥作用,但在大部分事例中见效。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之间也可能激起狂热的仇恨。 由此可见,想象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仅产生于政府的理性行为,设想战争会逐步摆脱情绪的支配,最终人们将无须运用战斗力量的打击力—只要进行数字化的力量对比就行了,这只是用代数演算的战争,显然是谬误。 理论家已开始朝这方面进行思考,直到近期的战争给了他们一个教训。如果战争是武力行为,必然会掺杂情感成分。战争也许不会源于情感,但情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战争,其程度不是取决于文明水平,而是取决于双方利益冲突有多重要,冲突会持续多久。 如果说文明人不再屠杀俘虏或蹂躏城市和村庄,那是因为在他们的战争方式上智慧起了很大作用,教会他们更有效地使用武力而不是赤裸裸地宣泄本能。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足以说明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没有改变或偏离消灭敌人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战争的核心。 这个中心主题必须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武力行动,对使用武力没有逻辑上的限制。因此,每一方都是迫使对方拿起武器反抗,这种互动一旦启动,在理论上肯定就会走向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互动,第一个“极端”。 4. 目标是解除敌人武器 我已经说过战争的目标就是解除敌人的武器,现在要说的是,至少在理论上这是势在必行的。如果要让敌人受到胁迫,你就应该把他放在更恶劣的环境里,比你要求他做出的牺牲还要糟糕。局势的艰难当然不能是转瞬即逝的—至少在表面上不应如此。不然的话,敌人就不会束手就擒,而是等待局面扭转。持续敌对产生的变化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是那种给敌人造成更加不利局面的变化。交战国所遇到的最差的条件就是毫无防御能力。因此,如果你要依靠战争逼敌人就范,你必须打得他无还手之力或至少把他置于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中。这就是说,征服敌人或解除敌人的武器—随你怎么称呼,必须是战争的目标。 然而,战争不是有生命的力量针对无生命物质的行为(毫无抵抗就不是战争了),而总是两个有生命的力量之间的对抗。上面阐述的战争的最终目标适用于交战双方。这又是一种互动。只要我没扳倒对手,我就有理由害怕他会扳倒我。于是,我不再掌控一切:他可以像我对待他一样对我颐指气使。这是第二种互动,导致第二个“极端”产生。 5. 力量的极限发挥 想征服敌人,你的努力必须与他的抵抗力相匹敌,后者可以说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的产物,那就是他可以使用的全部手段和他的意志力。能使用的手段多少是一个数字问题(虽然不是只能用数字表示),是可以衡量的;但意志力就不那么容易确定,只能依照推动意志力的动机来粗略地判断。假定你用这种方式已经相对准确地估计到敌人的抵抗力,你对自己的努力也可做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你或者加大努力,使其超过敌人的抵抗力;或者假如那非你能力所及,你就尽力而为。但敌人也会做同样的事,竞赛由此产生,在纯理论范畴内,这必然又把你们双方推向极端。这是第三种互动和第三个“极端”。 6. 战争实践中的和缓 因此在抽象思维领域里,好刨根问底的头脑不走极端是不会罢休的。目前就有一个极端要处理:自由运作、无拘无束的武力冲突。你可以从战争的纯粹概念去为所瞄准的目标、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推论出终极条件,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持续不断的互动会使你陷入极端,这种极端只是由一连串几乎是隐形的、细微的逻辑差别演绎而来的幻想。如果纯粹从终极条件来思考,我们大笔一挥就能避开所有困难,用不可动摇的逻辑宣称,既然极端始终应该是目标,我们就必须始终 把努力发挥到极致。这种宣告只存在于抽象领域,分毫影响不到真实世界。 即使假定这种发挥到极致的努力是一种可计算的绝对数量概念,人的心理也不可能同意被这种逻辑幻想所操控。这种操控常常会导致力量的浪费,与其他治国经纬原则相左。这需要把意志力发挥到与既定目标不相称的地步,但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细微的逻辑差异不会激励人的意志。 但从抽象世界来到现实世界,情形就完全不同。在抽象世界里,乐观主义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迫使我们设想双方不仅寻求完美的冲突,而且可以达到至臻完美的境界。在实战中会是这样的吗?那需要有一些前提,即:(1) 战争是一种完全孤立的行为,是突然爆发的,而且与战前政治世界里发生的事情毫无瓜葛;(2) 战争只包括一次决战或一系列同时进行的决战;(3) 决战本身完美无缺,不受任何关于战后政局的预先评估影响。 7. 战争绝不是孤立行为 至于这些条件中的第一条,应该牢记的是敌对双方都不是抽象的人,甚至在抵抗力中的那个因素,也就是意志力,也不是抽象的。意志并不完全是未知数,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基础上预测明天意志的状况。 战争不可能毫无征兆地爆发,也不可能瞬间蔓延。各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根据对方的实际所作所为做出判断,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怎样、应该做什么来判断。然而,人和人类事物总是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这些缺点对双方都有影响,因此就形成了和缓机制。 8. 战争不是一次短暂的打击 第二个条件可做以下评论: 如果战争由一次决战或一系列同时进行的决战组成,准备工作应是完备无缺,因为任何疏漏都无法补救。现实世界能够为准备工作提供的唯一标准就是敌人所采取的措施—只要我们知道这些措施。其余的部分又一次不得不由抽象世界来测算。但如果决战由依次接替的军事行动组成,那么任何一次行动连贯起来看,都能成为下一次行动的衡量标准。由此看来,抽象世界又一次被现实世界所取代,走极端的倾向也因此而得到缓和。 当然,如果所有手段被同时使用或能够同时使用,所有战争都自动形成一次决战或一组同时进行的决战—因为任何不利的决战一定会减少可用的手段,如果把手段全部投入到第一次行动中,就不会有 第二次行动。任何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只能是第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只是第一次行动的扩展。 然而,正如上面所述,战争准备一旦开始,现实世界就会取代抽象的思想领域,物质性的筹划就会取代极端的假设。如不出意外,双方的互动不再会倾力而为,因此,他们的全部资源也不会同时动员起来。 再者,这些资源的性质和使用特点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全部部署下来。这些资源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国家(包括其特征、人口)和同盟国。 国家(及其特征和人口)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军队的来源,国家本身就是推动战争的因素中不可分割的要件—虽然指的只是战区那部分,或对战争产生巨大影响的那部分。 毫无疑问,完全有可能同时使用所有的机动部队,但说到要塞、河流、山脉、居民等等,是不可能同时动用的。总之,整个国家是不可能说投入就投入的,除非国家太小,战争的军事行动一下子席卷了整个国家。另外,盟国不会纯粹按照交战国的愿望进行合作,国际关系一向如此,这种合作常常在后期才出现,或只在平衡被打破需要加以纠正时才会有所增进。 在多数情况下,不能立即使用的抵抗手段所占比例会比最初想象的要高。甚至即使在最初决战中耗费了大量的力量,平衡遭到巨大的破坏,均势仍能重新恢复。在以后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详谈这个问题。战争本身的性质阻碍了所有军队的同时集结,在现阶段指出这点就已足够。当然,这个事实本身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决战中倾力而为的理由,因为失败总是糟糕的事,没人愿意刻意去冒这个风险。即使第一次冲突不是唯一的,对后面的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与第一次冲突的 规模也是成正比的。但是,孤注一掷总是有悖于人性,因此,通常会找借口说后面还会有决战,从而避免在第一次决战中全力而为。于是,在第一次决战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军队集结情况往往就会不尽充分,一方的疏漏就会成为另一方付出较少努力的真实而客观的借口,走向极端又一次遭到这种互动关系的阻止。 9. 战争中没有最终结局 最后要说的是,即使是战争的最后结果也不总被看作最终结局。战败国常常把结果只看作暂时的不幸,在以后的时日仍能找到政治补救办法。显然,这也能缓和紧张局势,降低战争张力。 10. 现实生活的盖然性取代理论的极端性和绝对性 战争因此而避开了理论所要求的极端力量的使用。一旦不再害怕走极端或不再动用极端,事情就变成了要判断该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而这只能建立在现实世界和盖然性法则的基础上。一旦敌我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一旦战争不再是抽象事物,而是服从自身特殊法则的系列行动,现实世界就能提供信息,而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演出将来的未知事物。 11. 政治目的重新凸显 在第二节里提及的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即战争的政治目的。迄今为止,该问题一直在极端法则的光芒下默默无闻。极端法则就是使敌人屈服、使敌人丧失抵抗的意志。但当这条法则开始失势, 而这种意志不再那么坚定,政治目的便会东山再起。假如问题只是测算由特定个人和条件来决定的盖然性,那作为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就必须变成这个计算公式的基本因素。你从对手那里讨要的赔偿越小,他就越有可能偿还给你;敌人付出的努力越小,你需要付出的也越小。 另外,你自己的政治目的越小,你就越不重视,需要的话你就越有可能放弃。这就是你会减少努力的另一个理由。 政治目的—战争的最初动机—决定着要达到的军事目标和需要付出的努力。然而,政治目的本身不能提供衡量标准。既然我们处理的是现实问题,而不是抽象问题,政治目的就只能在交战两国共同的背景下提供衡量标准。同样的政治目的能在不同民族引起不同的反应,甚至处在不同时期的同一民族反应也不同。因此,只有在想到政治目的能对它想发动的军事力量施加的影响时,我们才能把政治目的当作衡量标准。这就需要研究那些军事力量的性质,其性质特点是推 动一个军事行动还是拖军事行动的后腿,结果完全不同。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紧张局势,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场小小的争吵就会制造惊天动地的后果—真正的大爆炸。 政治目的在两国中预期能激发的努力、两国政策所要求的军事目标都是同理。有时候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一致的—比如占领一个省;有时候政治目的不能提供合适的军事目标,这就需要采纳另一个军事目标为政治目的服务,并在和谈中把政治目的体现出来。但即使如此,交战国的特点不能不给予关注。有时候想要达到政治目的,替代目标必须比政治目的更重要得多。国民越少卷入战争,国内和国际的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要求本身就越占主导地位,就越能起决定性作用。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政治目的几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一般来说,在规模上与政治目的相匹配的军事目标会随着政治目的之减小而相应地减小;随着政治目的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军事目标会愈发壮大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战争顺理成章地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重要性的表现形式,从歼灭战到简单的武装观察。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需要分析和回答的问题。 12. 军事活动的中断仍未得到解释 不管任何一方的政治要求有多克制,使用的手段多么轻微,军事目标多么有限,战争过程能够中断吗?哪怕中断片刻?这个问题涉及事情的核心。 ‘ 每一次行动都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这段时间称为行动的持续时间,其长度取决于每个人的工作速度。速度不同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动作缓慢的人不是因为他想多花点时间而放慢工作进度,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导致他需要更多时间。要他加快速度,只会欲速而不达。他的速度是由主观原因所决定的,是这项工作实际持续时间的一个因素。 如果每次行动都允许有相应的持续时间,至少乍一看,我们会认为额外的时间花费(军事行动的暂停)似乎是荒谬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谈的不是任何一方的进展问题,而是军事互动的整体进展问题。 13. 只有一种考虑可以中止军事行动, 而且它似乎只能出现在一方 如果双方都在备战,一定有某种充满敌意的动机把他们带到那种境地。只要他们仍然处在备战状态中(没有签订协议),那个充满敌意 的动机就仍然起着作用。只有一种考虑可以遏制事态发展:行动之前等待更好的时机。乍一看,这种等待更好时机的愿望只由一方所持有,因为另一方的愿望应该正好相反。军事行动对一方有利,另一方就必须等待才不吃亏。 但是,力量的绝对均衡不可能停止行动,因为如果真有这种均势存在,那么主动权肯定掌握在有积极目的的一方—攻方。 但可以设想在一个均势中有积极目的的一方(行动由更充分)具有较弱的军事力量。这个平衡就产生于目的和力量共同制造的结果中。真是如此,我们会说除非在不久的将来平衡会有所变动,不然的话,双方应该选择签订和约。可是,如果能预知某些变动,而且只有一方是这种变动的受益者,就应该会激起另一方采取行动。用均势这个概念无法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按兵不动。唯一的解释是双方都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因此,让我们假定其中一个交战国是有积极目的的,如占领对方一部分领土作为和谈筹码。领土一旦到手,政治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必要做更多的事,可以偃旗息鼓了。如果对方准备接受这个局面,它就应该争取和平。如果不能接受,就必须有所行动;如果它认为在四星期以后能准备就绪,它显然有充足的理由不立刻采取行动。 但从那一刻起,逻辑似乎会要求另一方行动起来—目的是不给敌人留下做准备的时间。当然,纵观我所假设的这一切,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双方都对情况了如指掌。 14. 军事行动会持续并又一次激化矛盾 如果这种持续性存在于战役中,其影响力又会让所有的事情走向极端。这种停不下来的活动不仅挑起人的情绪,不仅在这种情绪里注入更多的激情和基本力量,而且各种事情还会纷至沓来,形成一条更为严格的因果链。每次单个行动都变得更加重要,也就更加危险。 但战争当然并不常带有这种持续性。在众多冲突中,军事行动只占一小部分时间,其他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是按兵不动。这并不总是反常现象。战争中停止行动是可能的,换句话说,措辞上并没有矛盾。让我摆出这个观点,谈谈其原因。 15. 两极性原则 由于设想双方统帅的利益正好相反而又彼此相当,我们就设定了一个真正的两极性情况。后面会有整个章节用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这里有必要做如下解释。 两极原则只在涉及同一事物时才站得住脚,在这一事物中,正面利益和反面利益正好抵消。在一场双方都旨在取胜的战斗中,真正的两极性就出现了,因为一方的胜利势必使另一方的胜利化为乌有。然而,当我们处理两个具有共同外部关系的不同事物时,两极性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事物的关系。 16. 进攻和防御种类不同,力量不对等,无法运用两极原则 假设战争只有一种形式,即进攻敌人,防御是不存在的;或换句话说,进攻和防御的区别只在于进攻的目的是积极的,防御的目的不是,而战斗的形式是相同的,一方的有利条件完全等于另一方的不利条件。如果真是如此,两极原则就可以存在。 然而,战争中清楚地存在两种军事行动:进攻和防御。下面会详细提到,两种行动截然不同,力量也不相等。两极性既不存在于进攻,也不存在于防御,而是存在于双方争取达到的目的:决战。如果一方统帅想推迟决战,另一方必定想加快决战,并且都认为双方在进行同种类型的战斗。如果说现在进攻乙方对甲方不利,四星期后进攻有利,那么对乙方来说,现在遭到攻击比四星期后遭到攻击要好得多。这是即时而直接的利益冲突,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立刻进攻甲方对 乙方有利。这显然是另一个问题。 17. 防御相对于进攻的优势经常破坏了两极性效果,这可解释军事行动的中断 我们要指出的是,防御相比于进攻是较强的战斗形式。于是我们要问,推迟决战对一方来说是不是像防御对另一方那样有好处。如果没那么好,推迟决战的好处就不能与防御的好处相抵消,就不能以这种形式影响战争的进程。显然,利益的两极化所造成的推动力会在进攻和防御力量的不同中消耗殆尽,并因此而失去作用。 于是,如果目前占有利地位的一方不够强大,还离不开防御带来的种种好处,它就不得不接受将来在不利条件下作战。即使在那些不利条件下打防御战也比立即进攻或求和要好。我相信防御的优势(如果理解正确的话)是非常大的,比初看时候要大。这就毫不矛盾地解释了战争中为什么很多时期都是按兵不动。行动的动机愈弱,就愈被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差异所覆盖、所压制,军事行动就愈会频繁中断—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战争理论必读典籍,西方近代军事理论鼻祖克劳塞维茨传世之作 影响世界进程的重要作品,对军事理论与思想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精选原书独创洞见,凝练兵学思想精髓 与其把战争比作一门艺术,不如把它比作商业更确切。因为战争和商业一样,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