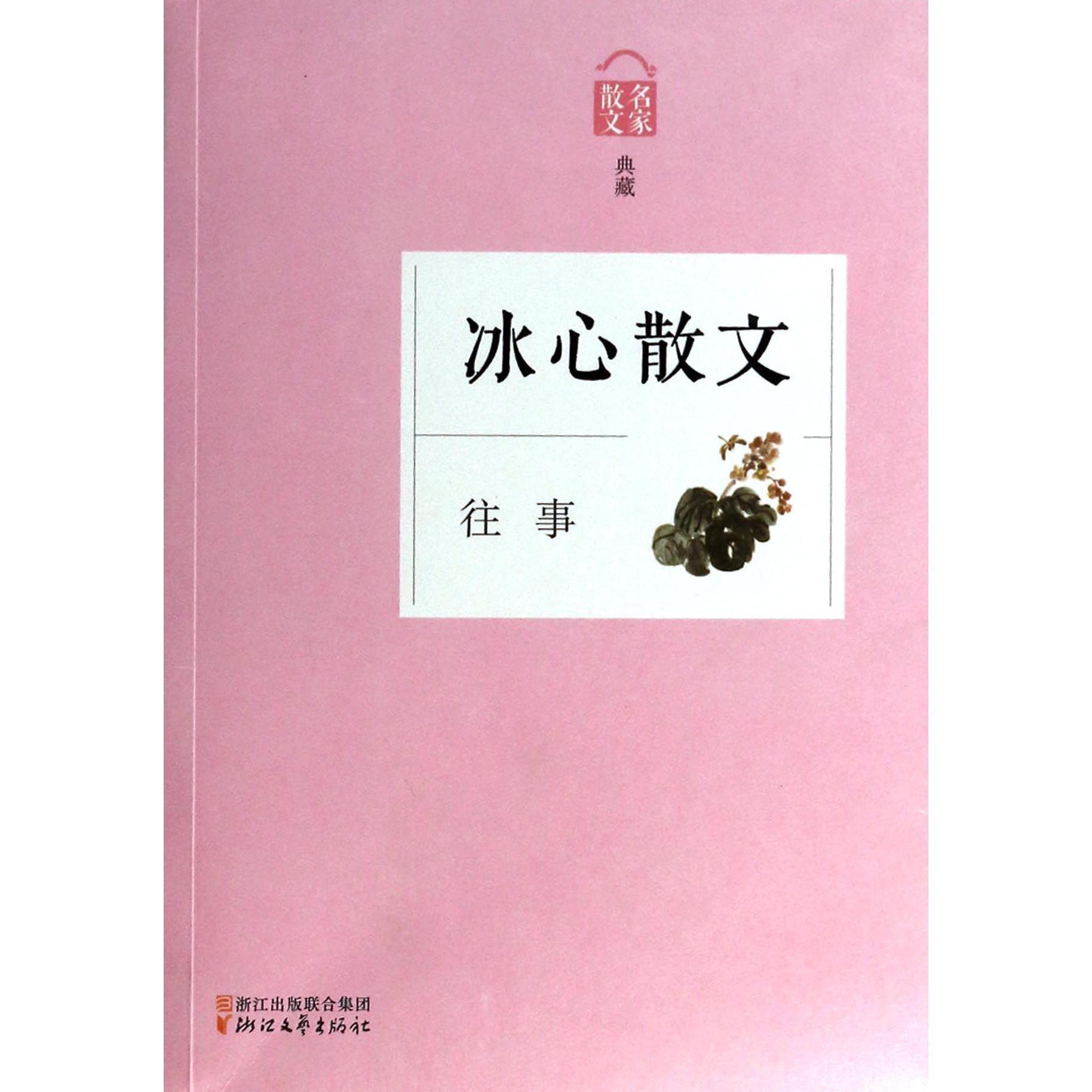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文艺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冰心散文(往事名家散文典藏)
ISBN: 97875339370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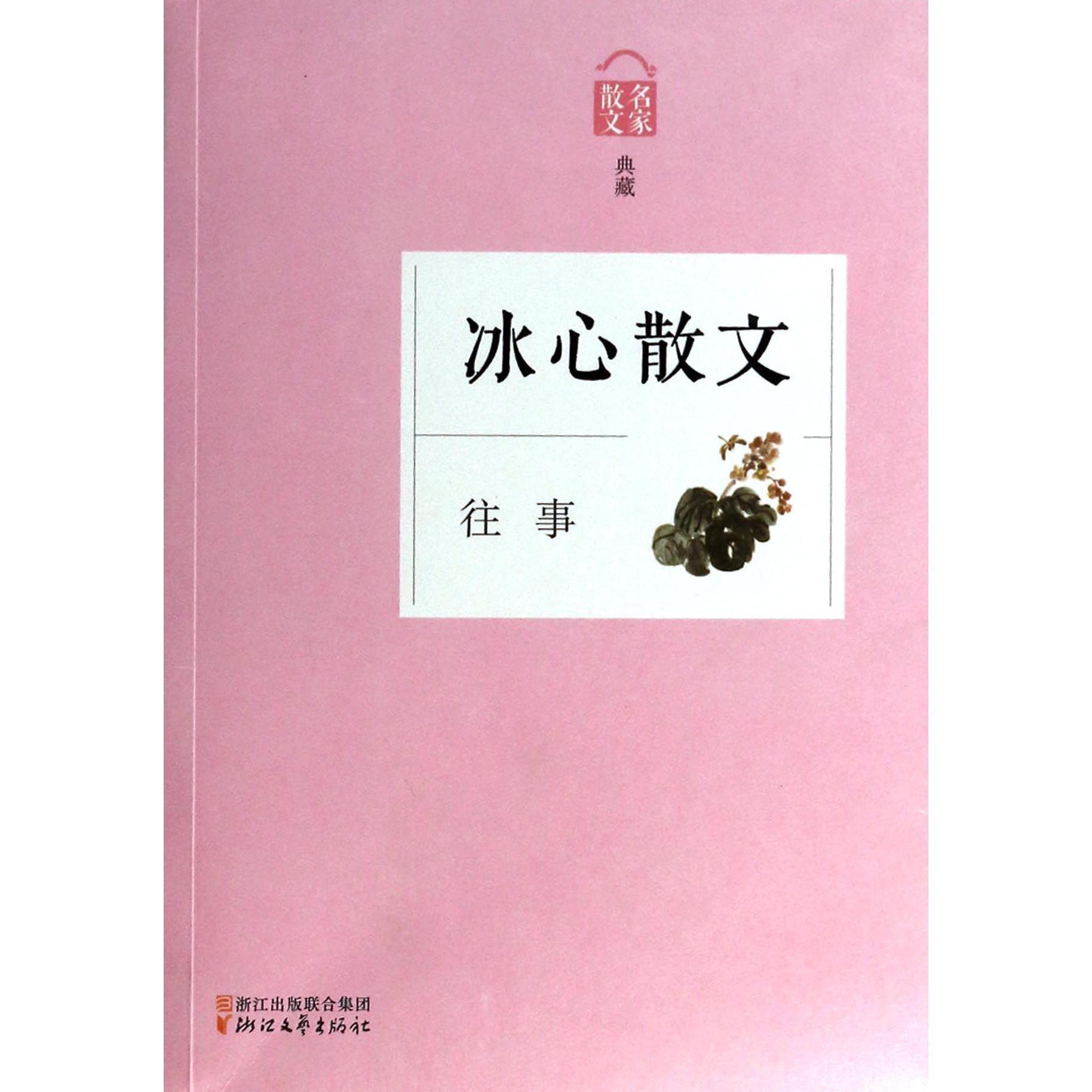
我生于一九OO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 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 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 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极其亲切 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 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 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 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 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 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 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 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父是昌武公,以 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 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 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 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 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 就原原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 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 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 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 漂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 、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 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 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 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 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 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 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 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 ;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 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 好替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 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 。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 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 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 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 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 弟”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 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 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 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 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 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 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 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 ,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 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 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 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 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 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 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 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 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 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 银角子,合起来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 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 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 小说,讲的就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 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 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 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 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 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1 …… P268-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