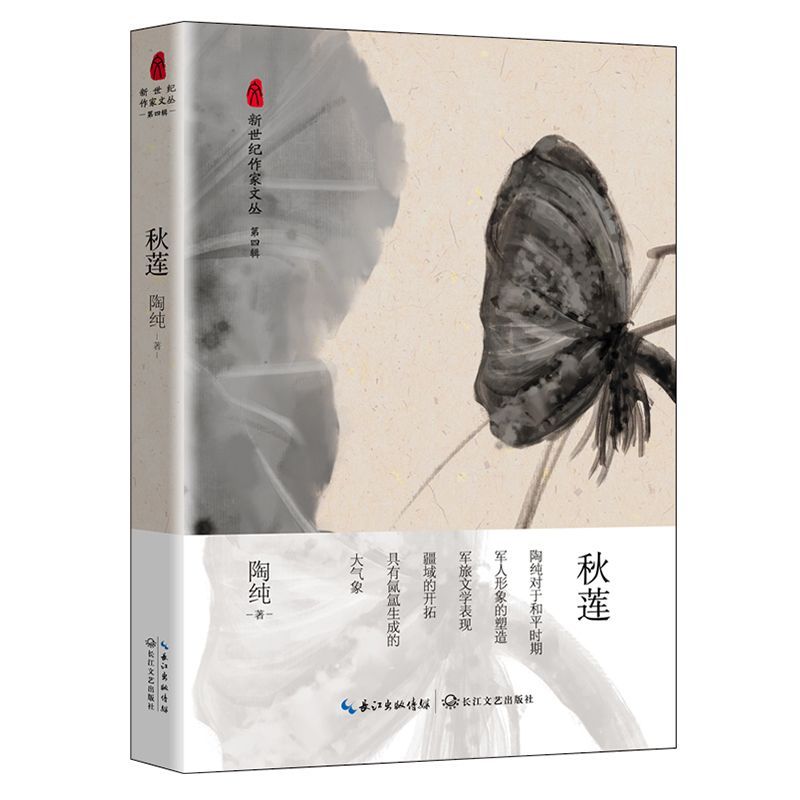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30.00
折扣价: 18.60
折扣购买: 秋莲/新世纪作家文丛
ISBN: 9787570207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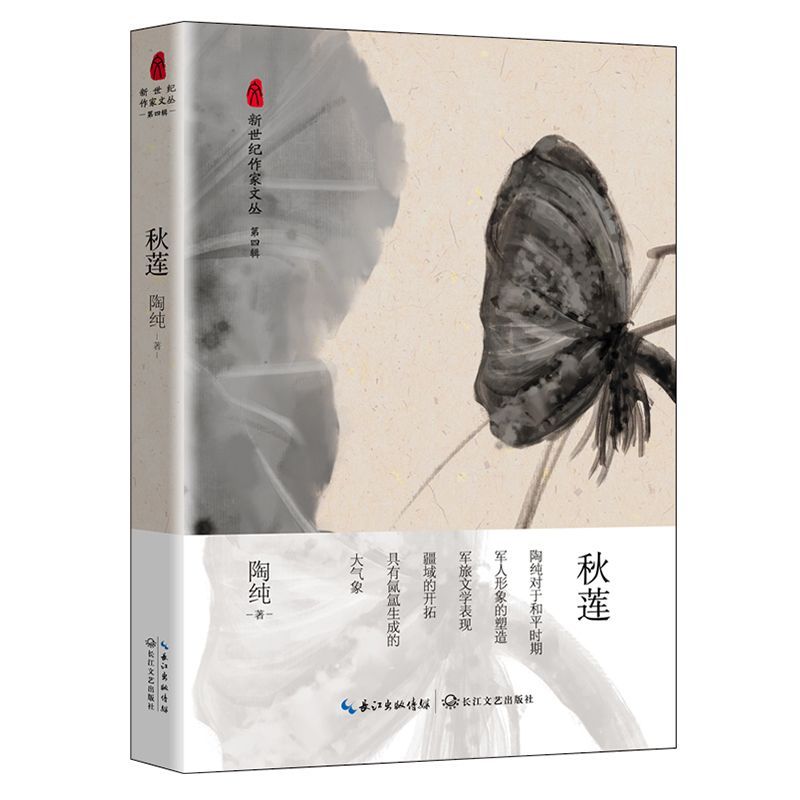
陶纯,本名姚泽春。山东省东阿县人,19**年生,1980年入伍,先后就读于解放*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各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各类选刊转载。曾两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文艺奖”,两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获得“全*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文艺》《中国作家》等刊物**作品奖;2003年后转向影视剧本创作,有8部剧作拍摄面世,影视作品先后五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2014年回归文学创作,长篇小说《一座营盘》入选201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7年出版长篇小说《浪漫沧桑》,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榜”。现为解放*战略支援部队专业作家。
秋 莲 一 秋莲的父亲两个月前在徐蚌会战中殉国,两个月后,她母亲翟桂芳肺病加重,不幸在广慈医院去世。 许宗衡阵亡的消息,一直瞒着翟桂芳,两个月来秋莲不让她看任何报纸,也不让她听广播,还叮嘱父亲生前派来的两个勤务兵,决不能把这个口风露出去。两个月来,翟桂芳一直住在这所法国人开办的医院里治疗肺病,病情虽有所反复,但不至于马上就没治。 本来许宗衡答应打完徐蚌会战,就带夫人到香港治病,身体转好的情况下,再把她们母女转送美国,秋莲也正想到美国读书。但是两个月前,在离徐州五十多千米的碾庄,黄百韬第七兵团被解放*粟裕所部重兵围困,黄百韬*望中**,一直跟随护卫黄长官的二十五*副*长许宗衡被流弹打死,****精锐第七兵团全*覆灭。两天后的沪上所有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报童举着报纸,大声叫嚷这条特大新闻,引来一群群的购报者,拿到报纸的人发出一片惊叹之声。 秋莲本来也想到医院门外买一张报纸,自从父亲去徐蚌前线后,她每天都要买报,但是听到报童刺耳的叫喊,她打消了买报的念头。从此以后,她就不再买报。 几天前,父亲生前派来的两个勤务兵借故跑了——一个说去买菜,没回来;另一个说去买烟,也没回来。母亲已经意识到不好,饭量降了。这天早晨,有个病号提着一台收音机从病房门口缓缓经过,里面正播放蒋总统的一篇讲话。总统提到1946年以后殉国的******将领,有张灵甫、蔡仁杰、韩增栋、刘戡、陈章、黄百韬、郭景云,*后说到了秋莲的父亲许宗衡。正在给母亲喂饭的秋莲想要掩饰,只见母亲剧烈咳嗽一阵,一口气没上来,就去了。 许家一年半前从南京搬来上海居住,在上海并没有私人住宅,租住的房子。许宗衡心细,他考虑的是,上海靠海,冬天比南京好*一些,没南京那么潮湿阴冷;上海外国人办的医院多,比南京医疗条件好,这些都对翟桂芳的身体恢复有利。许家在上海没什么熟人,许宗衡祖籍福建厦门,二十岁离开老家出来上黄埔*校,之后从*打仗二十多年,和老家族人的联系早已中断,秋莲是家中独女,因此许宗衡夫妇这么一走,秋莲在上海就没有了一个亲人,她真正算是举目无亲了。 母亲的后事料理,多亏一个人——汤正伦。汤正伦是许家在南京时候的邻居,两家在秦淮河边的别墅紧挨着,他比秋莲大五岁,他父亲是南京大华纱厂的老板,他排行老三,以前有熟悉的人叫他汤三。他大哥在****的一支部队当少将旅长,1947年在河南阵亡。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姐姐姐夫都在南京“***”工作,很少在人前露面,做了十多年邻居,秋莲没见过他们几回。 有**秋莲到三马路上一家药店给母亲抓药,一出门,看到一个面孔很熟悉的人,着西服,鸭舌帽压得很低,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一个穿长袍的男人,脚步快速地移动,从她面前经过。秋莲马上就认出,这不是汤正伦吗?他怎么也跑上海来了?他们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面了。 秋莲喊了他一声:“汤正伦!” 汤正伦愣了一下,扭脸认出秋莲,示意她不要说话,再转过脸往前瞅,发现那个穿长袍的人已经不见了。他伸手顶一下鸭舌帽,走到秋莲身边,露出久违的笑和一口白牙,说:“许小姐,想不到你也来上海了。” 秋莲好奇:“刚才那人,是谁?” 汤正伦淡淡一笑:“***的人。要不是你插这一杠子,**我能逮住他。” 秋莲抱歉地说:“这样啊,我打搅你公务了。” 汤正伦满不在乎地说:“没事,下回再逮他。” 那天中午汤正伦非要请秋莲吃饭,秋莲辞请不过,只得提着一大包药丸,跟在他屁股后面去了四马路上的一家西餐店。饭毕分手的时候,汤正伦告诉她说,他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外滩七号电报大楼的一个小经理,那里的人都知道他叫高伦,希望秋莲以后也叫他高伦,不要再提他以前的名字。 秋莲有些吃惊:“你怎么连姓也改了?” 汤正伦——高伦咂咂嘴说:“职业需要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秋莲母亲住进广慈医院后,高伦时常过来瞅一眼。翟桂芳对他过去的印象蛮不错,说他小时候像个洋娃娃,淘气聪明,人见人喜;又说他爸曾经和秋莲爸议论过,如果两个孩子以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好选同一所学校,互相有个照应。一次,翟桂芳问高伦,你爸你妈还好吧?都有一年多没见他们了。高伦头一低说,母亲还好,父亲半年前过世了,大哥在豫北前线牺牲后,父亲就一直没缓过劲来,加上厂子不景气,终于急火*心,**夜里犯病,天没亮人就撒手去了。翟桂芳叹口气说,世道不好,啥事体都可能发生啊。 翟桂芳终归是过来人,看出高伦对女儿有意,有**她说:“莲儿,万一我和你爸有个三长两短,你就跟他过*子吧,他还是靠得住的。”秋莲脸一红说:“现在说这个干什么。” 许宗衡在前线出事,高伦知道得略早一点,他来医院找秋莲,向她露了点口风,没说全,只说许长官可能在徐蚌前线遭遇不测。秋莲不信,埋怨他乌鸦嘴。直到第二天沪上所有报纸都登出来,秋莲不信也信了。 母亲一去,秋莲傻了似的,不哭不叫,像个木偶,双目低垂,一言不发。给母亲办后事期间,高伦跑前跑后地忙活,他亲自跑到外面买来水绿色的绣花寿衣,央求护士护工们帮死者穿上,又亲自把遗体推到医院太平间,然后到店铺置办寿材,直到雇车把棺材运到静安寺公墓下葬。不了解情况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死者的儿子。 帮忙料理后事的人都走开了,墓地里只剩下秋莲和高伦两人。秋莲仍然是呆若木*。高伦扶住她肩膀说:“秋莲,你就哭一声,哭出来就没事了。”秋莲张了张嘴,终于哇地大哭起来,边哭边翻来覆去地说:“都走了,谁管我啊……都走了,谁管我啊……” 许宗衡死在前线,骨殖不知丢到什么地方了,想给他们夫妻合葬已不可能。秋莲把父亲戴过的一顶帽子放到母亲的棺材里,算是给他们夫妻行了合葬。本想立个碑,上写“父母大人许宗衡翟桂芳之墓”,下面再落上“儿许秋莲”和年月*,高伦不同意。后来才知道他有意不立碑,是为了掩护秋莲的身份。 时间一长,这座坟堆就会被人当成无主坟。秋莲当时顾不上想这些,一切都由高伦来料理,她全听高伦的。 这一年秋莲十八岁,高伦二十三岁。 二 葬了母亲之后,秋莲有过回南京的打算,毕竟南京有个家——秦淮河边的那栋房子里,藏有不少她喜欢的书籍,还有一些她的画稿,她曾经**迷恋画画,画水彩,也画过油画。来上海后,她全部精力用来照顾母亲,书啊画啊,都丢到脑后了。 高伦不同意她回去。说你回去上学还是做工?她回答不上来,只说南京熟人多,有贵族学校的同学、老师,有一栋自家的房子,还有母亲家那边的几个远房亲戚。高伦说,天要变了,国破家亡的事,不幸让我们赶上了,这时候,熟人越少越好,房子越小越好,有些东西你是背不走的,不如放弃。 高伦在上海混了几年,明显比秋莲成熟。秋莲想起母亲临终前说过的,让她未来跟他过*子的话。她想,离了高伦,对她来说,天真要塌了,她还有什么可选择的?高伦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吧,也许这就是命。谁让你家跟他家做邻居呢?谁让你现在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呢?是不是天注定? 就当是天注定吧。 高伦有时出来,身上带*。他执行公务的时候,就像失踪一样,秋莲想找他都找不到。当你刚要生他气的时候,他又出现了。他陪秋莲逛商铺,逛公园,有时还去夜总会跳一场舞。等秋莲母亲过了“五七”,她心情好转了一些,他说,莲儿,该给你找个事情做了。 这天,高伦把她带到闸北的一座兵营,到*场上看了一会儿****士兵刺杀练习,有个人过来伏在他耳边说,老K到了。高伦带秋莲跟着那人来到二楼一间窗帘紧闭的大房间,有个三十岁左右、相貌堂堂的男人坐在藤椅上抽雪茄。想必他就是老K了。 他们进入后,老K半站起来,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老K简单问了几句秋莲的情况,这之前高伦肯定跟老K介绍过秋莲,所以老K对秋莲的家世比较了解。他身子前倾,盯着秋莲说:“许小姐,我问你话,你要据实回答。明白吗?” 秋莲诚实地点点头。 “你——恨***吗?” 秋莲以前很少想这个问题,她不知该怎么回答。老K身子又往前倾了倾:“令尊死在***手里,难道你不恨他们吗?” 秋莲想起高伦就在自己身边,望了他一眼。高伦朝她微微一点头。于是她回答说:“恨……我恨。” 老K满意地点点头:“你愿意参加我们的组织吗?像我、高伦兄一样。” 秋莲又看一眼高伦,然后点头说:“愿意。” “既然加入组织,*不允许背叛。你能做到吗?” 秋莲再看一眼高伦,目光转向老K:“我能。” “如果做不到……嚓!”老K做了个挥刀砍头的动作。 秋莲点点头,表示她不怕。 老K轻轻拍了几下巴掌,站起来,冲秋莲伸出手。秋莲赶紧站起来,也伸出手。她的手被老K黏糊糊的大手紧紧握住。 老K笑说:“欢迎你,张秋莲同志。” 秋莲一愣:“长官,我叫许秋莲。” 老K望着高伦。高伦小声对秋莲说:“加入组织,安全保密起见,得按纪律改名换姓。我向组织建议,只给你改姓,因为沪上现在知道你叫秋莲的,没几人,名可以不改。” 秋莲想了想说:“沪上知道我叫许秋莲的,也就你们二位。我既不*名,也不改姓,行吗?” 高伦望着老K。老K掏出打火机点燃手中的半截雪茄,用力抽了两口,这才点点头说:“先这样吧。” 秋莲松了一口气。她知道父亲在老家没兄弟姐妹,父亲没了,她再改姓,许家就什么也剩不下了。 就这样她成了组织的人。早年,她父亲曾经说过,希望她长大后远离政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现在她顾不得这些了,因为她一切都得听高伦的。 几*后,高伦把秋莲带到浦东地界的一个独立院子,她要在这里参加一期培训班,除了“洗脑”,还要学一些基本的谍报工作技术,比如密写、速记、收发报、破译、战场包扎救护、射击、照相洗相,等等。在这里不使用名字,名字严格保密,每个人都用代号,秋莲的代号为十六。以后为了工作便利和身份掩护,还要求每人选学一门技术,秋莲征得高伦同意后,选学的是医疗护理专业。 培训结束,根据上峰要求,秋莲被安排进了**劳工医院,她每天到那里上班,虽然很累,但却感觉很充实,因为她长这么大,终于有了为社会服务的机会。她家原先租住的房子是石库门的二楼三个房间,现在她单身一人,父亲留下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不能再住那么大的房子,高伦替她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有不少医院的姐妹在这附近租房子住,秋莲很快与她们混熟悉了。 只是她不理解:学了谍报技术,成了组织的人,跑到医院干啥?指望她在医院抓***?她把这个疑问说给高伦听,高伦说,到这个地方,是为了以后,你先洗白自己,等待上峰分配任务,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这时候,已经有传言说,解放*很快要打过长江,南京、沪杭一带的有钱人,纷纷自找出路,香港、南洋成了**,而*政*要员则把以前没怎么听说过的**,当作第二故乡,准备携家带口漂洋过海,追随虽然下野仍然权柄在握的蒋先生而去。秋莲想,如果父母还活着,她也许也要去**的。听说贵族学校的不少同学都走了。 很显然,***过江,首要目标一是南京——南京是首都;二是上海——上海*有钱。那一阵上海**的乱,世界末*来临一般,似乎人人惶惶不可终*。果然,解放*四月份过江,五月初就兵临上海郊外,大战一触即发。秋莲现在已经知道,老K是***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小头目,高伦是他的下线,而她又是高伦的下线。也就是说,她直接*高伦领导,高伦直接*老K指挥。这时他们又有了新的代号,高伦代号“野*”,秋莲的代号为“公牛”。 上海沦陷在即,上海的****正规*以及各路人马,都在做*后的挣扎努力。秋莲依旧没有什么任务,正常上下班,高伦却忙得不可开交,每夜都出去执行公务。秋莲好不容易和他见上一面,劝他说,***那么猛,咱们*蛋打不过石头,会碰破的。他的眼睛红红的,像个输光了钱的赌徒,他说,石头是死的,*蛋有生命,*蛋可以孵出小*,生生不息,我们要战斗到底。又说,即使碰破了,也要冒一个*蛋花,灿烂一下。 解放**城那天,除了一些留下潜伏的人员之外,保密局的人走得差不多了——一部分人员到福建、广东“继续战斗”,一部分人员直接撤到**,另图光复大业。但是高伦没走,秋莲自然也是走不成。高伦说,老K也没走,他们再搞一两个大点的行动就撤。高伦的姐姐和姐夫早在***渡江之前,就随“***”大部分人员撤到**去了,同时把他老母亲也带走了,这样高伦就没了牵挂,可以放手干事情。他还劝秋莲,别怕,上海守三个月没问题,有大*在,咱们不会有危险。 秋莲知道,高伦他们想在破城之前炸毁闸北发电厂。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上海并没有像汤恩伯总司令说的那样“固若金汤,守六个月没问题”,也不像高伦说的“能守三个月”,不到半月,上海就沦陷了。 秋莲记得很清楚,五月二十七*那天,解放*进城,而高伦此时还没接到老K让他们撤退的命令。秋莲感到害怕,跑了老远的路来高伦寓所找他,想和他待在一起。高伦很急躁,不停地摇电话找老K,好不容易找到了老K,老K说,他还要组织几个行动,请再坚持几天,到时候他会通知他撤退时间和集合地点。 城里城外零星的战斗仍在进行,*声像爆豆一样不时地传来。高伦的寓所在衡山路上的法租界,这里相对安全一些。高伦安慰秋莲,不要怕,他故作轻松状,说:“我手上有三条命,我都不怕,你是白纸一张,*不用怕啦。” 秋莲自打父母亲死后,一直没怎么缓过劲来,整天战战兢兢的,她把高伦当成了自己在世上**的依靠。高伦以为她怕,其实误解了她,她并不担心自己,她是怕高伦有事。一旦高伦再有个三长两短,她在世上就没有任何的依靠了。这让她感到无比的恐惧。 高伦给她倒了一杯咖啡,坐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他们认识这么久,头一回如此亲密,她闻到了他的呼吸,那么粗壮有力,令她有些眩晕。后来她就稀里糊涂倒在了他怀里。再后来他们就倒在了他的小*上。他像美国电影上那样,吻她的唇,吻她的脖颈,吻她的耳朵,抚摸她的胸。他动作笨拙,没有章法。这种新鲜的体验却使她魂不守舍,呼吸困难,感到微微的窒息。外面的*声依然散乱地响着,忽远忽近,他们都听不到了。昏昏然之中,他把她的长裙子撩上去,她没有做任何的反抗,心想反正早晚是他的人,就随他吧。 但是一阵急骤响起的*声突然把他们打醒了!*声就响在窗户底下!一颗流弹击碎了窗玻璃,碎玻璃碴子飞溅到*头,差点掉落到秋莲脸上。这个突然的变故让高伦一阵发蒙。秋莲比他清醒,她首先想到他有危险,推他一把说:“你快走!” 高伦胡乱穿上裤子和上衣,从后门溜走了。秋莲松了口气,感觉这儿不宜久留,她整理一下衣衫,出了房间,从前门走出来。 面前的景象让她骇然变色! 这附近是个小三岔路口,有四个身穿解放*服装的人扑倒在地,他们的鲜血一摊摊地印在马路上,像新鲜的颜料,带着刺鼻的气味。显然这四人刚才遭到了伏击。秋莲呆愣片刻,回过神来,拔腿就想走掉。她刚刚走出两步,就听身后有微弱的**声……她本能地回头,看到四人中的一人,轻轻动了动。**声就是他发出的。秋莲这时候什么也不怕了,什么也不顾了,毕竟那人还没死,她不能不管。她扑过来,看到那人腹部中了一弹,腿部中了一弹,左臂也中了一弹,要害处是在腹部。她当了两个多月护士,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她熟练地解开他身上自带的一卷绷带,快速包扎他腹部的伤口,然后又从他身边的两具尸体上解下另两条绷带,狠狠用力扎住他腿部、左臂部的伤口。血终于止住了,他身下的血团不再往外扩展。 做完这一切,她浑身汗涔涔的,瘫坐在地。她双手沾满了血,脸上也溅上了血点子,看上去她也像*伤的样子。 那个被她所救的伤者一脸络腮胡子,冬瓜脑袋,喉结粗大,方脸阔嘴,像是个长官。他是她从医以来所救的**个人。他在某一瞬间苏醒过来,因为失血过多,脸苍黄得吓人,他冲她艰难地笑一笑,表示感谢的意思,然后又昏了过去。秋莲呆呆地想,只要自己伸一下手,松开他腹部的绷带,他立马就完了。 这算不算是替父亲报仇呢? 此时,有不少人叫喊着什么,快步朝这边跑来。 新世纪作家文丛第四辑,陶纯中短篇小说集,对和平时期**形象的塑造、*旅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有氤氲生成的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