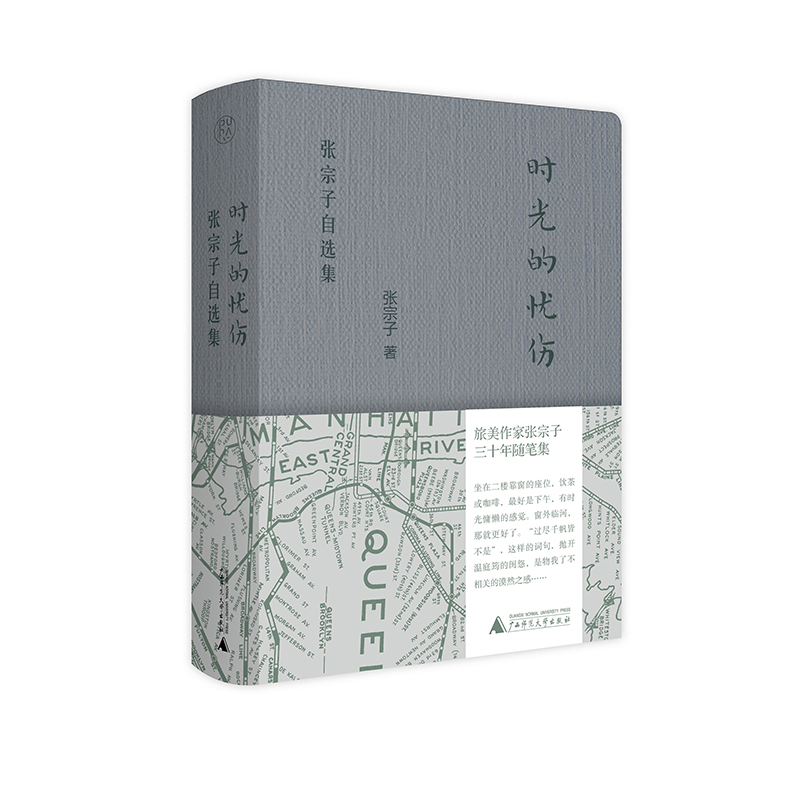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0.20
折扣购买: 时光的忧伤:张宗子自选集
ISBN: 9787559850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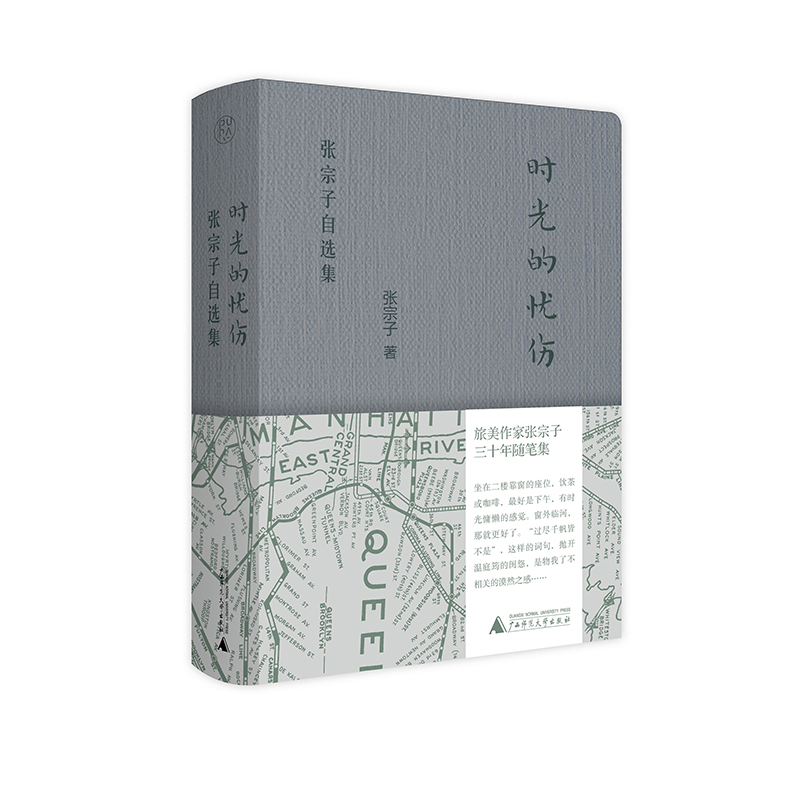
张宗子,河南光山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88年自费赴美,学习英美文学。在纽约《侨报》工作十余年,任编译和编辑。后在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九十年代以后,写作以散文和读书随笔为主,也写诗、译诗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作品见于《读书》《散文月刊》《南方周末》《财新周刊》和“腾讯?大家”等报刊和网络媒体。出版有散文集《垂钓于时间之河》《空杯》《一池疏影落寒花》《梵高的咖啡馆》,读书随笔集《书时光》《不存在的贝克特》《往书记》和《此岸的蝉声》等十余种,译有《殡葬人手记》。
黑鸟的翅膀 拉赫玛尼诺夫的《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怎么说它的人都有,旅法钢琴家傅聪直言不讳:他不喜欢拉赫玛尼诺夫,“拉二”是一碗糖水,加了太多的糖。在音乐里,忧伤总是和甜蜜在一起,能够迅速流行的,差不多都是这类东西。“拉二”开头命运的沉重撞击声,过于灰暗的调子曾经被人比拟为爱伦?坡的诗《乌鸦》,然而他们指出,《乌鸦》抒写死亡,并不单纯出自诗人神经质的臆想,瞻前顾后,都有现实的坚实基础。拉赫玛尼诺夫这一点个人的艺术困窘,何至于夸张到与死亡一般肃穆。何况这样的处理,很容易使人认为,它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不恰当的模仿。事实上,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协奏曲确实来之不易。1897年,他的第一交响曲在圣彼得堡首演,结果是一场惨败。受此打击,拉赫玛尼诺夫对创作失去了信心,在近三年时间里什么都写不出来,只能专注于钢琴演奏。无奈之下,他求助于莫斯科的精神病专家,靠催眠疗法恢复正常。病愈后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这首风靡一时的《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从江淹到席勒,很多作家和艺术家都曾经为创作的巨大困境而痛苦,最终能够跨越关山的少之又少。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描写席勒在创作诗剧《华伦斯坦》的过程中,因无法写好一个重要场面而产生的内心焦虑,不知是实事还是虚构。参照曼的描写,拉赫玛尼诺夫的痛苦我们感同身受。因此,在“拉二”中,强烈的情绪之后出现的那些如云间流泉的淙淙之音,纤丝细缕,空灵飘忽,又似松下之风,携花香,伴鸟鸣,洗愁肠,破溽暑,那是得自在后的欢愉,不在所取得成就的大小,只在欢愉,哪怕只是一点点。这是我们最能消受的情感,至少对于我,“拉二”的好处在此,这是他更了不起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里没有的。既然好,暂时不要想到贝多芬,更不要说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如何如何。 1945年的电影《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以此为贯穿影片的配乐,给人相当煽情的印象。一些乐评家一次次预言(更确切地说是希望),“拉二”将很快被人遗忘。但直到一百零八年后的今天,“拉二”和公众的蜜月似乎仍未结束。在网络和多媒体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传统文化形式并全方位地改变大众的阅读和欣赏趣味的情势下,“拉二”的夕阳不仅没有垂直沉落,兴许还能逆向攀爬得更高。 从糖水曾是待客饮料的中国迁居到葡萄酒之乡的傅聪,当然不会再去喝糖水。而另一位从法国出来的钢琴家埃莱娜?格里莫(He?en?e Grimaud),却对拉赫玛尼诺夫怀着特殊的感情(尽管她最爱的是德国浪漫派的大师们)。格里莫十五岁那年,凭着一曲拉氏的第二奏鸣曲扬名西方乐坛。她2000年为Teldec录制的“拉二”,据说销路极佳。一些心有不忿的乐迷说,这张唱片,卖点不在钢琴演奏,甚至也不在拉赫玛尼诺夫,而是封面上年轻貌美的女钢琴家的玉照。 2000年,格里莫刚过而立之年,清爽的男孩子似的短发,白色粗毛背心,仿佛来自安格尔画笔之下的蓝绸大裙子,双肘轻拄琴上,一手托腮,回眸浅笑。格里莫的唱片里,再没有这么动人的画面。古典音乐界难得出一个美女,不管是歌唱家还是演奏家,好不容易从天上掉下一个,如果不追捧,岂不是暴殄天物? 格里莫的唱片,听过几张,没有很深的印象,说不定也是因为她音乐之外的事太转移人的注意力了。她给人的感觉,有点野,有点异类,有点叛逆。她的自传名叫《野性的变奏》(Variations Sauvages),英译本略变一下,叫《野性的和谐》(Wild Harmonies)。她喜欢狼,视狼为亲人。1999年,千辛万苦,在纽约上州的South Salem建起一处野狼保护基地,她自己也移居纽约。自传的封面上,三头狼围着她,狼头紧挨着她的脸,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 狼也可以温柔。格里莫的钢琴,并不狂暴和怪异。弹贝多芬,她首选第四而非第五,似是一种本分的宣告。就是弹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在众多版本里,她的版本似乎还更轻柔一些。异类和野性,是迎风张扬的旗帜,还是天生的气质?我们不知道。 在“拉二”的唱片说明书里,有萨宾?施耐德(Sabine Schneider)写的一段,讲格里莫天生的色彩感受。 对于格里莫来说,音乐始终和颜色密不可分。十岁那年,她第一次发现,巴赫《赋格的艺术》在她心里唤起了色彩感。每个单一的音符都和特定的颜色对应,但通常的情况是,整部曲子从总体上印证了某种色调。调性本身也各有色彩:升F大调是鲜艳的红色,G大调则是绿的。在乐曲的进行中,一种色彩浮现,变化,而后消失。 弹奏和单纯的聆听不同,聆听时的感受更强烈。而当格里莫阅读乐谱或想着某一部作品时,她能够利用色彩帮助记忆。这样,在她凭记忆弹奏时,她记起的不仅是音符,还有颜色的印象。 至于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在格里莫眼里,那是黑色的所有浓淡变化,“就像黑鸟熠熠闪烁的羽毛”。具体地说,在第二乐章里,她看到“一块被铁匠烧得白热的金属,逐渐冷却,颜色也越来越暗淡,最后变为暗褐色”。 施耐德女士说,很多人具有听见颜色或看见声音的能力,这就是所谓“通感”。有通感的人,两千人里就有一个,但只有少数人能意识到自己具有这种天赋。很多大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品都受到通感的影响,如画家康定斯基、小说家纳博科夫、作曲家梅西安和利盖蒂。 施耐德的论断,在我看来,有装神弄鬼之嫌。通感,假如只是外物引起的情绪或感觉上的联想,那一点也不稀奇。我们常说冷色调暖色调,说某人的目光是温暖的,某人的话语是冷酷而尖利的,蛇“让我们的血液一下子降到零度”(艾米丽?狄金森的诗),琴声一会儿似烧红的火炭,一会儿像冰(韩愈),如此通感,人人都有。可是格里莫的通感是那么明确,那么具体,我们不能不觉得惊讶。事实上,这种带点神秘性质的异秉,更像是一种感觉的串位或错乱,不过是良性的。还有一些类似的颜色游戏,看起来是把也许实有的感觉加工和提高了,本身与创作无异。法国诗人兰波用诗排了字母和颜色的对照表,虽然看似神秘,说穿了,和帮助小孩子记忆的“3是耳朵,7是拐棍”差不多。 相比之下,倒是俄国作曲家斯克里亚宾在神秘之路上走得最远。他构想中的巨作《神秘物质》,是一部“包含了声音、视觉、味觉、感觉、舞蹈、舞台装置、管弦乐队、钢琴、歌唱演员、灯光、雕刻品,拥有色彩和幻想,处于催眠状态的各种媒介的狂想曲”(哈罗尔德?C.勋伯格:《伟大作曲家的生活》)。他的第五交响曲“普罗米修斯”的演出,“除了完整的交响乐团,还使用了一架钢琴、一个合唱队和一个用来把色彩投射到屏幕上的色彩机”。 斯克里亚宾为此列出了一个详细的音和色的对应表: C,红色;升C,紫色;D,黄色;升D,闪烁的青灰色;E,珍珠白和月光;F,深红色;升F,鲜亮的蓝色; G,橙粉色;升G,紫红色; A,绿色;升A,闪烁的青灰色; B,珍珠蓝色。 在《神秘物质》的演出设想里,场上要“弥漫着香水和烟草的辛辣味,以及乳香和没药的味道”,演出场地必须设在印度的神庙里。 说颜色,就想到很多人对某种特定颜色的迷恋。我说的不是个人介绍里常有的“最喜欢的颜色”,我说的是迷恋。严格地说,迷恋是一种病态,但大多数时候无伤大雅。而在艺术和艺术欣赏里,迷恋常常表现为一种趣味,一种很高级的趣味。一件寻常的事物因此附载和提供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就此而言,审美怎么说也是更多地决定于审美者,而非审美对象。 普鲁斯特喜欢红色:奥黛特初次登场是一身玫瑰红,这为“斯万之恋”那首洋溢着光怪陆离的激情的乐章定下了基调。男主人公马塞尔最崇拜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以她的红色裙子著名。其中一件是淡红色的天鹅绒连衫裙,普鲁斯特这样描写马塞尔的感受: 我不像往常那样伤感了,因为她脸上的忧郁表情和连衫裙的鲜艳色彩一道,仿佛组成了高墙,把她同世界隔开,使她显得可怜、孤独,使我感到放心、宽慰。我觉得,这件连衫裙向周围发出的鲜红光辉,象征着她那颗鲜红的心,对这颗心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也许能给它安慰:德?盖尔芒特躲在微波荡漾、神秘莫测的天鹅绒的红光中,就像早期的基督教女圣徒。 另一件是“下摆缀有闪光片的红缎晚礼服”。这件红缎晚礼服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大名鼎鼎。马塞尔说,穿上这件衣服的盖尔芒特夫人,“就像是一朵嫣红嫣红的花儿,一颗火红透亮的宝石”。第三卷第二部的结尾,盖尔芒特夫妇为了不耽误参加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的晚宴,对于老朋友斯万透露的自己病重、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假装不信,而以玩笑置之。盖尔芒特夫人为晚宴而精心准备的盛装,就是这件红缎长裙,而且“头发上插着一根染成紫色的鸵鸟羽毛”。公爵夫妇的义无反顾,斯万的被“抛弃”,如一位美国女评论家所言,被描写得“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盖尔芒特夫人一身的红艳,在夕阳中令人永世难忘。在第五部《女囚》里,马塞尔更是不厌其烦地打听这件衣服的细节,以便为女友阿尔贝蒂娜照样裁制一套。 对于那些值得仰望和热爱的女人,普鲁斯特说,特定的衣着“并非一种无所谓的、可以随便更换的装饰,而是一种确定的、带有诗意的现实,如同一天的天气,如同这一天里某个时刻特定的光线”。“这些长裙被赋予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使穿着这些长裙等你前去或是与你交谈的这个女人,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起来,仿佛这装束是长时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仿佛这谈话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有如小说中的场景。” 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艺术化,将意义皴擦在每一件被纳入关注和情感投射的事物上,普鲁斯特也许在试图告诉我们,流淌在时间之河上的广大世界,不过是心智和记忆的游戏而已。 联想到普鲁斯特的同性恋倾向,盖尔芒特夫人们的红色意味深长。 李贺也是颜色的迷恋者。早年的印象,现在可能不准确了。据说他眼中和幻梦中的颜色,和他长期的吐血有关:红,和红的对比色——绿。他的红往往牵涉到死亡,是一个触目即是的死亡过程。他的绿常被用来象征鬼魂的世界。红和绿本是强烈的对比,而在李贺那里,它们却能互相代替和转换,如《神弦曲》中的“笑声碧火巢中起”,如《苏小小墓》中的“冷翠烛,劳光彩”。《巫山高》的尾句:“椒花坠红湿云间。”注者以为,椒花本非红色,李贺此处是误用。王琦说椒花坠红是无人花自 本书是旅美作家张宗子三十年散文自选集。或对中外作家和艺术家的评论,将中外人物穿插交织,颇有意识流的跳跃思维特色。或对自己生活的回忆,通过叙述人与事,折射出时代的影像,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或是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的感悟,从中可窥见作者的生活阅历和人生见地。或借花草树木表达闲情逸致。 张宗子的文字雍容典雅,文气静穆平和,展现了汉语大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