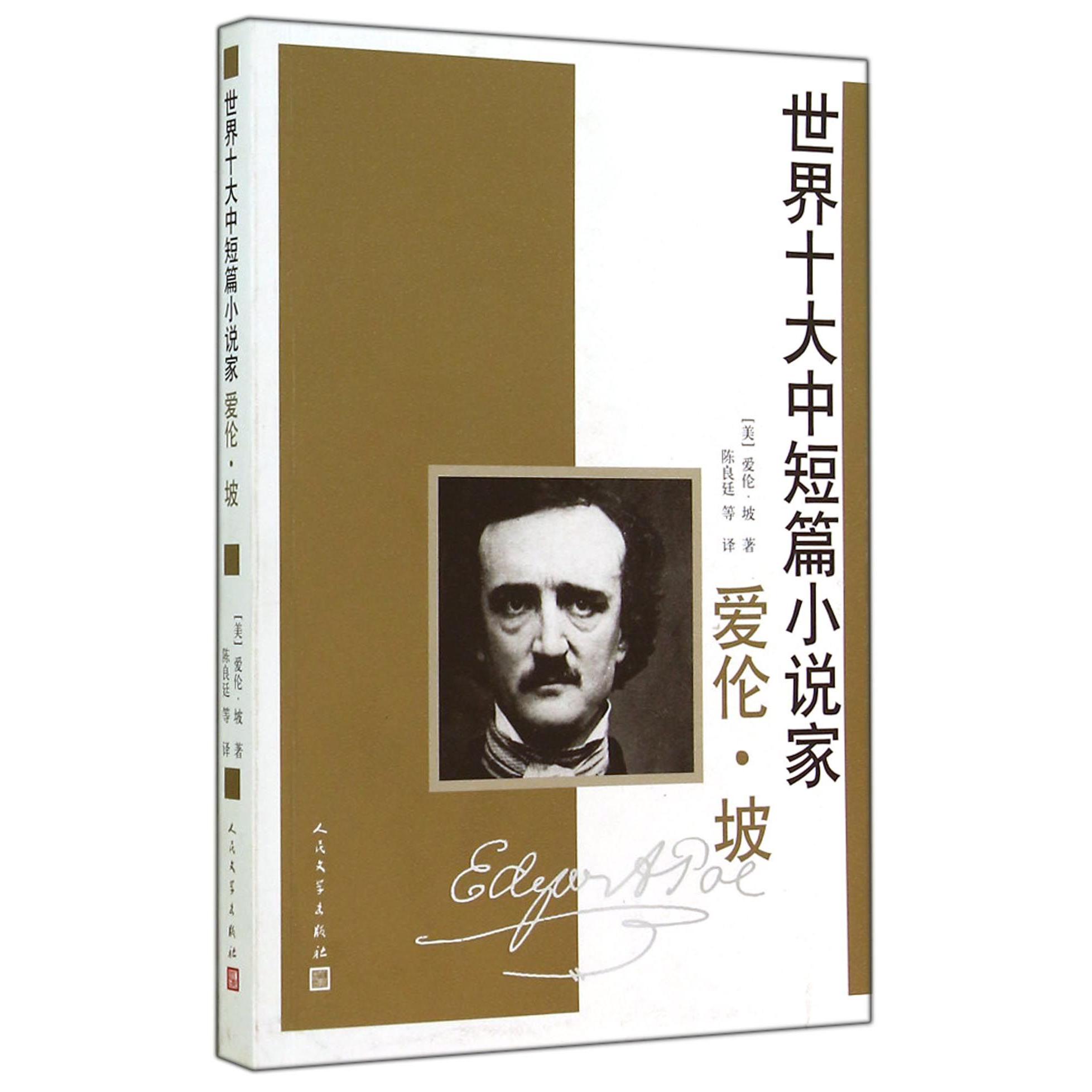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29.00
折扣价: 19.08
折扣购买: 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爱伦·坡)
ISBN: 97870201038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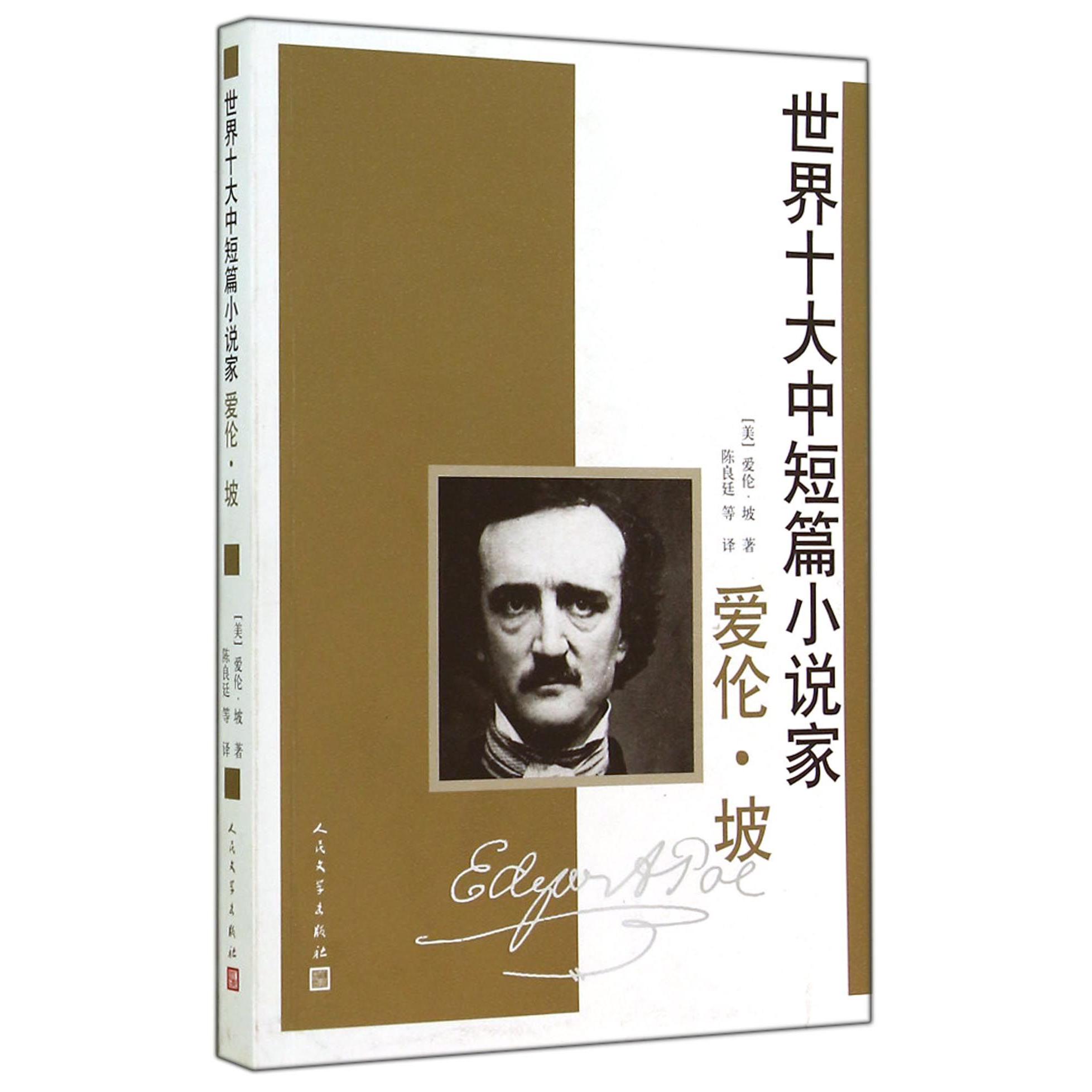
爱伦·坡(Allan Poe,1809—1849),19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出生于波士顿一个流浪艺人家庭,3岁时母亲去世,由富商约翰·爱伦收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后因酗酒而退学。21岁时,进入西点军校深造,又因玩忽职守被开除。之后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写过诗歌、小说、文学批评,后发现哥特式的恐怖小说很畅销,而转向写恐怖小说,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835年,爱伦·坡与表妹结婚,十余年后妻子因病去世,他便从此终日借酒浇愁。1849年在巴尔的孽的一次彻底的痛醉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爱伦·坡一生刨怍了六七十篇短篇小说,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他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先声,对西方现代派诗歌和现代派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因此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和“恐怖小说之父”。
我对祖国和家庭没什么可谈的。我受尽虐待,被 迫离国,经过多年漂泊,跟家庭也疏远了。祖传家产 供我受了不比寻常的教育,再加生性爱好思索,我才 能把早年辛勤钻研、积记于胸的学问分门别类。德国 伦理学家的学说尤其使我感到莫大的乐趣;这并不是 因为我对他们的雄辩狂有什么盲目崇拜,而是因为我 有认真思索的习惯,才能毫不费事地识破他们的虚伪 。人家经常责备我天赋贫乏;缺乏幻想力成了我的一 个罪名,我见解里的怀疑论调一向害得我声名狼藉。 世人向来认为无论什么事的发生都跟形而下学的原理 有关,甚至对根本毫无这种关系的事,也是这么看。 说真的,恐怕我非常爱好形而下学,思想上才受到这 时代中极其普遍的错误影响。总而言之,人人都跟我 一样,容易迷信鬼火,根本脱离事实。我想,最好还 是先来这么一番开场白,免得下文要说的这个荒诞故 事,给人当作胡思乱想的鬼话,不当作一个从来不信 空想也不会空想的人的实际经历。 我到国外旅行了多年,一八××年,在物产丰富 、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巴达维亚港搭了船,航行到巽他 群岛的海面上去。在船上我是旅客身分,心里可没什 么打算,只是感到鬼怪附身似的心惊肉跳、坐立不安 才出了门。 我们乘的是条四百吨左右的漂亮帆船,船身箍着 铜壳,是在孟买造的,用的是马拉巴麻栗木。船上装 着拉克代夫群岛出产的皮棉和油类。还载着椰皮纤维 、赤砂糖、酥油、椰子和三两箱鸦片。货物装载马虎 ,害得船身摇晃不定。 我们乘着一阵微风扬帆出海,好多天来一直沿着 爪哇岛东海岸行驶,只是偶尔碰到几条小双桅船,从 我们目的地——巽他群岛海面上开来,此外根本没什 么新鲜事可以排遣旅途寂寞。 一天傍晚,我靠在船尾栏杆上面,看到西北角孤 零零的有朵非常特别的云彩。我们离开了巴达维亚, 还是头一回看到云彩,而且颜色那么鲜艳,才这么引 人注意。我一直全神贯注地望着,等待太阳落海,这 朵云彩顿时向东西两边扩展,在天际形成窄窄一道烟 霞,看上去宛若一长列浅滩。随即一下子,暗红的月 亮和异样的海景攫住我的注意力。海景瞬息万变,海 水仿佛异乎寻常地透明。虽然海底看得清清楚楚,不 料抛下测深锤,才知船在十五英寻深的海里。这时天 气热得难熬,弥漫着袅袅暑气,正跟火烫的铁块上冒 出的热气一般。随着夜色降临,风丝渐渐消失了,四 下里风平浪静,简直想象不出有多静。船尾上点着支 蜡烛,一点都看不出火焰跳动,指头捻着根发丝,也 看不出飘拂。船长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凶兆,我们这条 船刚漂往岸边,他竟下令卷起风帆,抛下铁锚。也没 派人值班守夜;船上水手多半是马来人,不慌不忙地 在甲板上摊手摊脚睡了。我走进舱里——心头不无某 种大祸临头的预感。说真的,眼见这一切情况,我实 在担心来阵热风暴。我把心事讲给船长听;谁知他竞 理都不理,连句回话都不给就走了。可是,我坐立不 安,睡都睡不着,大约到了半夜时分,就走到舱外。 刚踩上后甲板楼梯上面一级,就听得嗡嗡一阵巨响, 恰如水车飞快转动的声音,我不由吓了一跳,还没弄 清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船身震动不已。一眨眼工夫, 滔滔白浪差点把船掀翻,一浪接一浪地冲洗着整条船 ,全船甲板从头到尾都给淹没了。 这阵来势汹涌的疾风,多半倒成了这条船的救星 。虽然船身完全进了水,可是由于桅杆折断,落在船 外,转眼间,船身好生费力地从海里慢慢浮起,在暴 风无比威力的肆虐下,摇晃了一阵,终于摆平了。 我凭什么奇迹才没送命,自己也说不上。我给海 水打昏过去,等到苏醒过来,才见身子卡在船尾柱和 舵当中。费尽力气,才站起身,头昏眼花地朝四下看 看,顿时想起我们的船原来在滚滚巨浪中,给卷进了 排山倒海、汹涌澎湃的大洋的漩涡里,这漩涡真可怕 极了,简直想象不出有多可怕。过了片刻,耳边听得 一个瑞典老头的声音,他是在我们离港时跟着一起上 船的。我用尽力气,大声喊他,他马上踉踉跄跄地走 到船尾来了。不久才知道只有我们两人逃出了这场浩 劫。船上其他的人全给扫到海里去了;船长和大副二 副准在睡梦中惨遭没顶,因为船舱里全都积满了水。 没人帮忙,可休想保住船,何况开头我们时时刻刻都 以为船要沉下去,竟吓得浑身瘫痪。不消说,台风乍 起时锚索就跟线一样给刮断了,不然早就一下子翻了 船。我们这条船飞也似的在海浪前掠过,海水迎面冲 洗着甲板,竟没把我们卷走。船尾骨架打得粉碎,几 乎到处都受到巨大损伤;幸好抽水机没出毛病,压舱 物也没抛掉多少,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疾风主力已经 过去,虽然明知道这阵狂风没什么危险,但还是垂头 丧气地盼望风暴完全停止;我们确信,像这样破破烂 烂的一条船,势必会葬身在接踵而来的滔天巨浪里。 不过好在这层有充分根据的忧虑看来还根本不会马上 成为事实。我们花了不少周折,才从水手舱里弄来一 点点赤砂糖,整整五天五夜,就光靠吃糖充饥。在这 五天里,我们这条破船乘着势如破竹、一阵接着一阵 的疾风,速度惊人地飞驶向前,这阵疾风虽不及头一 阵热风暴那股冲劲猛烈,但我从没碰见这么厉害的暴 风。开头四天,航向并没什么变动,一直是东南偏南 ,准是笔直冲向新荷兰的海岸了。等到第五天,风向 渐渐改变,更加偏北了,天气也冷到极点。太阳蒙着 昏黄的光出来了,爬上水平线,只高出几分——发出 有气无力的亮光。天上不见一朵云彩,可是风力有增 无减,间歇不定、变化无常地怒号。约莫估计快到晌 午时分,我们又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太阳的外表上了 。太阳发不出光,所谓真正的光,只有一点昏沉红晕 ,可没有辐射热,仿佛所有的光都化掉了。还没落到 滚滚大海里,太阳当中的火团就突然熄灭,恰似仓促 间给什么神力吹灭了。单单剩下一轮朦胧银环,刹那 间扎进深不可测的大洋里。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