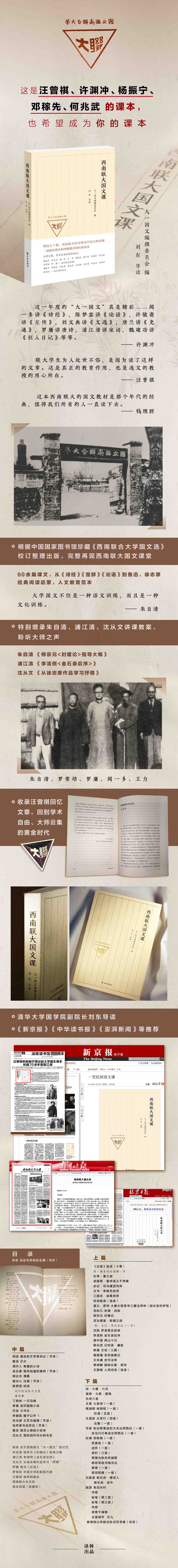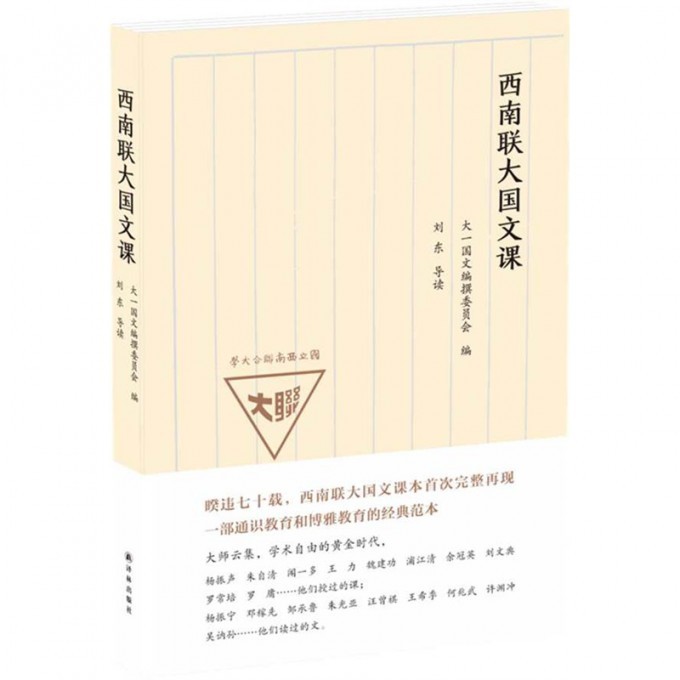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9.76
折扣购买: 西南联大国文课
ISBN: 9787544757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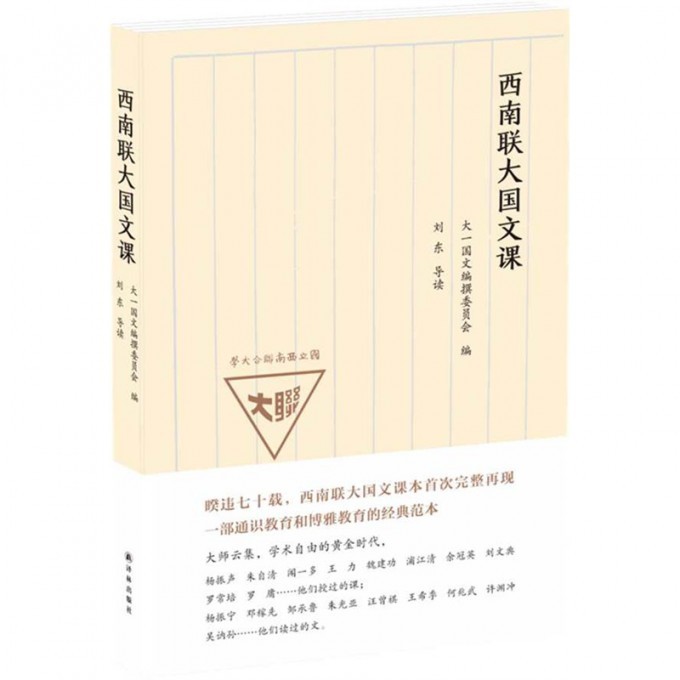
导读作者:刘东,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十七种;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 西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 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 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 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 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 。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 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 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 。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自由、开 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 系似乎比别的系*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 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 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 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 ,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 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 之,中文系的学生*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 精神*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 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 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 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突出的是《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 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 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 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 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 ,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 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 》,就有点特别。*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 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 ”。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后一 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 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 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 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 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 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 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 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 ,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 ,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 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 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 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 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 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 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 ”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 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 “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 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 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 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 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 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 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人。他讲《古代神话 与传说》**“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 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 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 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 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吸引人。还有一堂“ 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 ,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 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 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 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 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 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 )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 !”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 :“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 ,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 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 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 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 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 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啰 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 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 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 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 。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 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 ,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 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 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 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 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 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 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 ”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 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 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 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 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 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 ……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 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 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 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 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 ,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 **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 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 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 西北角,墙外是坟地,**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 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 而且可抽烟。有**,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 。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 ,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 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 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P333-337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
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王力、魏建功、浦江清、余冠英、刘文典、罗常培、罗庸……他们授过的课;
杨振宁、黄昆、邓稼先、邹承鲁、朱光亚、汪曾祺、王希季、何兆武、许渊冲、吴讷孙……他们读过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