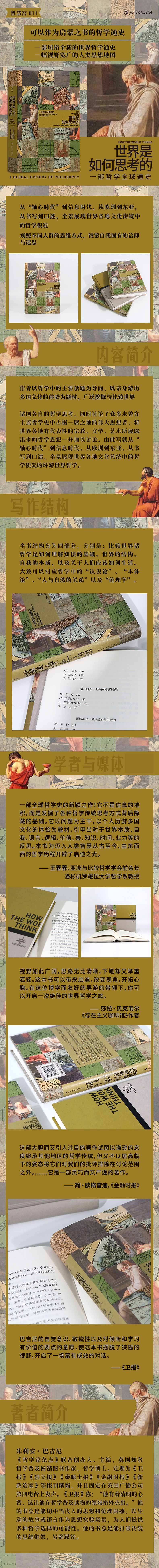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原售价: 70.00
折扣价: 44.80
折扣购买: 世界是如何思考的 一部哲学全球通史
ISBN: 9787513937399

朱利安·巴吉尼,《哲学家杂志》联合创办人、主编,英国知名哲学普及畅销图书作家,哲学博士。定期为《卫报》《独立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新政治家》等报刊撰稿,并且固定在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上发声。《卫报》称:“他有着清明的心智,这让他在哲学普及读物的领域格外杰出。”他的书总是能切中当代人的思想和伦理困惑,以生动的故事或语言作为思想实验场景,为人们提供多种哲学选择的可能性。他的书总是能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另辟蹊径。
在日本神户市中心的生田(Ikuta)神社,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在拥挤的游客群里表演简单的神道教仪式,自从神道教于公元3世纪建立以来,一直是这里常见的景象。这些年轻人也许并不记得在经过标志着神域和俗世边界的鸟居时要鞠躬,但每个人都会驻足在水榭的净手池(手水舎)边表演“禊”(洗礼仪式),以净化身体和灵魂。他们用右手舀起一瓢水,先在左手上倒一些,然后把瓢交到左手上,再将水倒到右手上。他们并不用嘴碰勺子,而是捧起水来漱口,最后把剩下的水倒掉。这样一来,他们就洁净了,准备好去迎接住在神龛里的女神(kami,或spirit)稚日女尊。 在圣坛上,他们先向女神献上硬币,然后摇铃向她致意。仪式一般是鞠躬两次,拍手两次,以表达与神相遇的喜悦和对神的尊敬,最后鞠躬一次并祈祷。在第二次拍手之后,双手合十停留片刻,默默地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最后再一鞠躬。 我有时候很怀疑这些信徒中到底有多少人内心真正信仰他们表面上敬拜的神。但这也许是个错误的问题。作为一个在基督教文化中长大的人,我认为宗教信仰主要就是赞同若干条教义的问题。在小时候经常去的罗马天主教堂里,我们会在仪式上反复念诵《尼西亚信经》,以“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万物,及一切有形无形之万物之主”开始,以“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门”作为结束。然而,在神道教寺庙里,仪式全程都是静默无声的,甚至表达内心的感激(一种情感而非思想)也是一样的沉默。由于去神社的游客不要求声张自己对信仰的坚持,如果你去问他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反而是不得要领的。 日本宗教中,教义相对而言没那么重要,这个事实有助于解释日本宗教的融合性质。在日本,“生时为神道教,以儒家方式生活,死时转向佛教”是很常见的情况。例如,当我参观京都的清水寺时,旁边的神社“九树金家”与寺庙无缝地衔接在一起,以至于我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意识到它们并不是同一个建筑体。而日本游客在这两处都会举行宗教仪式。 在日本,教义并不像在西方基督教那样重要,部分原因是日本人相信最纯粹的关于现实的知识来自直接经验,所以最本质的真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它们是无法言说的,即字面意义上的不可说。这在东亚是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在中国道家的例子中最为明显。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根深蒂固,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据说最早的道家大师是写了道家基本原典之一《道德经》的老子。老子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已难以考证,但对于大多数道家信徒来说,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道家的另一部核心典籍是《庄子》,这本书以作者的名字命名,可能写于几个世纪之后。每一个哲学流派都有其“道”,这个词最简单的含义是“道路”。道家的道与儒家的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自然性和一种自发性,而不是规则和仪式。 在中国,道家思想家常指出,语言无法捕捉道的真正含义,这有些难以理解,而且显得有些神秘。《道德经》以一种独具特色的自相矛盾的方式来表达:“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书中还表达了“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由于道的不可言传,所以行胜于思。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公元前3世纪的道家经典《吕氏春秋》中对道的描述是:“强为之名,谓之太一。”《道德经》里有一句非常相似的表述:“强为之名,谓大。”这两个文本都谈到了“强”,或“被迫”使用语言,暗含了最好就根本不用语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如果说道家一些自相矛盾的话听起来有点像是笑话,这倒不是巧合。道家崇尚幽默,而且经常显得很风趣。乔尔·库珀曼说,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一个人永远不会拥有终极真理,或者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最终‘看法’,或曰对世界的最终适应——庄子的哲学训练似乎旨在鼓励人们嘲笑自己的能力。这一哲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达到一种舒适的‘自满’。” 《庄子》中有一段精彩的内容,以其典型的嘲讽的方式阐述了语言的局限性: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道家对语言的不信任还导致了它对古典哲学文本的怀疑,这些文本在《庄子》中被视为“糟粕”而遭到轻视。在一段故事里,一个名叫轮扁的车匠以他的技艺为例向他的主人解释了这一点: 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 轮扁的技艺既不可通过言语,也不能仅仅通过展示来传授,事实上,每一代人都必须在细致的指导下重新学习这门手艺。同样,道家认为哲学智慧也无法简单地通过文本传递。伟大的圣人终生参悟的智慧,随着他们的逝去一同消失了。“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他的故事也强调了实践重于理论:与学者大师的理论相比,轮扁在他的技艺特长上算是另辟蹊径。 比起中国其他主流本土传统,道家更为强调“不可言传”,儒学中也经常提到语言的局限性。比如,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然而,孔子只建议在终极实在的问题上保持沉默,他认为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也能过好此生。在很多重要问题上,他强调名正言顺的必要性。在一篇著名的论述中,他说,如果要管理一个国家,首要任务是先纠正名分,使它们回归其真正的含义和用途。一个国君应当有作为君王的本分,一个儿子要有为人子的样子,等等。人们应该去做其分内之事。虽然他只提到过一次,但“正名”已经成为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在日本,本土神道教形成系统哲学的传统相对微弱,部分原因就在于其难以言传的特性。18世纪神道教诗人马贺茂真渊(Kamo No Mabuchi)写道:“欲以原则明定事物,乃是视之为死物。”这就是我们需要诗歌的原因:它带给我们的是无法用语言去精准捕捉的感觉。因此,神道学者富士谷御杖(Fujitani Mitsue)写道:“当我不能使用直接语言或隐喻来表达心中所想,也不能克制自己表达的渴望时,我就必须写一首诗。” 在日本禅宗里,语言的局限性体现得淋漓尽致。禅宗最初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中国,日本禅宗则是12世纪在日本本土兴起的禅宗派别。禅宗的创始神话是佛陀静静地拿起一朵花,在手中转动,并眨了眨眼。这是唯一一种不以某种话语开始的主流宗教或哲学传统。总的来说,佛教因其文本中常有建议人们无视佛陀的教导而闻名,其中最直白的一句是:“逢佛杀佛。”至道无难(Shidō Bunan)的描述方式则没那么暴力:“佛陀的教诲是很大的错误。学习它们更是多么大的错误啊。”佛陀的教导是错的,因为没有任何言语可以抓住真理,即便是佛陀的话语。所以避免犯错的最好方式就是不使用言语。公元2—3世纪的佛教哲学家龙树菩萨写道:“假如我提出任何主张,那么我就会犯逻辑错误。但是如果我不提出任何主张,我就不会犯错。”言语文字就像“指向月亮的手指”。“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 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最好的情况是,语言只是帮助我们超越语言的工具,到达一个无需语言阻隔在我与世界之间的状态,按照无难所说的方式:“直接看,直接听。” 在日本禅宗里,语言和理性都会束缚智慧。铃木写道:“语言是智慧的产物,而智慧是我们的思维对现实的补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现实的减法。”语言增加了现实,因为它在现实之上创造了额外的一层,而这反过来又通过模糊现实的丰满来减少现实。西田几多郎说:“意义和判断是原始经验的抽象部分,和实际经验相比,它们在内容上很贫乏。”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禅宗公案,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语言的不足,表面上结构完美的句子却可能毫无意义,比如“风是什么颜色的”或者“当你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你能做什么”。铃木说道:“那些认为禅宗愚蠢的人,仍然被语言的魔力所迷惑。 尽管禅宗倡导不立文字,禅师们还是留下了许多文本。许多人认为这种矛盾是一种不完美的妥协。梦窗疏石(Musō Soseki)说:“如果什么都没有被记录下来,那么引导人们的方法会失传。所以禅宗不得已要发表先人的记录,尽管这非他们所愿。”柏拉图决定写他的苏格拉底对话录,背后可能也有类似的理由。尽管苏格拉底本人拒绝着墨于羊皮纸卷,认为僵化的文字永远无法取代哲学化的实践。然而,当禅师们认真写作时,他们会非常谨慎地选择措辞。嘉指信雄(Kazashi Nobuo)认为,这既显示出对语言的尊重,也表现了怀疑。他告诉我一句源自中国的谚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伟大的禅宗哲学家道元禅师(Dōgen)在写作时,就试图以语言来建立这种心与心之间的连接。 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人对词语的尊重,他们的诗人和思想家才会如此谨慎地使用语言。与其说这是对语言的不信任,不如说是一种对语言的敬畏。前田直子(Maeda Naoki),一位密教真言宗的初级司铎,最近说过:“发表言论是一块银牌。但沉默可以得到金牌。”但是,“真言”的真正含义是“真实的语言”,因此,在真言宗,以沉默来表达对语言的漠视是没有意义的。 日本人对语言的深刻尊重体现在神道教对言灵的信仰中,言灵是言语和灵魂的合成词:言语的灵魂。在这种信仰中存在一些对听起来像是负面的、不祥的词汇的迷信。比如说“四”,可以读作“yon”(よん)或“shi”(し),shi听起来很像“死”,因此数字4被认为不吉利。在东亚,处处都能发现言灵的幽魂,词语的发音充满了力量,同音字会被认为是吉利的或者不吉利的。在汉语和韩语中,数字4听起来也像一些表示死亡的词,而且经常被避免使用,比如韩国的酒店经常没有带4的房间号。在中国,sān(三)这个字是吉利的,因为听起来像生。 当然,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佛教所反对的婆罗门传统中也可以找到不可言喻之处。在《奥义书》中,梵据说是不可思议的: 当你认为它不可想象时,你才有可能想象到它。 而当你想象到它时,你又深知它是不可想象的。 当你认为它不可感知时,你才有可能感知到它。 而当你感知到它时,你又深知它是不可感知的。 终极真理不仅超越了语言,也超越了任何理性的理解。《奥义书》警告人们“不要问得太多,以免身首异处。事实上,你们对神的质疑太多了,不能再追问下去了”。至高的自我是“无法理解的……无法被推理的,不可思议的。 梵的不可言说性在一个短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奥义书》和《至尊瑜伽》都将梵描述为“不是这个,不是那个”(neti neti)。另一个《奥义书》的段落说梵是“语言终止之处”。查克拉瓦蒂·拉姆-普拉萨德(Chakravarthi Ram-Prasad)说,这一点在不二论者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他们主张“语言不能触及梵,梵是妙不可言的”。 对语言局限性的深刻理解,拒绝将世界本身与人类的概念相混淆,这是整个亚洲哲学经久不衰的优点。根据我的经验,西方往往把所有知识的局限都看作一种冒犯,一种需要跨越的边界。“未知”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勇敢地去以前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但在另一些地方,人们不仅接受了人类的局限性,而且还颂扬之。在印度哲学大会上,杜万·钱德尔(Duvan Chandel)引用了现代印度最伟大的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话:“真理热爱它的极限,因为它在那里遇见了美。”这种观点在印度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 对“不可言说”的信奉也带出了一个的问题:在看到世界与我们对世界的语言概念描述之差异后,我们是否就能看到世界的真实面貌?许多东方传统的信奉者认为我们可以。但我对此存疑。即使我们能够感知未被概念框住的现实,它仍然会被我们的感知和认知器官框住。我们可以摘掉语言的有色眼镜,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仍有一些要透过人性的镜头。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完全消除我们人类特有的经验方式,并且看到现实本身或与之合一,这种观点是没道理的。没有一种观点会产生于无名之地,或是乌有之乡:每一个观点都必须来自某个地方。完全逃离人类的视角意味着我们将不再是人类,从而不再存在,这不仅是我们所知的,也是我们所能知道的。 一部全球哲学史的新颖之作!它不是信息的堆积,而是发掘了各种哲学传统思考方式背后隐藏的基础。它以问题为主干,以个人历游多国文化的体验为题材,引申出对于世界本质、自我、语言、逻辑、价值、善、知识、时间、业力等的反思。本书为迈入人类智慧从古至今、由东而西的哲学历程开辟了启迪之光。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学,接着说! ——王蓉蓉,亚洲与比较哲学学会前会长,洛杉矶罗耀拉大学哲学系教授 视野如此广阔,思路无比清晰,下笔却又举重若轻。这本书可以带来启迪,改变视角,开拓心胸。在这位博学而友好的导游的带领下,你可以开启一次绝佳的世界哲学之旅。 ——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