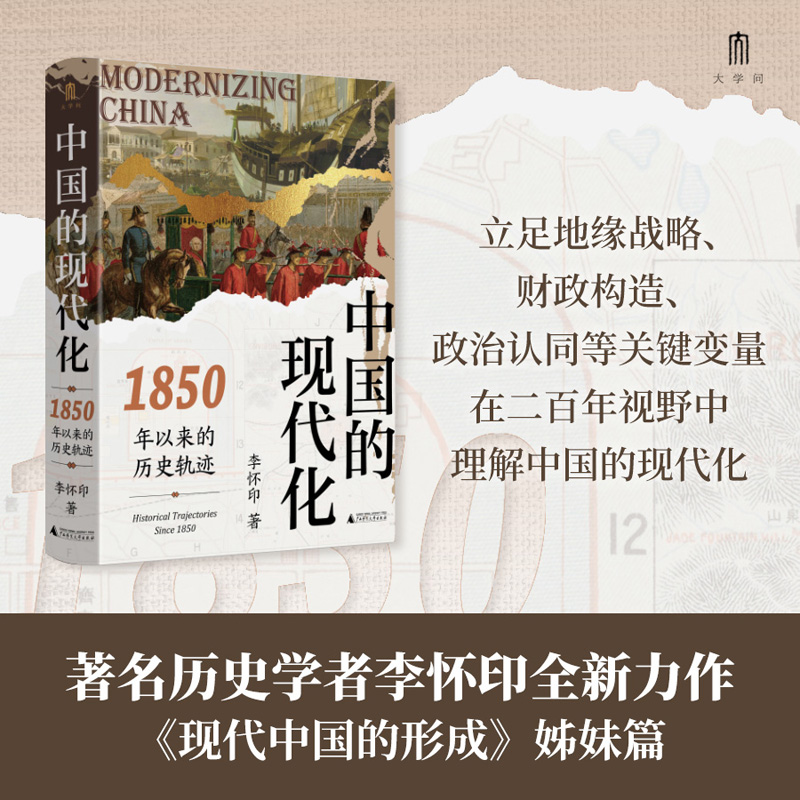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89.00
折扣价: 50.80
折扣购买: 中国的现代化
ISBN: 9787559874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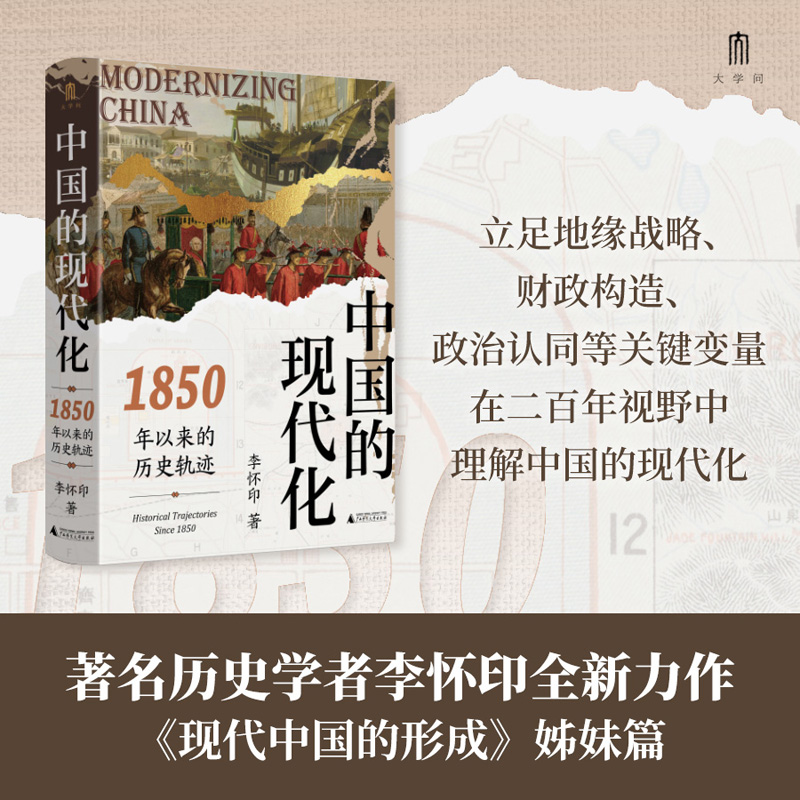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著有中英文版《华北村治》《乡村中国纪事》《重构近代中国》《现代中国的形成》,以及英文近著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现代化”视野下的世界地图 这里,首先要确定究竟什么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 所谓“现代化”,可以分两层意义来谈。一是人们日常话语和大众传媒中常说的“现代化”。按照一般的理解,现代化就是让相关的事物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或者说使之达到“现代”的水准。因此,“现代化”这个词几乎可以用到各行各业。过去讲“四个现代化”,也就是要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领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但现代化还有另一层意义。作为一个学术用语,它不是指某个领域、某一层面或某个时期的现代化,而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空间维度上囊括各领域的总体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在时间维度上涵盖不同阶段的整个的现代化过程。本书所要探讨的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宏观历史视角下的全面意义上的现代化。 这里,我把现代化初步定义为一个社会从依靠体力和手工劳动并且以地方内生技能为基础的传统经济,过渡到以非体力的能源结构为基础,以机器生产及信息处理为主的现代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全面变革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带来人口就业结构的转型,也就是从以传统的农耕、渔猎或采集为主的就业形态,过渡到以制造和服务业为主,进而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就是从原先主要居住于乡村自然群落,到逐步向城镇集中,最终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带来了更好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而且提高了全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延长了平均寿命,重塑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使原来乡村社会中以家族和村社的整体利益及其精神诉求为中心的价值体系,逐步过渡到都市社会中以个人和核心家庭为中心、以个人成就和物质报酬为主要追求的价值观。最后,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变革,还不可避免地驱动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发生转型,使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策制定过程更能有效地体现日益多样的社会群体的不同要求,将越来越多的人群吸纳到政府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就是走向政治的民主化。一句话,现代化是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等一系列侧面所构成的全社会的转型过程。 对现代化做这样一个面面俱到的界定,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屡见不鲜(详见本书第一章)。必须承认,这样的界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景,或者至多是一种建立在有限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概括、推导和预设。这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操作性,最终还是要回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近80年的历史表明,现代化是可能的,但绝不是普遍可以实现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这一转型过程的国家和地区,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现代化的“先行者”(firstcomers),即较早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例如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以及欧洲人在海外的移民和殖民所形成的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经过数百年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50和60年代,基本完成了全社会的现代化。二是现代化的“后来者”(latecomers),即前面所说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欧六国,其人口规模相对有限。 还必须看到,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没有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基础产业的支撑,也有可能退出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发达国家跌落到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以苏联为例,其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防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达到顶峰,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为发达国家和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紧随其后,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以及东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乃至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能力和人均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只能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中上水平。 再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这里首先去掉中东地区的几个石油输出国。它们虽然人均收入很高,医疗水平和人均寿命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社会整合、政治参与及文化世俗化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剩下的发展中国家,以2021年的数据做参照,又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低收入(low income)国家,人均GDP在800美元以下,一共14个,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属于典型的不发达(underdeveloped)国家。 第二类是介于不发达国家与发达(developed)国家之间的所谓发展中(developing)国家,其中又可细分为:(1)人均GDP在800至2,600美元之间的低中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国家,共40个;(2)2,600至6,0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middle income)国家,计41个;(3)6,000至13,000美元之间的上中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国家,有38个。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工业化,摆脱了不发达状态,但是关键产业部门大多受到西方跨国公司的控制,整个国民经济难以再上一个台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以截至2023年6月、更新至2021年的最新数据为准。 第三类是进入向发达国家过渡地带的国家(人均GDP在13,000美元至20,000美元之间),一共16个,其中人口在500万以上的,仅有上面图表中的4个国家。广义上也可以把它们纳入上中收入国家的范围。 为了聚焦于中等规模以上(人口超过3,000万)的发展中国家,下面的讨论暂且把诸多人口在3,000万以下的小国排除在外。在这些中等规模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中,我们进一步聚焦其中的中等收入国家。所谓中等收入,在不同年份有不同界定。以1990年为例,凡是人均GDP达到900美元的,即可视为中等收入国家。在人口超过3,000万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18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为了比较,这里把印度也考虑进来,尽管该国的人均GDP在1990年只有532美元。除了中国,所有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最近31年间(1990—2021),人均GDP一直在13,000美元以下的水平徘徊,经济增长的幅度和势头都非常有限。具体而言,这些国家可进一步分成三个类型。 第一种类型,在1990年至2021年的31年间,人均GDP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长,基本上停留在原有水平,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伊拉克、伊朗、南非、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阿根廷的人均GDP在2011年一度冲高到14,000美元以上,大有向发达国家转型的势头,但是此后10多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缓慢回落,到2021年仅为10,636美元。 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头20年(1990—2010),经济有所增长,但幅度很小;后10年(2011—2021)则停滞不前。 以上这两类国家的经济处境,常被学界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脱离了低收入国家的不发达状态;但一旦登上这个台阶,整个经济便长期停留在既有的水平上,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很难再上一个台阶,进入发达社会。 最后只剩两个国家,属于第三种类型,它们在过去30年间的经济增长幅度一直比较稳健。其中一个是印度,人均GDP从1990年的532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2,256美元,年均增长4.8%,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但距离发达国家人均20,000美元的最低标准尚遥不可及。另一个是中国,从1990年的905美元,跃升到2021年的12,556美元,平均年增8.8%,上升速度最快、趋势最稳,从起初在中等人口规模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垫底的地位,跃居到这些国家的第一名。只要中国在今后5—10年内能够维持5%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在2030年前后,最晚至2035年,达到人均20,000美元以上,从而跨越“中希大峡谷”,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便有很大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加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而更多的国家却依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挣扎,甚至根本还没有“化”起来? 如前所述,人均GDP从13,000到20,000美元是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鸿沟,进入这一区间的国家寥寥无几,能够成功跨越的少之又少。一个国家只有迈过人均20,000美元的最低门槛之后,才勉强可算“高收入”(high income)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上,也已经达到“成熟”程度(详见下文讨论),那么,这些高收入国家便可被视为现代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选取怎样的发展路径和增长战略,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全社会的现代化?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关注和纠结的话题。 ——节选自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自1850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不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而是中华民族主动上下求索、积极变革,最终有所蜕变的抗争史。作为《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的姊妹篇,本书延续了之前的理论框架,即以地缘、财政、认同多线条为一体,爬梳了中国现代化曲折复杂的历史轨迹,阐释其政治经济的多重逻辑。《现代中国的形成》中的未竟之语,作者都写在了本书。 此外,本书不忽视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不回避一些必须直面的问题,坚持正面的从容剖析,让史实说话,对改革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误区等问题,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历史分析,进一步突出中国的“大国竞争优势”。 同时,根据作者的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1850年代,始自国人有意识地探寻最适合自身国情的生存发展道路。从那时起,几乎每过半个世纪,中国便会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上一个新台阶。19世纪后半期,凭借大国的规模优势和古老文明的韧性,晚清政权避免了四分五裂的厄运。20世纪前半期,中国成功地从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转型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并且在随后的半世纪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21世纪以来,现代化进入全新阶段,即在大国竞争的条件下,再花半世纪的时间,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作者大胆预测,中国有望到2035年前后,稳步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最终将于本世纪中叶,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政治文明上,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前列,完成历时两百年的现代化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