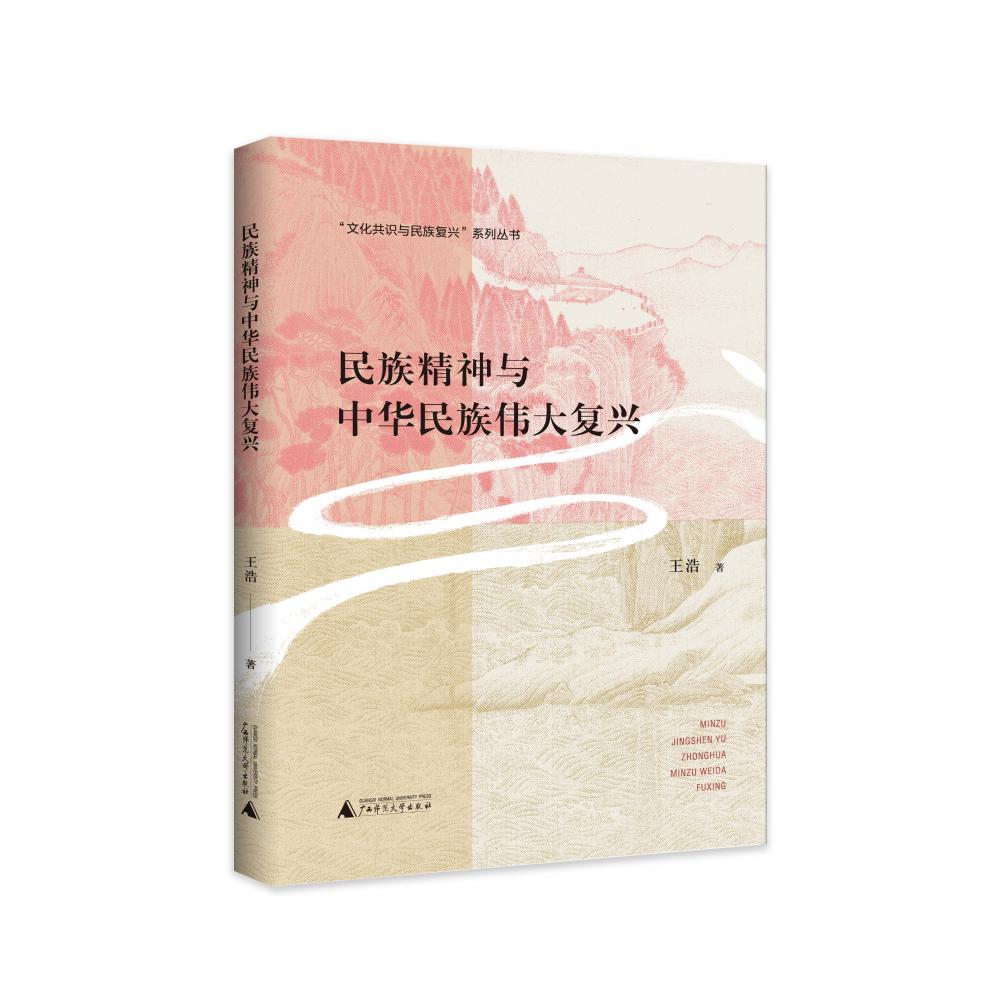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5.40
折扣购买: “文化共识与民族复兴”系列丛书 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ISBN: 9787559866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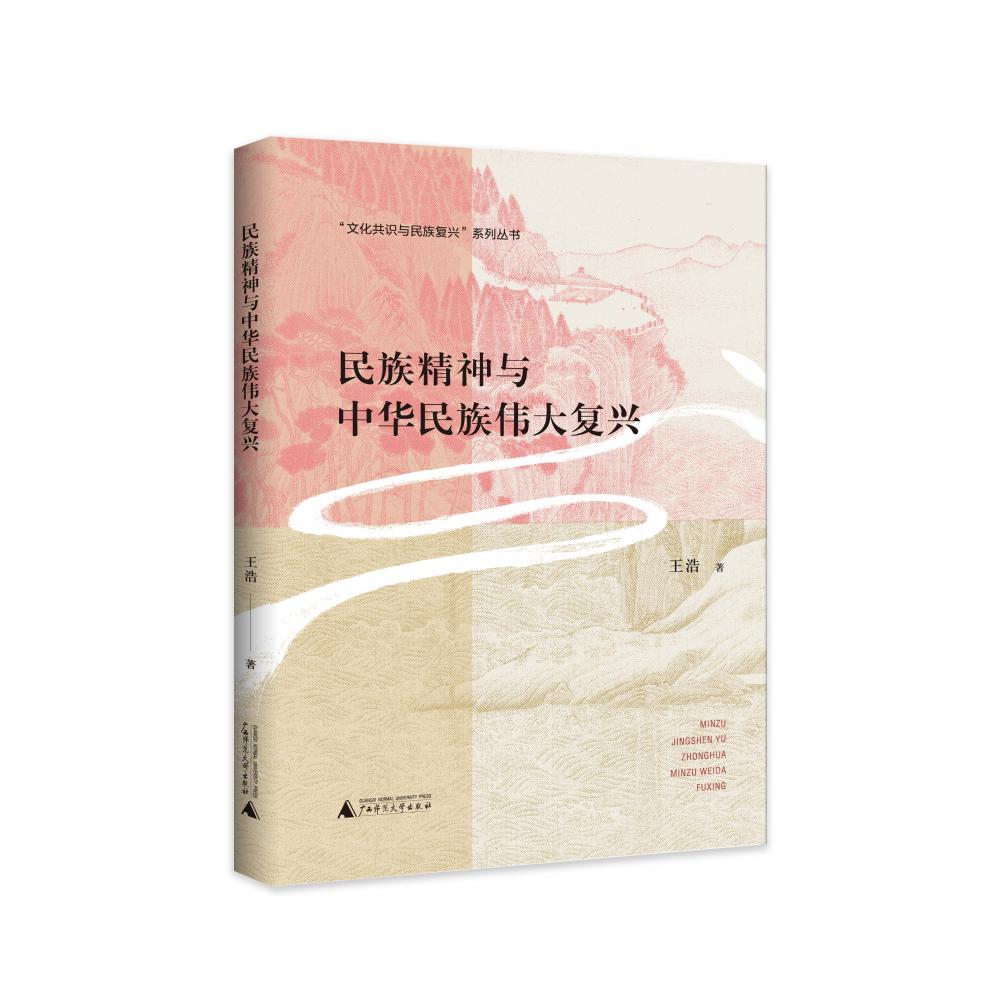
王浩,男,1975年生人,陕西周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现任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文化交流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战线基本理论与实践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著、合著理论著作8部,散文集1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第一章 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培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乃在于深深植根于民族基因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1)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何谓民族精神? 每个民族都具有一定内涵、品格和特质的精神世界,这些品格和特质,构成了该民族的民族精神。作为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民族精神既是个人精神的融合与升华,也是个人精神的民族化与国家化。 (一)“民族精神”文本概念的缘起 “民族精神”是随着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和民族主义兴起而提出的范畴,是由西方学者最早提出的一个近现代概念。“民族精神”的概念,产生于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由于法兰西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德意志知识分子感到民族认同与民族自尊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挑战。他们提出“民族精神”的概念,以期从德意志的历史、民间艺术和文学等方面,探寻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源泉,从而捍卫本民族的固有文化,表明其民族的优越性。孟德斯鸠(18世纪法国哲学家)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2)此处提到的“一般的精神”,指涉的就是“一个民族的一般精神”,尽管民族精神的内涵尚不明确,但其思想已然直指民族精神的内核。 (1)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20/c_1122566452.htm, 2018年3月20日。 (2)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5页。 稍后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思想和学术意义上真正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赫尔德对民族精神的最早表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精神和天赋。之后,法学家萨维尼将“民族的共同精神和天赋”用德语表述为“Volksgeist”,即“民族精神”。具体来讲,赫尔德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演进中的核心要素,生活在一个特殊团体中的人,由于他们的地理条件、种族、历史传统相同,彼此享有共同的语言、制度、文学艺术和教育方式,由此形成了代代相传的集体精神,这种集体精神就是民族精神。(1)赫尔德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发展的权利,在人类大花园中,所有的花卉都能和谐生长,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激励,“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2)。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的,都有它“特殊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精神的特性,即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的宗教、政体、风俗、伦理,甚至科学、艺术以及机械技术,都带有民族精神的印记。(3)由此可见,这种民族印记使得同一民族中的每个人的交往互通成为可能,由于使用同样的民族语言、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当人们在民族危亡关头时,更容易形成休戚与共的一体感,继而通过民族意识的共通感而凝聚为一体。这种超越个人的民族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所在,也是该民族集体人格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反映了人们生命活动的性质和向度,也使人们因为共有的历史记忆,而产生共同的情感寄托。 (1) 参见王希恩《关于民族精神的几点分析》,《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2)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152页。 (3) 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民族精神与该民族的整个历史相伴随,与该民族共存亡。民族精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从哲学的视角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是推动民族精神变化的深层原因;从民族的视角看,每个民族是体现该民族精神的主体;从历史的视角看,民族精神要借助固有精神资源与时代精神、未来精神的碰撞,经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选择,才能发生现实的作用。 (二)国人对于“民族精神”的早期关注 中华民族精神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古国的精神家园,因其强烈的历史传承性和民族包容性,而形成了厚重的心理积淀。尽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一直存在着民族精神这样一种自在的情感和心理样态,但在20世纪以前,人们更多地使用“国性”“国魂”“中国魂”等词语,以指涉中国的“民族精神”,而绝少使用“民族精神”一词。 “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出现,是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以及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压力下,从梁启超的类似民族意识的观念,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念,两者逐渐结合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和自我认同,而形成的有关“民族精神”的思考。在传统学术的经学和史学研究中,未见有专门论述民族精神的论者,民族精神往往散见于天人关系、家国观念、人际伦理等具体精神内容。如《尚书·泰誓上》的“惟人万物之灵”,《中庸》的“唯天下至诚……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论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各路史家的“殷鉴不远”“鉴往而知未来”等思想,都折射出民族精神的光芒。 国人关注“民族精神”的最早文字,出现于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一文。此后,梁启超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国民之元气”“国民之特性”“国民之精神”“中国武士道”“民族的活精神”“根本之精神”“独立之精神”等诸多概念,来指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实际上,梁启超所言的“国民之精神”“国性”,指的是一个民族在漫长而共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逐渐形成和积淀的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性,亦即民族精神。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积,国乃成。”(1)梁启超该文中谈及的“国民独具之特质”,已经非常接近民族精神的要义,透过这些“国民独具之特质”,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意志品质、审美观念和风俗习惯,可以清晰地折射出该民族的精神。 1904年,留日学生刊物《江苏》发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民族精神论》,作者在文中谈道:“民族之倏而盛倏而衰,回环反复兴废靡常者,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2)这是国人首次将“民族”“精神”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由此开创了国人研究民族精神的先河。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2) 转引自郑渠、史革新主编《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三)对于民族精神的三种界定 关于民族精神的界定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致有以下三种看法。一是从积极的、进步的角度界定民族精神。认为真正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进步观念、精粹思想和优秀文化,应该体现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宜包括中性意义上民族精神中消极的、落后的成分。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他认为,民族精神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1)二是将“民族精神”界定为中性概念,认为民族精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风貌,其中既包含进步的、优秀的成分,也包含落后的、消极的一面。三是主张采用具体场合具体分析的方法,认为如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应将民族精神视为精华与糟粕的共同体;而如果作为正面的宣传对象,则仅指民族精神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须知,尽管“民族精神”和“民族的精神”有着内在联系,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明显差异。“民族的精神”(又称“民族意识”)含义极为广泛,泛指一切与民族有关的精神现象,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情绪、民族性(国民性)等,都属于“民族的精神”范畴;当我们在研究“民族的精神”时,更多地属于事实判断。而“民族精神”是一个专有名词,含义较为单一,具有特定指向,仅指“民族的精神”中积极向上的部分,不应包括消极落后的成分,因而能够激发一个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当我们在研究“民族精神”时,固然属于事实判断,但更多地属于价值判断。 (1)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二、新时代赋予民族精神新的科学内涵 对于古今中外民族精神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认为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禀赋,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1)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质,这些历久弥坚的鲜明特质,对全民族具有高度的团结力和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民族精神具有“灵魂”的意义。(2) 我们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 本书将典故、理论、现实紧密结合,旁征博引,阐释理论,回望历史,放眼国际,贴近现实,语言通俗流畅,有助于大众理解、把握、弘扬民族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部较好的普及类主题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