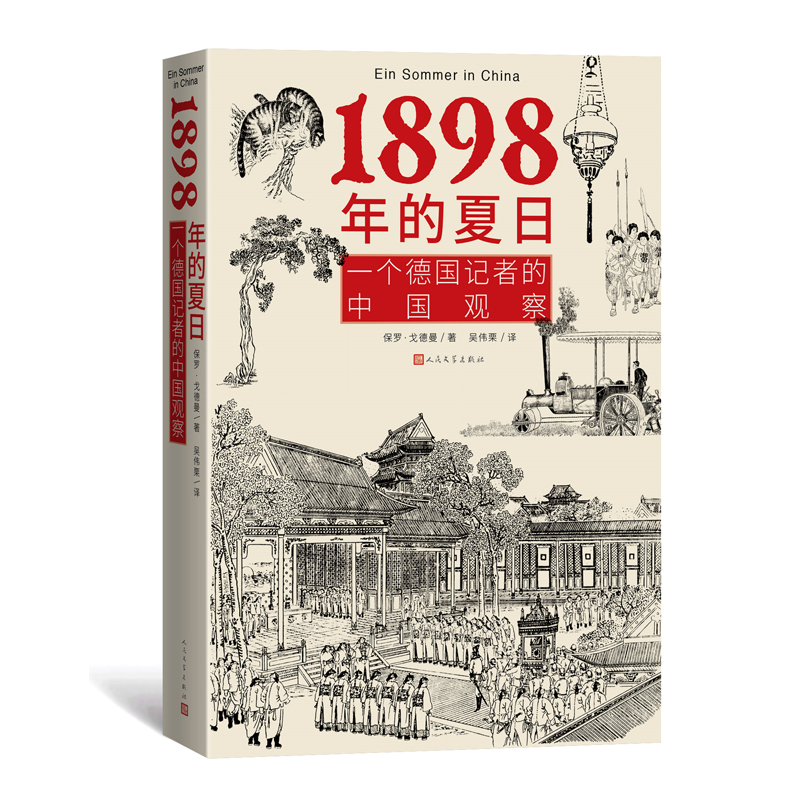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90
折扣购买: 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
ISBN: 9787020165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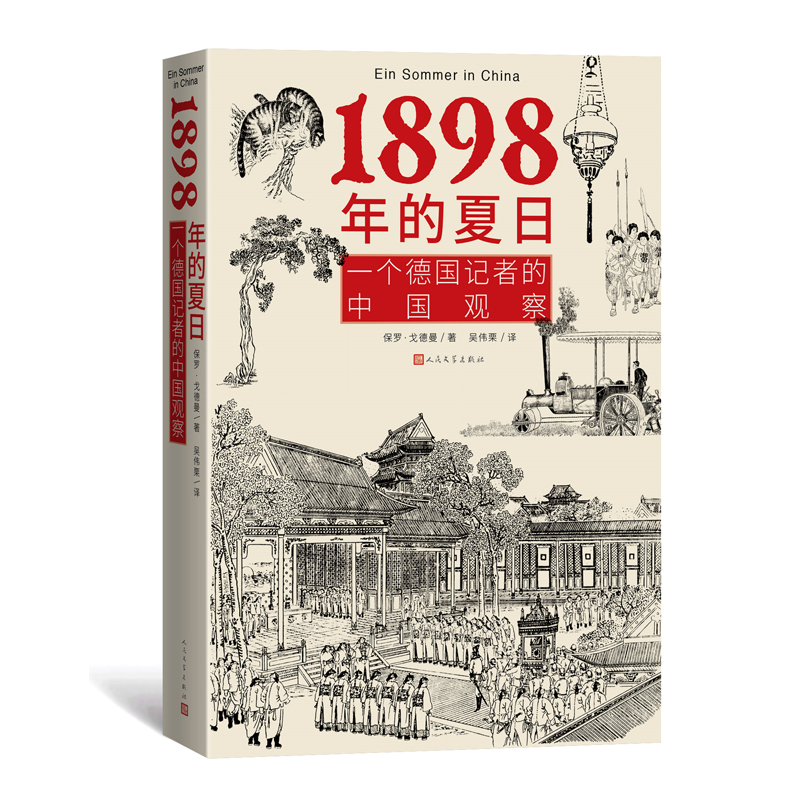
保罗·戈德曼(Paul Goldmann): 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市(现为波兰弗罗茨瓦夫市),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奥地利及德国新闻工作者、公关人员、旅行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1892年至1902年,他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中国担任《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并于1898年期间在中国进行游历和采访。 吴伟栗: 旅居德国华侨,长春市人,曾主修通讯工程、汉语言文学、经济信息学等专业。九十年代曾在中国从事边贸、运输、酒店、房地产等业务,1998年赴德国留学,2001年创立德国格兰茨公司(GLANZ GmbH),在国际贸易、酒店、文化交流等多领域发展。2013年整理出版本书的德语版。
第二十八章 拜访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少荃、子黻、渐甫,号仪叟、省心,谥文忠,人称李中堂、李傅相。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官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 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北京 德国使团友善地请求李鸿章先生同意与我进行一次对谈。至于他是否会接见我,我们心里没底。此时的中国官员都尽可能地回避与欧洲人士接触,如果在谁住处附近出现了一位欧洲记者,那他们很可能直接在大门外横摆上一根大木棍。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局面会如何演变,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心惶惶,所有人都避免进行任何会危及自身安全的访问。 而李鸿章一如往常,他是唯一一个不会心怀恐惧的高官。他同意了使团的要求,并安排第二天就接见。这一天,也正是欧洲军队进入北京的日子。当我们正要准备出门进行拜会时,李鸿章让他的秘书捎来了一封信,信中表示:由于身体微恙,请原谅他取消当日的会谈。欧洲联军进入北京,不难设想中国官员会为此感到头昏脑涨。但李鸿章处理会谈的事情还是典型的中国风格。对德国记者的申请,答复是同意的,因为他不想直接反对而显得不礼貌,但同时他也力图避免这样的会面,因此在会谈举行的当日,他“生病”了! 不过,李鸿章可能不太像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中国人。几天之后,他的病痊愈了,于是又重新敲定了会谈时间,德国使团通译冯·达高兹先生将会与我同行。在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专业人士中,冯·达高兹先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而且他身上还常带有容易让欧洲人困惑与误解的中国式素养。他能呈现出清新、吸引人的独特人格特质。在拜访李鸿章时能有这样一个通译,能将谈论的事务在各细节处忠实地迻译成中文,并以同等的精确性努力予以答复,对这次对谈而言真是难得的机缘。 我们坐上一辆马车,是那种底下没有避震弹簧的北京马车。行进中它会将路面上的不平之处和遇到石头产生的震动都传到身上,堪称是人类所发明的事物中最可怕的一种“酷刑”交通工具。在前方带路的是领事馆的骑士,后面则跟着一位骑着马的中国仆役。我们从领事馆向右转,在通往皇宫的大道上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向右转,走到了窄巷之中。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后,马车与骑士停在了一条不甚宽广的街道中央。这条街道人车较少通行,安静、人烟稀少。李鸿章在他儿子的住处等着我们。这栋房子是木制的,如同一般的中国建筑一样,房间仅有地面上的一层。屋子是新建的,鲜亮的绿色外漆与邻近脏污的灰色民屋形成了强烈对比。从屋前宽广的临街与空地可以看出,这里一定住着有钱人。 领事馆的骑士先去递交我们的中文拜访函,他回来告诉我们拜访被核准了之后,我们便立即走下马车。步行走过大门,穿过用大片长方形石板铺成的干净园子,踏上石板阶梯,李鸿章老先生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门几乎跟他的身高一样高,让他看起来比实际上要高大一些。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样貌,令人肃生敬意。 他穿着简单的居家服饰,一件红棕色锦缎长袍,一件蓝色丝质外衣,外衣上的纽扣没有扣上,脖子领口附近还有些磨损。晒得黝黑的脸孔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欧洲时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他鼻子上挂着一副眼镜,不是一般中国文人用的那类怪异样式的(夸张、奇异、不寻常的),而是金色细框的欧式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精明的、细小而灵活的眼睛,有时也会目露凶光。他说话的声量很小,听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为上了年纪声音有点儿糊在一起(法国人称此为口齿不清)。可能的话他尽量寡言少语,起码一开始是这样。 之后他的话变得稍微多了起来,但依旧掌控着话语的内容,并带着狡黠的目光。有时候他会在说话时突然冒出短暂的笑声,此时,他嘴巴里的黄牙便清晰可见,那是牢固、修长的犬齿。当他这么笑的时候,脸上便会闪过一丝嘲讽的神情,但随即又恢复严肃与呆板。这位老先生的头上已经毛发不剩,头皮下是骨骼强健的圆形头骨。 李鸿章手上拿着一根有着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质拐杖。由于他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中国的俾斯麦(这是某些欧洲马屁精一直对他说的奉承话,说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来一支铁血宰相晚年携带的拐杖复制品也不无可能李鸿章的遗物中,有一根镶满钻石的手杖,据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杖,原是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一八七七年格兰特卸任,偕妻子朱莉娅作环球旅行。一八七九年四月抵达中国,成为美国总统中第一位到达中国的人。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行馆设盛宴款待格兰特夫妇,对格兰特的精美手杖爱不释手。格兰特于是说:中堂既爱此杖,我本当奉赠。只是此杖是我卸任时,国会代表全国绅商所赠,我不便私下赠人。待我回国后将此事公布,如果众人同意,我即当寄赠给您,以全中堂欣赏雅意。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格兰特遗孀不忘当年承诺,将该手杖赠予李鸿章。自此李鸿章与此手杖形影不离,直至去世当作遗物陪葬。。 我们现在所在的房间是一间有着石头地板的前厅,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在角落旁放着一张欧洲皮椅,皮椅前方另有几把中式椅子,后面是房子的内部,被一面漆着绿色的木板隔着。当没有访客时,板子似乎会被摆回去。李鸿章同我们握手,让我介绍自己的名字,并看我们给他的拜访函。他尝试着读我的名字。之后他便坐到皮椅上,并请我们在椅子上入座。他伸着两只脚,穿的是柔软的中国布鞋,腿上是白色麻布制成的裹腿。之后他向我们介绍他的孙子,年仅十三岁、想法十分开明的中国青年。德国的反犹主义者大概会把他隆起的鼻子视为他亚洲纯正血统的一种反证。这位年轻先生穿着深紫罗兰色华丽长袍,礼貌但有点害羞地向我们伸出手握过之后,就在一张稍远的椅子上直挺坐下,专心听他的祖父说话。 皮椅的不远处已经有一位赖姓仆人随侍在侧。双方在谈话时,李鸿章一会儿要他拿东一会儿要他拿西。首先他要香烟。他用一个小巧的镀金滤嘴抽着,之后又要金属制的水烟烟斗,忠实的赖姓仆人得把烟管放进他嘴里。然后是一杯茶。除了水烟之外,他也给我们提供了所有服务。李鸿章在他的皮椅上放了一只壶,像是一个被开启的容器。他不时会把它拿到嘴前,往里头吐上一口,然后再放回原处。由于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风吹得有些夸张,我们身上都穿着外衣,但还是感觉冷。“赖”在没有被呼叫的情况下,主动拿来了一顶中国家居帽,戴到老先生光秃秃的头上。 从试图了解我开始,李鸿章开始和我对谈。他用拐杖指着我,提出了一堆问题:为何从德国过来?在中国多久了?拜访过哪些地方?在胶州停留了多久?何时会回欧洲? 之后出现了空当,我便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提问,并把谈话内容带到重点上。我说道:因为《法兰克福日报》正确地预料到眼前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才派我来到北京。目前我只是个异乡客,不懂得如何去理解这场危机,如果能够从您那里得到对以下这个问题的答复我将感到十分幸运:“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鸿章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说道:“错在年轻官员。” “为什么?” “资深、有经验的官员,被不曾处理过国家事务的年轻一代排挤出去了。他们想从中获得利益,直到最终不能再走下去为止。经过这次危机,这些比较年轻的官员已经被铲除了。” “这次的巨变,若是能让资深官员重新回到职位上,应该会是好事。但这样的事情似乎没有发生。而人们已经从中看到,目前处于艰困时期的中国还没有给像您这样的人职位。” 老先生兴奋地点了点头,确认这也是他的看法。但他仍旧迟疑,没把话说得更清楚。因此我必须稍微试着催促他一下。 “就我所知,”我说道,“如果没有一个适当人选能够代表中国政府的话,是无法掌握目前状况的要害的。外国使节们眼下要跟谁进行协商呢?我可以想象,他们现在正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 之所以如此想象,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冯·达高兹先生(Herr Von Goltz)确认了我的想法,他表示,德国使团如今已不再进出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已经被弃置了,李鸿章也被赶出衙门了,那谁还会留在那里呢? “是呀,但是政府一直都在。”李鸿章回答。 “政府光在那里是不够的。”我回应说。 “政府必须发挥点职能。现在事情已经过头了,中国会面对后果的。最起码,中国的信用会遭受损害。” 李鸿章解释说:“只要中国还能支付贷款利息,便不需要为金融信用一事担惊受怕。目前利息都是按时支付着。” “与这些贷款与利息有所关联的是过去。关键是未来,中国更需要信用。欧洲企业的时代现在正要开始,这需要动用欧洲资本。如果欧洲不给你们钱,中国连铁路也不能修了。” “那就不要修。”李鸿章沉着地说着。 在欧洲,这位先生被当作是追求现代化的先锋,但从他口中听到这番话,让我感到讶异。冯·达高兹先生则提出实例加以说明,中国是如何在最近的事件中丧失信用的:比利时人不想再为北京至汉口这条由他们负责的路线提供更多资金。德国商业联盟也对新疆到天津的铁路计划感到茫然,表示想要撤回。 我再次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欧洲能信任的人在中国官府里头坐镇。对中国的信用来说,李鸿章先生是最好的代言人。实在无法理解,竟然不让您继续服务。在领导中国的官员之中,您几乎等同于中国信用的名号,如今竟毫无作用。” 李鸿章眼睛眨也不眨地听着这些赞扬的话,似乎可以察觉到,这些话打动了他。他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外国人是依照过去的成就来理解我并推崇我,但如果中国人并不这么想,我又有何可供效力的呢?”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 “这毫不虚假。俾斯麦首相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赢得所有文明国家的信任,唯独没办法让他的皇帝信任他!”李鸿章说。 “那么您又为何失去了贵国皇帝对您的信任?” “人们抨击我,认为我对外国人太过偏袒。他们称我是卖国贼。” 当李鸿章这么说时,脸部因怨恨而出现了一丝抖动。当他说到“卖国贼”这三个字时,爆出了一阵大笑。 …… …… …… 出版说明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4月10日,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对中国进行采访。 戈德曼乘坐的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出发后,穿越地中海,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远航至欧洲式东方新城——新加坡。而后,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进行详尽考察。途中,他先后采访了时任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长王存善、上海道台蔡钧。从上海又沿长江乘船而下,在镇江、汉口、武昌等地停留。 在汉口,戈德曼参观了欧洲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机构与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德国教官主持训练的新式军队。在胶州湾的青岛、威海、芝罘(烟台)等地,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 戈德曼此行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人物颇多。在烟台,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在北京,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 他记下的目睹所见,对于我们了解19世纪末沿途城市的风光风貌以及中国社会的面貌,有一定的帮助。尤为可贵的是,在书中,戈德曼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当时曾预言:上海会以数十年的努力,成为东方一座伟大的城市。这个预言后来成为了现实。 在书中,他也以记者的客观,披露了最初中国铁路规划过程中,欧洲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以及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融相斥的情况和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通过与清政府不同级别官员的互动,他记录下清末官员对改革和与西方合作的不同主张,以及民间对这种主张的不同反应。 保罗·戈德曼在中国的这段采访记录,观察细微,文笔优美,对中国民间和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度也很高。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能可贵。时隔百年,这本书能够被发现、翻译、出版,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保罗·戈德曼作为德国记者,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在反对纳粹等重大历史问题上,他的立场和气节也是令人赞赏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这本书中,他是站在德国的视角看中国的,有时候表达就难免会沾染一些殖民的色彩,某些时刻甚至会流露出殖民者的口吻。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局限,也是他的偏见,所以我们中国读者在肯定这本书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同时,还需要对殖民化表达提高警惕,需要持批判的立场去阅读与理解相关内容。 读史以明志。放眼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国终于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厄运,迎来了崭新而令人振奋的局面。 中国与世界,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我们需要历史的沟通、文化的沟通,需要消除偏见,需要相互尊重。这也是这样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所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后记/吴伟栗 2011年的初秋,我第一次前往亚得里亚海岸。在地图上看,从维也纳出发,穿过斯洛文尼亚,是到达亚得里亚海边城市的里雅斯特的最近路线。在夜幕低垂的傍晚时分,我进入斯洛文尼亚边境,斯国海关警察把我拦了下来。尽管斯洛文尼亚是申根协定国,按协约应当撤消边境检查站,但他们依然要求检查我的证件。我递交了我的全部合法证件,斯国海关警察看后说,证件没有任何问题,但我没有买高速公路票,要缴纳罚款160欧元。事实上,在进入斯洛文尼亚之前,我一直都在留意公路两边的商店、加油站。我已经预想到进入这个国家是要购买高速公路票的,但是,一路上并没有看到任何营业场所。按理这个时候再买也是可以的,可是两个警察不由分说就要罚款,而且,态度十分蛮横,直接扣下我的护照与驾照。看来不交罚款人走不了了,这个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国家,经济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警察也是见钱眼红了。对我来说,时间可比金钱更重要,只好交了160欧元的买路钱,继续这趟亚得里亚海的旅程。 我原打算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停留一两天,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文化与城市风貌,但经历了与斯国海关警察不愉快的纠葛,我对这个小国家兴趣全无。驱车穿过斯洛文尼亚进入意大利,大约有两百多公里的路,汽车疾驰不到三个小时,我就来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意大利城市——的里亚斯特市。 已经是午夜,汽车驶出高速路沿着盘山公路向下,远处是一片灯光,看来这座城市的规模很大,远远超出我之前的想象。驶入市区,马路开始由宽变窄,柏油路变成了石头路面。古老的街道、老旧的房屋,一切都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应该有的样子。 我在欧洲学习、生活多年,每到一座城市我都喜欢去看古董店和邮票店。徒步古老的街道寻觅历史痕迹,是我在外旅行的最大爱好。这座城市依山而建,环抱亚得里亚海岸。我住的威斯汀酒店位于城市的山顶,从高处沿着狭窄的石头街道走下来,山脚下就是这个城市的中心。这一天是星期六,恰逢城市的周末跳蚤市场,我逛了一圈并没有什么收获。于是,我沿着古老的街道漫步前行,来到一家古董店前,这么偏远的地方,应该会有什么宝贝吧?旧货琳琅满目,然而我在里面足足转了近半个小时,也没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当我打算离开的时候,礼貌性地问了一下店老板:“您这里有来自亚洲的东西吗?”老板看了看我,想了一下,然后,用德语回答道:“我们店里有本一百多年前的书,里面写的是中国的故事,您有兴趣吗?”说着他从身后书架上找出两本书,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书的封皮:Ein Sommer in China,意思是:一个夏天在中国。这是一套上下两册的旧书,泛黄的封面与僵硬的纸张略有破损。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来看,竟然全是古典字体的德文。我没有学过古典字体德文,一时间看起来有些吃力,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和价值来,但我想,既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出版物,就当是古董买了也不错。 只经过一个回合的讨价就成交了!这店铺里陈列的旧书不计其数,我估计店老板自己都没有读过这本书。他或许也不会想到,这本书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意义重大,它给了我们一幅尘封百年的中国历史画卷。 一周以后,我回到了法兰克福的办公室,立即把书拿给我的朋友乌利先生,请他认真看看,然后把里面的内容大致整理一下,告诉我。乌利先生是德国的经济律师,父亲曾经是德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接受过德国和瑞士两国的大学教育,如今年近七十岁,知识渊博,他是看得懂古典体的。乌利先生用几天时间把书读了一遍,然后,兴致勃勃地来到公司,坐下来给我详细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时任《法兰克福时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先生,受报社指派,于1898年前往中国,专程对大清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司法、出版、宗教等进行考察。他四月从意大利北部热亚那港口出发,乘坐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由地中海经埃及萨德港、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远航至东方欧洲城新加坡。他从香港登陆中国,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1898年是中国的戊戌年,整个夏天,他先后拜会了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市市长、两个通商城市的地方要员。他沿长江乘船而下,在汉口、武昌、镇江等城市都有所停留,对中国铁路建设中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有所了解。他在武昌考察了德国军官训练营,结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记录了德国工程师与军事教官在中国工作的全过程。然后,他又前往胶州湾青岛、威海、芝罘(烟台),探访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接着,他从烟台继续北上到达天津,访问、参观了天津武备学堂,拜访了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此时,北京发生了戊戌变法,他被困在天津多日。待北京戒严解除,他进入北京城采访,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 听了乌利先生的介绍,我顿感这本书的重要性。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有两本,一本是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一本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这本《一个夏天在中国》时间正好介于这两本书之间。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这应当是第三本历史价值重大的、外国人探访中国的书。德国记者对1898年中国社会的描述,无论是什么样,应该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是他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份,与清政府高级官员对话,一定能够为已有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些参照,说不定能提供我们更多关于戊戌变法,关于中华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我预感,这一定是一本记录中国历史的好书! 我马上请乌利先生着手调查这本书的作者。首先,我们从记者任职的《法兰克福时报》入手,由乌利先生代表公司发了问询函,遗憾的是,今天的《法兰克福汇报》与之前的《法兰克福时报》之间,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继承关系。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亦无法找到关于这本书的更多信息。但是,他们告诉我,因为作者反对纳粹,这本书曾经被列为禁书,纳粹时期要求全部销毁。我们在报社的建议下,马上与德国版权管理机构联系,他们很快给了我们书面答复:该书已经过了七十年解禁期,我们可以申请获得再版的权利。由于原书是古典字体德语,普通人阅读困难,于是,我委托乌利先生用了一年时间,将古典德文逐字转换成现代德文,2014年在德语国家出版。为完成这套书的整理工作,我的朋友乌利先生用眼过度,患上了严重眼疾,待完成文字转换的时候,他的左眼几近失明。2017年12月21日,乌利先生因骨癌在法兰克福去世。他是我亲密的朋友,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好朋友,在德国法兰克福、巴登洪堡,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曾获得过他的法律援助。他爱中国,乐于帮助中国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来过中国。我答应要带他一起来中国看看,我们说好了,晚年他在我身边养老……这成了我一辈子的疼。 自2015年开始,我就着手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由于作者的宗主国横跨普鲁士、奥匈帝国以及魏玛共和国向第三帝国的演变进程中,他的语言南北混杂,我几乎找遍了中国的德语翻译大家,都无人肯接受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我也深知这套书的翻译难度很大,但是,我也深知,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价值而言,这样富有现场感的记录有多么难得!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与描述,从“他者”的视角,换一个眼光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真实风貌。就算是“片面”的真实,也万分宝贵。 我下决心要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没有人愿意干,我就组织人自己干。我和乌利先生,还有他能找到的,能够识别古典德文的朋友和专家一起工作,2017年,中文直译工作基本结束——深切怀念我的朋友乌利先生! 原著于1899年在德国出版发行后,1900年很快发行了第二版。作者为了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在再版时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做了一些注解。我买到的恰恰是第二版,所以,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本书的全貌。翻译过程中,查阅历史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为了便于今天的读者理解,我也对一些人物与事件做了注释,这些注释在这本书中都以脚注的方式呈现出来了。 这本书在翻译整理的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同学全晓煜、李雪玉,中央电视台董浩先生,山东大学白洪声教授,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程晓刚老师的支持。2018年夏季,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员郭一鸣先生来德国,我向他介绍了这本书的发现过程和内容,他以职业嗅觉肯定这本书的价值,为此,在香港《大公报》对这本书做了大量报道,并获得了《大公报》社长姜在忠先生,香港皇朝家私谢锦鹏先生的支持。根据郭一鸣先生的建议,我对保罗·戈德曼的生平做了深入调查,很快,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查到了作者的生平资料以及后来的命运。 保罗·戈德曼(Paul Goldman),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市(现为波兰弗罗茨瓦夫市),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他是奥地利及德国新闻工作者,公关人员,旅行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和戏剧散文和小型戏剧的作者。保罗·戈德曼父亲古斯塔夫·戈德曼是当地的商人,母亲克莱门汀·尼·玛姆罗斯是家庭主妇。 他在德国布雷斯劳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在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后前往维也纳,在他叔叔马姆罗斯主持的《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杂志工作。保罗·戈德曼是现代戏剧的狂热者,通过其叔叔认识了阿瑟·施尼茨勒这样的作家,并与他的亲密朋友理查德·比尔·霍夫曼和雨果·冯·霍夫曼施塔尔进行了早期的出版。 施尼茨勒在1889年与戈德曼的一次会谈中写道:“我接受了马姆罗斯先生的邀请访问编辑部,这次与他的代表和侄子会面,这是那封友好的录取通知书的作者,二十四岁,和蔼可亲的绅士。保罗·戈德曼博士,身材粗壮,有点驼背,卷曲的头发,”明亮、美丽的蓝眼睛。我们立即彼此非常了解,对生活和艺术中的大多数事物都有相同的看法。 而在 Bernhard Reich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花花公子。戈德受是维也纳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他曾担任维也纳国家石油公司和蒙达格斯的外部雇员。从1890年到1892年,他是维也纳 NeueFreiePresse编辑协会的成员。 戈德曼与艺术赞助人珍妮·毛特纳和她的丈夫,实业家伊西多毛特纳在一起。他结识了记者兼作家朱利叶斯·鲍尔和作家兼文化历史学家埃尔明·克洛特。 从1892年至1902年,他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中国担任《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1896年,由于德雷福斯事件,他与法国反犹太新闻记者Lucien Millevoye之间发生了一场手枪决斗,最后以放弃告终。 从1902年开始,他在维也纳,也在柏林担任《维也纳新自由报》的戏剧记者。他负责奥托·勃拉姆斯的导演工作,有时还涉及麦克斯·莱因哈特的喜剧评论。1908年8月,他在维也纳与伊娃·玛丽亚·弗朗克结婚(1937年11月2日,自杀身亡)。女儿 Franziska生于1911年5月29日,1938年3月29日离开维也纳前往米兰,1940年底移居巴西里约热内卢,于1963年去世。 戈德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了战地通讯员。战后在德国将权力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者之后,他因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于1933年8月在米兰被盖世太保逮捕,同期遣返回维也纳,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享年七十岁,葬于维也纳城市公墓。2018年10月我们查到他的资料,并在维也纳找到了他的故居,同时在维也纳公墓管理处,找到了戈德曼先生墓地的编号。由于墓地费用支付到1994年6月5日,此后无后人前来支付,墓地管理部门无法联系上其后人,只能按惯例给予20年的延期,2014年6月5日作为无主墓处理。现在墓碑已经不存在了! 保罗·戈德曼的主要作品: 《中国的夏日》,游记,共2卷,1899年; 《一个不应该的合谋》,三幕喜剧,1902年; 《新方向》,(关于柏林剧院表演的辩论性论文)1903年; 《引人入胜的迷宫》(关于柏林剧院表演的文章),1905年; 《徳国舞台的衰落》关于柏林剧院表演的辩论性论文,1908年; 《文学作品和创作方向》(关于柏林剧院表演的辩论性论文),1910年; 《与兴登堡元帅一起——1914年在总部的一个晚上》,1914年; 《从里尔到布鲁塞尔》(包含德国陆军西方阵地和战斗的照片),1915年; 《与兴登堡的对话》1916年; 《赖兴巴赫伯爵的沦陷》1923年。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的大力支持,感谢资深编辑付如初博士对翻译稿件的精心打磨。如果不是这本书的特殊价值,我原本是不会想到自己此生会做翻译工作的。尽管我拼尽了全力,但在文字方面依然有很多欠缺。付如初博士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职业操守,协助我完成了近四十万字文稿的整理工作。她逐字逐句帮助我修改润色,核对史料,核对原文的准确含义,探讨表达的分寸和细节。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您面前的这本书,不会是这样令人欣慰的面貌。当然,此中错讹还是难免,这些都是我的责任,盼望读者慧眼指出,帮助我让书稿更臻完善。我的邮箱地址:info@glanz-verlag.com 我期望这本书能够留存下去,为中国历史保存一份珍贵的史料,更为中国人保存一段值得铭记的记忆。古老的中国步履艰难走过的那段岁月,学过历史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我们无法忘记国家贫弱时候的屈辱,因而才会更加珍惜国家富强之后的自豪。 2021年7月于德国国王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