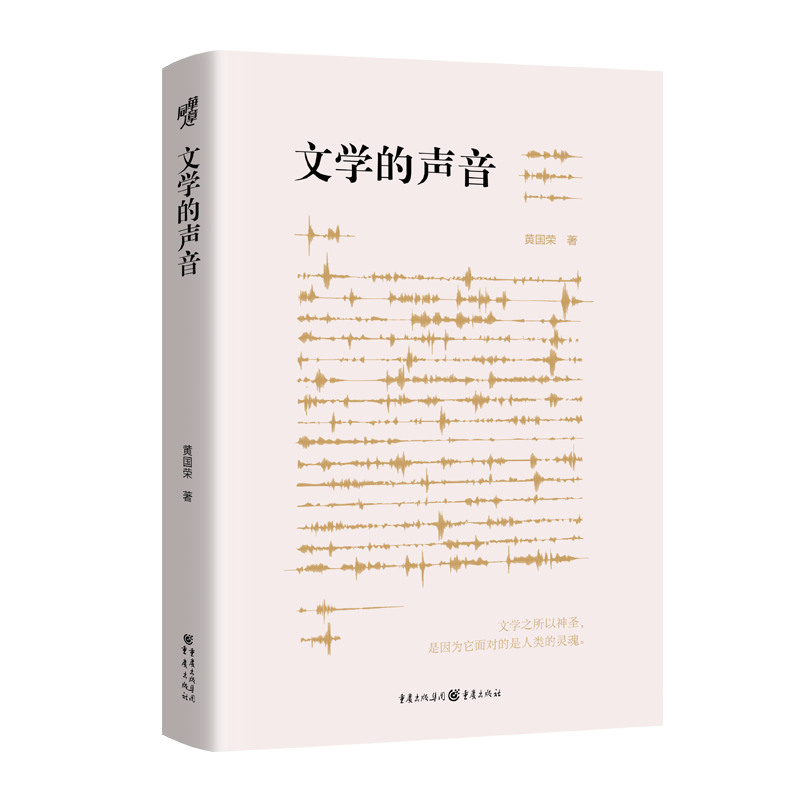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59.80
折扣价: 37.10
折扣购买: 文学的声音
ISBN: 978722917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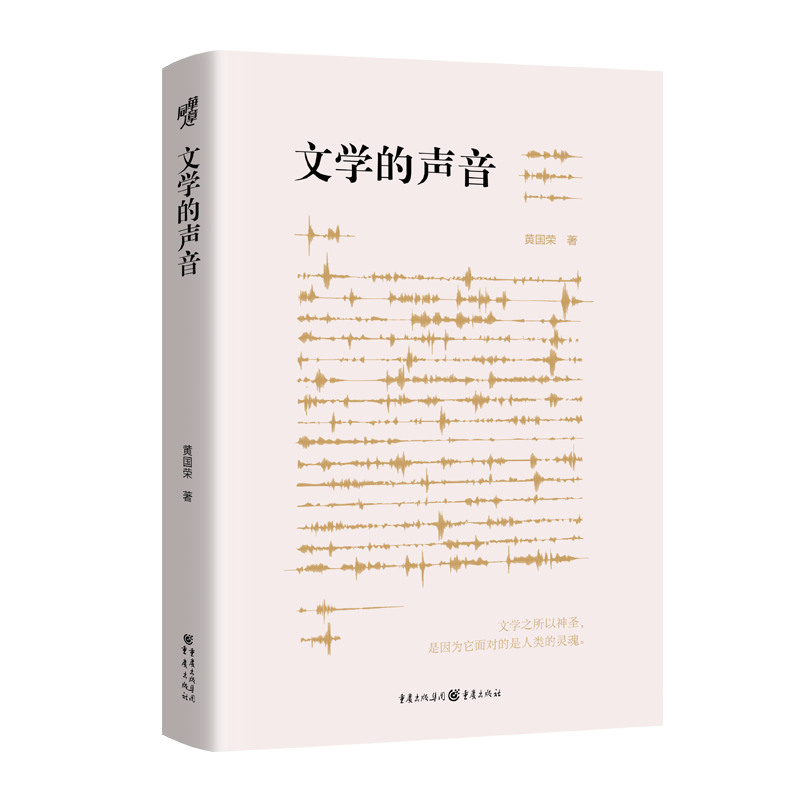
黄国荣 笔名秋野,江苏宜兴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兼副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创系专家组专家。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800余万字。 长篇小说《兵谣》《乡谣》《碑》获总政全军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等奖;《乡谣》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兵谣》《碑》选入“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百年百部红旗谱”“百年百部红色经典”等经典丛书;中篇小说《苍天亦老》获总政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长篇小说《极地天使》获2015年度人民文学奖特别奖。电视连续剧《兵谣》获飞天奖,电视连续剧《沙场点兵》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最佳收视率奖。编撰《经典军事文学作品研究》《图书编辑学》。 2018年,被中国发行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评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图书发行业致敬影响力人物”。
文学的声音 一 我不赞同顾彬先生“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说法。但是,我非常欣赏顾彬先生近期与李雪涛先生《对谈》中表达的一个观点。他说:“我认为: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一位作家。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声音。所以我要问,中国有这样一个声音吗?……一九四九年以前好像有过,就是鲁迅。而这之后呢?还有吗?还需要吗?”(《万象》2010年第2期) 一个成熟的作家,绝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主张。昧着良心随波逐流,为功利而写作,捞取政治资本;一味迎合某种需要,或把文学当作敲门砖,或醉心于低俗、媚俗、庸俗的市场效应而写作―这都不能称为成熟。成熟的作家面对时代,面对社会,面对芸芸众生,面对现实,必定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不为别人所左右。这种声音很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声音。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国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状?英国有个名叫赫德的人在一八九五年就给中国这个“巨人”画了像。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着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蒙眬地睡着了!”鲁迅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时期,我们国家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国家的状态如此,民族和国民的状态可想而知。鲁迅先生心痛地看着这样的国家、民族和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为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们叹息和呐喊。他的叹息和呐喊,便成为国家和中华民族面对现实应该发出的声音。 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先是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结束了长达百年的被侮辱被奴役的时代,中国人的“虾形”脊梁终于挺直起来;后来的一些日子,我们忽略了被认为是马克思一生的第一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国家经济和社会面临很大困难;改革开放到今天40多年, 我国经济实现腾飞,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抖擞,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殷实富足,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顶天立地。然而,中国的崛起让国际上仇视中国的那些人非常不舒服,他们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用种种手段遏制中国;伴随着经济发展,国内一些问题也愈加凸显,例如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贫富差距拉大、东西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下岗失业、就业难、高房价、潜规则等等,都可能成为阻碍发展的隐患。面对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和人,国家和民族需要什么声音呢?我们当代作家又发出了什么声音呢? 二 我不能说当代文学家和作家发出的声音都是怪音,也不能说都是杂音, 更不能说都是不和谐音,但整体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噪音。当代文学家和作家所形成的声音缺乏独特的音律,这是因为独特的音律依赖于独立的思考与立场, 而当代作家缺乏独立的文学立场和主张,“墙头草”多,具有摇摆性。今天追求某种时髦,明天模仿着践行某种主义,后天又想表现自我,再一天又可能彷徨观潮,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意志。诚如顾彬先生所说:“其中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作家可靠吗?中国出版社的书和版本可靠吗?(有人批判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她就重新写了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否定了第一部,读者应该怎样相信丁玲的话。)”中国当代作家很少在作品中表现出个人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主张,这便是与鲁迅先生的差距所在,即缺乏那种精神界之战士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他实在不能发出声音的时候,宁愿十年沉默。 反映战争历史的作品,童庆炳先生认为:“这些年的作品,《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和《亮剑》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合乎你的文学理想?我不能不说出我的真话,这几部作品不错,但很难称为优秀,更难称为伟大,因为这几部作品的基调仍然是《青年近卫军》式的,《红日》式的,最多是苏联作品《夏伯阳》式的。”(《文艺报》2010年10月15日2版《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 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历史的作品,基本按照《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重复,其主题、人物、结构和文学价值几乎没有任何新意:不是阶级斗争,就是家族斗争;不是权力争斗,就是公私较量。 反映改革开放至今的作品,如顾彬先生所言:“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人类太多,民族太多,国家太多。国家是政治家的事情,不一定和作家有关。所以不少中国当代的作品在德国很难找到读者,因为作品的题目太大了。”大家不妨到网上搜一下,标题中带“国家”“天下”“人间”“大”等字眼的小说有多少。一部作品分量有多重,影响有多大,不在于标题有多大,而在于作品中人物有多新,文学意蕴有多深。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用的都是极普通的书名,但它们却都是划时代的作品。 三 就作家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主张而言,大江健三郎先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大江先生晚年在干什么?他被一桩官司缠了近六年!一九七〇年,他用自己的文字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强制渡嘉敷岛和座间味岛岛民集体自杀的真相,三声“天皇万岁”便让数百名岛民顷刻命丧黄泉。日本军队这一残暴行径今天竟被美化成为国殉节的义举,制造这一惨剧的一个守备队长及另一个已故队长的遗族居然把大江先生告上法庭,日本文部科学省也参与其中。年迈的大江先生遭此讼累并没有退却,而是继续工作,完成了《水死》这部小说, 他要在这部作品中验证“天皇万岁”这句具有象征性的话对日本人的心灵究竟有多大操控力。 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不是垃圾,但能代表国家和民族声音的作家、作品确实太少。顾彬先生说:“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文人和作家,他们应该尊重自己的文学及文学传统。比如某一个中国作家跟我在一起,他会骂其他很多不在场的作家,也包括他最好的朋友在内,最后剩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是中国唯一的伟大的作家。”尽管那种自我感觉特好的人不在少数,但他们不过是狂妄自吹而已。中国缺少伟大作家,除了作家自身的素养、立场、主张和精神等方面的原因之外,环境和氛围也非常重要。说句实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人之间那种做人原则和友情,现时已不复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编辑对作者那种真诚和无私奉献也已罕见。 既然从事作家这个职业,尤其是中国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大多享受事业编制待遇,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国家给了你应有的生活保障,你起码得对得起那份工资,应该实实在在干点儿属于作家本分的事情。起码该想一想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们,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了,他们今天怎么样了呢?他们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他们是“英雄”了呢,还是仍然“狗熊”着?是发达了,还是继续贫困着?是高尚了,还是沉沦堕落着?能够想到这些,看清他们,并使他们再次成为文学人物,即使不一定能发出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声音,起码也尽了一位作家的本分。 1.给年轻人的启发之书。作者从事写作几十年,在本书中,将自己的学识与阅历和盘托出,用真挚文字回应当下年轻人在写作以及生活上的困惑,有如暗夜里的一座温暖灯塔。 2.高产作家,荣获多项大奖。作者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800余万字,作品多次获总政全军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乡谣》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3.行文质朴、真切,文风简洁,没有长篇大论,又能一针见血,特别适合空闲时间读一读,放松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