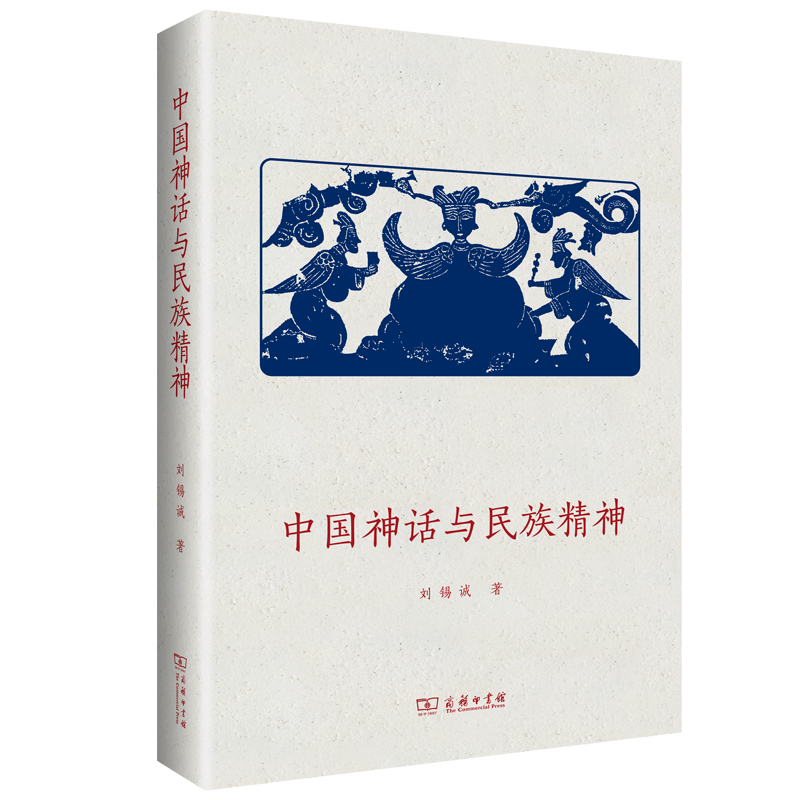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88.40
折扣购买: 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
ISBN: 9787100197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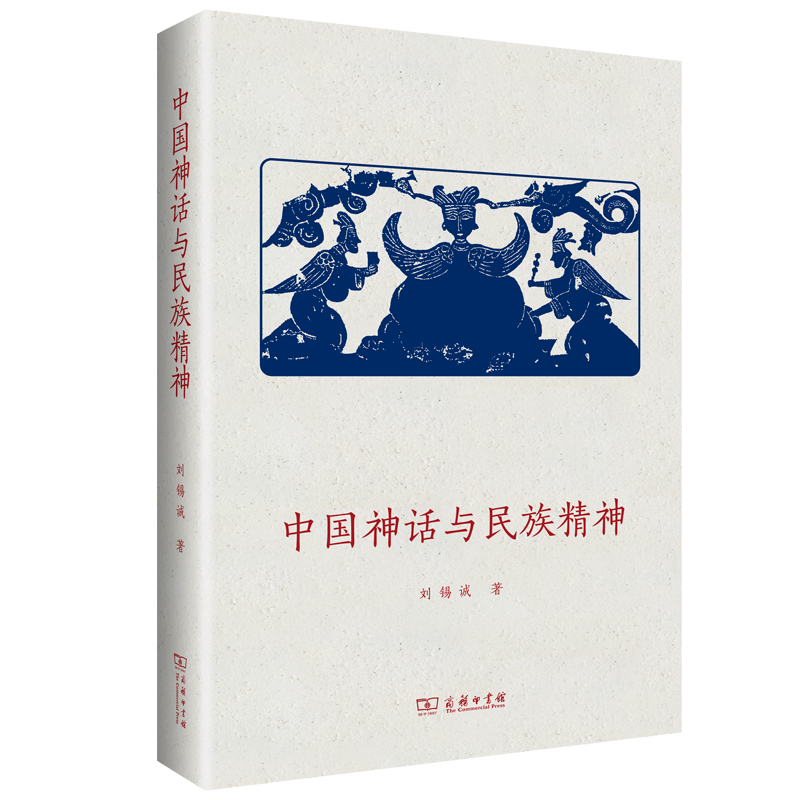
刘锡诚(1935—),山东昌乐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供职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曾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研究员,《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主编。1997年退休。
论原始诗歌与神话 以口传的方式创作的诗歌和神话是初民最早的艺术之一。当原始初民的“自我意识”业已萌生,清晰的语言业已成熟并在心理要求的激发下成为人们交往的必要手段时,简单的诗歌便随之产生了;当原始初民凭借他所投射于世界而形成的种种原始意象去经验世界时,神话便随之产生了。在书写的文字还没有诞生之前,原始诗歌和神话是靠原始先民的记忆并以口传的方式“创作”和流传的,所以不可能有原始诗歌和神话传说的写本传到现在。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被认为是原始诗歌和神话传说的作品,部分是后世的文人根据先民部族群体的口头传承而写定的,部分是旅行家、传教士或研究家在现存原始民族中间搜集记录下来的,即使如此,其总数量也是并不很多的。这就给我们研究诗歌和神话传说的起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诗歌的起源与原始诗歌的特点 一般认为,诗歌起源于民族学上所说的“野蛮初期阶段”。原始诗歌在它产生的初期,是非常简单、粗糙的,但它却是原始先民的愿望、心灵和情感的外化。《尚书·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诗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古人所说的 “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非是社会生活在人脑中所激发起来的那些快感或情感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野蛮初期阶段上产生的诗歌,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或人类感情,无疑是很简单、很浅薄甚至是很粗野的。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起源或原始诗歌的见解,与西方学术界一样,是多元的。 一种观点侧重于强调诗歌是劳动的产物。如汉代刘安在《淮南子·道应训》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劳动在原始诗歌的发生上起着重大作用,其情景正像刘安在《淮南子·道应训》中所描绘的那样:一群原始先民抬着沉重的 大木头,将它搬运到另外的地方去,他们前呼邪许,后亦应之,这号子(原始歌)声协调着他们的动作。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关于劳动在诗歌起源中的作用的论述,在我国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说:“人的觉察节奏和欣赏节奏的能力,使原始社会的生产者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乐意按照一定的拍子,并且在生产动作上伴以均匀的唱的声音和挂在身上的各种东西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 在原始部落里,每种劳动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 研究劳动、音乐和诗歌的相互关系,使毕歇尔得出这个结论:‘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部分只具有从属的意义。’”这个论断在一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它的得出,并非出于想象和推论,而是从事实出发的,我们即使从现存原始民族所流传的一些劳动歌也可以看得出来;但一旦原始诗歌超出了与劳动有关的范围,这个结论就未免显得片面了。 本书是当前我国关于中国神话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