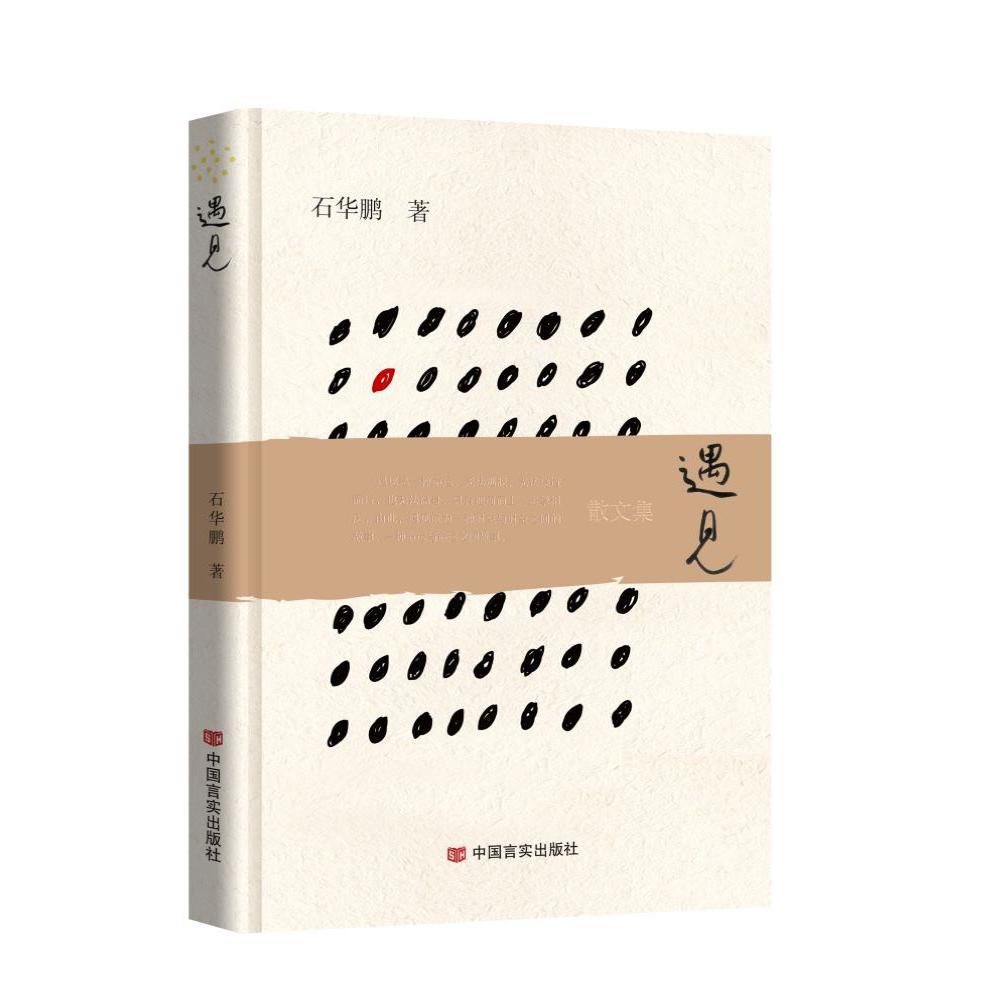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言实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遇见
ISBN: 97875171386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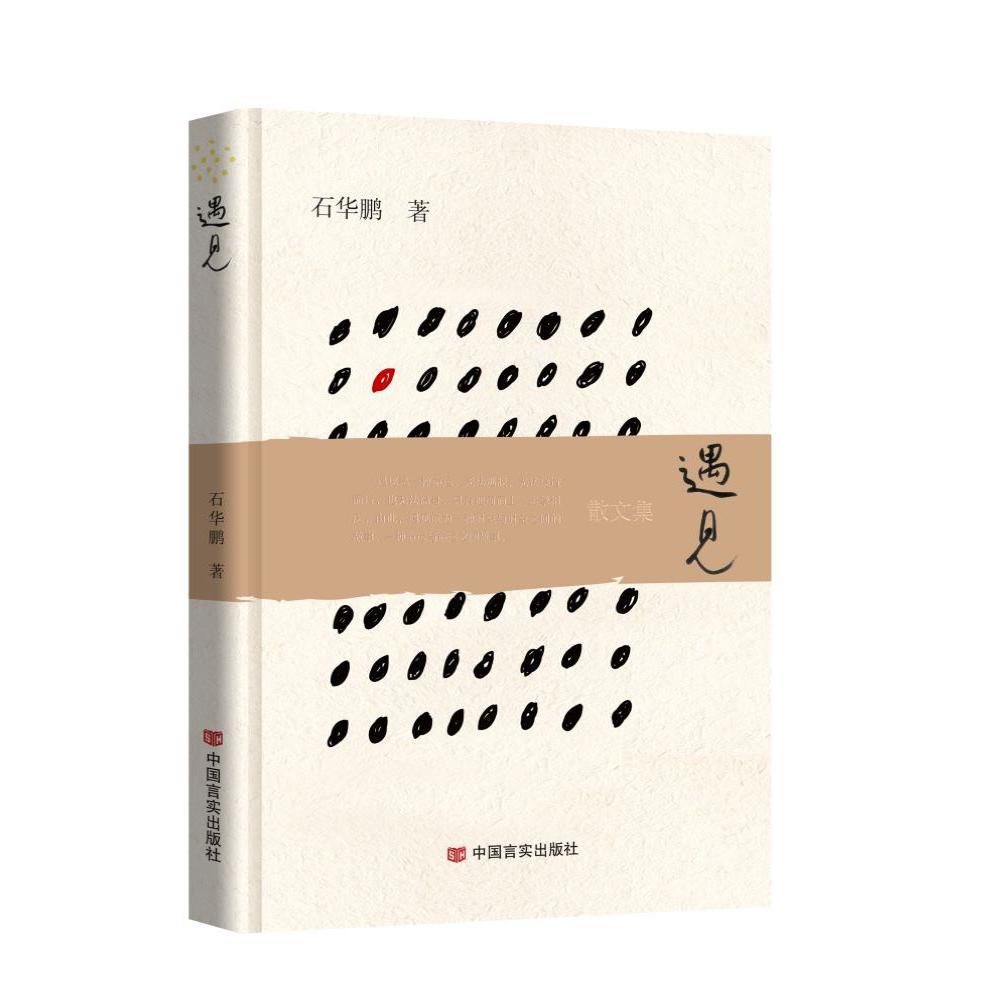
石华鹏,生于1975年,湖北天门人。中国作协会员。现任《福建文学》常务副主编,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98年开始写作,在《文艺报》《文学报》《文学自由谈》《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小说、随笔300余万字。出版随笔集《鼓山寻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时代》《大师的心灵》,评论集《新世纪中国散文佳作选评》《故事背后的秘密》《文学的魅力》《批评之剑》。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首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等。
今宵酒醒何处:魏晋酒事断想 一 如果把夏禹时期一个叫仪狄的人酿造的第一壶酒作为中国酒的起源的话,那么,酒在华夏大地上至少走过了四千年的历史,一部酒史几乎逼近于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史籍《吕氏春秋》《战国策》最早有“仪狄作酒”“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的记载,是为中国酒起源的文字佐证。 无论独享美酒,还是把酒庆祝,无论借酒浇愁,还是因酒祸事,千百年来,酒总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体内心情感纠缠在一起。但是有一天,酒挣脱了自身的物质属性,逃离了兴奋的个体饮者,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成为一个时代的群体风尚和生存哲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词,成为后人进入一个时代的精神通道,那么酒就不仅仅是酒了,那么这个时代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庸常的时代了。 这个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时代,叫魏晋;因为喝酒纵歌,因为酒醉放浪,因为风流自赏,这个时代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叫魏晋风度。 历史,有时犹如一部勾魂摄魄的悲情影片,轻轻地落幕却沉沉地敲打在观众的心上。魏晋便是这样一部影片。鲁迅先生说,魏晋的天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悲情、悲凉——一个时代为什么会如此?两个字可以概括:乱、愁。 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之后,魏到两晋的时期,也就是公元 220 年到公元 420 年。短短 200 年,便有二十几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王朝频繁更替。有王朝更替,便有连绵不绝的战争,有战争便有死亡,有死亡,便有无尽的哀愁。历史学家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这种说法一点儿都不夸张,可谓兵荒马乱、灾连祸接。所以,在战乱、哀愁的现实土地上,魏晋天空笼罩着悲情、悲凉的云雾。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任何一个极端都伴生另一个极端。战乱、哀愁的另一面是群雄并起、英雄主义行天下,悲情、悲凉的另一个极端是思想解放、个性张扬。时光总会暗淡哀愁,流年也会老去英雄,当一切走远之时,在魏晋时代夹缝间生存的士人文人们,却用自己的清谈、服药、饮酒等外在行为,成就了内在的率性至真、慷慨任气,追求绝对自由的“魏晋风度”。 魏晋过去将近 1600 年了,在今天,当人们重新回味那段缥缈如烟的历史时,战乱与哀愁的场景很难被再次想象,而心中留存的对“魏晋风度”向往的火焰总在默默燃烧——这向往,并非因为嗟叹当前现实对魏晋自由精神的缺失,仅仅是因为自身内心的某种朝圣;而这向往的火焰的燃烧,一定是因为那个时代,那些人物,那些清谈,那些药物,那些逸事,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酒,做了人们心中的助燃剂。 1800 年前,一切都曾鲜活地演绎着。大约在公元 200 年左右,汉帝国大厦开始倾覆,作为国家学说的儒学日益僵化和教条,没有自我蜕变和提升,无法从精神和思想层面去解决国家危机,朝野上下很多人借仁义以行不义,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自身的生生死死之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统统都是假的,人们开始转向道家学派,开始仰慕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和风度。 于是,我们看到魏晋士人一个个粉墨登场:阮籍手持麈尾,宽衣大袖,嘴角露出讥世的微笑;山涛赤袒上身,抱膝而坐,背倚锦囊,双目前视,表情深沉;刘伶双手捧酒杯,回头作欲吐状,一位侍者手捧唾壶跪接…… 他们奇装异服,我行我素,觥筹交错,困酣醉眼,他们毫不掩饰地炫耀自己的才华,他们从容应接明丽澄净的山水。一句话,他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向外发现了自然。为了亲近自然,彰显自我,酒成了他们抵达彼岸的载船,甚至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盛唐气概了。酒,与这群人结下了妙不可言的缘分。 被文学史家称为“后英雄时代”的魏晋,英雄主义的冲动与对生死焦虑的超越,像划过空中的一条彩链,穿南北之史。一代枭雄曹孟德,无疑是这条彩链上最炫目的链珠。他“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气韵沉雄地吟咏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酒,成为英雄渴求功业与嗟老叹岁的一种意向指归,成为英雄激情蔓延与自我爆发的“点火石”。 曹操这一吐纳建安风骨的吟咏,揭开了魏晋这一方酒窖的缸盖,从此芳香四溢…… 书摘二: 艺术的敌人和朋友都是时间 我一直有读画和读画家传记的习惯,前不久读到了丰子恺编著的《梵高生活》一书,讲述梵高的生活和他的艺术故事,书里边还插有梵高的画,梵高的画和故事让我一如既往地感动,梵高已经被无数人谈过了,似乎意犹未尽——大师留给人们的总是如此——所以,我也想谈谈梵高。 一 艺术的敌人是时间,艺术的朋友也是时间 丰 子 恺 先 生 编 著 的《梵高生活》(原名《谷诃生活》),1929 年 11 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84 年之后的 2013 年,此书重新出版。此时,距作者丰子恺先生去世 38 年。书的面目变了,由繁体竖排变为简体横排,插入梵高大量画作,译名改为如今通用译名,没变的是丰子恺的文字。书中所述对象——梵高和他的那些画作,距今也已 120 多年了。 今天的我们读这本书,一是读丰子恺隽永的文字和他独到的见解,二是读梵高的生活和他的艺术世界。无论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什么,但有一份奇妙存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本小小的民国时代的书,穿越几十年的时空距离来到另一个时代,还有再版重新被人阅读的价值,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84 年,多少文字,多少书灰飞烟灭,而这本《梵高生活》留了下来。这恐怕是所有的艺术都渴望获得的一种幸运吧。 艺术与时间,是一对摔跤手,它们是“不打不相识”的关系。如果时间把艺术打败,它们将成为敌人,艺术也将成为伪艺术,被时间抛弃;如果艺术把时间打败,艺术和时间将会成为一对亲密朋友,艺术也将成为真正的艺术,与时间一起永存下去。 没有一个艺术家或作家不愿意自己的艺术成为时间的战胜者,所以在有些场合,比如文学研讨场合,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的作品是写给五十、一百年之后的读者读的”,“五十、一百年之后再看吧,我的作品还活着”……说这种话的人是带有底气的,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打败时间。而拥有这种信心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天才,比如梵高,生前的价值不被人认识,他用最终打败了时间的作品来为自己获得声誉;还有一种是蠢才,自高自大者,作品不行,活着得不到重视,用时间来给自己开脱,其实百年之后,他自己也死了,在场听到这话的人也死了,谁知道是否还有人读他呢。 艺术与时间的对垒终究是残酷的,所以梵高就说:“我认为这是伟大人物经历中的一幕悲剧……他们往往在作品被公众承认以前就死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遭受着为生存而斗争中的障碍与困难的不断压迫。”但梵高对自己作品的遭遇却全然不介意,丰子恺先生写道:“他并不因了俗众的不理解而失望,也不因了商卖的美术界的屏斥而灰心,毕竟他是有实际的精神的根据的。”——梵高说我的内心仍然是安静的,是纯粹的和谐与音乐;我的最大的愿望是创造美的作品。 梵高相信时间。“我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说。 本书为著名作家、评论家、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石华鹏的散文集。其内容广泛,有写古建筑、古乡村、美丽新乡村,有些历史人物、现实人物,有写生活思考、艺术思考。文章从个体的生命境遇出发,珍视人生旅程中遇见的城与村、人与物,变换着叙述者的生命坐标、地理坐标或时间坐标加以再次打量,穿透人间烟火、岁月光影笼罩着的寻常细微处顿悟出深沉的感动和感悟,呈现生命的温度、历史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