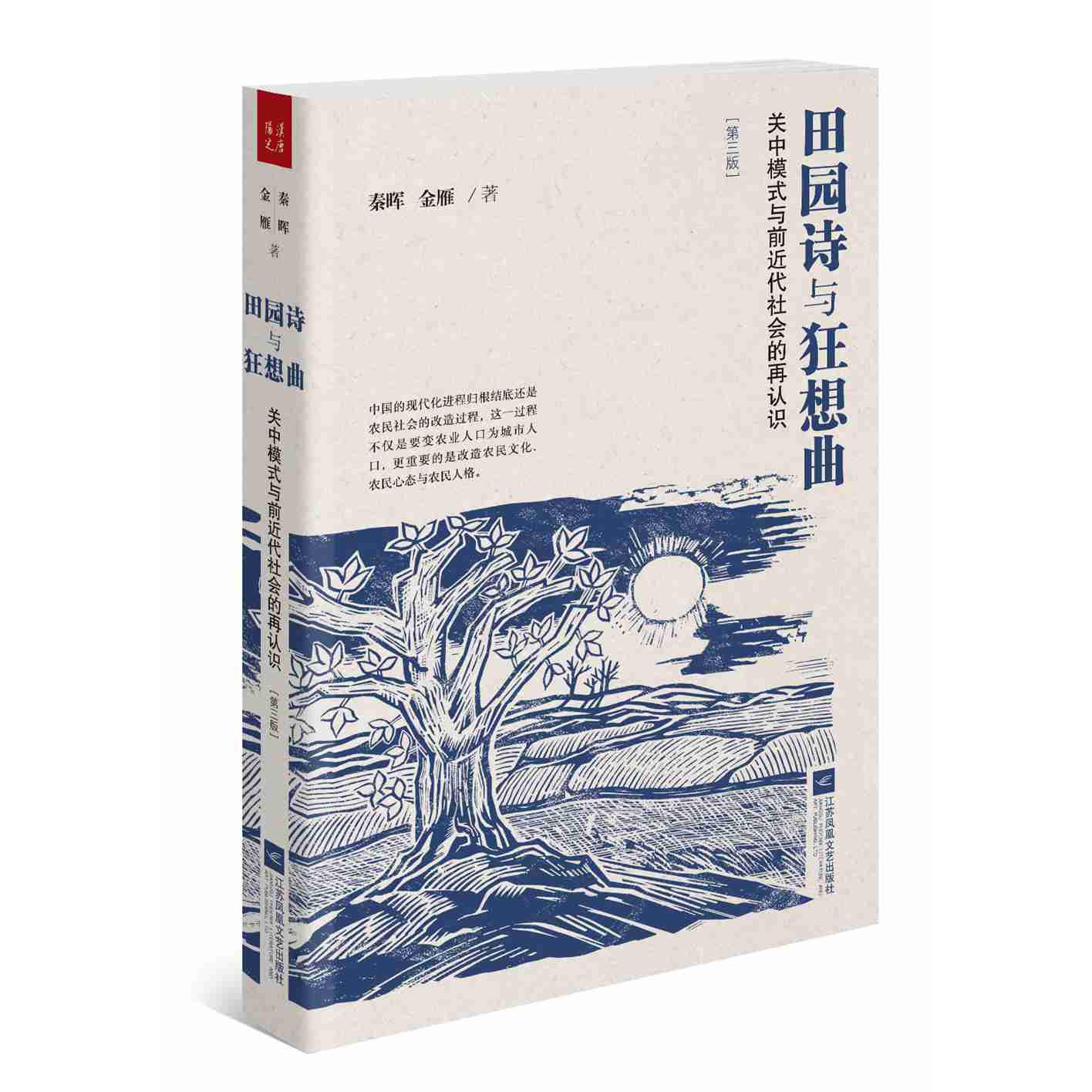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6.10
折扣购买: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版)
ISBN: 97875594044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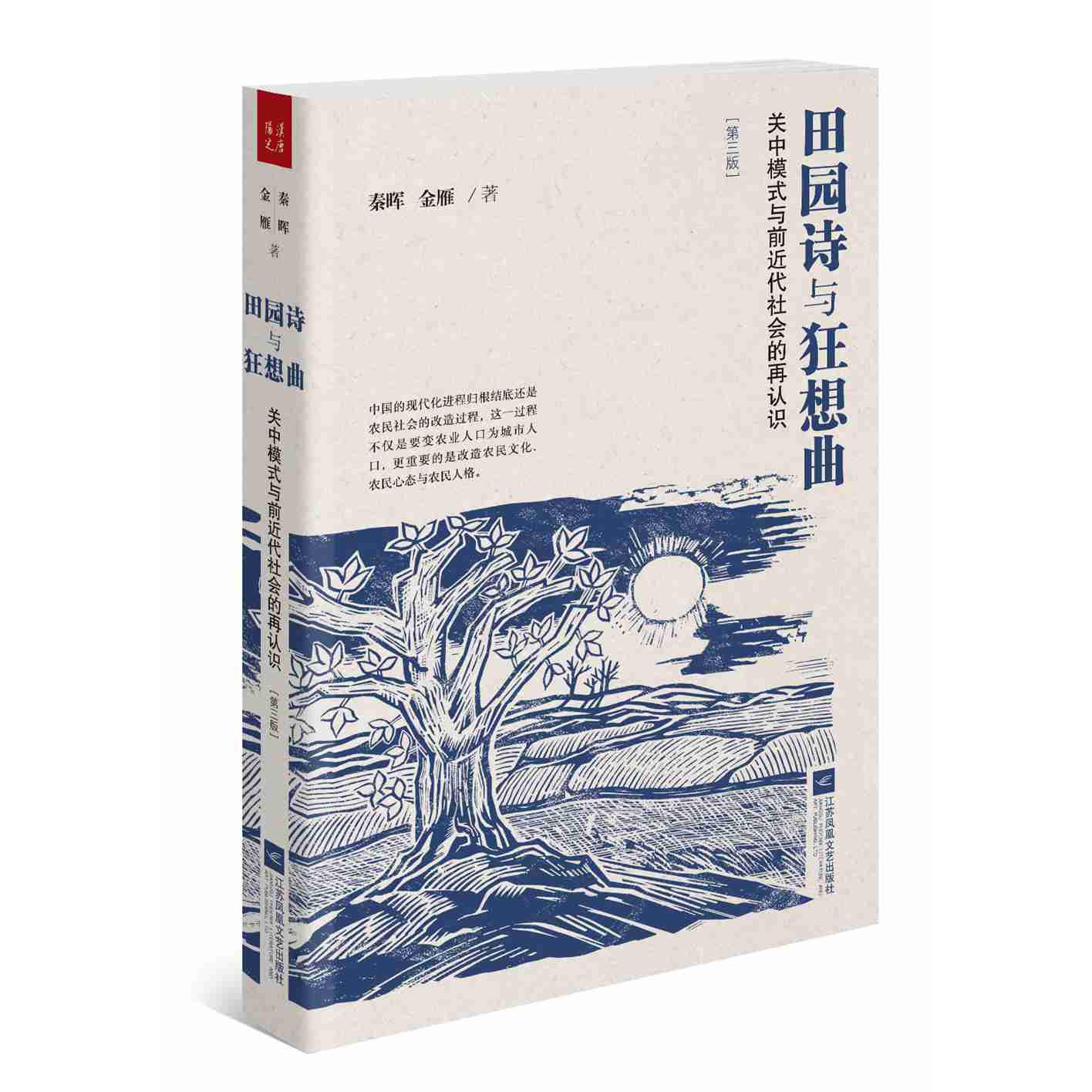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已退休)、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南非的启示》《共同的底线》《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问题与主义》等。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新饿乡纪程》《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火凤凰与猫头鹰》等。
束缚与“保护”:一张恢恢天网 封建主义对农民意味着什么? 在农民的理想中,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应该意味着保护而不是束缚,由这种关系形成的宗法共同体应该只有宗法式的温情而没有严酷的父权,只有田园诗式的和谐而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在这种共同体中的自然经济应该只有“鲁滨逊式经济”中那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的幸福”而没有“命令经济”下的超经济榨取。如果封建社会中的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没有这样的价值追求,那么仅仅靠封建主的淫威,这个社会是无法维持的。封建社会绝不仅仅是一小撮坏蛋犯下的罪行。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是经历过封建制的每个民族的每个社会成员共同背负起来的。 但是,为人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化、个体化的发展终将与这种自然人的宗法式纽带不相容。为了维护这种纽带,便需要限制乃至扼杀这种个性发展,而为限制这种发展就必然要有等级的权力,要有高高在上的“天然首长”,而只要社会生产能够提供剩余产品,“自然人”的私欲便会使“天然首长”运用这种权力把它作为攫取的对象,从而置广大共同体成员于被束缚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宗法农民作为价值追求的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他们所反对的封建主义的“坏的方面”恰恰互为因果,和谐统一。他们要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他们若要摆脱束缚,便不能依恋任何外在的保护,而必须按“人不靠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生活。他们要么成为同时摆脱了束缚和保护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获得任何自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完全达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以前,这是个铁的逻辑! 因此,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面前,每个想卸掉这一十字架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每个人,都要在这种两难处境中经受考脸。他们必须学会面对一个竞争的、动荡的、有风险的世界,而不能期望在打倒封建主以后重建一个田园诗式的乐园。 “家族凝聚力”之谜 前面我们论证过宗法共同体与自然经济(习俗—命令经济)之间的逻辑联系。并谈到前近代中国“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的若干特征。按逻辑,这样的共同体似乎应当在习俗—命令经济全盛时最为巩固,而市场关系兴起后它们就处于解体过程之中了。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当60—70年代“命令经济”一统天下时,中国的传统家族纽带曾遇到空前的危机。当时在“彻底”反传统的口号下,不仅宗族组织、祠堂、族谱没有存在的权利,就连家庭关系也受到“亲不亲,政治分”的强烈冲击,子造父反、夫妻分派、“划清界限”、六亲不认成为时髦,而“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则成为那时典型的“时代语言”之一。而到80年代后,随着改革的进程,“命令经济”逐渐为市场经济所排挤。传统家族纽带在这一过程中却似乎恢复了蓬勃生机。当前在农村中,农民自发地修谱建祠、联宗祭祖、敬宗收族已成为新的时髦,而且这种现象的中心与当前农村市场经济发达的中心高度重合,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宗族复兴”的势头最盛(其中又以“市场性”更强的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闽东南更突出,而以社区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地区则稍逊之),相反,在市场关系不发达、较为闭塞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宗族复兴”的现象却不明显,一些贫困农村甚至完全处在一种闭塞加散漫状态中,传统宗族意识、旧体制培养起来的政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契约性社团意识一概不起作用。 “宗族复兴”现象引起了两种议论。有的人惊呼“封建宗族势力复活”,主张对此大力抑制。有人则认为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活力和独有魅力之所在,主张增强这种传统凝聚力以填补原有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凝聚力逐渐淡化之后出现的空白。后一类观点强调宗族复兴与东南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步性,认为宗族文化对中国农村“经济奇迹”具有重大意义。在他们看来,宗族文化比“个性文化”更优越,它是东亚发展模式的灵魂,甚至是“东方救世”、克服“西方病”、走向“后现代”的基础,等等。 我们觉得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其实只要上溯于历史,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始于今日。近古中国社会一直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一般认为产生于并适应于自然经济的宗族观念与宗族组织,在经历了秦(西)汉与宋元两个“淡化”时期后,并没有随着宋元以后商品经济的兴起而进一步衰落。仅仅如此还不足为怪,人们可以解释为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变化滞后。或者说那时的商品经济毕竟不够发达,未能根本改变自然经济格局,因而也不足以瓦解宗族组织。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宗族组织在宋元以后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局部出现了日趋强化之势,而且这种变化似乎与通常的逻辑推论正好相反。从时间上看,明清商品经济的发达无疑要胜于宋元以前;从地域上看,明清商品经济的成长无疑在南方比北方明显,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明显,东南沿海又比长江流域明显。然而宗族“传统”的“复兴”与强化,却都以前者为甚。宗族观念与宗族组织,以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宗族法规、族长、族权、族产、族墓、祠堂、谱牒乃至祠堂审判等制度,总的来说都是明清比宋元发达、东南沿海比长江流域发达,长江流域又比黄河流域发达。近代中国许多经济落后、风气闭塞的北方农村已经遍布多姓杂居村落,宗族关系淡漠,而不少南方沿海农村却是村多独姓聚居,祠堂林立,族规森严,族谱盛行。这就不能仅用“意识形态滞后”来解释了。 那么,难道“中国文化”竟是如此之特别,以至于商品经济瓦解宗法共同体这一几乎遍见于各民族的发展趋势(无论其强弱缓急与人们对它的褒贬)在华夏大地上竟然被相反的趋势所代替? 其实未必如此。许多资料表明,市场机制对宗法关系的冲击在近古的中国同样是存在的。明代著名官僚、广东人庞尚鹏所著的《庞氏家训》正是那种明清多于前代、东南多于内地的宗族法规类著作中十分有名的一种。书中规定:庞家族人必须乡居,远离商品经济活跃的市井,否则“住省城三年后,不知有农桑;十年后,不知有宗族。骄奢游惰,习俗移人,鲜有能自拔者”。类似的劝诫,在那时的族规家训类作品中比比皆是。抛开其中视非农行业为“骄奢游惰”的陈旧价值观不谈,这类劝诫指出的事实是,在“宗族复兴”的彼时彼地,商品经济对宗法关系同样形成了冲击。以至于卷入其中的人们不久便“不知有宗族”,而且这不只是个别“堕落”者,而是普遍现象,即所谓“习俗移人,鲜有能自拔者”。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彼时彼地的“宗族复兴”的呢? 答案也许是多元的。例如以M.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功能学派社会史家认为“水稻经济”的特点(剩余率高,适于劳动密集型家族,兴修水利需要合作等)使它比旱作业更有利于宗族的发达。 再如,社会史的个案研究显示,近古中国宗族观念与宗族组织发达程度之差异,至少一部分实际上是发生在“土、客”之间。即土著居民与移民社区(南方许多地方称为“客家人”)之间。只是由于客家势力近古以来在东南的崛起,才使这种差异仿佛成了北方人与南方人、内地人与沿海人,宋元人与明清人的差异。事实上,在许多历史上长期存在“土客”矛盾的地区。客家人中上述宗族“传统”保存与发展的程度最高。与此同时,当地的土著居民社区尽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客家邻居差不多,却存在着明显的宗法传统淡化趋势:多姓杂居村落普遍存在,宗族组织解体,祠堂、族规与宗谱往往失修,族产(以及宗族对个人财产的干涉权)若有若无,在社会生活中已无足轻重,等等。而客家人祖先所来自的北方地区(如所谓“大槐树”所在的“洪洞县”等地)宗族关系的发达程度也同样低得多。 这种差异不难理解。客家移民到南方后,在面临当地土著包围与敌视(至少是异视)的条件下,只有强化自身的群体凝聚力,更紧密地抱成一团,才能在严峻环境的挑战下生存、竞争并得到发展。而宗法关系是当时条件下群体凝聚力所能找到的最适合的象征形式。另一方面,当客家人借助于群体凝聚力生存下来并增强了实力后,也就会给予宗族关系以新的经济支持,如投资扩建祠堂、置族产、修族谱等。而土著居民缺少这种环境压力,他们的宗法传统便很“正常”地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淡化了。 ◎本书是中国农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研究农民学不得不看的力作。 ◎现今“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从书中找到某些答案。 ◎此次修订,增加了第三版序言,以及附录“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土地关系: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