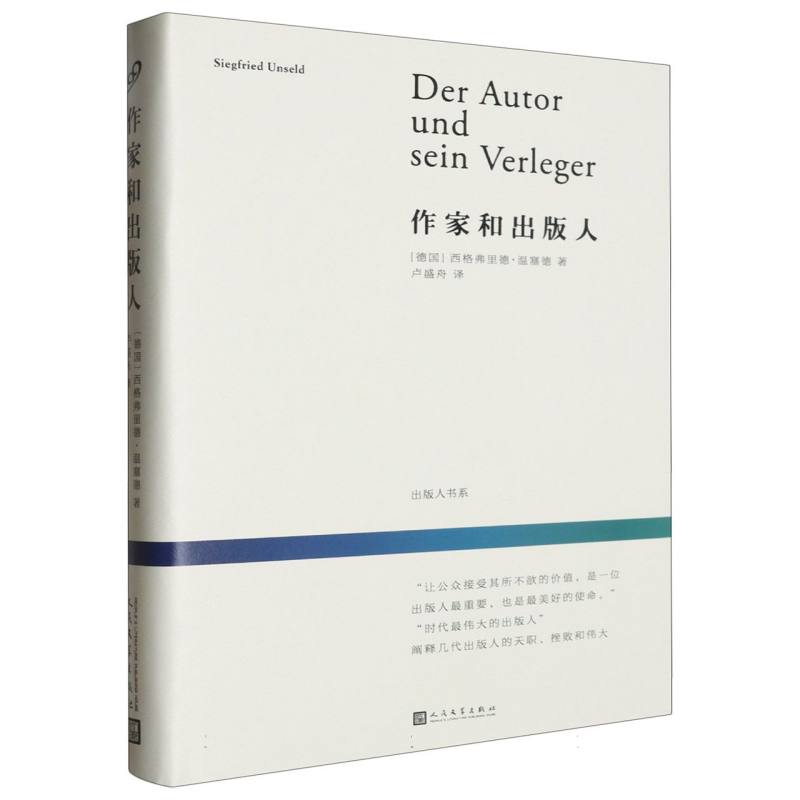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49.00
折扣购买: 作家和出版人(精)/出版人书系
ISBN: 9787020132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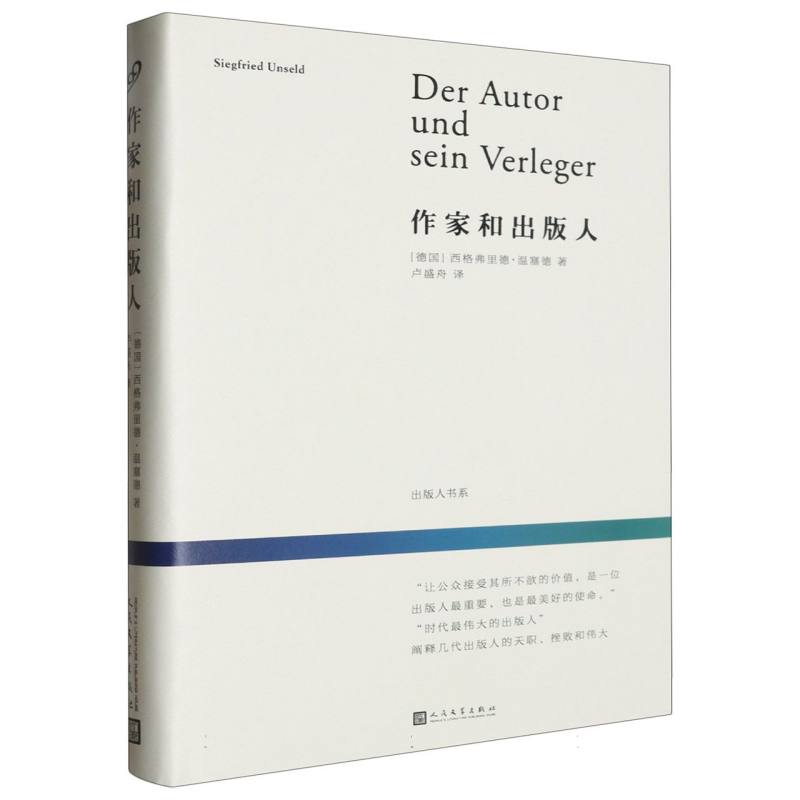
西格弗里德·温塞德(Siegfied unseld),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出版人之一。1924年生于德国南部的乌尔姆,1941年应征入伍,担任海军无线电报员。“二战”结束后,受黑塞《悉达多》的影响,决心投身文学,遂考入图宾根大学,并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 1952年,经由黑塞的推荐,温塞德加入苏尔坎普出版社。1959年彼得·苏尔坎普去世后,温塞德领导苏尔坎普成为德国最经典、多元、进步的出版社,并在1963年收购了岛屿出版社。温塞德秉持冷静而热忱的出版理念,出版德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如赫尔曼·黑塞、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马丁‘瓦尔泽、莱纳·玛利亚·里尔克、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等的作品。苏尔坎普出版社也坚定地出版推动时代思想进步的哲学思想类图书。其出版的西奥多·w.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斯、沃尔夫冈·科朋等的作品也早已有定评。 温塞德以其博学、冷静、务实、清醒和理想主义,深刻改写了20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出版和教育版图。其亦著有《与赫尔曼·黑塞的通信》《歌德和他的出版人》《黑塞及其作品的影响史》等。 2002年,温塞德在其位于法兰克福的寓所去世。
1.作家与出版人的冲突 前不久,一位社会学家 在给一家出版社的信中称: 拿破仑曾下令枪毙过一位出 版商,单凭此举,他就堪称 伟大。歌德对书商(他指的 是出版人)的愤怒更是家喻 户晓:“所有的书商都是魔 鬼,必须给他们单独造一间 地狱。”黑贝尔知道:“与耶 稣行走于浪尖,要比同一位 出版商过活容易得多。”古 典时期的作家是如此看待出 版商的(在这方面,从前的 出版人的工作似乎要容易些 ,因为我们得出版当代作家 ,同时也要出古典作家的作 品!)。马克斯·弗里施在 他的第二本日记里描述了他 对法兰克福书展的印象:“ 一位作家和一匹马的区别在 于,马听不懂马贩子在说什 么。”若干年前,伟大的英 国出版家弗里德里克.瓦尔 堡给他的回忆录命名为《绅 士的职业?》(当然得加个 问号),现在,他的同行们 可是不敢这么做了。如今, 出版人的形象成了“富有、 精英、保守、权威”的代名 词,他被说成是从事审查工 作,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和 受益人。纽伦堡的出版商约 翰·菲利普·帕尔姆在不惑之 年被法兰西军事法庭判处死 刑,理由是其“撰写、印刷 和传播对领袖大不敬的污秽 文章”。如今,我们会对帕 尔姆的出版行为作出有别于 法兰西军事法庭的判断,同 时也得一分为二地看待歌德 当年的愤怒,这并不是因为 他在同出版商打交道上发展 出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克里 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将 他与科塔就《与席勒的书简 》出版一事所作的讨价还价 描述成“不成体统”),而是 他首先有权利为盗版感到愤 怒,因为盗印者无需支付稿
书籍目录
章 文学出版人的职责 第二章 赫尔曼·黑塞和他的出版人 第三章 贝尔托德·布莱希特和他的出版人 第四章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和他的出版人 第五章 罗伯特·瓦尔泽和他的出版人
试读内容
作家和出版人的冲突
作者和出版人之间时有发生的不愉快来源于出版人这份工作奇怪的两面性。他必须——正如布莱希特所说——生产并且销售“神圣的商品——书籍”,也就是说,他必须把思想和买卖捆绑在一起,使得文学家得以维持生计,出版商得以维持出版。1913年,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用他的方式描述了这一情形:“出版商用一只眼睛盯着作家,用另一只盯着读者,但他的第三只眼——智慧之眼——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钱囊。”
但是,思想加买卖这个公式未免以偏概全。按照拉尔夫·达伦多夫的描述,出版人具有“社会地位”,他的个人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公共职能。任何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必须满足一定的期望。达伦多夫谈到了“期望”中的“必为”、“应为”和“能为”。以出版公共书籍为己业的出版人特别受制于这些“期望”。他欲使文学成为可能,就需要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出版人根据自身的个性和特点(他是对这份职业的艺术层面、技术层面或者经济层面感兴趣,还是对纯粹的文学层面)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彼得·迈耶尔多姆在他的论文《出版人的职业理想和主要准则》中首次发展出一套出版人类型学。他立论道:“在制定出版人类型时运用族群认同的现象,相较于定然不恰当的‘商业/文化’模式,能更好地考量其不同动机。” 出版人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他为企业行为承担着思想上以及经济上的责任,因为他凭一己之力为这些书和他的企业担保,不仅要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思想责任和法律责任,还要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只要书籍还具有商品性,这样的情况就会持续下去。作者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出版商交织在我们社会的经济中,只有当这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了,书籍的商品性才能发生改变。但这是否值得期待,对此我们心存疑窦,因为我们目睹了现如今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为了改变书籍的商品性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查禁、审查、自审、沉默,这一切并不鲜见。在此,我们已经引入了第二个问题:一个像其他所有企业一样以资本为组织、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社,在多大程度上能生产出继承伟大传统、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文学,特别是那些明确反对利益化、反对毫无节制的增长、反对剥削我们生态基础的技术和文明、支持新的个人基本权利的政治文学。出版商支持那些巩固个人基本权利、使甘为邻人做事的个体变得愈加强大的书籍,支持那些讨论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新形式、新理论的书籍,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他出版主张不断突破社会强制以获得自我解放的书,同时作为一名企业家,他又必须强求效益和工作纪律。
这难道就是迪特尔·E.齐默尔所指的“出版人不能承受的角色冲突”吗?、
出版人的角色冲突
我认为,出版人向来就必须承担这种角色,包括那些反映或推动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化史发展的文学出版人。文学史向我们表明,贫瘠之年如铁律一般紧随诗意年代到来,那时,次要之物会粉墨登场。有的时代,作家肩负政治介入的责任,有的时代,作家必须踏上“通往内心之路”。1830年后的德国文学,“青年德意志”的自由革命派作家尾随浪漫派而至,随后一个向内的时代重新到来,直到终又让位于自然主义之潮。
在瑞士文学史中,我们能观察到同样的进程。裴斯泰洛齐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的前言让我难忘:“告诉人民一些重要的真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本书愿为此尝试作历史奠基。”七十年后,年轻的凯勒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那些不把自身命运和公共团体联系在一起的人是多么不幸,因为他不光不会寻找到安宁,反而会失去内心所有的坚持,遭受人民大众的鄙夷,宛如路中央的杂草。”还是七十年后,准确地说是1914年12月14日,卡尔·施皮特勒在苏黎世的一个行会大厅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政治演说,它引发了一系列充满政治关键词和人性思想的宣言,其中美的一份宣言来自莱昂哈德·拉加兹的《新瑞士》一书,书中提到了“世界公民权”,并要求这种权利必须高于所有公民权。一晃又是七十年,马克西·弗里施为了重建瑞士人的自我意识,考察并分析了瑞士神话。
1945年,争结束后,当面临重建家园的那一代人的震惊消散、创伤愈合后,文学变成了纯粹的文学。这种新文学以沃尔夫冈·波尔谢特的《在门外》一剧起头,紧随其后的是海因里希·波尔的短篇小说、君特·埃希和保罗·策兰的诗。直到后来,文学和作家作为那场青年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和伴奏家,才日趋政治化。
当代的出版社必须从自身出发,反思凡此种种的进程。出版人必须在心中划清讨论的界限,恰因我们德国人凡事都倾向于,无法获得赫尔曼·布劳赫所言的“折衷式的激进”。恰因我们肯定了这个社会,想给予它改良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出版那些传播进步理论的书籍,以供人讨论,因为现如今我们看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讨论是无法进行的:我们每天都能听到作家和作品遭受打压的新闻。索尔仁尼琴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个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例子。还有其他许多案例,比如罗马尼亚作家保罗·格玛,他在一次采访中强调,他希望他的书能重新在罗马尼亚出版,当然,他不知道何时,他的哪些书能得以出版,能多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通过法律手段获得了布莱希特遗作的出版权,但直至1977年,它甚至连苏尔坎普出版社早已出过的文章都没出全。有些出版人希望只出版文学作品,却发觉自己受旗下作家牵连,也被卷入到了政治漩涡中。不管是帕尔姆、葛申还是科塔,出版人总是身处这种冲突之中。主张社会变革的人即便不是先锋,也是小众,因为文化历来就不属于大众,它属于少数派,属于富有,往往是一种偶得的幸福。谁主张改变,谁认为文化必须民主化,谁把文化理解为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进程,谁就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与自身时代的冲突中,这句话特别适用于那些不追求畅销书籍的出版人,那些为进步书籍出力的出版人。
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出版进步书籍并不抵牾。因为人们应该想到,一家以资本主义为经营模式的出版社若能致力于澄清个体的心灵发生结构和社会的发生结构,从而对它的自身基础进行反思,那么客观来说,它对社会的进步所做的贡献是要大过由于自身基础就放弃进步的行为,这种自身基础能使它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能通过改变个人进而有机地改变社会本身。里尔克(在1915 年6 月28 日的信中)写道—— 这句话会让没有读过里尔克作品的人大吃一惊——“我们的工作如果不是促进单纯、伟大、自由的变革,那还会是什么?” 因为变革是一切伟大文学的动因。伟大的文学通过让人不安而使人强大,伟大的文学讲述现在曾经,也述说将来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