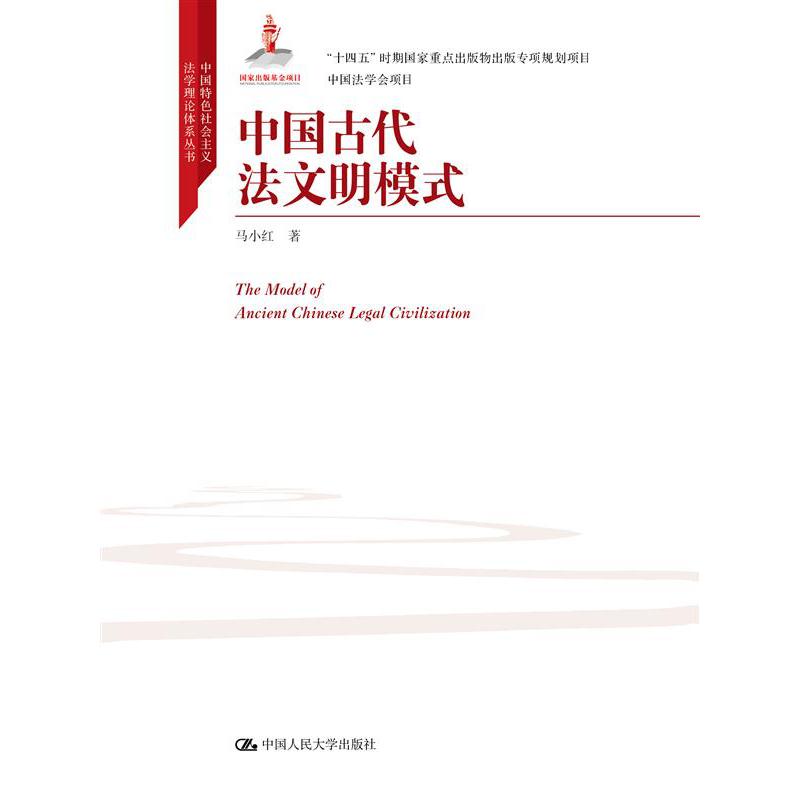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原售价: 168.00
折扣价: 117.60
折扣购买: 中国古代法文明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丛书)
ISBN: 9787300318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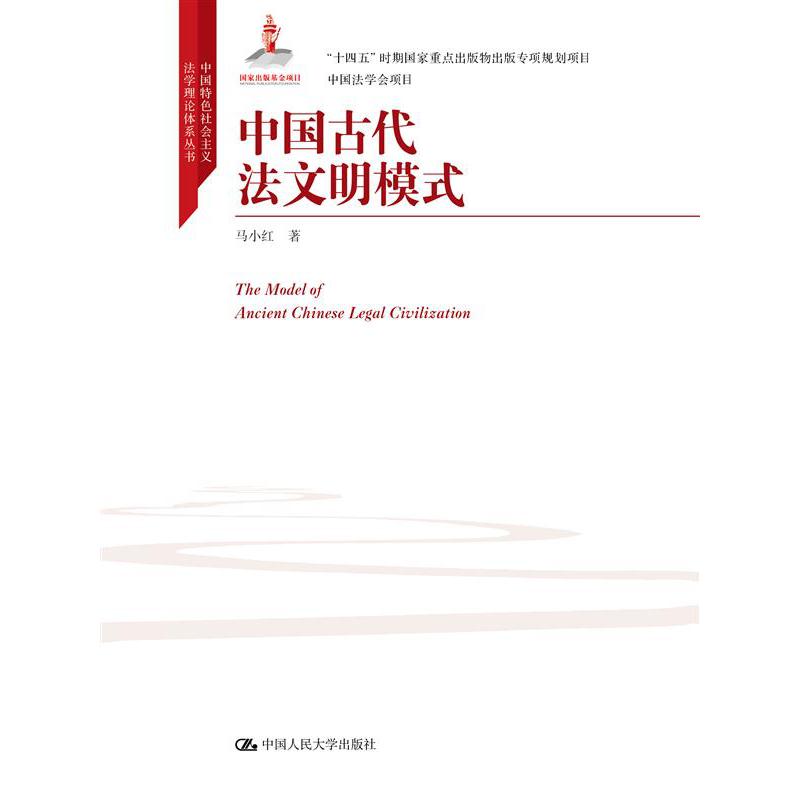
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与学术委员、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曾就职于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教学与研究,为本科生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文明史”(全校通识课)、“全球法律文明”(全校通识课,与其他老师合开),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专题”、“《唐律》选读”、“中西法律思想史概论”(与其他老师合开)及“法律史概论”(与其他老师合开),为博士研究生讲授“法学方法论:史学的方法”“法学前沿:中国法律史”等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作有《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中国法思想史新编》《古法新论:法的古今连接》等。多部专著和论文被译为英文、韩文出版。
本书欲探究的问题
本书是对课题研究成果的修订,课题从2010年立项到结项历时5年,从2015年结项到现在又过去了7年多,其间有两个问题始终萦绕在笔者的脑海,即:中国古代法文明模式的特点究竟是什么?独树一帜的中国法文明与其他法文明的共同之处又是什么?其实,这“不同”(特殊性)与“同”(普遍性)的问题同样一直存在于近代法史学界。探究起源、梳理沿革、介绍典章、分析体系、描述制度、思索先人的思想理念,笔者在这些年中一个一个专题地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回答中国古代法文明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如果不关注法文明的普遍性,我们在现实的法治发展中就会迷失方向;而如果不关注法文明的特殊性,现实的法治发展则难以接地气,难以寻求到现实法治发展的传统动力。
(一)寻找中国古代法文明模式的“特点”
说到中国古代法文明模式的“特点”,应该注意两点:第一,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是近代以来西法东渐的产物。从1902年清末修律开始,西法成为中国“变法”的仿效目标,这是近代中国无奈的被动选择。西来之法不仅改变了中国承袭了数千年的法的制度与体系,而且也冲击着人们的法律价值观。第二,一脉相承的中国数千年的法在近代解体后,其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就习俗及观念而言,古代法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消失。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总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传统法的影响和约束。在变法中,仿效的西法模式在传统影响下不自觉地变形。古代法文明在西来法文明的冲击下,虽支离破碎但仍然顽强地存在并影响着现实。中法与西法两者在变异中融合并摸索相互兼容的途径。然而,这个“兼容并蓄”也并非一成不变。
19世纪以来,每当立法之时,人们必会问西法的规定为何。清末修律时,修订法律馆派出了大量的法科留学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法律及法学名著,并请外国的法学专家来中国帮助立法。借鉴、吸纳甚至仿效西法,其实一直是近代中国法律变革的主旋律。每预立一法,国人便会放眼看一看美国如何、欧洲如何、日本如何等等。但在20世纪的后半叶,中国学界在关注国外的同时,也开始关心起中国古代法如何。如今法学界更是有很多学者将眼光投向中国古代法文明蕴含的现代法因素。中国古代法文明中是否有权利观念、权力制约的思想、类似宪法的母法、类似民法的理念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说明中国古代法确实离我们渐行渐远,以致非经“专门”的研习而无法确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现实社会的法律发展中,兼容并蓄不仅是中西的融合,而且包括了对古代法的借鉴。法的古今连接已经改变了以往被动地被影响的局面而成为自觉复兴。
说到中国古代法文明究竟“有没有”的问题,其实涉及法文明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但凡是人类社会,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大致是相同的。其实,从贴近民生的法律看,便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中国古代社会有纠纷的存在,西方社会、现代社会同样也有纠纷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中有罪与刑的规定,西方与现代的法律中同样有这样的规定。古今中外面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在于对同样问题阐述的角度、表达的方式和解决的方法不同,这就是特点。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从“二十五史”的《礼乐志》中看到礼就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根本大法”,从《选举志》中看到科举制就是中国古人对“权利”“平等”的追求,从《五行志》中寻找到中国古典式的以体恤弱者为特征的“自然法”思想……当我们从浩瀚的资料中勾勒出中国古代法文明模式,澄清了一些误解后,再用现代社会的法思维方式或理念去阐释中国古代法文明时,过去的法便具有了现实的价值。
中国古代法在近代的变革中不仅证明了其优秀因素是可以与时俱进的,而且在实践中也证实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凡是自觉地利用了传统作为支撑的法律制度,比如人民调解制度、综合治理等等,在实践中就会执行得较为顺利,基本能获得立法的预期效果;反之,与传统抵触较大、从西土引进却又缺乏本土法资源支持的一些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往往会产生“南橘北枳”的结果,如梁启超所总结的那样:
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即20世纪的初期,在中西法融合中发生“南橘北枳”的现象,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当时的中国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无暇对来自西方的自由、平等、竞争、权利等新观念以传统为平台主动地发掘与融合,也无法对西来的这些概念或观念细致地正本清源,所以难免产生误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中西法契合点的考察也不免片面,因为效法西方法则必解体中国法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是必然而合理的。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明、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传统永远是融合与创新的基础,合理地维护、利用、改造、更新传统,才会产生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就如同古代中国对来自天竺之国的佛法的兼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一样,外来的法治也只有在以传统为基础的兼容并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活力。
(二)寻找不同文明中法文明模式的“共性”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阐释“灋”(法)字的含义是:“水”部表示法律的目的在于公平,即“平之如水”;“廌”表示在法的形成时期人们对神断的信赖;“去”表示法律“去不直”的本质。其意为以神兽廌来裁断,使有罪或“不直”的一方受到惩罚以达到公正。廌是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独角神兽,其特点是明察曲直,性知有罪。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官”皋陶进行裁断时的工具。在裁断中,皋陶常以廌的是非为是非,廌以独角触碰的那一方,即为有罪或理屈的一方。而在西方古代,法的正义理念是通过“正义女神”的形象传递给世人的。古罗马时期的正义女神,将古希腊传说中的诸正义之神集为一体。女神以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宝剑的形象立于世人面前。持天平,象征着依法裁断的公平,如中国古代“灋”字中的“水”部;一手持宝剑,表示对恶行决不姑息,如中国古代“灋”字中的“廌”去“不直”。中国古代的“灋”字与西方的正义女神,反映了中西法文明中所具有的共有理念———对正义的维护和追求。
法正义性的实现,在中西的发展也经历了相同的路径:从寄希望于神明到寄希望于人类制度的自我约束。公元前621年,雅典的执政官德拉古将不成文的雅典法律汇集起来并公之于众,西方史学家的评论是:尽管德拉古颁布的法典像大多数古代法典一样,很严厉,但这毕竟是走向公正和民主的一步。因为它使民众明确知道了法律的内容是什么。而在公元前536年的中国,杰出的改革家子产也将“刑书”铸于象征权威的鼎上并公之于众。当时的贵族反对道:这种破坏了等级制的一视同仁的做法,将会导致民众据法为一己私利而争斗不息,即“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但同时,有更多的政治家和民众接受了这种较“神断”更为公平的做法,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中出现的“权利”思想的萌芽。其实,公正与权利的理念,伴随着法文明的产生而产生。这种相对独立发展的不同文明中的古代法所具有的共同理念,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社会的法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正是中西法文明,也是古今法文明的契合点。让我们以调解制度为例,剖析这种不同法文明中的“共性”。
调解,是农耕社会中中国古人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我们今天看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便可发现其中蕴含着法主张的“公正”与“权利”的共性。第一,调解主持人须在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裁决。纠纷的双方可以充分地申诉;而参加调解的众乡亲也可以依据礼教及法律发表个人的见解,并根据双方的日常表现和自己的观察对双方陈述的真伪进行判断。第二,纠纷调解的主持人是生活于乡民之中的德高望重的人,有着“公正”的口碑。其较官员更具有民望并容易了解事实的真相。调解主持人的威望是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所以他的裁决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参与者都有着官员无法比拟的说服力。第三,乡间的调解不仅较到衙门打官司更能保全双方的脸面,而且成本也低得多。这种程序便于启动,可以及时地将矛盾化解在初起之时。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调解过程也是一个有效宣扬礼教与法律的过程,更是一个深入解析“天理、国法、人情”的过程。正因为古代的调解制度中蕴含着不同法文明中“正义”“权利”“和谐”等共有的价值观,所以它才能“与时俱进”,延续到今天并走向世界。
即使在近代传统法律制度瓦解之时,调解制度在中国的立法与司法中也未曾消失。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自治施行法》《区自治施行法》,规定了在乡镇、区一级设立调解委,以办理民间调解事项。1935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组织、调解事项、调解期日、调解方式和调解结果等作了规定。从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人民调解制度”,也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翻阅《人民调解手册》,可以检索到大量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案例。
产生于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不仅在近代的中国没有中断,而且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法文明的相互冲撞融合,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西方学者认为,近年来,西方“ADR运动”和“恢复性司法”直接借鉴了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因为其较单纯地通过法庭的裁判解决纠纷,更有利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更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调解制度使纠纷的双方或多方都能达到满意,开创了纠纷解决的多元途径。调解制度是一种既节省成本又不损公正的法律智慧。
寻求中国古代法文明与其他法文明中的“共性”,是促进中国古代法现代化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