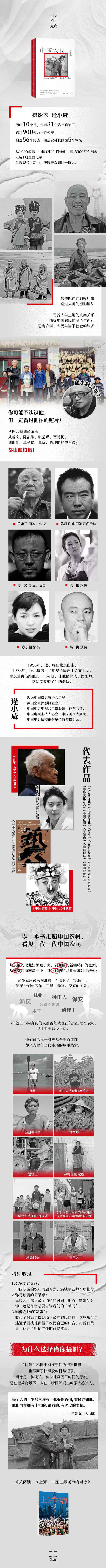出版社: 上海光启书局
原售价: 189.00
折扣价: 122.90
折扣购买: 中国农民
ISBN: 9787545219814

逄小威,1956年生于北京,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体育频道、中国电视主持人协会等单位特邀图片摄影师。亚洲资本论坛、《亚洲资本》、《中国银幕》杂志社首席摄影师。长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风采。代表作包括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黑白肖像摄影作品《面孔》、中国历届奥运冠军肖像摄影作品《英雄》、《光荣与梦想》、《国家大剧院与艺术家》、《中国京剧》、《王佩瑜》、《山河记忆》等。
序?中国农人与社会演变(选摘) 温铁军 在中国,“农”是最重要的家国大业。古代是,今天还是。所以我们的日历称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也是为农耕而设。古人文字中有“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出自战国时期的《谷梁传 · 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而一般文献中的“民”往往与“君”相对。近代文字中,“民”的词汇丰富了许多,有人民、国民、平民、村民、渔民、牧民、湖民、山民、草民、良民、刁民之说,随之也就有了农民。直白地解释,农民就是以农耕为生的普通老百姓,但习惯上又把渔民、牧民、果农、茶农、棉农、花农等所有在农村百业之中生活着的人都列入“农”之下,统称“农民”。加之近代以来城市化加快,相对城乡二元结构而言,就有了集中在城里的“市民”与分散在十里八村的“农民”之别。这两大类人群在1958年户口制度确立之后,唯城里人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体制相对完整,可以“生老病死有依靠”,而国家财政不能承担农村人口的社保、医疗、教育。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城乡人群不能自由流动,甚至很少有通婚的情况。 近年来,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包括久住城市但无户口的农民,有三亿之多,但这部分人的户籍仍为农民。由于统计指标改为“居住”和“就业”六个月就可被计入城镇人口,这造成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并超过60 %。可实际上,很多农民仍处于两栖状态。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农民和土地都是一体的。古人认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因此大多数朝代更迭都伴随“均田免赋”这一基本国策;今人则“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权益”。孙中山发起土地革命强调“平均地权”;毛泽东发起湖南农民运动则“打土豪、分田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 随着国家工业化要求集中占有农业剩余才能完成资本积累的需求,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民合作社被以乡为单位的高级社取代,接着在“大跃进”时期参照苏联集体农庄的大规模生产组建了人民公社,农民身份很快被人民公社“社员”替代。这一时期,乡村的“五小工业”只能依托人民公社才搞得起来,且主要服务于因国家需求而被推动起来的集体化生产。农民这一政治主体被制度安排进工业化生产的组织化体系中,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引入西方设备技术,形成了较长时期的财政赤字,国内工业品还不具备出口竞争的能力,只能尽可能增加农产品和农村工副业产品的出口。中央在1979年出台了价格“双轨制”,促进了农村的社队工业发展及农民的分工分业,也构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名的改革条件。在集体化解体全面实施的1984年,农民实际上重新拥有了大部分土地权益,农村也由过去的种植养殖业为主,全面转向了“种、养、产、加、销、工、商、建、运、服”等多种产业,乡镇企业获得较快发展。同期,农村贫困大幅度缓解,购买力提高助推了“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 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遭遇1988年恶性通货膨胀和1989年外资撤走“双重危机”造成的“大萧条”后,一方面农村企业大部分歇业倒闭,或转化为私人企业;另一方面,在农村集体经济全面解体期间,“种粮的变吃粮的”“养猪的变吃猪的”……农民群体中的大部分从传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低风险意义的“自给自足”,转为“现代化”的市场化消费,随之开始了复杂的身份演化进程。 一是农户家庭之间开始由以前的“互帮互助”转化为短期的雇用和被雇用关系。每个农民既可是雇用者,又可作为受雇者(彼此雇用)参与生产。各种私人经营的小卖部、饭 馆遍布农村地区。 二是大批农村劳动力从过去那种农忙时节经营或帮助经营家庭农业生产、农闲时节进城务工的模式,改为从事工副业的劳动力流出乡村成为“农民工”,加入产业大军。没有城 市户籍的农民工,往往麇集在“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形成所谓“低端人口”与“低端产业”相结合的过渡性群体。 三是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地产开发而“中产化”。那些通过被征地获取补偿的农民从“小资产阶级”属性的“小土地出租者”变为“房产主”,主要依靠“吃房租”而上升为“中产阶层”。此外还有很多占据着土地使用权但主要靠外部收入的农民群体继续其农地“吃租人”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但在沿海或郊区主要由外地来打工的农民租入有使用权的本地农民的土地,这造成了所谓“租地农场”的生产模式,因增加了地租成本而导向过度化学化、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或者造成基本农田被大面积“弃耕撂荒”。 鉴于此类不安全、高污染的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的城郊和集镇。而大量增加的各类亚健康症状和疾病,以及城市快速攀升的医疗开支等,都促使这些相对发达地区的市民转向自主寻求食品质量安全。于是,21世纪以来“都市农业”和“市民农业”引人注目,中下层市民和“青年白领”为主体的“新农人”成为时尚。同期,随着过剩资本在城市没有投资空间而纷纷下乡,很多新富阶层开始返乡或下乡圈占乡村资源,开办“私家庄园”或“度假农庄”,与一部分农村本身就已开始经营的小型“家庭农场”交相辉映。资本越多流入,资本化农业就越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的产业化全面转向高附加值的领域,如花卉、水果、经济林木等,城郊地区家庭作坊、农家乐、民宿经济体等“三产融合”现象大量涌现。城市与农村在原来二元结构条件下形成的身份差异渐趋模糊……于是,有关部门顺水推舟地提出了城乡融合战略。 此前,1995年以来主流学者们一直在强调“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有一个报告认为,每个农民进城都能带动二十万元以上的投资,如果三亿打工者都进城落户就能够实现70 %的城镇化率,那就是几百万亿的投资需求,就能够带动国内生产总值(GDP)长期的高增长……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那时我们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融入全球化,到2005年中国碳排放量与美国持平,接着又走了十年老路,现在已经是美国碳排放量的两倍。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央在2007年开始强调转向生态文明,并在2012年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举措。 生态文明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多样性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有机整合。自然多样性在城市里有体现吗?没有。真正能跟自然多样性有机整合的就是乡村社会。因此国家2017年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得全面贯彻落实生态文明转型的举措。那以什么作为生态化转型的基础呢?就是乡村振兴。 面对2018年开始的激烈的贸易战,无论转换成什么都得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基础在哪里?也是乡村振兴。我们已经开始以乡村为载体探索推进中国自主货币体系的生态资源货币化和自主资本体系下的生态资本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乡村资源价值化来吸纳国家大量增发的货币。 如此,生态化转型也就使连续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有了软着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农村、农民发展了,发达了,才会有持久增长的内需,才能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