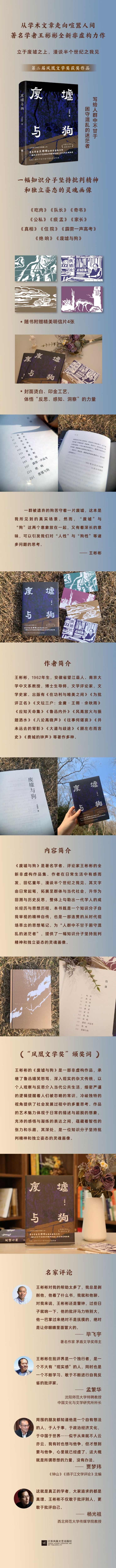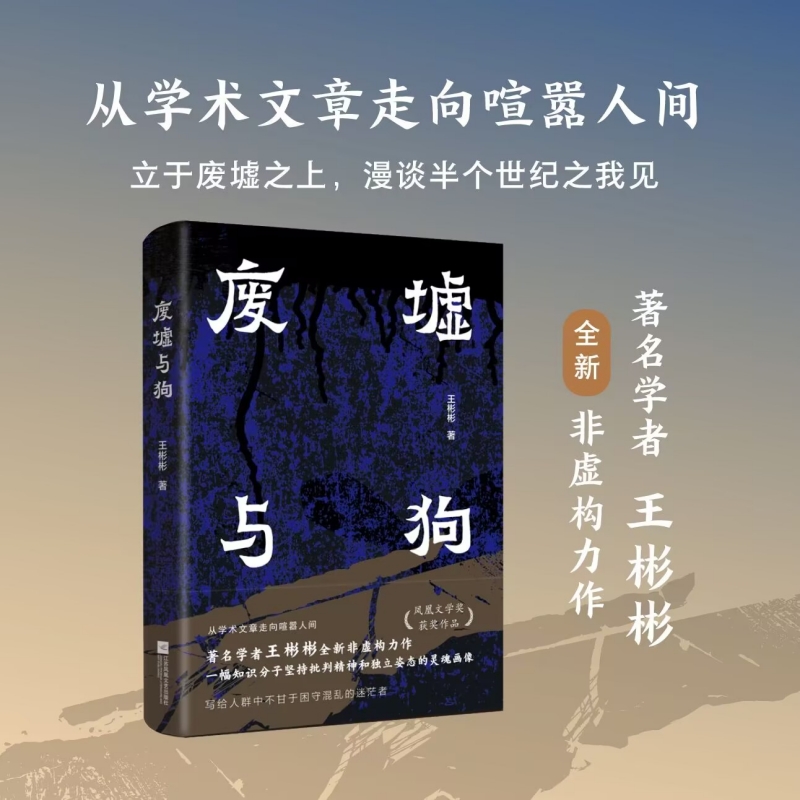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废墟与狗
ISBN: 9787559476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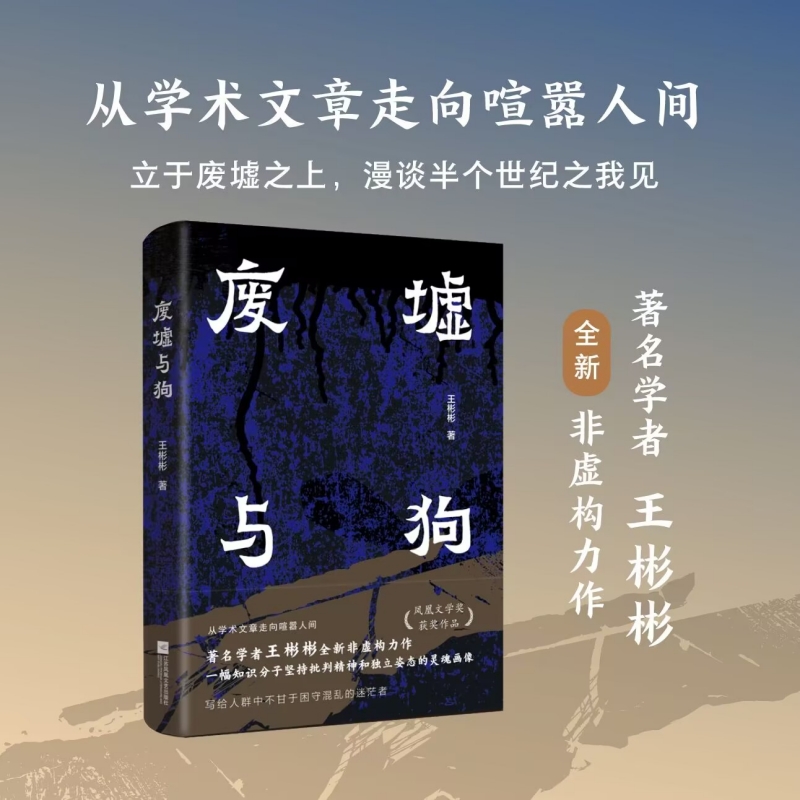
王彬彬 1962年生,安徽省望江县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等著作多种。
废墟与狗 数年前,我在生活方式上奉行的是“四不主义”,即不戒烟、不戒酒、不节食、不锻炼。奉行到五十多岁时,终于觉得应该把“主义”调整一下,变“四不”为“三不”,开始节食了。那原因,就是胖得实在有些难为情;尤其是肚腹,便便得自己都不忍低头看一眼。到个地方去,无论怎么做收腹运动,也是肚子先进门。买条裤子,营业员拿个软尺量了腿长再量腰围,总是轻声惊呼。也难怪,两者实在不成比例。终于决心进行瘦身运动。其实就是节制主食。数月下来,效果是显著的。体重减少了十来公斤,其中自然有一部分是从腹部消失掉的。于是惊喜地发现,几条多年不能穿的裤子,又勉强可穿了。 体重降了十来公斤后,再降就难了。虽然离标准体重还有一定的努力空间,但终于小瘦即安,满足于将体重维持在一个差强人意的水平。就这样维持到了2020年的1月,新冠疫情爆发,于是过了几个月足不出户的生活。到了4月初,百花盛开了,莺飞草长了,我又开始了肚肥裤瘦,好几条裤子,又扣不上裤腰扣了。于是决定再对“主义”进行调整,变“三不”为“二不”:我要开始运动了。 我唯一能坚持的运动,是走路。我居住的小区,十多年前还是山地。周边都是山,虽然不算大山,但也不能说是丘陵,且草木茂盛。山上山下,时有野猪出没。在4月初的一个下午,午睡起来后,我开始了走路运动。出得小区南门,任意往一处山边走去,有一点探险的刺激。我想,春天了,应该有蛇了,于是拣了一根木棍,边走边击打着前面的草丛。最初几天,是在离小区比较近的区域转悠。几天后,想走得远些。翻过一座山梁,走完一条山间小道,眼前突然一亮:一树桃花在眼前盛开着。这是野桃树,很大的一棵。每一朵桃花都像一个笑靥。一大棵桃树就这样在春风里欢笑着,笑得疯疯癫癫的。桃树后面,是一口池塘。池塘也很大。池塘的那一面,有人家了。那前面,应该是一个村庄。 我于是沿着塘坝向似乎是村庄的方向走。拐过一个弯,出现了一座小院,院门左侧竖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废品收购站”,白底黑字,十分醒目。我好生纳闷:在这样的山野之地,怎么会有废品收购站? 继续往前走,开始看见正在拆除中的房屋。沿着进村的小路,两边的房子,房顶都没有了。有的内墙外墙都拆得只剩矮矮的一截;有的则刚刚拆除房顶,窗户还在,只是窗门窗棂都没了。继续往前走,突然一阵狗叫声响起,便见十几只狗向我扑来。大多数是黑狗,有几只是黄的、白的或花的。我是不怕狗的。藏獒一类特别凶猛的犬类,我没有遇上过,不敢说。至于中国农家养的土狗,我很懂得它们的习性。只要你做个下蹲的动作,它便以为你是在捡石头,就会停下扑来的脚步,至少是放慢扑来的速度,显出后退、逃跑的姿态。如果你手里有一根棍子样的东西,哪怕是一根芦秆,只要朝它比画着,它就绝不敢真的近你的身。十几只狗叫喊着向我扑来,我于是举起木棍,迎着它们冲过去,显得比它们更为愤怒。它们立即向四处散去。大多数停止了吠叫。也有几只,退到自以为安全的距离后,仍侧着身子,盯着我,嘴里还发出叫声,但已经像嘟囔了,声音里表达的像是委屈、疑惑,而不是护家的正义、御敌的激昂。 把这群愤愤不平的狗扔在身后,我往前走着,又见一处院落,周边的房子都半拆了,这个院子里的房子还完好着。从开着的院门,可以看见系在两树之间的绳子上晒着衣服。刚才那些狗,便是从这家门前向我发起冲锋。又走了几步,拐过一个弯,一大片断壁残垣在我眼前参差支棱,让我不禁停住脚步。一户又一户,两层或三层的没有房顶的房子,鳞次栉比着,整体上呈半圆形,四周是山。这些房子,有的被拆除得多一些,剩下的少一些;有的被拆除得少一些,剩下的多一些。在忽高忽矮的断壁之间,夹杂着些片瓦未损的人家。片瓦未损的人家,墙上都写着两个字:“有人”。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绿色,也有是褐色。字体各各不同,有的长长的,有的扁扁的;有的好看些,有的难看点。但“有人”两字都很大,且都一笔一画地写着,没有一丝潦草。显然是有意让人远远就能看清。我驻足观看了良久。一幢两幢房子倾圮形成的废墟,当然不难见到。但如此大面积的废墟,我此前只在地震后的 汶川县城见过。地震后,很多遗址原样保留着。面对那样的废墟,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心中的感受。现在眼前的这片废墟,是拆迁造成的。在性质上,当然与汶川县城没有可比性。只是这片废墟之大,自然令人想到四川山区的那座曾经繁华的县城。 往前走一段,又见路边一座小院,在四周的颓败中兀自齐全着:顶是顶、墙是墙;门仍然是门,窗依旧是窗。里面的房子好像有两三进。最前面进大门后的第一进,靠墙是货架,货架上是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当然也有玻璃柜台横在离大门很近处,隔着玻璃可以看见香烟之类的物品。这是村中的小卖部了。院门外,竹子躺椅上坐着一位男子,年龄与我相仿。见我走来,似看我非看我地微笑着。我于是与他聊了起来。终日枯坐在这里,难得遇到一个人,也很寂寞吧,他很愿意解答我的疑问。原来,这是一个大村子,有五百多户人家。当地政府要把此处建成科技园,便要把村民迁走。在别的地方建造安置房,村民三年后可去领房。在这三年里,村民自行到外面租房过渡。租房费用当然由政府出。基本上都搬走了。但还有十多家没有谈妥,他便是这十多户之一。这我就明白了,那些写着“有人”的墙壁,便表达着一种僵持,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钉子户了。在墙上写着“有人”二字,是防止各种各样的人把这房子当成了无主的弃物。当然,主要是防止负责拆房子的工人把这房子也一起拆了。 我向来时的方向望去,见刚才试图围剿我的那群狗,有几只在路上半卧着,也就是腰以下侧身贴地,以两条前腿支撑着前半身;有几只站立着,或慢慢移动脚步,鼻子在路边的杂碎物什上嗅来嗅去;还有几只站在那里,愣愣地,一动不动地看着远方。我指着那群狗,问这小卖部的主人:“这些狗是留下来的啊?”“是的,外面租房子,狗带不走,就丢下了,成了流浪狗。”小卖部主人以轻描淡写的口气回答了我。我这才意识到,它们刚才扑向我时,叫声和姿态都缺乏一点力度。狗毕竟是狗。身后没有了主人,身后的家已成废墟,它们哪里还有底气? 告别小店主人,往前走着。我想,大概村中被留下的狗都集中在路边那家仍然有人生活的院子前面了。说它们是流浪狗,并不贴切。它们没有流浪。它们仍然固守在自己的村子里。它们只是没有了主人。对于狗来说,没有了主人就是没有了家,何况,本来的家也的确面目全非了。我一直以为丧家犬与流浪狗是差不多的意思。见到这群废墟边的狗,我才知道二者意思并不一样。丧家犬未必是流浪狗,流浪狗也未必是丧家犬。第一代流浪狗当然是丧家犬,但“流二代”“流三代”,则是母亲在流浪中产下,在母腹中便流浪着,从来就无家可丧。 边走边想着,见有一条支路,也是通往废墟。我走上支路,往废墟深处走,忽然又响起一阵稚嫩的狗叫,便见两只小狗,兔一般大,从乱砖中站起,慌乱地跑着,在砖块和水泥块的羁绊下,跑得跌跌撞撞、叫得奶声奶气。我想,它们卧着的地方,就是本来的家了。原来,并非村中所有的丧家犬都集中到了那一处人家,还有仍然不肯离开原来的窝者。 折回本来的路,走到尽头,是一条国道,于是往回走。路过那已经无人问津的小店,朝仍然坐在那里似笑非笑着的主人摆摆手,便又走到了那群狗的聚集处。这回,它们已经布不成阵了。在路上半卧着的,站起身,哼哼着走开;原来在路边的,也悻悻地躲闪着走开。虽然也有几只低吼着作跃跃欲试的扑咬状,见没有追随者,也就作罢,低吼几声走开。我旁若无狗地走过它们的聚集地,只把手中的棍子在脚边拖着,防止它们从身后突然袭击。我知道,只要有一根棍子在路面吱吱作响,它们就绝不敢扑上来。走过了这群狗,我仍然想着它们。我想,它们的主人扔下它们,那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政府按人口支付了租房费,至于租了什么样的房子,则由村民自己决定。最大限度地节省租房的钱,当然是村民们自然而然的选择。一家人挤到不能再挤地挤在一起,也就可以把租金缩到不能再缩。没有哪家会考虑狗的生存而把房子租得大一点,从而把租金花得多一点。在这样的时候将狗扔下,那是毋须考虑的做法。如果有哪家为带上狗而多付一点租金,就违反了固有的伦理观念,就不合乎情理了,甚至要受到村人的责难。政府是按人口给钱,没有把狗口算在内。即便政府也给了狗口一份钱,这钱也一定不会花到狗身上。狗仍然可能被遗弃。那么,这些狗如何生存下去?答案是:如果它们固守这里,它们只能饿死。虽说村民们养狗不会每日特意喂食,但五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狗每天总能在地上找到些吃的。一旦这里没有人生活了,狗也就断了粮源。它们唯一可能活下去的方式,是实现从丧家犬到流浪狗的转型,沿着我来的道路走出村子,走出群山,到城市里加入流浪狗的行列。然而,看起来没有这种可能。 此后,我隔三岔五还到这废墟村走走。已经有人在清理垃圾了。与政府僵持的人家在缓慢减少着。写着“有人”的墙在艰难地倒塌着。但那小店还在,主人依然每日坐在那里,做开店状。这家小店,可能是最难与政府达成协议的了。这家的事情应该特别令政府头痛。他开个小店,每日有一定收益,这笔账,算起来实在烦难。一定是卡那小店的赔偿上了。那些狗,仍聚集在那里,但狗毛一天比一天长,狗身则一天比一天瘦,身上也越来越脏。渐渐地透过长长的狗毛能看见狗骨了。但是,它们没有显露出任何离开这片废墟的迹象。从这个村子进入城市,像我这样的人,走起来也就个把小时;像它们这样的狗,小跑起来大概只需几十分钟吧。然而,要让它们完成从丧家犬到流浪狗的身份转换,似乎比登天还难。这不只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更新。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完成一次必需的蜕变呢?或许有人认为是对原来主人的依恋。其实并不是。不能认为它们固守在这里就是在等待主人的归来。我后来从它们身边走过时,它们看我的眼神里已经基本没有了敌意。仍然有一丝警惕,但也有些许期待。它们中有几只,还会尾随着我,迟迟疑疑地走几步。我知道,它们绝不是要找机会咬我一口,而是试探着是否能跟我回家。我确信,只要我扔掉手中的棍子,再扔一点面包馒头之类在地上,它们就会跟上我。我从它们的眼神,从它们的身体语言中获得了这份确信。只要我把它们带回家,我就成了它们新的主人,很快就会对我忠心耿耿。所以,它们依恋的并非某个唯一的人,而可能是任何人。那种只认一个主人的狗,在一些故事中永生着。这样的狗,即便真有,也绝对是狗中的极其另类者。绝大多数的狗,是只要有人就行,是随时可以换个主人的。 对人的依恋、依赖,是人喜欢狗的根本原因;对人的依恋、依赖,却又是狗被抛弃、被杀戮的根本原因。据说,狗是从狼“进化”而成。我以为,“进化”这个词肯定用反了。从狼到狗,分明是生命的退化。我不清楚狗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狗与人之间,相互十分信任。人是极其信任狗的。人对狗的信任,远远超过人对人的信任。而狗确实是值得人无限信任的。狗会更换主人,前提是原来的主人已经消失。如果仅仅是被主人抛弃而主人仍然在那里,狗是赶不走、打不跑的。狗如此粘着人,也是因为对人的无条件信任。而它们不知道,人有时是多么不堪信任的东西。抛弃狗算得了什么?抛弃父母、抛弃孩子,在人类那里,也不算稀奇事。狗如果有思想,早就应该对狗与人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 ………… 从学术文章走向喧嚣人间 著名学者王彬彬全新非虚构力作 一幅知识分子坚持批判精神和独立姿态的灵魂画像 写给人群中不甘于困守混乱的迷茫者 王彬彬的《废墟与狗》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承继了鲁迅嬉笑怒骂、深入现实的杂文传统,以个人观察与反思介入当代公共生活,细密严谨的逻辑提醒着人们被忽略的常识,冷峻独特的视角提供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多重思考。作品的艺术魅力体现于日常的描述与超脱的想象,充沛的感悟与凝练的表达之间,蕴藏着智性的张力和乐趣,其深处,是一位知识分子坚持批判精神和独立姿态的灵魂画像。(凤凰文学奖颁奖词) 废墟的简陋与不声张恰恰是言说真相的关键地带,回望的现场。废墟是一种结构,它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本书不仅从历史出发,朝花夕拾般回味过去所在,也兼含了当代社会人们生活的改变。 王彬彬的文笔独到,常常是慢条斯理地先说无关紧要之物,结果是请君入瓮般的说到要害,结构精巧,带有“先顾左右而言他”的设计感,平淡而有张力,似观潮令人出一身汗般、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