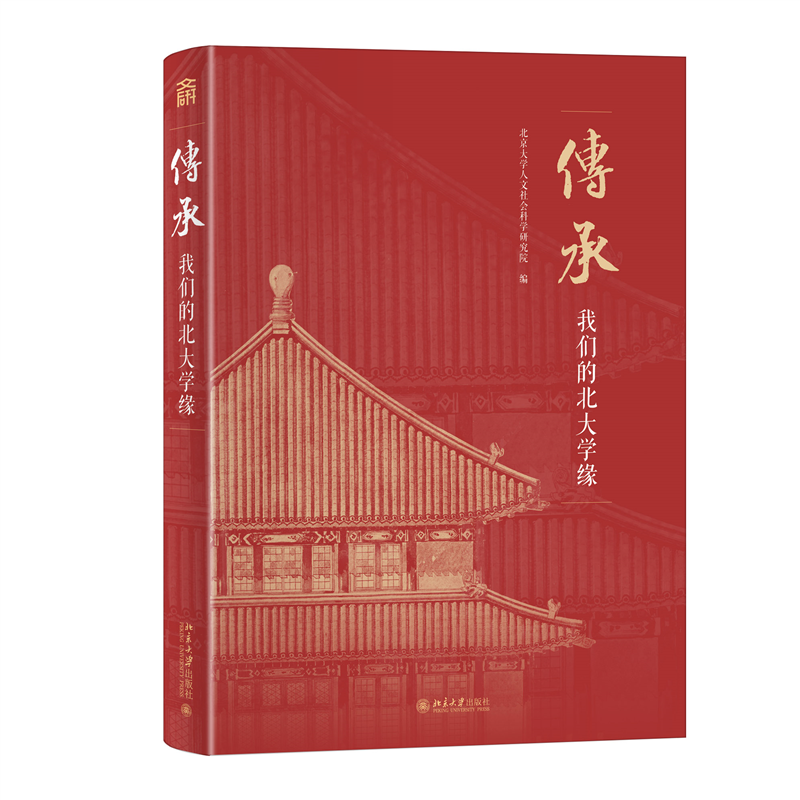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125.00
折扣价: 80.00
折扣购买: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
ISBN: 9787301338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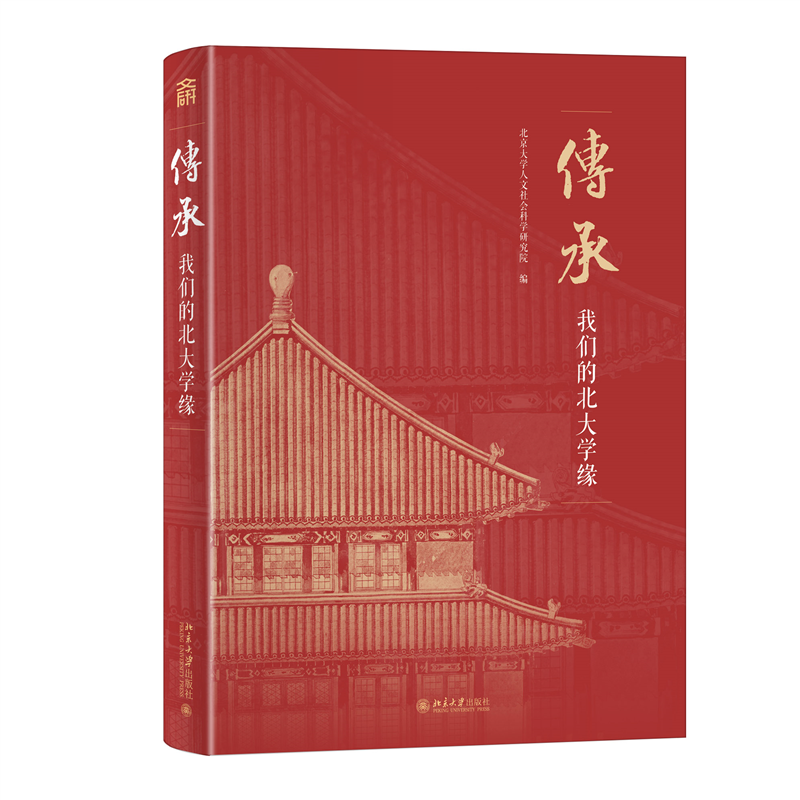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北京大学,是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实体学术机构。文研院的宗旨是:涵育学术,激活思想。文研院的目标定位是:依托北大综合优势,立足于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研究,探索学科之基本原理及前沿领域,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凝聚多方学术精华,促进与海内外学界的深度交流,建设更有竞争力的学术队伍;基于中国历史变迁的经验和理论,从世界诸文明的演进路径出发加以比较和审视,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振兴的道路;继承传统,弘扬人文与科学精神;引领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周飞舟:我的师生缘 非常感谢文研院举办“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这个活动,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反思过去三十多年里与北大、北大的人和事的关系。我现在五十多岁了,心境会有一些变化,好比走一条路隐隐看到了终点,突然知道自己这一生其实有很多以前想干的事情都干不了了,不像此前那样总是觉得人生有很多可能性。在这种心境下回顾过去的人和事,更容易想到许多过去想不到的道理。 我想主要讲讲我和我老师的故事。 我在1986年考入北大,也就是80年代。那个时代的少年人都有文学梦,北大中文系也是当时汇聚全国最多状元的地方。高考之前,我和当时的很多中学生一样,也是个有着文学梦的文艺青年。所以我也梦想进入北大中文系,把它填到了第一志愿,其他三个志愿都是随便填的。但是我高考考得不好,以至于最后去了随便填的第四个志愿——社会学系。我当时也不知道北大除了中文系还有什么其他院系,更不知道社会学是什么。填写社会学志愿是我一个同学的主意,他说他在电视上看到过费孝通,经常跟随胡耀邦出国,费孝通学的是社会学,所以社会学肯定不错。现在想来,这也不能证明社会学这个专业“不错”,但当时我本来就是随便填的,所以也觉得无所谓,费孝通的名字也是那时候才听说的。 因此后来回想起来,发觉是特别偶然的因素决定了我与社会学结缘,并且一生从事社会学研究。事实上,高考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大事,如果能够考上北大、清华,那么选专业就好像是一件更重要的事。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好像意味着只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又做到了所选择的事情,就走上了人生正确的道路——对此我深表怀疑。在我看来,我们只是把自己的选择看作正确的选择,又看成是极为重要的选择而已。如果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来做“事后评估”,就会发现即使是选专业、选行当这种事情,我当时的选择和当时作为一个孩子的愿望既不重要也不正确。所以我如今回想起来,还庆幸当时没能如愿以偿进入中文系。这倒不是说中文系不好,而是我后来知道中文系不适合自己,相比之下社会学则太好了,我和社会学有缘分。 当时的社会学系刚刚恢复重建,从1983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我在1986年考入社会学系,是第四级学生,因此入学的时候还没有毕业的学长。那时学生少,老师们也都不是特别专业,大部分老师是从哲学系、中文系转过来的,他们也是边教边学。80年代,应该是北大120多年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做到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时期。作为一个来自小县城的学生,我眼界大开。 当时社会学系刚恢复不久,专业课比较少,难度也小,因此我在本科期间没有学到太多专业的知识。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是听了许多讲座。如今的百周年纪念讲堂那时叫大饭厅,虽然只有一层,但是非常大,有1000多个座位。我记得最热闹的一次讲座,挤了近2000人,把六个门中的三个都挤掉了。回想我的四年本科生涯,可以说过得轰轰烈烈。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折腾了很多事,也被折腾了很多;培养了很多热情,但没受到多少真正的社会学专业训练。 我真正开始懂一点社会学,是在研究生时期,这全靠我的导师,所以我要讲讲我导师的故事。我认识我的导师,也非常偶然。社会学系的老前辈,像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等,都特别强调做社会调查;费先生更是身先士卒,行行重行行,在七八十岁高龄时跑遍了全国的村庄、田野——这是社会学系的传统。秉承这一传统,我们社会学系的学生在大三到大四期间都要在老师带领下去做田野调查。那是1990年2月,我所在的小组一共六人,跟随当时社会学系的在读博士,也是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王汉生老师去江苏昆山调研。那时候的昆山跟现在完全不同,还是一个古旧的小县城。带队的王老师虽然还是在读博士,但她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返乡知青,所以当时已经40岁出头了。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两周的调查时间里具体都聊了些什么,只是清楚地记得除了睡觉和调查,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听王老师给我们讲她调研和插队时的事情。就我而言,那是我在本科四年期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这么全方位地接触一位老师,我深深地被老师身上热情、真诚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卓越的学识见地所感染。这次昆山调查是我本科四年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将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一定要成为王老师这样的人。 认识王老师,坚定了我学习和研究社会学的志向。我在1990年毕业之后,先在北京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了三年,然后又千辛万苦地考研回到北大社会学系。说是千辛万苦,不是因为研究生多难考,而是因为当时有工作单位的人考研必须经过领导的同意。我那时工作的单位是个不讲绩效的事业单位,那时事业单位的领导一般都愿意让人离开。我回到北大社会学系读研究生,找了王老师做导师,也非常有幸遇到了一群善良热情而优秀的研究生同学,他们对我的人生影响都特别大。研究生三年才是我真正学习社会学的开始。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一心一意考回来,就是为了找王老师做导师,跟她学习社会学,同时跟她学习如何做人和做事。 我是王老师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学问上的导师,我们都是彼此的“第一个”。王老师第一次带研究生,也没有太多经验,但她尽心尽力地带我,指导我读书,指导我做调查,要是我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她就帮我兜底。她也自称是一个特别“护犊子”的老师,每次说是教训我,但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我虽然不是闻一知十的聪明学生,但我能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期望和关切。正是这种期望和关切,成了我学习和生活中最大的动力,成为我人生中特别坚韧的支持力量。 我回来读研是在90年代,那时北大校园里没有现在这么强劲的成功学风气,恰恰相反,很多同学把人生看得比较超脱、比较轻,甚至带着看破红尘的心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佛系”——暂且毋论真假,当时确实比较流行,推开一个宿舍门,经常会看到有人打坐。我当时既没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也没有什么高远的志向,并且为生命中的很多问题而困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我有什么执着一点的意志或者志向的话,其实就是想让王老师满意,不想让她感到失望,我想让她觉得自己带出了一个好学生。 我想这就是一个我非常喜爱、崇敬的老师对我产生的影响和给我的力量。就是这种喜爱和崇敬,这样一种特别真切的感受,而不是一些精细的人生设计或缥缈的玄想,决定了我以后的道路。为了让她满意这个想法一直驱使着我,我也不能确定我后来所做的努力是否真的让她满意。这就像一个孩子一定要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做得多好,而在证明的过程中,孩子长大了,父母则变老了。我后来去香港读博士,毕业后又回到北大社会学系教书,和王老师虽然表面上成了同事,但其实仍然是师徒。我们俩一起带着学生开读书会,一起带着学生做田野调查。王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她很少疾言厉色,但我仍能感受到她的关怀和期待,我能读懂这种关怀和期待,是希望我在教学和科研上做得更好。 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满意,我能确定的就是我在她眼里和心里一直没有变过,还是她的第一个学生。我们做师生,后来又做同事好多年,她还是不断地原谅我的冒失和不懂事,还是护犊子一样地护着我。我也一样没有变过,一直努力想要证明给她看我是好样的,我会让她自豪。我期望她看我时的眼神,她和我说话时的语气,能够由关怀和期待变成满意和喜悦。2015年,王老师查出了癌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然离去了。但我扪心自问,我的努力还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是永远的师生,我永远要证明给她老人家看。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像个小学生,会因为某个老师讲课好或者特别喜欢自己,或者自己喜欢某个老师而努力学习,于是在这个老师教的这门课上的成绩就会很好,并表示自己就是为老师而学。我反思自己学习社会学的过程,从读硕士、读博士,到做老师,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王老师,就是为了成为王老师那样的人。我始终为这样一种向往慕念之心所驱使,即使到了知天命之年,仍然难以释怀。我想我和王老师之间有一种缘分,从我们相遇相识起,我就对她有一种莫名的投缘和亲近感,仿佛似曾相识一般,我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这种缘分,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它就是古人所说的“莫之致而至者”,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温暖的东西,是每个人都会在生命历程中不期而遇、深有会心的东西,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晚年一直在谈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心心相印、不言而喻的感通。费先生晚年的一篇文章里谈到,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感通的精神世界,来作为我们深刻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社会、理解世界的基础。就像他的十六字箴言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他看来,这是在开辟社会学研究的新世界。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后进,我用自己的生命体验,衷心地对费先生的说法表示赞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赞成。 2018年的教师节,我和一个师妹一起去了趟延安,到了王老师当年插队的地方,也就是延川县张家河村。老师生前从未回去过,2015年她本打算回去看看老乡,我们也计划好行程准备陪她一起去,结果临走前她查出癌症住了院。因此,我和师妹去到“故地”,是代她完成最后的心愿。我们在当地老先生的带领下,找到了王老师当年插队住的窑洞。窑洞很多年没有人住,已经塌了一半,堵住了一半的入口;窑洞前的磨盘也已经烂了,地上长满了草。我在窑洞前站了很久,回想着王老师讲的各种插队时的故事和她讲得高兴时的笑声,即使阴阳两隔,我好像又通过这种方式和她老人家有了会心的交流。 最后,我要感谢北大,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老师,我的众多同学、好友,还有我的学生。这些全部都是在北大这个神奇的地方发生的缘分,发生的生命奇遇。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作“缘分天注定”。是上天赋予了你和我心心相通的机会,因此我们要把握好,要对得起,不能放弃,直到永远。 感受北大几代学人的群像,了解北大学术澎湃的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