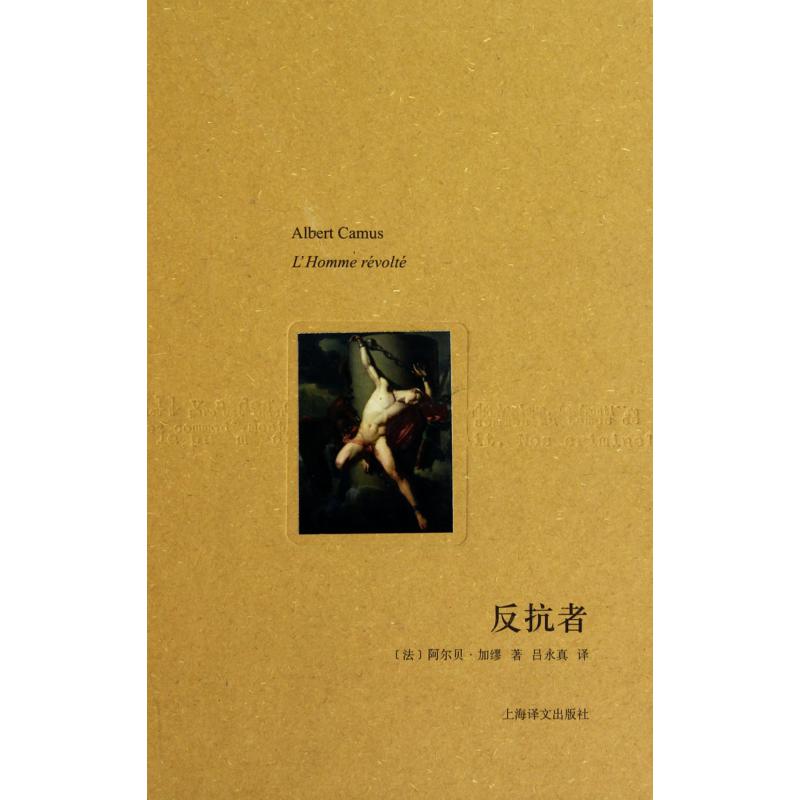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23.60
折扣购买: 反抗者(精)
ISBN: 9787532752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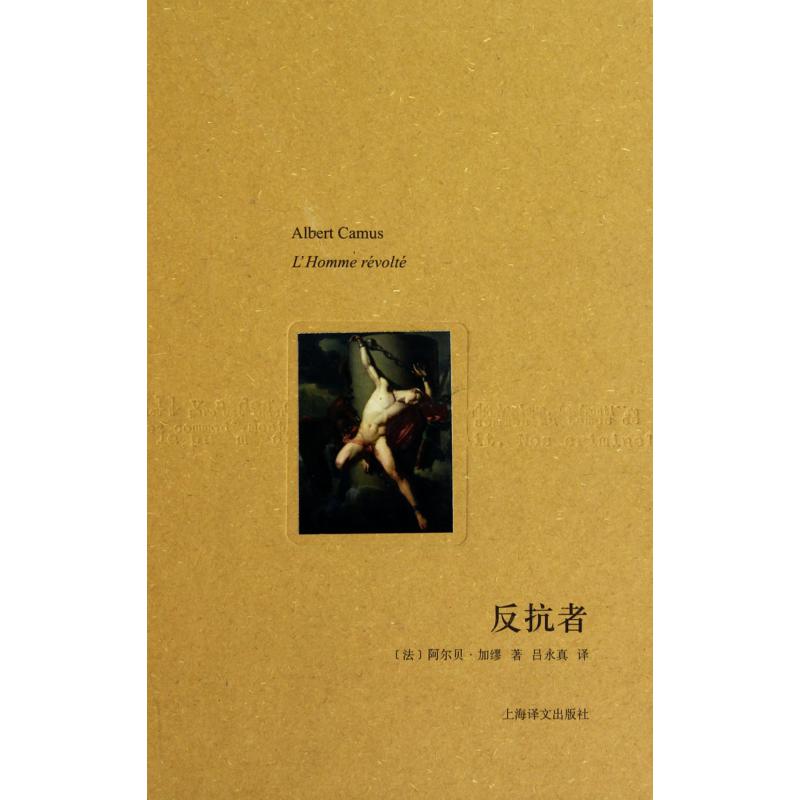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著名小说家、哲学家和戏剧家,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父亲在一战中阵亡后,他随母亲移居外祖母家,生活极为艰难,靠奖学金读完中学。一九三三年起,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二战期间,他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负责《战斗报》的出版工作。加缪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局外人》、《鼠疫》、《堕落》和短篇小说集《流放和王国》,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反与正》、《反叛者》和剧本《卡利古拉》、《正义者》等。一九五七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幸的是,三年后,加缪因车祸去世。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人狱以前在《一个神甫与临终者之间的 谈话》中是这样说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他作品中最为残忍的人物 之一——圣奉,丝毫没有否定上帝,而仅限于发展诺斯替派关于邪 恶的理论,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人们会说圣奉并非萨德。他当然 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然而有 些时机,小说家可能同时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人物。因而,萨德作品 中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都提出了上帝并不存在,理由是上帝若存 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最杰出的作品以 展示神的愚蠢与仇恨而结束。无辜的茹丝汀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犯 罪的诺瓦瑟耶竞发誓说,她若不被天上的雷电击死,他便改信异教。 惊雷终于把茹丝汀击死,诺瓦瑟耶获胜了,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着神 的罪恶。这样,不信教者的打赌便成为对帕斯卡尔打赌的反驳。 萨德对上帝的看法就是上帝是摧残与否定人的有罪的神。萨 德认为,神乃杀人者,这种情况在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人为何要 讲道德呢?这个囚徒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追求极端的后果。既然上 帝杀害与否定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人去杀害与否定同类。这 种愤激的藐视与1782年的《谈话》中表露的那种平静的反抗已毫不 相似。他此时大喊:“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 我。”他声言:“不,不,不论是美德还是邪恶,一切在棺材中都混而 为一。”他心境既不平静,生活也不幸福。他说“他所不能原谅人 的”惟一事情就是关于上帝的思想。“原谅”一词在这位大谈折磨 的作家的笔下实不寻常。然而他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正是他对世界 绝望的看法与囚犯的状况所绝对反驳的那种思想。双重的反抗此 后指引着萨德的理智:反抗社会秩序与反抗他自己。由于这两种 反抗在一个受迫害者的迷乱的心灵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矛盾的,他 的理智始终是含糊不清或者合理的,这要视人们是从逻辑的角度还 是以同样的态度研究他而定。 既然上帝否定人及其道德,他也会这样做。但他所否定的上帝 直到此时一直作为他的担保人与同谋。以什么名义?以他身上最 强烈的本能即性本能的名义。正是对人的憎恨使他在监牢的铁窗 后活了下来。这种本能是何物?它一方面则是本性的呼喊;另一 方面是要求完全占有一切生命的盲目冲动,甚至以毁灭他们为代 价。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定上帝——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为他 提供了机械论的观点,又使本性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对他而言, 本性就是性,他的逻辑引导他走向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那里惟一 的主人就是欲望的难以限制的力量。那里就是他陶醉的王国,他在 那里听到了最美好的呼唤:“让大地上一切生命都面对我惟一的欲 望!”萨德的英雄们指出人的本性需要罪恶,它必须毁灭才能创造, 人们毁灭了自己就会帮助它创造。这冗长的推论的宗旨仅仅是为 囚徒萨德建立绝对的自由。他极不公正地遭到压制,于是渴求毁灭 一切的爆炸。在这方面,他与他的时代作对:他要求得到的自由不 是原则的自由,而是本能的自由。 萨德无疑曾梦想一个全世界的共和国,让扎美这个有改革精神 的智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共和国的’轮廓。他向我们指出,反抗运动 在加速发展,越来越不受到限制,其目标之一就是解放全世界。然 而他身上的一切都与这个炽热的梦想背道而驰。他不是人类的朋 友,他憎恶博爱者。他有时谈到的平等是个数学概念:人皆为等价 物,迫害者拥有可恶的平等。他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必须主 宰一切。他真正所完成的功业就在仇恨之中。萨德的共和国并非 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奇特的民主主义者 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它是一切情欲的崇拜对象。”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多芒塞在《小客厅中的哲学》中读到的 那段著名的诽谤性文字更能说明问题。这部作品有个奇怪的标题: “法国人,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彼埃尔·克洛索 夫斯基正确地指出,那段诽谤性文字向革命者表明,他们的共和国 是建立在对享有神权的国王的屠杀之上,他们在1793年1月21日 处死了上帝,便永远禁止自己放逐罪恶与批评有害的本能。君主制 度在维护自己的同时,维护了建立法律的上帝思想。共和国完全依 靠自己,品行在那里是不受约束的。可疑的是,萨德如克洛索夫斯 基所希望的那样,怀有深深的亵渎宗教的感情,而这种几乎是对宗 教的恐惧把他引导到他所陈述的后果。情况更可能是,他首先承受 其后果,然后找到了适当的论据证明他向当时的政府所要求准许的 品行是合理的。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把结论置于前提之 上。萨德在这篇文章中用一系列令人称绝的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 与谋杀是合理的,并要求在新城邦中容忍这些行为。他极其欣赏这 些诡辩,从而心安理得。 然而,正是在此时他的思想是最深刻的。他以当时无与伦比的 敏锐拒绝将自由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当自由是这个囚徒的梦想时, 它尤其不能忍受任何限制。它是罪恶,否则便不再是自由。萨德对 此基本论点从未改变过。此公宣扬的理论矛盾百出,只有在涉及死 刑时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绝对的一致。他这个巧立名目的执行死 刑的爱好者,性犯罪的理论家,从来不能容忍法律所判定的罪行。 “国家对我的监禁,在眼皮下执行的断头刑,这些给我带来的痛苦百 倍地超过可以想像的一切监狱。”这种恐怖使他丧失了在恐怖时 期公开表示出克制的勇气,那时他还勇敢地为岳母求情;虽然她 曾使他人狱。几年以后,诺蒂耶清楚地概括了萨德所顽固捍卫的立 场而不自知:“由于极度狂热的感情而杀死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以一个可尊敬的政府的部门为借口,在经过认真思考后,冷静 地让别人去杀人,这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里所流露的一种想法 为萨德加以发挥:杀人者应当以其人身偿命。可以看出,萨德比我 们同时代的人更讲道德。 他对死刑的憎恨,开始是憎恨那些相当相信自己的品德或他们 美好事业的人们,他们因此才敢于惩罚,虽然他们是有罪的。人不 能同时为自己选择犯罪而为他人选择惩罚。应当打开牢狱,否则便 证明自己的美德,但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一旦认可杀人,哪怕仅仅 一次,就会普遍地认可杀人。按本性行动的罪犯不能置身于法律一 方而不判罪。“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这句话的含义 是:“接受犯罪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惟一合理的,并且要永远进行反 抗,如同想得到圣宠一样。”完全屈从于恶会走向一种可怕的禁欲状 态,这会使充满智慧与善良的共和国感到惊恐。这个共和国第一次 的骚乱就焚烧了《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可谓意味深长的 巧合。它必然会揭露这种异端的自由,重新禁锢受到牵连的拥护 者。这样一来,便使他有可怕的机会把反抗的逻辑推得更远。 全球共和国对萨德可能是个梦,而从来不是一种愿望。在政治 方面,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在他的《犯罪的朋友们的社会》一 书中,他公然声称自己拥护政府及其法律,然而却打算违犯法律。 这样,追随者们便投票支持保守派议员。萨德所思考的方案要求一 种温和中立的政权。罪恶的共和国不可能是全球的,至少暂时是如 此。它必须装出服从法律的姿态。然而,在一个只有杀人规则的世 界,在罪恶的天空下,萨德以犯罪的本性的名义,实际只服从无穷尽 的欲望的法律。然而,无限制地渴求他物,意味着被他人无限制地 渴求。允许毁灭意味着自己可以被毁灭。因而必须斗争与统治。 这个世界的法律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力量的法律,其动力就是权 力意志。 与罪恶为友,仅仅真正地尊重两种权力,一种是在社会中可以 见到的基于出生偶然性的权力,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往上爬而捞到的 权力,他们玩弄卑鄙的手段,终于和达官显贵平起平坐。萨德以这 类人物来塑造其出身寒贱的英雄。这一小撮有权势者,这些被接纳 入权力阶层的人,知道自己拥有一切权力。有谁若怀疑这令人生畏 的特权,即使是须臾间,也会立即被贬斥,重新成为受害者。人们于 是在道德上信奉布朗基主义,一小撮男人和女人由于掌握一种离 奇的知识而坚定地自居于奴隶阶层之上。对他们说来,惟一的问题 就是自己组织起来,完全地行使权力,以满足其惊人的欲望。 P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