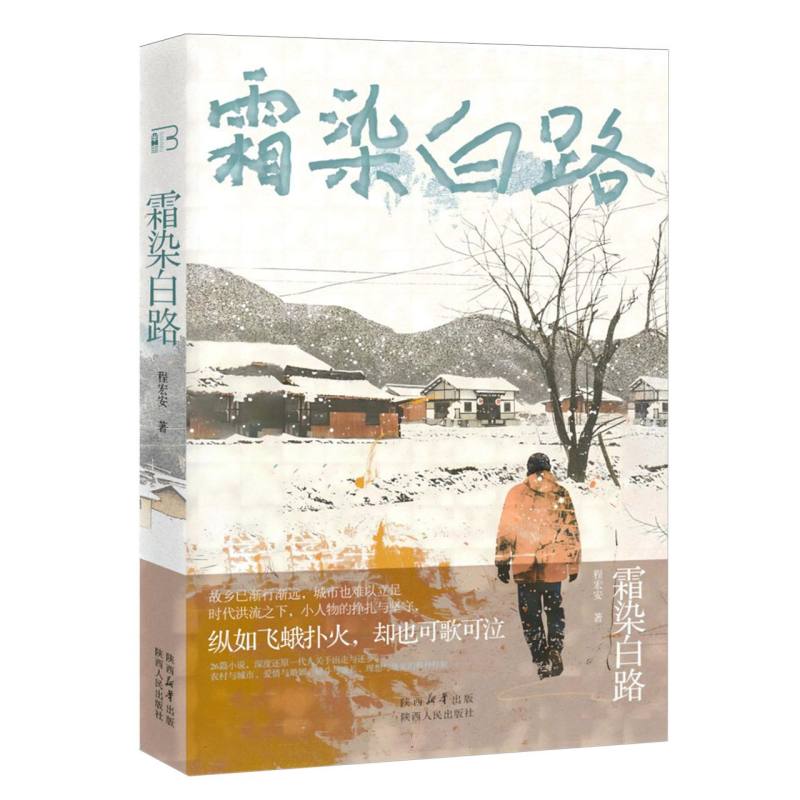
出版社: 陕西人民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4.90
折扣购买: 霜染白路
ISBN: 9787224153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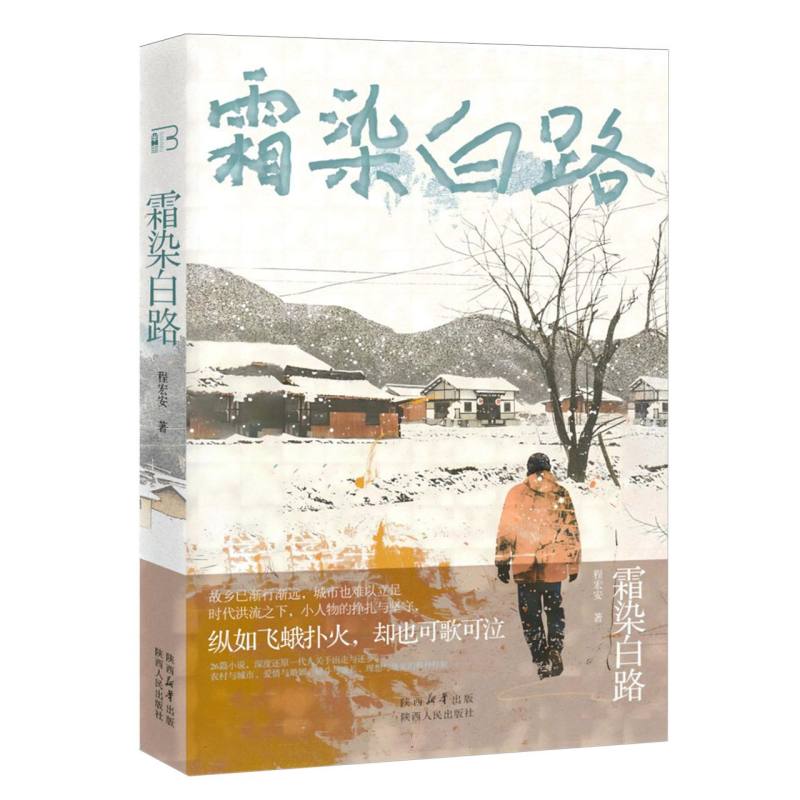
程宏安,1967年生,陕西洋县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散见于《延河》《燕赵晚报》《陕北诗报》《文化艺术报》等。出版有散文集《守望原乡》。
安大可回乡 01 安大可打算回一趟老家 。 对有的人来说,回家不 仅仅意味着和亲人相聚,有 时还是一种精神上的皈依。 安大可就是这样,这一次他 将带他的妻子明兰回到他出 生的地方。 明兰将是他今生的最后 一个女人,和她结婚是他给 爱情画的句号,从此开始, 他打算老老实实过普通人的 日子。过去他爱过的和爱过 他的女人统统都翻个篇儿, 所有红颜的、蓝颜的情感统 统都打个死结,永不再见。 在老家,在父亲、母亲 那一辈,“三子”——房子、 孩子、女子(指妻子)—— 是一个男人甚至一个家族在 村子里必需的三面旗帜,缺 一都不会受人敬重。“三子” 中的两子都和女人有关,婚 姻绝对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 有爱就可以这么简单。在婚 姻中,一个女人走向的不仅 仅是一个男人、一个家庭, 她很可能还涉及一个家族、 一个姓氏的共同荣誉。可以 说,在他们这个地方,缺少 上一辈德高望重者祝福的婚 姻注定不会幸福。祠堂在人 的心里,仪式在看不见的地 方不可省略。对于这种人生 大事,乡俗的认可和加持的 重要性大过那一张红纸。这 里的人都知道,唾沫星子是 一片汪洋大海,异样的目光 是大海里生猛的食神兽,身 披青春披风高高飞翔的你完 全可以无视这种虚无的威胁 ,但你不能保证,你老迈不 善游泳的亲人同样可以安然 无恙。这一点,安大可有着 深刻的体会。 上一次,安大可领回家 的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乡 亲们在背后骂得很难听,他
故乡已渐行渐远,城市也难以立足,时代洪流之下,小人物的挣扎与坚守,纵如飞蛾扑火,却也可歌可泣。26篇小说,深度还原一代人关于出走与还乡、农村与城市、爱情与婚姻、奋斗与成长、理想与现实的种种样貌。 这些小说充分关照社会现实和生活本身,尤其是聚焦于农村青年群体在离乡与还乡之间的矛盾挣扎,以及城市底层人物的奋斗历程和人生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社会的认知和思索。李星先生在序言中认为,本书作为改革开放、物欲横流时代的记录,具有很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
书籍目录
001 安大可回乡
009 初恋之谜无解
022 白果树下的儿女之一 老左
029 白果树下的儿女之二 承明
037 白果树下的儿女之三 容容她大
045 白果树下的儿女之四 菊花嫂子
053 师 者
059 户 口
066 汪 生
072 来福的一天
080 非常丈母娘
087 霜染白路
096 炼 金
105 办事处副主任
115 奔忙在北京
140 生命中那些令人动容的瞬间
149 扶都之花 梅
158 扶都之花 兰
168 扶都之花 竹
180 扶都之花 菊
192 再见 五道河子
207 大凌河西有村庄
215 柏山 阿香
222 我的朋友和他的女人
245 黑山大龙
265 苍天的孩子
287 后 记
试读内容
安大可回乡
01
安大可打算回一趟老家。
对有的人来说,回家不仅仅意味着和亲人相聚,有时还是一种精神上的皈依。安大可就是这样,这一次他将带他的妻子明兰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明兰将是他今生的最后一个女人,和她结婚是他给爱情画的句号,从此开始他打算老老实实过普通人的日子。过去他爱过的、爱过他的女人统统都翻个篇儿,所有红颜的、蓝颜的情感统统都打个死结,永不再见。
在老家,在父亲、母亲那一辈,“三子”——房子、孩子、女子(指妻子)——是一个男人甚至一个家族在村子里必需的三面旗帜,缺一都不会受人敬重。“三子”中的两子都和女人有关,婚姻绝对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有爱就可以这么简单。在婚姻中一个女人走向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一个家庭,她很可能还涉及一个家族、一个姓氏的共同荣誉。可以说,在他们这个地方,缺少上一辈德高望重者祝福的婚姻注定不会幸福。祠堂在人的心里,仪式在看不见的地方不可省略。对于这种人生大事,乡俗的认可和加持的重要性大过那一张红纸。这里的人都知道,唾沫星子是一片汪洋大海,异样的目光是大海里生猛的食神兽,身披青春披风高高飞翔的你完全可以无视这种虚无的威胁,但你不能保证,你老迈不善游泳的亲人同样可以安然无恙。
这一点,安大可有着深刻的体会。
上一次,安大可领回家的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乡亲们在背后都骂得很难听,他都知道。虽然他们和他迎面碰见也不打招呼,但安大可还是可以从他们匆匆而过、嘴里的念念有词里认出那些不好的词语:“二锅头”“破鞋”“卖 × 的”……
安大可的父母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也没有把自己的犟牛儿子拉回到正常轨道上,就叫了安大可的大哥(代表大伯)、堂伯、舅舅、当时的生产队长,以及左右邻居开了个扩大会,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儿子能悬崖勒马。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沉淀了太久的传统被一些胆大先行、肆意妄为的年轻人拿出来充分反思、恶搞、嘲弄、翻晒,甚至践踏,在那样的大环境里,正处于青春期的安大可汹涌的荷尔蒙毁天灭地,他根本无法接受那种形式的教育。他觉得那场家庭会议就是给自己和自己的女人开的一场批斗会,在那样的场合,历数他们的丑行,目的就是让他体无完肤,褪尽胞衣,把自己的五脏六腑、肠肠肚肚全部暴露在众人面前,这哪里是什么教育?分明就是对他的公开羞辱,比杀了他更让他觉得难受。好歹自己也是个站着尿尿的汉子,打掉了他最后的尊严,让他以后怎么抬头做人?他只是找了个名声不好的女人,这是犯了多大罪?
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他舅舅本来私下答应在会上在众人面前为他灭火的,最后竟然站到群情激昂的一面,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甩手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你是那个谁的谁?没生过我没养过我,凭什么打我?那一刻,安大可热血上涌,真有一种冲上去打回去,报一掌之仇的冲动。
安大可觉得,不懂得爱情、不懂得荷尔蒙为何物的老家人抛弃了他,所有人都是。他,走了。这一走,就是十五年。安大可私下发过誓:尿尿都不朝那个地方(方向)尿!
02
这一次,他决定要真正回一次乡,正大光明地回,回到那个抛弃过他的故乡,带着他的女人。
他在一线城市有房、有车,有自己的事业,这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在他心里,只有十五年前离开的那个村子才有他的家。他在没人知道的夜晚,偷偷回去过几次,绕着自家的老房子转了几圈,发现院里全是一人深的荒草,他蹲在地上哭过。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算是写在纸上又能怎么样呢?十五年前的字迹放到今天还能那么清晰可见吗?
誓言是当初自己给自己立的,他不说,别人便不知,何况当初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早就不一样了,时间和人都变了,誓言对应的早成了虚空。再说,是自己单方面的决定,当年没有任何人撵他走,现在也没有人说过故乡不接受他安大可回去看看呀。不是吗?
十五年了,父母不在了,大伯不在了,堂伯不在了,舅舅不在了,队长也早就换了几茬了,但老房子还在,姐姐在,大哥在,父母的坟在,他,得回。
明兰是个简单的女子,以她的单纯、善良、热情,相信如果父母活着的话,会很满意这个儿媳妇的。虽然和明兰之间早就有了红本本,固定了关系,老丈人一家也举办了隆重的仪式,但他觉得这还不够。在老家,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他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神圣的人生仪式没有完成。他要让他的女人从他生命开始的地方融入他的生活、喜欢上他爱吃的食物。他相信老家的食物里有根神奇的绳,一定可以拴住驿动的胃口;老家的天空充斥着魔性,只要呼吸了那里的空气,只有回乡才是唯一的解药;老家的泥土里有无名的蛊,脚一沾上就无法远离!村里的老房子框住了一代又一代的居家女人,也一定会帮他留住明兰。他还要让牵挂他的姐姐、大哥、小弟、小妹们放心,并分享他的幸福。他要带着明兰去给父母上个坟,他要让父母用另一种方式“批准”、祝福他们的婚姻。
对于父母,安大可有深重的罪孽感,他一直无法释怀,不管是睡在自家床上还是大酒店豪华的席梦思床上,他总是时常梦中惊醒,然后望着空白的天花板长时间出神,他说他爸他妈就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
明兰说,你该回去看看了。
安大可说他走的那天风很大,有只大黑鸟一直在头顶盘旋,明兰说,你看清楚了,是只鸟不是风筝?安大可说,我没抬头,但我确定那是一只鸟,我们那里没人放风筝,一定是宿命的神在天上。很多年之后碰见邻居,听说我妈的头发一夜之间就全白了,去世的时候一直喊着“可儿,可儿”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也合不上眼睛。
安大可曾偷偷去看过父母的坟,父亲的墓碑上孝子一栏没有他的名字,但母亲的碑上有,据说是母亲监督着石匠刻上去的,那清晰的錾痕是母亲留给他儿子的一条路,森森的月光下,明明白白。“安大可”三个字大体都是工整的楷体,唯独“可”字的“丁”这一部分刻意变一个弧形,这分明就是母亲的授意,她在用一个开放着的环抱,等着她的儿子归来,空空落落地等待了十几年。
03
出走十五年之后,安大可第一次和一个女人一起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汉中的十月,多雨,潮湿。在人行道上,一片发黄的梧桐树叶提醒你季节变了,天气也变了。南来北往的电动车上撑着不同颜色的雨伞,穿梭在雨雾中,像漂着不同颜色的莲,而莲下一张或数张自在、满足、闲适、不疾不徐、有点诗性、略带忧郁的脸,从你面前倏地一闪而过,然后没入田垄一样并不宽阔的小巷中不见,虽不熟悉,但很田园,让你想起小时候路遇一只从一块菜地向另一块菜地转移的小青蛙,在你面前调皮地一声“呱”之后,迅速地穿越了你的视线。
有些冷。但在这里出生的安大可完全可以忍受,他甚至对这种潮湿、有些凝滞的天气有些说不清的偏爱,因为这种清冷可以帮助他,让他的记忆中他不愿意忘记的那一部分,很原味地保持在某种电影的情境里而不走样。而这对明兰这个东北姑娘显然是个考验。她说风往骨头缝里钻。安大可承认自己还是考虑不周,一没料到下雨,没准备伞;二是回乡这件事虽然经过反复思量,还是想得简单了,他认为无须提前做攻略。可能真是离开得太久,忘记了多少年以来在故乡这季节就是多雨的季节。
明兰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架,安大可就想着买件厚些的衣服给她,最好能是当地风格的。可从北大街一路下来一直到中学巷口,服装店里都还是夏秋季的时装,不是裙装,就是薄款套装,没有一家冬装上架的。终于在一家运动品牌店的角落里找到一件带绒的冬款运动服,营业员坚持不卖,说是去年冬天剩下的,已经报了过季库存,准备过几天邮回总部换新款的。反复交涉才买下来,明兰穿上,觉得暖和了很多,可她说很不舒服:满大街都是眼睛,看她像看怪物。安大可就安慰她说,管他的,又没人认得你。
“汉中师范学校”这块牌子已经不在了,据说和农校、商校合并,在别的地方建了更大更漂亮的校区。好在汉中一中还在原址,汉师附小也还在,还有中学巷九号这个地址证明着安大可这段经历是真实、可信的,他没有对明兰说谎。曾经帮助他建立过自信的赵老师据说几年前过世了。带过班的焦老师呢?说是调到了党校。安大可带明兰找到了党校,打听了好几个人,最后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才找到了学校的档案室,在一个矮小瘦削的老头面前,安大可叫了一声“郑老师”,一张满是狐疑苍老的脸横亘在他面前。“我是安大可,83级班上很瘦的那个,羊县的。”“羊县是哪个县?”十五年,不短的岁月,会发生很多事,当年儒雅的郑老师早就认不出他这个现在和曾经都很普通的学生了,这没什么奇怪的。
“郑老师离婚了,十多年了都一个人过,平时也不爱跟人说话。”
带他们去的人这么一说,安大可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然后一阵空白。
中学巷口原来的老书摊隐身于时间深处,渐行渐远,远得看不见了。出了巷子不远,有家叫老王家面皮的店,可能是新开的,味道还可以,但完全是现时的味道,和过去一点都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