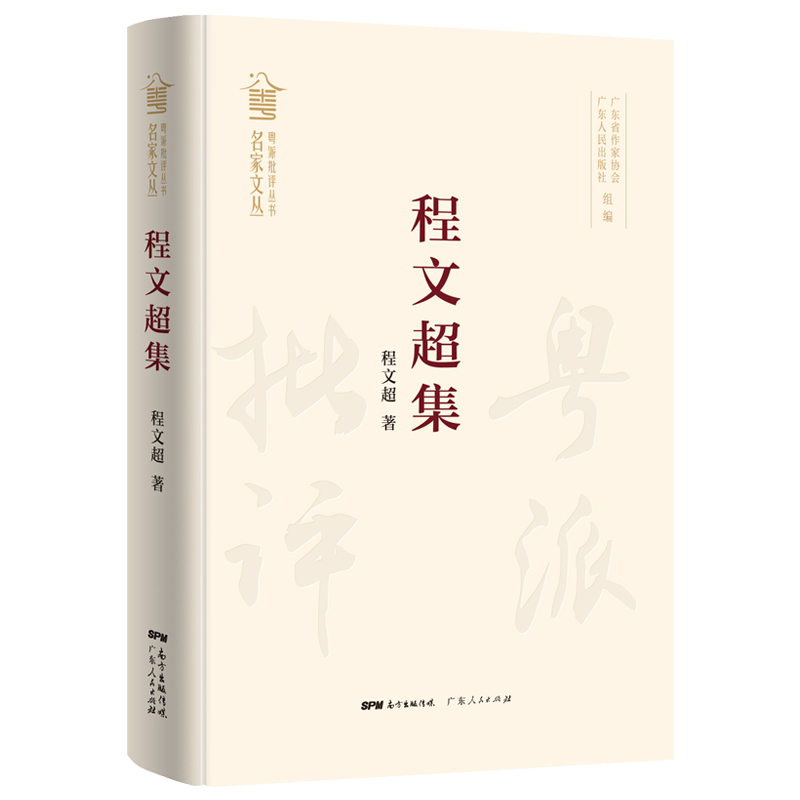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2.00
折扣购买: 程文超集(粤派批评丛书?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144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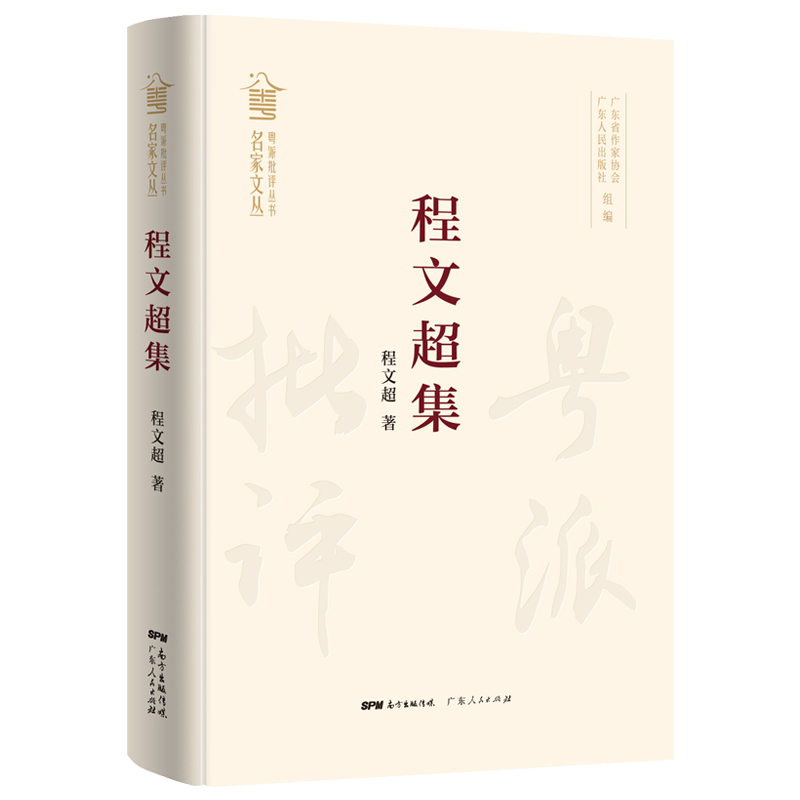
程文超(1955—2004),湖北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著名学者、评论家。1976年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谢冕先生。1990年赴加州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系留学,1993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专著《1903:前夜的涌动》曾获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理论奖,2001)等多种奖项。
梁启超:落伍者的超前追问 1903年2月20日。日本。横滨的轮船码头与横滨的街道一样,并没有显出与平日特别的异样。站在趸船上,再往前跨一步,便是那艘远洋客轮了。 梁启超跨了过去。 这一步,他跨得很不轻松。 可以说,从脚的跨出到落下,时光逝去了三年多。 三年多之前,他便迈出了去往美洲新大陆的步子。那是1899年底,旧金山中国维新会成立,应该会同志邀请,梁启超离开日本,准备经由檀香山去往美国大陆。尽管这次出游的原因里另有微妙,但梁启超希望到美国考察之心实在是早已有之。因而那次行程仍然给梁启超带来兴奋。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乘坐“香港丸”号向檀香山进发。那时的梁启超,二十几岁,生命和才华都正如大海的波涛,豪气冲天。船行海中,他觉得自己在时空上正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乃“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于是胸中万千块垒突起,斗酒倾尽、荡气回肠,挥笔写下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歌中以颇为不凡的口气写道:“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 表达了自己去美国观光的宏愿和目的,从中可以见出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在渴望和拥抱着未来的美国大陆之行! 可惜那一次他并没有如愿。正遇淋巴腺鼠疫威胁着檀香山的神经,有关当局规定过往乘客不得登陆。梁启超不管不顾地登陆了,却因为实行强行检疫不能按期离岸。梁启超意外地在檀香山停留了半年。本想再去美国大陆,国内形势却发生急变。唐才常的汉口起义枪声即响,梁启超于7月密回上海。迎接梁启超的是起义失败和赴美大陆计划的搁置。梁启超去往美国大陆的脚步提起了,却并没有跨出。这一“跨出”直到三年多之后才完成。 这一“跨出”的并不轻松还远不在于时间意义,更在于其生命的意义上。这一步,标志着梁启超生命史上的又一次转折。这一转折非同小可。转折完成之后的梁启超虽然在政治、文化舞台上不断扮演过各种角色,但作为中国舆论界之执牛耳者,其“言论界之骄子”的地位已逐渐丧失,其在思想界那种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已不复再来了。在当时的革命派眼中,曾是“同志”和朋友的梁启超落伍了。更不用说在以后的“五四”时期,梁启超只能代表过去的时代。革命派至少还把梁启超当做论敌,而在《新青年》那儿,梁启超连作论敌的荣幸都基本上失去了。 这似乎是一个谜。一位差不多成为革命派“同志”的人,在去另一个世界“问政求学”之后,怎么竟会变成一个“革命”思想上的落伍者? 更意味深长的是,梁启超与他的那次“跨出”,并没有真的消失。梁启超是这样一个人:在历史车轮前进时,他是一个被抛弃的落伍者。他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但是,他之“落伍”,却并不像人们曾经否定的那样轻飘,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题时的思维方式都远远超越了他的否定者。多少年之后,当他又成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时,人们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提问题的“问题性”。 西方学者较早发现了梁启超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勒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先后出版,成为汉学史上重要的学术著作。而中国学者对梁启超的兴趣再起则是因为世纪之交的触发:当又一个世纪之交来临时,人们发现,梁启超当年所提的问题,连同他发问时所用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再次凸现在了历史的天幕上。 这种“凸现”又迫使我们思考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多少年来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单向度描述,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世纪初的一些历史人物,比如梁启超,一个世纪之交的重要思想家,一个当之无愧的“天才”,为什么在历史变革面前会变得“保守”?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多向度和深刻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的艰难。被曲解了的历史简化了我们的思维、弱化了我们的智力。 重新理解梁启超对我们今天从简单进化论式的、单向度的、浅表的历史观中走出来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正面临着复杂的历史思考和历史性选择。 一、回到那次“跨出” 让我们先回到那次“跨出”。 梁启超实际上是带着复杂的心情跨上那艘远洋客轮的。 在此之前,只说1902年梁启超就相继创办了《新民丛报》《新小说》,倡 导了“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给文界、思想界带来了一系列爆炸性影响。 而这些事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新文体”实践。这一实践在1902年达到了顶峰。他用令人耳目一新、痛快淋漓的言说方式震惊着文坛、摇撼着思想界。梁启超自己对这一“发挥”也不无得意。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说自己为文“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唐才常汉口举事失败后,他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专以宣传为业”时,为文“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里大致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文体的追求与特色。 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将梁启超的“新文体”放在当年一班青年文豪的比较中来评价。他谈到谭嗣同、章炳麟、严复、林纾、陈三立、马其昶、章士钊等人,说他们“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各有芬芳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