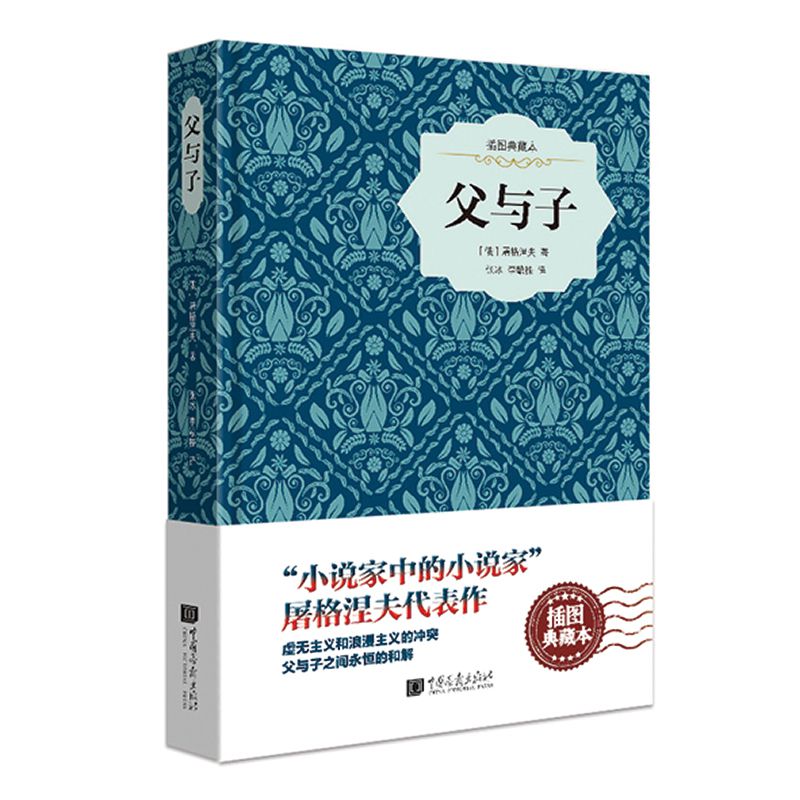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画报
原售价: 30.00
折扣价: 14.70
折扣购买: 父与子(插图典藏本)(精)
ISBN: 9787514613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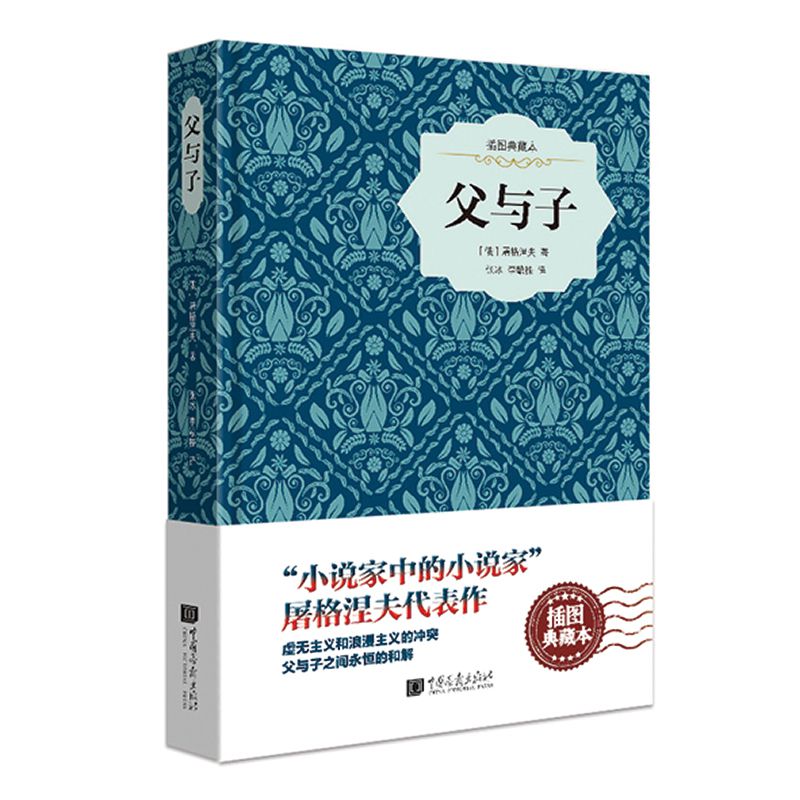
李毓榛,山东章丘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翻译作品有《白天的星星》《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合译)、《甜蜜的女人》(合译)、《父与子》(合译)等。 张冰,内蒙古巴盟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作品有《雅典与耶路撒冷》《钥匙的统治》《父与子》(合译)等。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奥勒尔省的贵族世家,早年丧父。十五岁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第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毕业于一八三六年。其间思想倾向于民主,并开始诗歌创作。二十岁时赴柏林大学留学,四十年代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自然派”的代表人物,一八五二年因发表悼念果戈里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并遭流放。一八八三年于巴黎病逝。
“怎么?彼得,还没看见?”问话的是位40岁左 右的贵族老爷。这会儿,1859年5月20日,他光着头 ,穿着落满尘土的大衣和方格纹裤,正从某某公路上 一家客店走出来,站在低矮的小台阶上,跟他的听差 ,一个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柔毛、两只小眼睛浑浊无 神的小伙子讲话。 听差的一切:无论是他耳朵上的绿松石耳环,擦 了油的杂色头发,以及文雅的举止,总之,一切都显 示出他属于崭新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了事地向路 上望了望,回答道:“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什么也看 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吗?”贵族老爷重复问道。 “什么也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了一句。 贵族老爷叹了口气,便坐在了一条小板凳上。现 在,我们趁他盘腿坐着,沉思地向四周张望的时候, 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他。 他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在离这 个小客店十五俄里的地方,他有一处有二百个农奴的 上好庄园,或者,按照他同农民们划清地界、建立起 “农庄”以后,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处有两千俄亩 的田产。他的父亲,一位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将军, 是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但是人不坏,是个地道的俄罗 斯人。他一生都在辛劳奔波,起初做旅长,后来任师 长,经常驻扎在外省,在那里凭借自己的官职,成了 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生在俄国 南部,同他的哥哥巴维尔(以后会谈到他)一样,14 岁以前一直在家里受教育,周围尽是些庸俗的家庭教 师,举止随便、却又奴颜婢膝的副官和其他联队以及 司令部的军官们。他的母亲,出身于科利亚津家庭, 出嫁前叫阿嘉特,当了将军夫人后改称阿加福克列娅 ·库齐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成了名副其实的“司 令太太”。她戴着华美的帽子,穿着窸窣作响的绸缎 衣服,在教堂里总是第一个走到十字架前,她讲起话 来声音响亮,而且说个不停;孩子们照她的吩咐每天 早晨吻她的手,每天晚上接受她的祝福,——总而言 之,她过着舒心的生活。作为将军的儿子,尼古拉· 彼得罗维奇——不仅没有一点儿勇敢之举,甚至还落 下个“胆小鬼”的绰号,——可是,他也必须像哥哥 巴维尔那样去入伍当兵;然而,恰好就在他得知任命 消息的那天,他跌断了腿,于是,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后,他便一辈子都成了“瘸子”。父亲不再对他抱有 什么希望,让他去做文官。等他年满18岁以后,父亲 带他到彼得堡,安排他进了大学。正好这时,他的哥 哥做了近卫军一个团里的军官。两个年轻人开始住在 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表舅伊里奇·科利亚津是位 大官,虽然能够照看他们,但鞭长莫及。父亲回到了 他的师里和妻子在一起,偶尔给儿子们来封信,灰色 的大四开纸上,涂满了一个个粗大的公文体字。这些 四开信纸的末尾处是他费力地用“花边”围起来,十 分显眼的签名:“彼得·基尔萨诺夫,少将”。1835 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 ,基尔萨诺夫将军由于阅兵中出现差错而退伍,携妻 子去彼得堡定居。他在塔夫里切斯基花园附近租了房 子,并加入了英国俱乐部,但是却突然间死于中风。 阿加福克列娅·库齐米尼什娜很快随他而去:她过不 惯首都沉闷的生活;退职闲居的日子使她郁郁寡欢, 愁苦而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父母在世时便爱 上了他从前的旧房东、官吏普列波洛维恩斯基的女儿 ,这件事颇使父母伤心。她很漂亮,一般说来还是个 很有教养的姑娘:喜欢读杂志上“科学”专栏里的严 肃文章。服丧期一满,他就娶了她,并辞去父亲为他 在皇室地产局里谋到的职位,带着他的玛莎过起了快 乐的日子。起初他们住在林学院附近的别墅里;后来 搬进城里一所很讲究的小住宅,楼梯很干净,但客厅 有些阴凉;最后到了农村。他在那儿最终安顿下来, 又很快有了儿子阿尔卡季。年轻夫妇的日子很美满、 很安宁:他们几乎从未分离过,一起读书,一起用四 只手弹钢琴,一起唱二重唱歌曲;她种花,照管家禽 ;他偶尔去打打猎和料理家产,阿尔卡季也一天天长 大了——长得又漂亮又文静。十年的时光像梦一样逝 去。1847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辞世而去。他勉强经 受住了这一打击,几个星期的工夫,他的头发全白了 ;本来他打算去国外散散心……可是,1848年到来了 。他只好回到乡下,很长时间过着疏懒的生活,后来 便开始了经济改革。1855年,他送儿子进大学,同儿 子一起在彼得堡度过了三个冬天。他几乎从不出门, 只是尽力结交阿尔卡季的那帮年轻朋友们。最后一个 冬天他没法再去彼得堡,——于是在1895年5月我们 见到了他。他头发花白,开始发福,背有点儿驼,正 在等候像他从前一样得到学位回家的儿子。 那个听差因为礼节的缘故,也许是不想站在老爷 面前,便来到门口抽起烟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 下头,注视着一级级破旧的台阶,一只肥大的花雏鸡 正顺着台阶走来走去,黄色的大鸡爪颇用力地敲打着 阶面;一只脏乎乎的猫蜷曲着身子趴在栏杆上面不怀 好意地看着它。烈日当头;客店里阴暗的过道中散发 出一股烤热的黑麦面包的气味。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陷入了沉思。“我的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季 ……”这些字眼儿在他的头脑中不停地转来转去,他 试图去想点别的事情,可是又回到这些念头上。他起 想了过世的妻子……“她没能活到这一天啊!”他痛 苦地喃喃自语道……一只灰色的胖鸽子飞到路上,急 匆匆地奔向井旁的小水洼里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 奇注视着它,可是,他的耳边已经传来了渐渐驶近的 车轮声。 “好像是少爷来了。”听差从大门口过来报告说 。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起身凝神向大路望去。一辆 驾着三匹驿马的四轮大车出现了;四轮大车上一闪一 闪地晃动着大学生制服的帽圈和他熟悉的、亲爱的面 孑L的轮廓…… “阿尔卡季!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喊了起来 ,一边挥动着双手跑向前去……一眨眼的工夫,他的 双唇已经贴在了年轻学士没有胡须、落满灰尘、晒黑 了的脸颊上面了。 P1-4
是人类文化意义的阐释者,使得每个读者与书中所描述的国家和时代的文化紧紧相融合。 在思想和情感上阐释出的进步观念和思想,起着传承和净化,启迪和感悟的作用。 “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屠格涅夫的经典之作。 虚无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冲突。
试读内容
“怎么?彼得,还没看见?”问话的是位40岁左右的贵族老爷。这会儿,1859年5月20日,他光着头,穿着落满尘土的大衣和方格纹裤,正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走出来,站在低矮的小台阶上,跟他的听差,一个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柔毛、两只小眼睛浑浊无神的小伙子讲话。
听差的一切:无论是他耳朵上的绿松石耳环,擦了油的杂色头发,以及文雅的举止,总之,一切都显示出他属于崭新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了事地向路上望了望,回答道:“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吗?”贵族老爷重复问道。
“什么也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了一句。
贵族老爷叹了口气,便坐在了一条小板凳上。现在,我们趁他盘腿坐着,沉思地向四周张望的时候,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他。
他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在离这个小客店十五俄里的地方,他有一处有二百个农奴的上好庄园,或者,按照他同农民们划清地界、建立起“农庄”以后,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处有两千俄亩的田产。他的父亲,一位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将军,是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但是人不坏,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他一生都在辛劳奔波,起初做旅长,后来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在那里凭借自己的官职,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生在俄国南部,同他的哥哥巴维尔(以后会谈到他)一样,14岁以前一直在家里受教育,周围尽是些庸俗的家庭教师,举止随便、却又奴颜婢膝的副官和其他联队以及司令部的军官们。他的母亲,出身于科利亚津家庭,出嫁前叫阿嘉特,当了将军夫人后改称阿加福克列娅·库齐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成了名副其实的“司令太太”。她戴着华美的帽子,穿着窸窣作响的绸缎衣服,在教堂里总是个走到十字架前,她讲起话来声音响亮,而且说个不停;孩子们照她的吩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每天晚上接受她的祝福,——总而言之,她过着舒心的生活。作为将军的儿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仅没有一点儿勇敢之举,甚至还落下个“胆小鬼”的绰号,——可是,他也必须像哥哥巴维尔那样去入伍当兵;然而,恰好就在他得知任命消息的那天,他跌断了腿,于是,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他便一辈子都成了“瘸子”。父亲不再对他抱有什么希望,让他去做文官。等他年满18岁以后,父亲带他到彼得堡,安排他进了大学。正好这时,他的哥哥做了近卫军一个团里的军官。两个年轻人开始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表舅伊里奇·科利亚津是位大官,虽然能够照看他们,但鞭长莫及。父亲回到了他的师里和妻子在一起,偶尔给儿子们来封信,灰色的大四开纸上,涂满了一个个粗大的公文体字。这些四开信纸的末尾处是他费力地用“花边”围起来,十分显眼的签名:“彼得·基尔萨诺夫,少将”。1835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基尔萨诺夫将军由于阅兵中出现差错而退伍,携妻子去彼得堡定居。他在塔夫里切斯基花园附近租了房子,并加入了英国俱乐部,但是却突然间死于中风。
阿加福克列娅·库齐米尼什娜很快随他而去:她过不惯首都沉闷的生活;退职闲居的日子使她郁郁寡欢,愁苦而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父母在世时便爱上了他从前的旧房东、官吏普列波洛维恩斯基的女儿,这件事颇使父母伤心。她很漂亮,一般说来还是个很有教养的姑娘:喜欢读杂志上“科学”专栏里的严肃文章。服丧期一满,他就娶了她,并辞去父亲为他在皇室地产局里谋到的职位,带着他的玛莎过起了快乐的日子。起初他们住在林学院附近的别墅里;后来搬进城里一所很讲究的小住宅,楼梯很干净,但客厅有些阴凉;后到了农村。他在那儿终安顿下来,又很快有了儿子阿尔卡季。年轻夫妇的日子很美满、很安宁:他们几乎从未分离过,一起读书,一起用四只手弹钢琴,一起唱二重唱歌曲;她种花,照管家禽;他偶尔去打打猎和料理家产,阿尔卡季也一天天长大了——长得又漂亮又文静。十年的时光像梦一样逝去。1847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辞世而去。他勉强经受住了这一打击,几个星期的工夫,他的头发全白了;本来他打算去国外散散心……可是,1848年到来了。他只好回到乡下,很长时间过着疏懒的生活,后来便开始了经济改革。1855年,他送儿子进大学,同儿子一起在彼得堡度过了三个冬天。他几乎从不出门,只是尽力结交阿尔卡季的那帮年轻朋友们。后一个冬天他没法再去彼得堡,——于是在1895年5月我们见到了他。他头发花白,开始发福,背有点儿驼,正在等候像他从前一样得到学位回家的儿子。
那个听差因为礼节的缘故,也许是不想站在老爷面前,便来到门口抽起烟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下头,注视着一级级破旧的台阶,一只肥大的花雏鸡正顺着台阶走来走去,黄色的大鸡爪颇用力地敲打着阶面;一只脏乎乎的猫蜷曲着身子趴在栏杆上面不怀好意地看着它。烈日当头;客店里阴暗的过道中散发出一股烤热的黑麦面包的气味。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陷入了沉思。“我的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季……”这些字眼儿在他的头脑中不停地转来转去,他试图去想点别的事情,可是又回到这些念头上。他起想了过世的妻子……“她没能活到这一天啊!”他痛苦地喃喃自语道……一只灰色的胖鸽子飞到路上,急匆匆地奔向井旁的小水洼里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注视着它,可是,他的耳边已经传来了渐渐驶近的车轮声。
“好像是少爷来了。”听差从大门口过来报告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起身凝神向大路望去。一辆驾着三匹驿马的四轮大车出现了;四轮大车上一闪一闪地晃动着大学生制服的帽圈和他熟悉的、亲爱的面孑L的轮廓…… “阿尔卡季!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喊了起来,一边挥动着双手跑向前去……一眨眼的工夫,他的双唇已经贴在了年轻学士没有胡须、落满灰尘、晒黑了的脸颊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