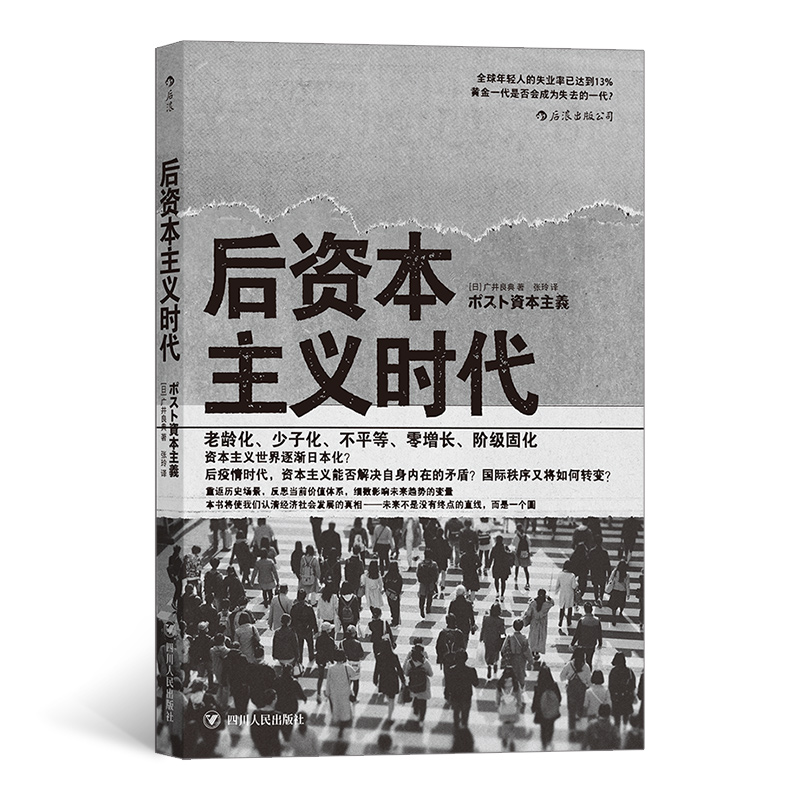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8.60
折扣购买: 后资本主义时代
ISBN: 97872201226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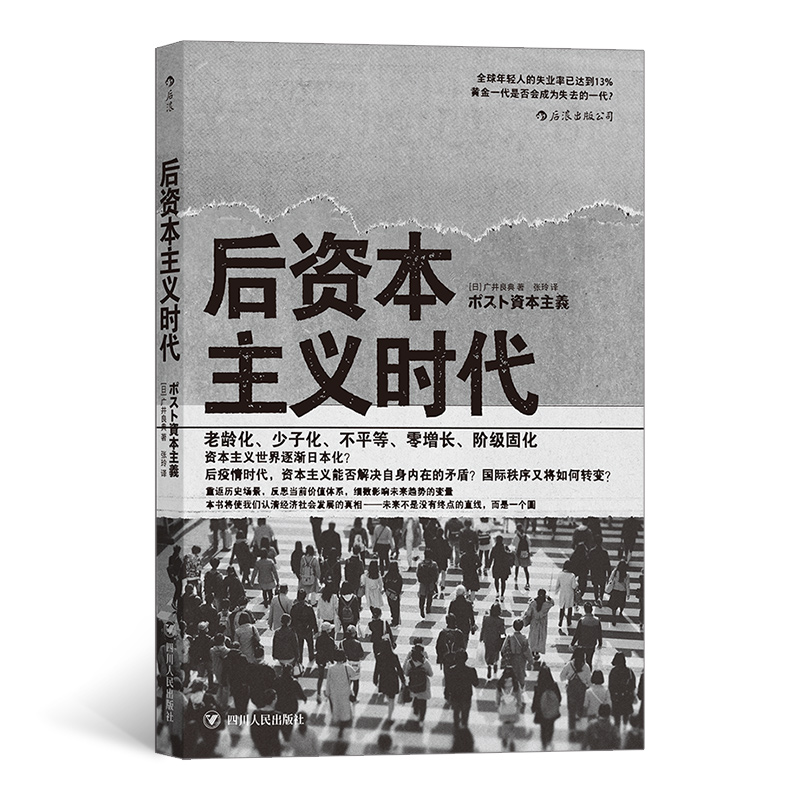
广井良典,京都大学心灵未来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共政策和科学哲学。毕业于东京大学,曾在厚生省任职十年,后任千叶大学法经学部助理教授及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客座研究员、东京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客座助理教授及客座教授等,自2016年起任现职。期间曾多次在日本民间机构及政府部门主办的各项政策研究委员会中出任委员。著有《日本的社会保障》《生命的政治学》《全球化稳定社会》《生命与时间》《人口减少社会的设计》等,曾获经济学家奖、大佛次郎论坛奖等多个奖项。
社会的安全网 前面介绍了今后发展方向的两大支柱(1)抑制过剩和(2)加强和重组再分配中的前一项,那么后一项,即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分配”和保障平等呢? 我们首先从“社会安全网”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图7-1 对目前日本及各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的构造做了简单概括。 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就业安全网”(C)。这一层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拥有工作并获得工资是维持生活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自然不过的。 不过人们可能会生病或失业,老年人退休以后会失去收入来源。此时就需要位于金字塔中间的“社会保险安全网”(B)发挥重要作用,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等都属于这一类。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险的前提是需要有工作,以“社会保险缴费”的形式事先支付一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它是与(C)“就业安全网”配套的。所以,没有工作的人、生病的人或失业时间较长的人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安全网。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最后的安全网”(位于金字塔中最下层的A)—最低生活保障—发挥作用了,它依靠税收为人们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以上是社会安全网的一般构造,这里要讨论的是下面这一点。 从历史来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安全网是按照金字塔由下向上的顺序依次构建起来的,与前面介绍的顺序相反。 社会安全网最早的代表性事件为英国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由伊丽莎白一世制定的《济贫法》,这一年碰巧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第二年。正如第2 章曾提到的,当时英国的毛纺织业等农村工业兴起,市场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其负面影响也显现了出来,城市出现了贫困阶层并不断扩大,《济贫法》正是为应对这些情况而制定的慈善救济政策。 到了18 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带动工业化快速发展,也造成了大量城市劳动者,《济贫法》等事后救济政策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便出现了劳动者(在生病或失业之前)事先按期存入一些钱作为公共资金池,提前预防陷入贫困的体系。国家强制必须参加的“社会保险”由此诞生,正如大家熟知的,社会保险发源于当时迅速工业化并开始威胁英国地位的德国(普鲁士),由首相俾斯麦实施(在19 世纪70 年代设立了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相当于社会安全网的中间部分(B)。 修正资本主义 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终于在1929 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萧条。 马克思主义阵营认为资本主义陷入了生产过剩,必须由国家对生产进行计划性管理,这时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救世主出现了。凯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事业或社会保险介入市场,创造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需求,由此便能形成金字塔最上层的“就业”。 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是对资本主义核心的“修正”,正如第2 章介绍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理念和政策也被叫作“修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借由这些政策走出了恐慌和战争的阴影,实现了20 世纪后半期(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为止)的空前增长。 从这个过程可以发现,正如前文讨论的,资本主义是按照从下向上的顺序构建出图7-1 所示的社会安全网的。 应该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介入从资本主义体系的终端部分逐渐深入到更为核心的部分。 也就是说,最初从《济贫法》等事后救济(第1 阶段)开始,发展为社会保险等事前介入(第2阶段),再到20世纪后半期以后,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介入市场,直接创造就业(第3 阶段)。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上述过程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着分配不平等或增长动力枯竭等危机,其应对措施或“修正”从“事后”和末端逐渐深入和扩大到了“事前”和体系最“核心”(乃至中枢)的部分。 “修正”的内容是政府或公共部门不断扩大对市场的介入,这也是资本主义对其体系依次进行社会化或向体系中导入“社会主义要素”的过程。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空前增长(被部分社会化)的资本主义,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逐渐进入低增长期,如同第2章介绍的,经过金融化和信息化及全球化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复兴之后,遭遇了2008 年金融危机。 那么,资本主义今后的设想或构筑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呢? 我们需要新的安全网 按照前文论述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修正或社会化逐渐从体系末端深入核心”的大方向,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今后的特征就应该是“深入体系最核心(及中枢)的社会化”。 对照图7-1 所示的金字塔,这就意味着金字塔顶端部分的社会化,或新型社会安全网的构建。我在以前的著作中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广井,2009b,2011),总的来说我认为应该以下面几点为核心: (1) 通过“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等进一步保证人生中的“共同的起跑线”或“机会平等”; (2) “ 存量社会保障”或资产(土地、住宅和金融资产)再分配; (3) 恢复社区安全网的作用。 这其中(1)和(2)与“社会化”的方向有关,(3)则略有不同,它与超越市场(私人)和政府二元论的共同领域有关,也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发展等理念密切相关(下一章我们将详细讨论这部分内容)。 首先看(1),其内容为加强包括教育和就业、住宅等与年轻人和儿童相关的社会保障及公共补助(充分应用遗产税等为财源),充分保证每个人能在人生的最初阶段站在“共同的起跑线”上。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深入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社会化”呢? 在近代理念当中,社会由“独立、均等的个人”构成,个人(通过契约)组成社会。近代历史的舞台上产生的“福利国家”也拥有同样的社会观,因此福利国家在本质上以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自由从事经济活动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在出现贫富不均等问题时)进行事后修正。 但这种社会观忽略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不言自明的)事实,那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家庭或家族,个人并不是作为“赤裸的个人”以平等的条件出生的,而是存在于世代间的继承关系当中。 因此如果不以某种形式对世代之间继承的部分进行“社会介入”,或者不对“遗产继承”等私人行为进行某种再分配或社会化,前一世代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原封不动地被下一代继承。 最根本的问题是, 应该将这种现象视作“ 是” 还是视作“非”?这个主题关系到最基本的人类观或社会观,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其关键在于将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看作是“个人”还是“家庭(或家族)”。 回归个体机会平等 前者认为应该使个人在出生时尽可能处于平等的环境中,确保“个人的机会平等”,而后者认为父母取得的成果或遗产理所当然应该由子女继承和享受,不应受到侵害或由政府介入。 正如前文确认的,近代理念原本以“个人”为基本的社会单位,所以简单来说比较接近前者。但实际上,继承或由父母到子女的传承却被作为最“私人的”领域保留下来,政府的介入被控制在最小范围(虽有遗产税等制度,但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生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措施的结果就是,现实中的“不平等的延续和积累(或贫困循环)”十分严重,现在已经到了无法再忽视下去的程度。近些年来在日本引发关注的“儿童贫困”问题,以及大学升学率与父母收入相关等事实(孩子所在家庭的收入越高,大学升学率越高)都与此相关。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只有在这方面加强政府介入,由政府进行再分配,才能确保机会平等,同时(在保证每个人拥有均等机会的意义上)也有利于活跃社会和经济。 我曾讨论过其中最有趣的一点(广井,2001),每个人在人生的最初阶段站在“共同起跑线”上,这原本是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理念。但在现实中放任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发展,便会导致不平等的延续和累积,而无法实现这种平等的起跑线,因此必须采取前面提到的相关政策措施,如对继承进行一定的社会化或加强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等。 这里存在一个本质上的悖论,即为了实现个人机会平等这一资本主义理念,就需要某种意义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换句话说,保障个人的自由无法靠自由放任实现,而必须积极地依靠社会创造。 世袭:不平等的延续 关于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我还想从具体层面做一些补充。基本的事实情况如图7-2 所示,日本的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在国际上处于极低的水平。 此外,作为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教育对青少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比较各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发现,丹麦(7.5%)处于第一名,此外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也位居前列,而日本只有3.6%,连续五年都在发达国家(OECD成员国)中垫底(OECD成员国平均为5.3%)。 尤其日本的特点是,上小学之前的学前教育和大学等高等教育中个人负担的比例极高,严重损害了机会平等。根据OECD在2011 年的数据,日本学前教育的个人负担比例为55%,而OECD成员国平均为19%;日本高等教育的个人负担的比例为66%,OECD成员国平均为31%(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战败以后在占领军主导下进行的主要改革有“农地改革(即土地的再分配)”和“中学义务教育”,这两项改革其实都具有大力保障人生最初阶段共同起跑线的性质。农地改革也关系到下文将要讨论的“存量资产再分配”(广井,2009a)。 正是这些彻底的改革保障了个人的机会平等,同时也推动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但同一体系在持续多年的过程中,不平等的延续和“世袭”特征会不断加强,这就是现如今日本社会的情况。日本的社会本身很容易固化,所以应该推出相关政策,强化遗产税,将其用于教育等“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对此后文还会详细论述。 另外,关于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还有一点绝不能忽视的是关于(社会保障等)的“世代间分配”的问题。 请先看表7-1。这是对社会保障的整体规模和其中老年人相关支出(这里为养老金)规模的国际间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要注意的是,日本的社会保障整体规模在这些国家中属于最小群组,但老年人相关支出(养老金)的规模却是最大的。 将日本与丹麦加以比较,这一点会更加明显。丹麦的社会保障整体规模接近日本的1.5 倍,但日本的老年人相关支出(养老金)却要多于丹麦。除了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整体规模也都远远大于日本,而养老金规模却都没有日本大。反过来说,这说明这些国家对老年人相关之外的社会保障(儿童相关,对年轻人的补贴、就业和住宅等)是极为优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从表中也可以看出, 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与日本结构相似,它们的特点也是社会保障的整体规模相对较小,但养老金规模却很大。2010 年希腊经济危机的主要背景之一就是养老金问题,大家对此大概仍然记忆犹新。 代际公平 这样来看,日本的社会保障在代际之间的分配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倾斜和扭曲,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将社会保障从老年人相关转为分配给“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不过这其中还包含着以下更为复杂的因素。 因为说到养老金或者老年人,老年人与老年人也各有不同,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简单来说,在日本目前的养老金制度中,对老年人的给付同时存在着“过剩”和“过小”的现象。 也就是说,老年人中收入较高阶层(因为在职时收入较高,所以相应地)拿着相当高的养老金,但另一方面,全额国民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缴费交满40 年)为6.5 万日元,但现实中女性的平均领取金额只有4 万日元左右,有很多人还要更少。实际上,日本65 岁以上女性的“(相对)贫困率”为约两成,单身女性的这个数字则更是高达52%(数据来自2009 年的内阁府统计)。 因此,从现状来看,一方面有人领着可以说是过剩的养老金,另一方面真正需要的人却领不到足够的养老金。2012 年日本的社会保障总支出为108.6 万亿日元,其中养老金多达近一半,为54万亿日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日本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中,报酬比例占了很大部分(即被称为福利养老金的“二楼”的部分),这一部分制度本身就具有“收入越高以后领到的养老金越多”的性质。而且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质上采用的是现收现付方式(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来自在职一代缴付的保险),因此是由在职一代负担的。 从基础养老金(保障基本生活)的特点来看,这部分原本应该用税收充当,但却并没有实现(一半源自保险费),于是就产生了上述越是低收入阶层越得不到足够养老金的情况。 从整体来看,无论对“世代内部”来说,还是对“代际之间”来说,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逆向的”,也就是说反而会加剧贫富差距。 前文对日本和丹麦做了对比,丹麦的养老金制度与日本相反,以“基础养老金”(财源全部来自税收)为主,这部分比较优厚而且平等,而报酬比例部分则十分有限。这样就能在充分保障低收入者权益的同时,又使养老金整体给付规模小于日本,与日本的情况完全相反。 我认为政府养老金的基本作用原本就是为了平等地保障老年人能维持一定水准的生活。因此从大方向上来说,日本应该实施改革,(像丹麦一样)用税收支付充足的基础养老金,缩小报酬比例部分。这样既能在老年人之间实现“世代内部的公平”,又有助于实现他们与年轻一代乃至在职一代的“ 代际之间的公平”。 具体来说,除了遗产税,还应该加强对(高收入退休者的)报酬比例部分养老金征税,建议今后制定政策,将这部分税收用于“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通过这样的政策,上述每年超过50 万亿日元,而且还在稳步增长的养老金支出中,就可以拿出比如与报酬比例部分相关的两三万亿日元再分配给与年轻人和孩子相关的补贴,这将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资产和土地的再分配 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决定了今后应该实行“深入体系核心的社会化”。前文讨论了其中的第一个支柱—保障人生的共同起跑线,下面再看我列为第二个支柱的“存量社会保障”或资产(土地、住宅和金融资产等)的再分配。 我在最近的著作中从多个角度讨论过这个问题( 广井,2009b,2011),这里只做简单介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 年所著的《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the Twenty-Firt Century)一书的核心内容也与这个问题有很多重叠(Piketty,2014)。这本书在2014 年出版后在全球引发热议,成为全球畅销书。 我在上述拙作《反思社区》中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在GDP不断迅速扩张和增长的时代,即第2 章提到的20 世纪40 年代后半期至60 年代左右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GDP(即流量)增长十分显著,因此土地、金融资产等“存量”的比重相应比较低。但在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成熟期或“稳定社会”,流量的增加已经极少,存量的意义相对变大,特别是“不平等”和“分配”就成了社会的重要课题。 日本对不平等的讨论几乎都是关于“收入”(也就是流量)不平等的。但其实“存量”或资产(金融资产、土地和住宅)方面的不平等程度要更为严重,实际上分析基尼系数就能发现,2009年2 人以上的普通家庭年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1,而储蓄的基尼系数却是0.571,住宅和宅基地资产金额的更是高达0.579(数据来自2009 年全国消费实际情况调查),与收入不平等相比,金融资产和土地等的不平等要大得多(图7-3)。 存量(资产)是流量(收入)积累的结果,因此上述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这里所说的“积累”也包括从父辈到子辈的代际传承。与前文提到的“继承”一样,对近代资本主义或福利国家来说,“存量”和资产的领域也是“盲点”,处于政府干预的范围外,被保留在私人领域。 实际上,福利国家或社会保障一直都把“流量”再分配作为基本任务。无论是养老金制度,还是医疗和福利服务、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都是与“流量”相关的。唯有“公共住宅”属于例外,是关于存量的社会保障,但日本在这方面与欧洲相比还十分落后,公共住宅在住宅全体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且“小泉改革”以后又进一步压缩了公共住宅(广井,2009b)。 但是在如今这种成熟化乃至稳定社会中,流量的增长已经微乎其微,所以“存量”或资产的分配和再分配成了整个社会的重要课题,必须开始考虑“存量社会保障”这一新的构想和措施。 资本主义的终结 这个课题恰恰又与我们讨论的“深入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社会化”一致。因为是将“存量”或资产完全交给“私人”领域,还是对其实行一定的政府限制或公有措施,一直被看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分歧点。 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不过也要注意,与大部分土地都是私有的日本和美国相比,欧洲国家的公有土地比例相对要更大,特别是在北欧国家,“土地公有”其实很普遍,存量和资产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社会化。如赫尔辛基市的土地有65% 为市所有(包含国有地的比例是75%),斯德哥尔摩市的土地也有70%为市所有(日笠,1985;日端,2008;广井,2009b)。 总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今后就需要从“资产再分配”或“存量社会保障”的视角考虑应对措施。具体包括加强住宅保障,对土地所有进行再调整(加强和积极利用公有地),以及加大对金融资产和土地的征税力度,由此实现存量再分配和充实社会保障,这些都将是今后的新课题。 这个问题还可以扩展一下,关于土地和住宅的公有和共有的讨论与近些年来各种形式的“共享”(或共享经济)也有关系(三浦,2011)。 针对这些问题,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cent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是“r >g”,也就是说“r(从土地、金融资产等资产获得的平均收益)”要大于“g(经济增长率或收入增加率)”。 概括起来就是,运用拥有的资产得到的(不劳而获的)收益要多于劳动获得的工资。皮凯蒂列举了一些事实作为依据,如德国、法国和英国“资产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呈现出“U形”变化,即在1910 年到1950 年期间逐步降低,之后又再次上升。 皮凯蒂认为,造成上述局面的背景是“向相对较低增长体制的回归”,他指出,“在经济增长减速时代,以前的资产自然会对贫富分化带来重大影响”。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食利者(rentier)”(注:rentier 源自法语,也有“靠投资收益生活的人”的含义)。 创业者的消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或自杀行为。要避这种情况,就必须实行“深入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社会化”。也就是说,为了使资本主义理念存续下去,需要采取社会主义措施。这个悖论的构造与前文讨论的“人生较早阶段的社会保障”和机会平等的关系具有相同性质。 或者我们回想第1 章介绍的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和“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的观点就会发现,包括皮凯蒂的观点在内,我们这里讨论的方向也许可以说是“从资本主义的压制下保护市场经济或个人的自由”。 第3 章结尾介绍的经济学家西部忠认为,现在资本主义以系统风险的名义救助大肆销售次级贷款商品等的金融机构,是否定了“自由竞争”和“为自己负责”原则本身,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自相矛盾。这些都是布罗代尔提出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在不同形式上的体现。 对新的“财富源泉”征税 皮凯蒂说的是“向相对较低增长体制的回归”,其实“存量”所占比重变大的现象具有向高度增长(或迅速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回归的一面,而不是走向完全未知的领域,这一点其实与税收密切相关,税收是财富再分配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的。 这个问题我也在之前的著作中反复讨论过,因此这里只做简单介绍(广井,2006;广井,2013)。有趣的是,日本在整个明治时期,税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地租”,也就是对土地征收的税。 1877 年,地租收入占税收总额的82%。考虑其原因,税收作为“财富再分配”的主要工具,当然要对当时的“财富源泉”征税。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生产以农业为中心,土地是最大的“财富源泉”,所以对土地征税是税收的核心部分。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的生产活动成了“财富源泉”,所得税和法人税成了税收的核心(工业化时代前期)。日本大正前半期的总税收中,所得税也确实取代“地租”成了最大的收入来源。时代进一步发展之后,物质匮乏的时代结束了,人类进入消费社会,消费(需求)取代生产(供给)成了驱动或决定经济的主要因素,再加上老龄化因素(没有收入的退休人员也要缴纳一定的税),消费税开始登上舞台(工业化时代后期)。1969 年法国最先引入消费税。但是现如今,正如本章讨论的,在经济趋向成熟和饱和的过程中,“存量”的重要性再度提升,同时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及其有限性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和自然才是最终极的“财富源泉”。在此,对“存量”(资产)的征税和前文讨论“从劳动生产率转向环境效率”时提到的环境税(对土地这种重要的自然存量征税)在新的背景下变得重要起来,其“分配(再分配)”方式也成了重要课题。 属于生态学流派的英国经济思想家罗伯逊(Dennis HolmeRobertson)在对公共资源(common resource)征税的构想中,论述了对土地和能源等征税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应该对“人类开发的价值”而不是“人类增加的价值”征税。 这体现了人们在认识上的根本转变,即“财富的源泉”首先是自然本身,而不是人类的劳动和活动(Robertson,1999;Fitzpatrickand Cahill,2002)。 他的观点不同于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可以叫作“自然价值论”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本来是人类的公共财产,利用自然资源获利的人当然应该交税作为“使用费”。这种对人类使用自然的行为征税,而不是对劳动和生产征税的设想是对税收以及“财富源泉”的终极理解,与本章论证的主题相关,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将不断深入,并在资源和环境限制日益明显以及需求趋于成熟和饱和的背景下继续发展。 上述内容可以整理为图7-4,这些理解对应着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视点,即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修正已经从“外围”逐渐深入到“核心”部分。 ◎当全球年轻人的失业率已达到13%,黄金一代是否会成为失去的一代? ◎老龄少子化、不平等、阶层固化、过劳与高失业率并存,资本主义世界逐渐日本化? ◎后疫情时代,资本主义能否解决自身内在的矛盾?国际秩序又将如何转变? ◎重返历史场景,反思当前价值体系,细数影响未来趋势的变量,将使我们认清经济社会发展的真相:未来不是没有终点的直线,而是一个圆。
图书资料整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