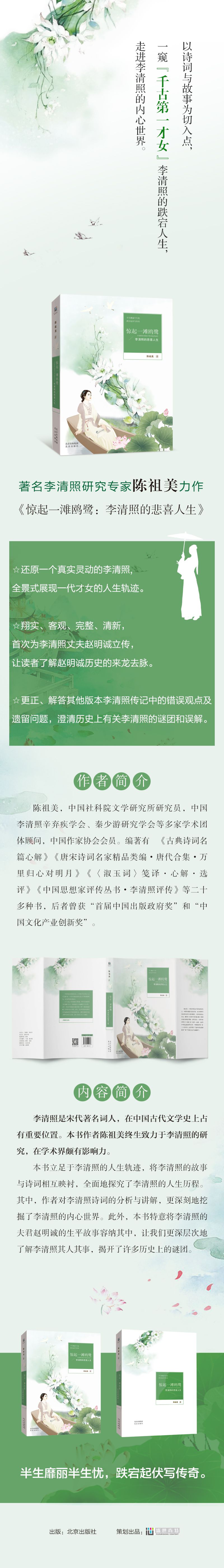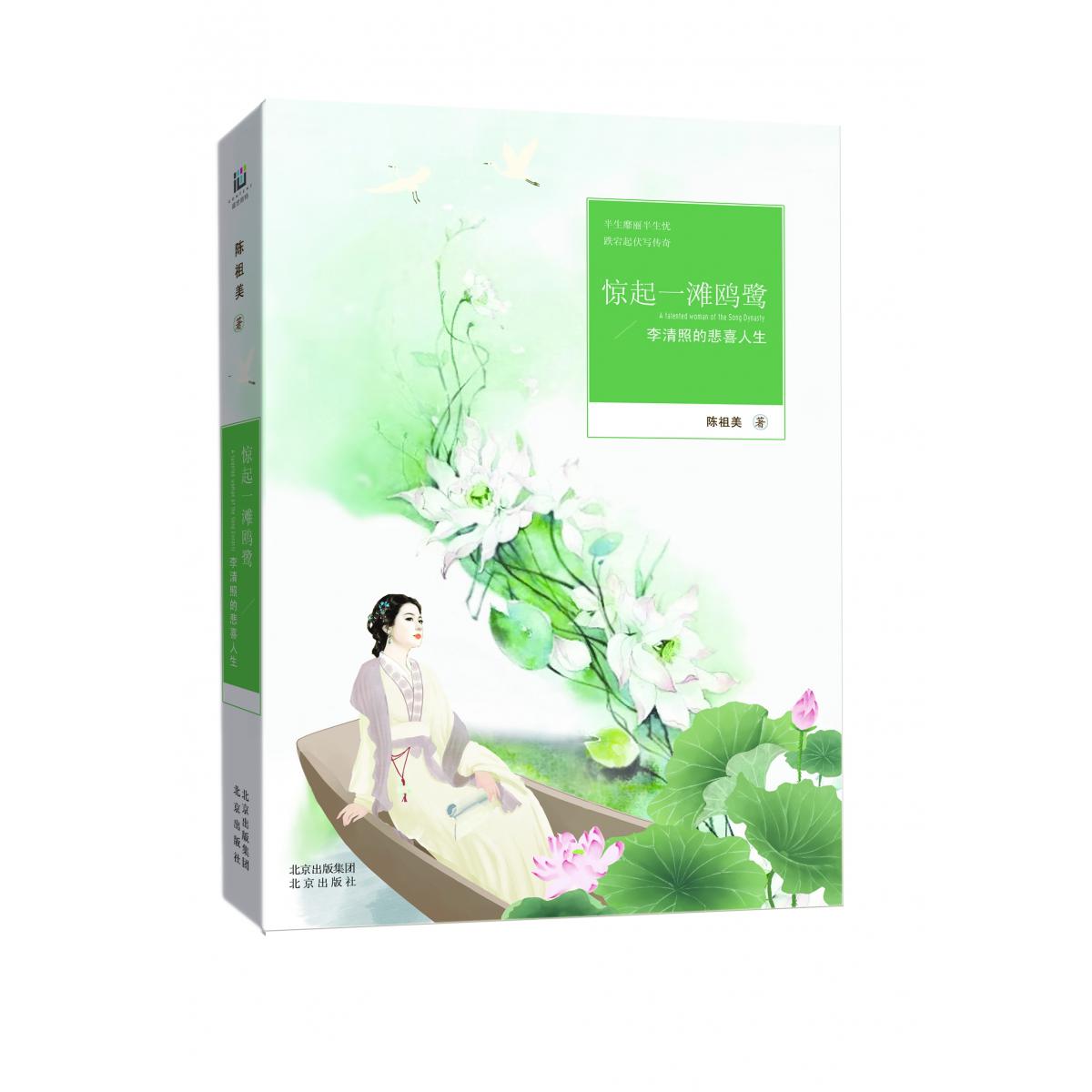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原售价: 68.90
折扣价: 37.30
折扣购买: 惊起一滩鸥鹭:李清照的悲喜人生
ISBN: 9787200174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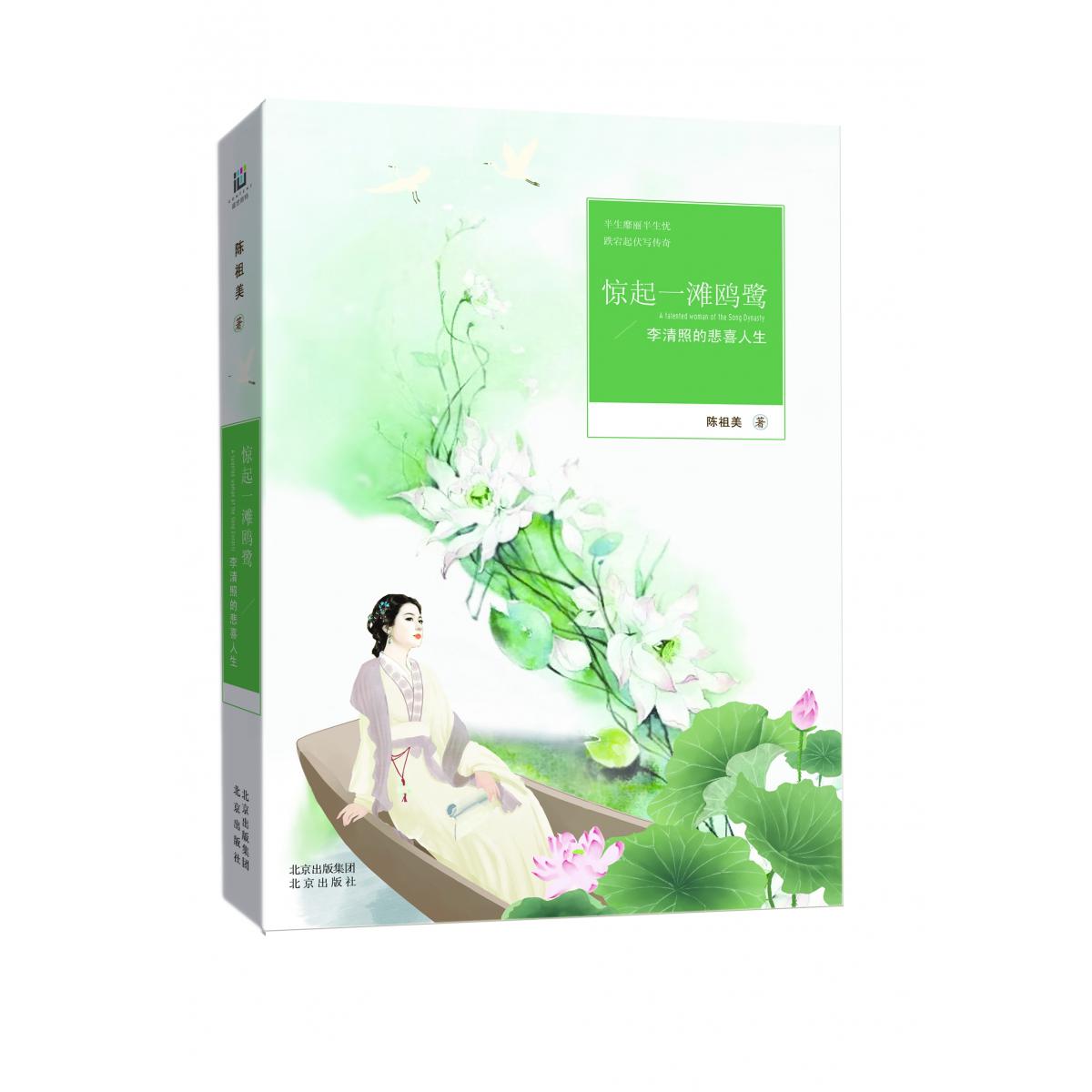
陈祖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秦少游研究学会等多家学术团体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著有 《古典诗词名篇心解》《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唐代合集?万里归心对明月》《<淑玉词〉笺译·心解·选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李清照评传》等二十多种书,后者曾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奖”。
一、学诗伊始 李清照有一首自叙创作经历、题为《分得知字韵》的小诗: 学诗三十年,缄口不求知。 谁遣好奇士,相逢说项斯。 作诗事先规定若干字为韵,各人分拈韵字,依韵作诗,叫作“分韵”。李清照“分得知字韵”是指拈得“知”字,限其押“知”字韵。此诗约作于宋高宗建炎二年春。至于其自谓“学诗”,实际上是指她的“作诗”历程,其学步阶段当开始得很早。因为她既有无与伦比的天赋,又有文学气氛极为浓郁的生活环境,其牙牙学语的同时即可学诗。 由公元1128年上溯三十年,她的诗歌处女作当产生于十六岁那年。那年她可能刚到汴京,京都的诗情画意更浓,她家也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其父格非文章几乎无人与之匹敌,但是作诗却不如秦观和晁补之。李清照则不甘示弱,年方及笄不久,所作诗已为士大夫称赏不已,所以“相逢说项斯”句便很耐人寻味。 “项斯”是唐朝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人,字子迁。其当初能诗而无诗名,遂以诗卷谒见国子监祭酒杨敬之。杨赏识其才,作《赠项斯》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见《唐诗纪事》卷四九)“说项斯”即替人说好话,并使其增重于世。故此句既是诗人渴望像杨敬之那样德高望重的人为自己“说项”,亦当隐含着对曾为自己“说项”的文学长辈晁补之等人的怀念之情。 这虽然是一首小诗,但从用语看,却有其独到的文化含量。比如“缄口”一词,在此诗中不一定有明哲保身之意,仅指不求闻达、闭口不言而已,但作者恐不是随意拈来,很可能是从这样一段话中受到启发:“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刘向编著《说苑·敬慎》) 《说苑》是一本历史故事集,原有二十卷之巨,后只存留五卷。大致是李清照祖父辈的曾巩,广搜佚文,恢复到二十卷的规模。书中所辑的自先秦至西汉的历史故事,于家国兴亡、政治成败多有鉴戒,且文字精练。此类书籍对李清照的影响恐怕非同一般。 二、上元节的日日夜夜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此日夜晚叫元夜,也叫元宵。其实元宵节不单是指一个夜晚,从十四日晚的张灯预赏(也叫试灯)到十六日收灯毕,都人士女跨马乘车出城探春探春:探望春光,即初春至郊外宴游。详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探春》。此处及本书其他章节所涉及的汴京元宵节的盛况,有些系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邓之诚注本铺衍而成的。,前前后后的好几个日日夜夜均热闹非凡。李清照更是提前“进入角色”,本来她在故乡明水时的穿戴,已是地道的“京都样”,不少服饰当是外祖母指定京城的上等手工为她制作的。来到汴京后,她前去探望两家的舅父、舅母及众多表兄妹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夸赞她气质高雅、打扮入时。或许是应了那句“女为悦己者容”的话,或因其素有争强好胜之心,李清照蓄意要把自己打扮得通身济楚,向都人展示她那些花色新颖、质地贵重的首饰…… 大家闺秀的继母颇具大家风范,当她知道李清照早就盼望元夜来临时,便把一个手脚麻利又颇具见识的侍女,割爱安排到李清照房中,还特意为这年龄仿佛的主仆二人购置了合体的衣饰。家里也安排得停停当当,节日气氛极为浓郁。小弟李迒更是欢天喜地,提着自己最心爱的花灯跑里跑外。在阳光还映照着帘钩时,他就要上车出发。这时李清照亦已盛妆待发,听到小弟催促,遂走出室外观看天色。她心里也盼着早些日落西山,一举首但见:落日像融化在一片金色的霞光之中,暮云夭矫,刹那间聚合成一块巨大的玉璧——不禁脱口赞道:好一派融和天气…… 继母带领李清照姊弟、侍女及仆妇等人登车前往御街方向驶去。车马刚到不远处的巷口,见一灯火通明之处,继母对李清照说:这叫影戏棚子,此间灯亮烛明,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失则引聚于此。一路宫观寺院不时可见,均灯烛竞陈、光华夺目,鼓乐笙簧齐鸣,此谓之乐棚。御街两廊,奇术异能,歌舞百戏,火树银花,流光溢彩。万街千巷,游人如织,雅会幽欢,彻夜不眠。 时至十六,李清照与侍女来到唐睿宗赐名并御书题额的相国寺。待大殿前乐声四起,贵家老小悉入内游赏。李清照刚一露面,被亲友招至贵近看位。乐声鼎沸之中,佛牙、诗牌尽收眼底。她正在向侍女比比画画讲解诗牌的含义时,突然全身有一种异样之感。转瞬往另一贵近看位一扫,但见迎面射来一束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时她早已稔熟于心的“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的《楚辞·九歌·少司命》之句,差点儿脱口而出。定神一想,顿感羞云遮面,急忙拉了一下侍女,躲开这双大胆投来的凝视目光。此后诸般新奇景致她再也无心观赏,思绪和眼神都陷于慌乱之中。在回府的路上,她佯作困乏,闭目而思,连日来的盛事美景,固令其触目难忘,更难忘的是那双大胆的炯炯清眸…… 三、怀春之什 李清照在晚年回忆其少年时代时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是的,从她十五六岁到十九岁前后的几年间,是她一生中少有的美好时光,这还不仅是指年龄的如花似锦,更包含其生活环境的富贵闲雅。有两首《浣溪沙》分别写道:髻子伤春慵更梳,晚风庭院落梅初。淡云来往月疏疏。 玉鸭熏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遗犀还解辟寒无。 ? 莫许莫许,当为“莫诉”。许、诉形近而误。“诉”有辞酒不饮之意,如韦庄有《离筵诉酒》诗,其《菩萨蛮》词有“莫诉金杯满”句,与李清照此句词意相同。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融。疏钟已应晚来风。 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烛花红。 第一、第二首词中都出现过的“瑞脑”,就是名贵的龙脑香。而“遗犀”的来历则是这样的:“开元二年冬至,交趾国进犀一株,色黄似金。使者请以金盘置于殿中,温温然有暖气袭人。上问其故,使者对曰:‘此辟寒犀也。顷自隋文帝时,本国曾进一株,直至今日。’”(《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在第二首词中,不仅有色如琥珀的美酒,下片的“辟寒金”在宫中妃嫔眼中也是一种稀罕的首饰:“宫人争以鸟吐之金,用饰钗佩,谓之辟寒金。”(王嘉《拾遗记》卷七)生活在如此优越的环境里,主人公并不以为然,相反还有一种似乎是难以排遣的骚动不安的意绪。为此种意绪所左右,她醉也不是,梦也难成,不知如何是好。类似的意绪还表现在题作《春景》的第三首同调词中: 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理瑶琴。 远岫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禁。 即使略窥主人公当时的举止,也不难发现她“倚楼无语理瑶琴”时想的是什么,令其“难禁”的仅仅是“梨花欲谢”吗?她的另一首同调词也是从中窥视其闺情隐秘的窗口: 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 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清明”仿佛是只属于未婚女子的节日。此词所写的“寒食天”,离清明佳节只有一二日,寒食到了,清明就在眼前。何况“寒食天”已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好季节。在主人公的卧室里,名贵的香料快要燃尽,只有残烟袅袅。她一觉醒来,贵重的首饰已脱离秀发、隐藏在凹字形的枕头里。春日昼眠,竟睡得这样香甜,“梦”自然也是与美好爱情有关的“昼梦”。 词的下片写少女生活的悠闲自在。早春的天气寒意未消,燕子还没有从南方飞来,她就和女伴们做“斗草”斗草:竞采百草,以比优胜。白居易《观儿戏》诗:“抚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过家家之类的游戏,尽日快乐无比。下句的“江梅”,是梅中上品。从室内到室外,凡是与主人公有关的东西大都是贵重之物,其身份如何可想而知。结拍的“黄昏疏雨湿秋千”,是常为人提及的好句,它好在与清明时节的应景上。试想,一个少女在润物细无声的“疏雨”中,或是荡秋千,或是站在秋千旁边若有所思,二者均有可能。这情景即使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含有一丝淡淡的哀意,如同下片起拍所暗含的双飞燕的象征之意,那么主人公的这一丝哀意,也无非是“幽居之女,非无怀春之情”,只是在婉转俏丽的“易安体”中,托之花草、翎毛、闺物出之罢了。 四、不速之客和秋千小阕 正月十六日晚,李清照在相国寺大殿诗牌花灯前,与之有“目成”之想的那位贵公子,不是别人,他就是当朝中书舍人兼侍讲的赵挺之(字正夫)的第三个儿子赵明诚(字德甫,又作德父)。赵明诚不仅是一位学业优胜的太学生,当他还是一位倜傥少年时,便成了颇有名气的金石碑拓的收藏者。 这年元夜,他因同伴李迥回乡省亲,原不想在外逗留过久。无意中看到了一位他在梦中隐约出现过的才颉文姬、貌若宓妃的女子时,为之倾倒得几难自持。尽管事情发生在一瞬间未被他人察觉,但从那以后赵明诚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等到正月过后,李迥自明水返回汴京时,被赵明诚不时出现的恍惚神态弄得莫名其妙。他正欲盘诘时,赵明诚倒先把自己的内心秘密向李迥和盘托出——他有点儿诡秘地对学友说,自己在正月十六日晚曾有交甫、子建之遇交甫、子建:即郑交甫和曹植,二人都曾遇仙女。郑交甫遇仙事见《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列仙传》。曹植遇仙事见其《洛神赋》并序。,并把其所遇之人的神态风采做了一番描绘……又因他们“目成”于诗牌、佛牙之旁,所以故称其所遇为“诗仙”。李迥听罢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堂妹李清照,遂含笑不语。 又过了约一个月,在清明即将来临时,赵明诚已拐弯抹角地打探到“诗仙”与李迥有关,而且有可能就是礼部员外郎李格非的长女李清照。当时明诚之父为礼部侍郎,官职略高于李格非,加之格非曾长期在太学任职,是朝野公认的学识渊博者。因此赵明诚表面上是请求李迥带他诣李府拜访格非这位前辈师长,而他内心的小九九则是根据当时京师风俗,先斩后奏地为自己“相媳妇”,也就是想亲自验证一下已崭露文名的李格非之女,是不是就是自己亲眼所见的那位“诗仙”。然而,对李清照来说,此时的赵明诚完全是一位不速之客。 当赵明诚出现在李家院落时,李清照刚刚从秋千横板上跳下。打秋千时,人或坐或立在横板上,技高胆大者腾空而起,上下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骤然摆动,两手得紧紧握住秋千索。大家闺秀的如荑纤手,往往被绳索摩擦得又脏又疼,加之剧烈运动,汗水湿透了罗衣,就像柔弱的花枝上沾满露珠。她气喘吁吁,还懒得把手擦干净,猛然间看到来了一位客人,慌忙中跑掉了鞋子,着袜藏到了半掩着的门后,头上的金钗也滑了下来……当她认为自己的狼狈相已被门户掩住时,便调皮地回头观察来客,定睛一看,竟是与自己“目成”于相国寺的那一位。这次在她倚门嗅梅之时,耳闻目察的竟是一位声姿清亮、进止有致的端庄书生,而她在“客人”的眼中则更是“秾纤得衷,修短合度”,比曹子建笔下的“惊鸿”越发翩然可爱。不久,她以此为素材写了一阕小令《点绛唇》: ?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 这本来是一首反映待字少女心态的传神之作,作品本身和所缘之事,与李清照的手笔和行事,均多有契合之处。然而它却引起了多位资深李清照研究专家的怀疑和非议对于李清照的这首《点绛唇》,自清初贺裳《皱水轩词筌》疑系无名氏演韩偓诗以来,后世资深论者亦有持此说者。《李清照集》将其作为“附录”,《王集》则作为“存疑之作”。对此笔者试做过探考,以为此词当系李清照所作。详见拙文《关于易安札记二则》,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辑。,乃至被屏于《漱玉词》之外,其口实主要有两点:一是把“倚门回首”解作“倚门卖笑”,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倚门”语出《史记·货殖列传》的“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是以此说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而“倚门卖笑”是后人的演绎,以之形容妓女生涯是元代和清代的后起之义。鉴于“倚门”含义之演变,如定要为此词中的“倚门回首”寻找出处的话,那它只能出自《史记》而与后世的引申义无涉。况且此词中的“倚门”句,只是靠着门回头看的意思,不必有何出典。 ? 二是认为名门闺秀的李清照不可能演韩偓诗。实际上李清照的词屡演韩偓诗。单就这首《点绛唇》来说,尤其是下片的“见客人来”以下五句,岂不是对韩偓《偶见》诗的“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的精心隐括!即使按照被人误解了的思路,如王灼所指斥李清照的:“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顺藉也……其风至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碧鸡漫志》卷二)又可从反面印证这类有涉于“闾巷”的“通俗歌曲”式的小词,正是出自一向爱赏新生事物的李清照之手。何况这类词又是青年男女真实心态的写照,恐不应将其从《漱玉词》中涤除,尤其是下片这五句更生动地说明,李清照没有端起大家闺秀的架子,反倒别具一格地向世人展示她作为待字少女的内心世界,比起韩诗来,大有青蓝之胜。《词林万选》卷四、《三李词》等七八种版本之所以收载此词,恐怕也是事出有因、值得考虑的。 当然上述对此词的归属之见,尚为一家之言,即使能够解释李清照词早期的权威版本《乐府雅词》,因其“不雅”未收这首《点绛唇》;但是对诸如视其为苏轼、无名氏词的那许多版本,一时则难明所据。况且对《漱玉词》版本的甄别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赵万里和王学初先后所讲的这样两段话:“词意浅薄,不似他作。未知升庵何据”……《词林万选》中不可靠之词甚多,误题作者姓名之词,约有二三十首,非审慎不可也”,恐亦有再思之必要。 本书为著名李清照研究专家陈祖美的力作。陈祖美终身致力于李清照的研究,创作出既精彩又真实的李清照传记。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灵动的李清照,全景式展现一代才女的人生轨迹。 本书为翔实、客观、完整、清新的李清照传记,书中首次为赵明诚立传,让读者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本书驳斥并更正了其他版本李清照传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包括关于诗词的错误注解,以及关于李清照生平的错误观点,澄清了很多历史上的谜团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