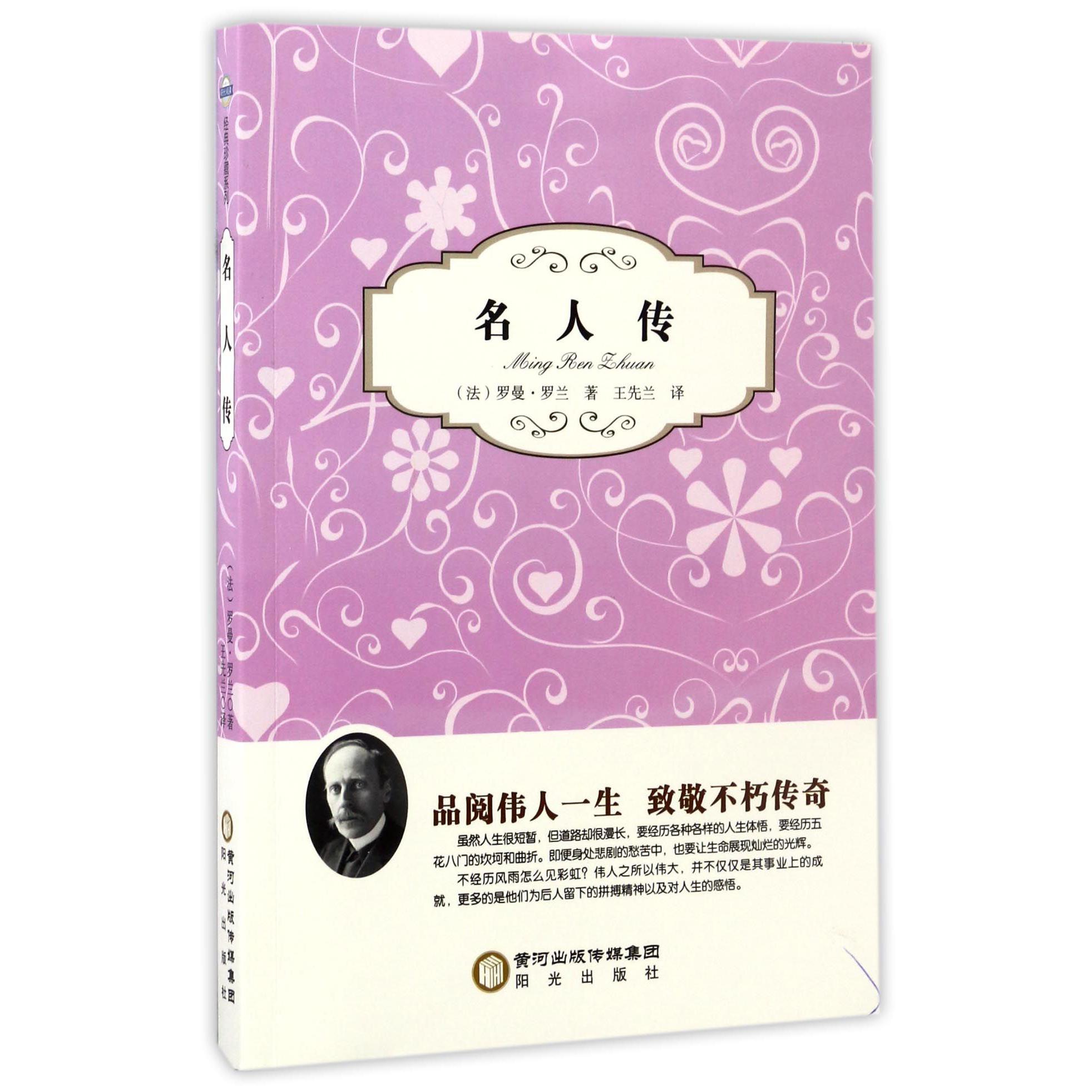
出版社: 阳光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20.16
折扣购买: 名人传
ISBN: 9787552517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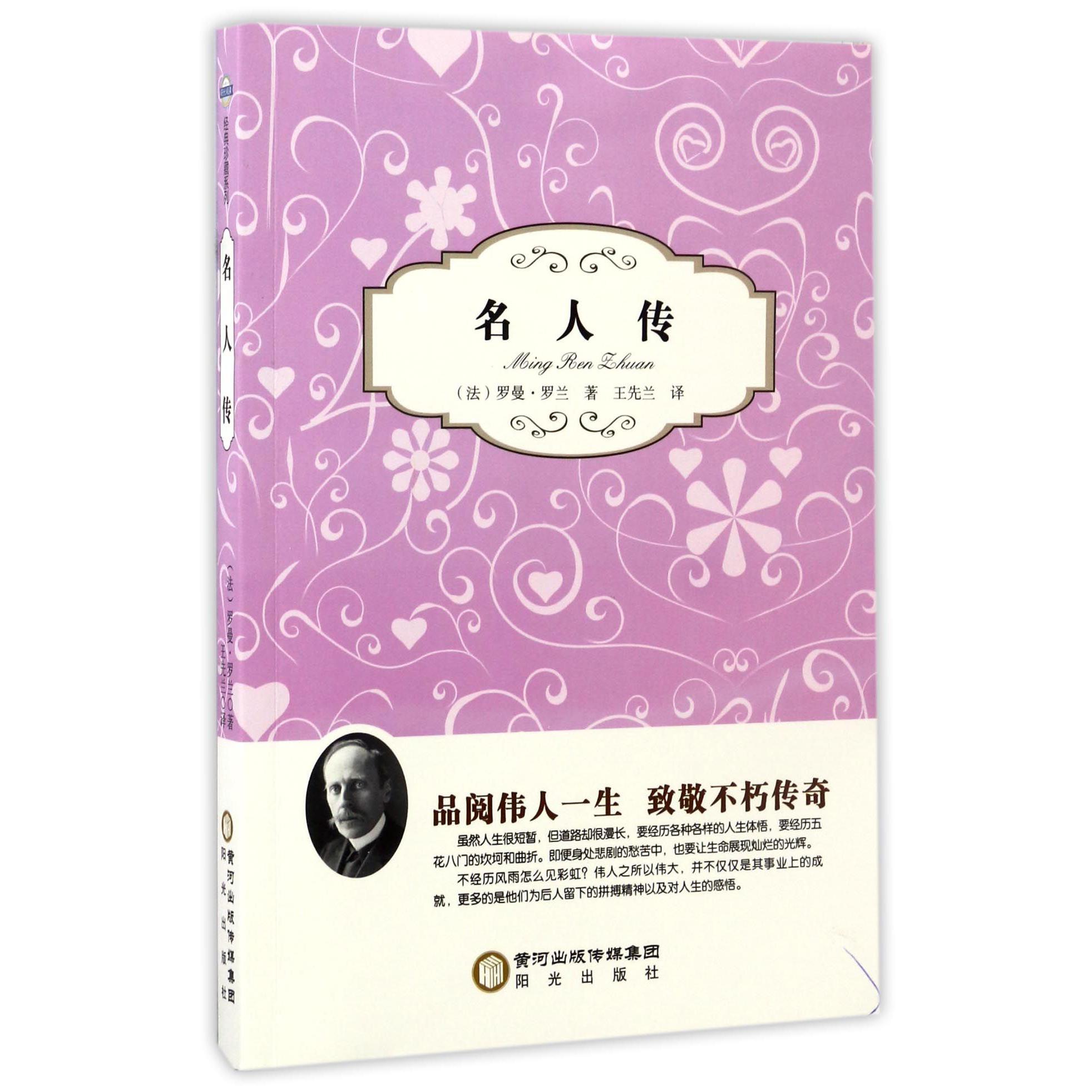
张辛,字此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家,文物和书画鉴定家,书法家,古诗文、碑志写作名家。主要从事商周考古、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古代文物、中国书画和国学的教学和研究。数获北大优秀教学奖,被学生评为“北大十佳教师”。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他凭借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获得1913年法兰西学院文学奖,后因其“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与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而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把不同时期写就的三部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为我们今天所称道的世界衔己文学的典范之作《名人传》。
他们家在佛罗伦萨历史悠远,他对自己的血统和 家族甚至比对自己的天才还感到自豪。他不允许别人 把他看作艺术家:“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 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他是精神上的贵族,具有这个等级的一切偏见。 他甚至说:“从事艺术的应该是贵人,而不是平民。 ” 他对家族怀有一种宗教般的、古老的,几乎是未 开化蛮族的观念。他愿为家族牺牲一切,且要求别人 也这样做。据他的说法,“为了家族,他卖身为奴也 在所不惜。”在这方面,一点小事他也会动感情。他 看不起他没出息的兄弟。看不起他的侄子——他的继 承人,虽然仍尊重他们作为家族代表的身份。他在信 里不断提到他的家族: “我们的家族……La nostra gente……维护我 们的家族……好使我们的家族不致后继无人……” 这个家族所具有的一切迷信、狂热,他都具备。 他整个人就是用这些迷信和狂热的泥土塑造出来的。 但从这泥土里进射出一道光焰,将这一切都净化了, 这就是:天才。 不相信天才,亦不知何谓天才的人,请看看米开 朗琪罗吧。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为天才所俘虏。这天 才似乎不同于他的本性:那是一个征服者,冲进他的 内心,将他牢牢抓住。他的意志对此无能为力。几乎 可以说:他的精神和他的心灵无能为力。这是一种狂 热的亢奋状态,一种可怕的生命力,他的身心过分疲 弱,无法控制。 他不断生活在亢奋的状态之中。体内聚积着的旺 盛精力让他痛苦,迫使他行动,不断地行动,难得有 一小时的休息。 “我干得精疲力竭,从来没有人这样干过。”他 写道,“我日夜工作,其他什么也不想。” 这种病态的活动需求不仅使他工作量目增,还使 他接受了许多难以兑现的订单。他简直成了工作狂。 他甚至想雕刻整座山。如果要建造某个纪念性建筑, 他会经年累月地跑到采石场里挑选石头、修筑道路运 输石头。他什么都想做:工程师、操作工、凿石工。 他事必躬亲,修建宫邸、教堂,样样自己动手。简直 是苦役犯的生活!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在他 写的信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 我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没有时间吃饭… …十二年来,我累 垮了身体,连日常必须的东西都没有……我一文 不名,身无长物,浑身是 病……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我在和贫困作 斗争…… 这种贫困纯属臆造。他有钱,挣了很多钱,非常 富有。可钱对他有什么用?他日子过得像穷光蛋,干 起活来像拉磨的马。没有人明白他这样自虐的原因。 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适可而止地工作,谁也不明 白这样自讨苦吃已成为他的一种需要。甚至许多特点 与他极为相似的父亲也来信责备他: 你兄弟告诉我,你生活非常节省,甚至到清苦的 地步。节俭固然好, 自虐就不好了,这是上帝和人类都不喜欢的事, 会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年 轻时还过得去,待年纪一大,贫苦生活带来的病 痛会一起冒出来。别再过 苦日子,生活要有所节制,必需的营养还是要的 ,千万别过分劳累…… 但怎么劝也没用,他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只 吃面包,喝点葡萄酒。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在波伦亚 忙着为尤里乌斯二世塑铜像时,他和三名助手只睡一 张床。睡觉时衣服靴子都不脱。有一次他腿肿了,只 好将靴子割开。脱靴时,腿上的皮也被扯了下来。 这种可怕的卫生习惯,恰如他父亲警告过的那样 ,使他经常生病。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患过十四 或十五次大病。有几次高烧,差点要了他的命。他的 眼睛、牙齿、头部、心脏,都有病。他常被神经痛所 折磨,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真是苦不堪言。他未老先 衰,四十二岁便感到老了。四十八岁时,他写信说, 如果他工作一天,就要休息四天。但他顽固地拒绝就 医。 这种工作狂的生活,对他精神的影响比对身体的 影响更甚,悲观主义侵蚀着他。这是一种遗传病。青 年时期,他想尽办法去安慰不时突发受迫害妄想的父 亲。米开朗琪罗自己比父亲的症状更重。永无休止的 工作,难以承受的疲劳,使他从来得不到恢复,总是 处于多疑的精神误区之中。他猜疑他的敌人,猜疑他 的朋友、父母、兄弟和养子,总怀疑他们盼着他早死 。 一切都使他不安;家人对他整天心神不定感到好 笑。他自己也说,他总处于“一种忧郁甚至疯狂的状 态”。久而久之,他竞把痛苦变成了一种嗜好,似乎 从中找到了一种苦涩的快感: 越是加害于我,我越快乐。 一切的一切,乃至爱和善,都成了他痛苦的主题 : 忧伤是我的享受。 P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