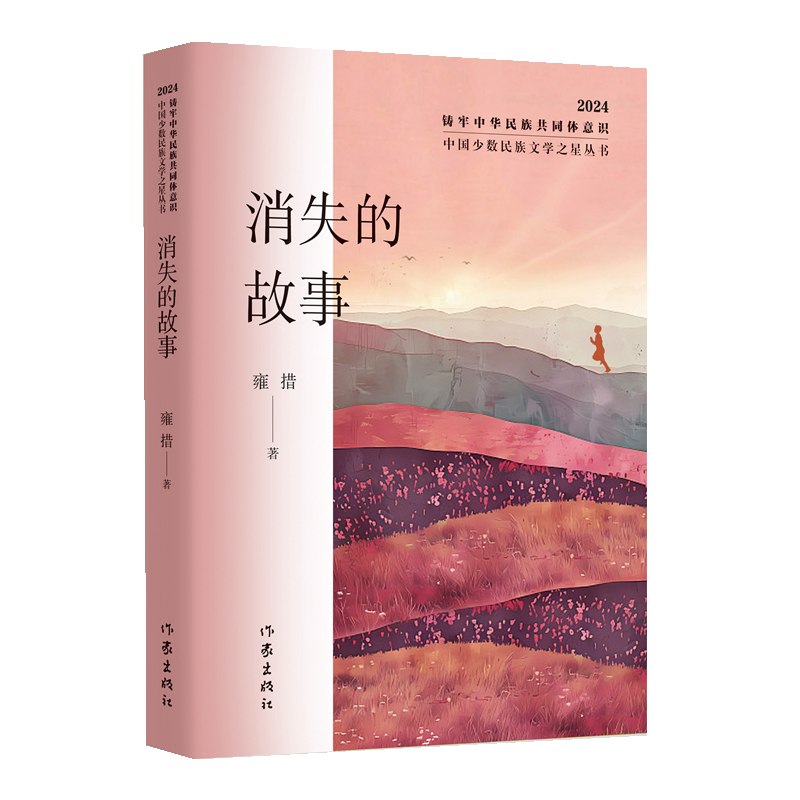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6.48
折扣购买: 消失的故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2024年卷)
ISBN: 9787521230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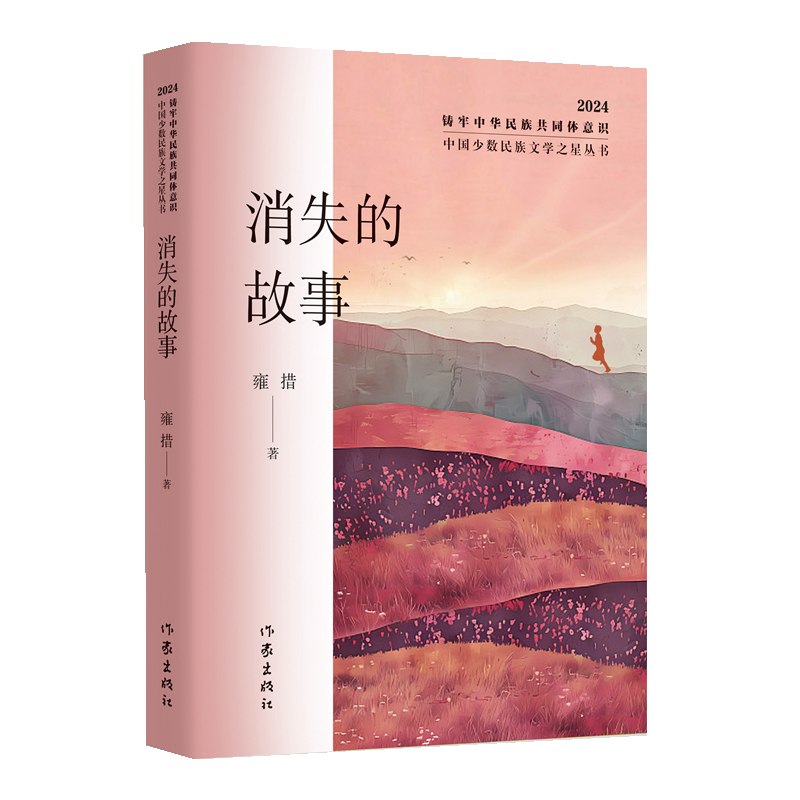
雍措,藏族,四川康定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在全国公开刊物发表散文、小说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散见于《十月》《花城》《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期刊,出版散文集《凹村》《风过凹村》,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四川文学奖“特别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花城》文学奖散文奖、《收获》无界漫游计划入画散文奖等奖项。作品翻译成朝鲜文、蒙古文、藏文等。有文字收入各种选本。
\"第一辑 光把他陷了下去 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 我忘记那是什么日子了,凹村走出去很多年的人,都在那段阴雨绵绵的日子回到了凹村。 一条很久没有热闹起来的土路热闹起来了,一个很久没有点儿说话声的村子活泛起来了,一座座很久没有人住过的泥巴房夜里到处亮着灯,灯光从每家每户的木窗户里透出来,忽闪忽闪的,仿佛灯在夜里也不敢相信自己还会亮似的。 其他村子跑得快一点儿的家畜像马呀,牛呀,狗呀,都从自己的村子跑到凹村来凑热闹,他们想来看看一个突然热闹起来的村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从自己的村子偷偷跑出来时,尽量不让村子里的人看见自己正火急火燎、兴头十足地往另外一个村子赶,他们怕村子里的人看见自己对另外一个村子那么感兴趣,会彻底对他们灰心丧气。人一旦对自己养了几年或十几年的家畜灰心丧气了,整个村子都会有一种灰心丧气的气味飘在空中。空气会受到影响,土地会受到影响,树木会受到影响,村子里的风会把这种灰心丧气的气味,刮得到处都是,让别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村子现在已经灰心丧气了。 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那些从自己村子里跑出来的家畜,把平时常走的一条出村路,绕着走,逆着走,歪着走,把留在地上的脚印走得不像一个脚印,他们想让人误以为,那不是自己养了几年或十几年家畜的脚印。不是自己的脚印,人就放心了,人想自己养了几年或十几年的马呀,牛呀,狗呀,可能只是一时偷懒或调皮,睡在了哪棵俄色树下或哪片虫草山上,谁都在自己的一生里,有过一次或几次谁都不想见,谁都不想理的时候。人理解这一点,就不会去怪罪自己养的马呀,牛呀,狗呀了。 人不怪罪他们,有些跑不出村子的同类,会怪罪从自己眼皮底下跑出去的他们。这些同类跑不出去的原因有很多,腿短、力气不够、眼睛看不见、被束缚、怕主人发现等等,他们对着那些一心想去凹村凑热闹的同类发出恼怒、不甘心、指责的叫声,他们不想眼巴巴地待在原地而什么事情也不做,那样把他们显得太懦弱和无能了。 那几日除了凹村,其他村子也显得不同寻常,只是其他村子的不同寻常在家畜身上发生,而凹村的不同寻常是在回来的人身上发生。 那些从自己村子赶到凹村来凑热闹的家畜,躲在凹村附近的山坡上、树林里,虽然他们费尽心思、想尽办法来到凹村,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凹村是别人的村子,在别人的村子里,他们不敢大口喘气,不敢想走歪一条路就去走歪一条路,别人的村子始终是别人的村子。 那几日,凹村的四周到处弥漫着一种陌生的气味和一声声诡异的喘息声。那些出去多年再回来的人,感觉不到这种陌生的东西,他们早在一个曾经熟悉的村子里,把自己陌生了。 那些回来的人,好像是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他们说话的口音都带着四面八方的口音。每个不同的口音混在一起,凹村显得奇奇怪怪,仿佛凹村不是凹村,凹村成了别人的村子。 我一晚上睡不好觉,我的觉被说不清楚的什么东西抢走了。我早早就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木床被我翻来覆去的身体弄得“咯吱咯吱”地响。木床的响声在那几日也响得不同寻常。 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堂屋里走了一圈,在睡觉的屋子里走了一圈,在放粮食的黑房子里走了一圈,在做饭的灶房里走了一圈,走完这些地方,我在自己的泥巴房里再没有可去的地方了。我在这座泥巴房里住了几十年,闭着眼睛也能走上好几十圈。有的时候,我真不想在这个屋子里再走下去了,就像今天这样。我问自己,在这样一个天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出门走走吧,一个声音告诉我。 我打开院门,木门的“吱呀”声响在倒亮不亮的夜里,像给夜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没再关上那扇木门,我家的门哪怕是在夜里整整开上一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屋里除了有点去年生虫的粮食,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让别人心动的了。不过我知道,外面回来的人吃惯了外面的好粮食,他们嘴吃大了,味吃重了,再吃不惯生了小虫的凹村粮食,我可以放心地走。 我把自己跨出门的第一个脚步放得轻轻的,我不想让人知道,刚才是我把一个平静的夜打扰了。 不过我又安慰自己,即使有人在夜里听见我刚才的开门声,也没几个人会猜出是我,在还没有大亮的夜里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他们走后,我天天一个人生活在村子里,该走的路都被我走尽了,该看的风景都被我看完了,像我这样一个人,绝不会还对这个村子再感兴趣。有人即使听见我刚才的开门声,也在夜里分辨不出那声音来的方向。在一片夜里,声音会拐弯,会变着花样地糊弄人。那些听见我刚才开门声的人,他们想肯定是像他们一样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一个人,想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走进一片夜里,找寻一些自己曾经丢失在黑夜的东西。 无论怎样,他们都怀疑不到我的头上。 而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在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真正的原因是那几天我突然住不惯自己的村子了,仿佛我才是一个真正出去很久,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人。 拐过两道弯,走过三堵废弃的老墙,我站在天还没有大亮的夜里,累得不行。夜里的累来得比白天要快些,夜自身带着重量。我把手扶在老墙上,我需要一堵老墙支撑我的累。我的手刚放上去,老墙上的土就“稀里哗啦”地往下掉,我想一堵老墙也是在白天强撑着自己,一到晚上那股强撑劲儿过了,真的累和老就出来了。我把手从老墙上缩回来,手僵硬地垂在我的身体旁边,我突然觉得我的手在那一刻离我很远,一种近距离的远,莫名地让我恐慌。 我不想把自己直直地站在天还没有大亮的夜里了。直直地站着,我感觉自己正在夜里丢失自己。那种缓慢地丢失,那种你无法控制的丢失,那种知道自己在丢失自己的丢失,让我无奈和害怕。 我慢慢向有人住着的房子走。那几日,凹村所有的房子里都住着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人,不会有一座空房子像以前一样空在夜里。我轻轻地走,生怕吵醒那些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人。吵醒他们,就相当于吵醒了四面八方。当四面八方的声音响在天还没有大亮的夜里,凹村的夜又不是凹村的夜了,凹村的夜成了四面八方的夜。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路走下来,每座房子里都有低低的说话声响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那些声音很小,是故意不想让人听见的,但还是被我听见了。那些人不知道,我在凹村一个人待得时间太久了,一个人待得太久,眼力和听力都会特别地好。 在还没有大亮的夜里,那些人说着凹村的土话,摆着凹村陈旧的龙门阵,说到高兴时,他们还在夜里偷偷地笑。那笑是凹村人一贯的笑法,我即使没看见他们的笑脸,也知道他们笑的动作,嘴皮上翻,舌头顶着门牙,只有这样的动作才能发出凹村人一贯的笑声。 在夜里,凹村突然回到了很多年前的凹村。很多年前,凹村没有一个向外走出去的人,所有人都待在村子里,所有人都说自己死也不出去,即使死也要死在一座自己熟悉的村子里。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那些回凹村来的人说话声和笑声都很谨慎。他们说几句,马上停下来,笑几声,马上就不笑了。他们在屋里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声音,他们怕外面有像我这样的人,听见他们说着凹村的土话,笑着凹村一贯的笑。自从他们当年从凹村走出去,又从四面八方走回来,他们想自己总该有点变化。如果一点变化没有,他们怕别人说自己在外面白待了那么几年或十几年。如果没有一点变化,这些年走出去,就像荒废了自己一样。他们不喜欢这种荒废自己的感觉。 其实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哪怕他们在外面生活几年还是十几年,外面永远是外面,外面永远活不进他们的骨头里。他们在外面生活,过着外面人的日子,身体看似融进了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是否真的让他们融进,自己是否真的能融进外面的世界,只有他们在外面次次碰壁,一次次受到嘲笑,一次次在夜里唉声叹气的时候,他们才最清楚。 他们在外面生活,只是选择了一种背着凹村在活。这种背着,有种逃不脱的宿命感。他们在外面一心想回来,他们住不惯别人的城市。他们早就在外面为回来做打算,他们一天天计划回来的日子,一次次告诉外面认识的人说,自己要回来了。他们在说自己要回来时,说得趾高气扬的,说得洋洋得意的,好像外面的世界还没有自己的村子大,外面还没有自己的村子好。 但一旦定好了回来的日子,他们又开始担心。他们怕有人问自己为什么从外面回来了。他们不知道这个问的人,是从外面回来的还是一直没有离开过凹村。他们要提前想好,如果有人问他们这种话该怎么回答别人。他们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回来,也不能告诉别人自己融不进外面的世界才选择回来的,他们要脸面,都说人活着是为一张脸。 从外面回来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种办法,他们用外面的口音说话,说些四面八方的话,说些别人听不懂自己也听不懂的话给遇见的人听。他们在问话的人面前装。装久了,嘴巴就痒,嘴巴痒了也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痒,他们就偷偷在夜里说凹村的土话,凹村的土话能治愈他们嘴巴痒的毛病。一家人凑在一起说,一个人偷偷地说,对着一堵老墙说,面对一片暗说。 我的脚步声很轻,那些从外面回来的人耳朵里装着很多嘈杂的声音,即使他们把要讲的话停在那里,要笑的声音空在那里,他们也听不见我的脚步声。他们在好一会儿之后,又接着上半句说,接着上半声笑。停了好一会儿的话和笑重新接上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话和笑,要有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消失,会是真的消失吗?消失或许是另一种生长。 降泽从树洞里消失了,凹村人往土里挖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时在地底下消失了,一个刚出生的娃在阿妈的眼睛里白白消失了,一座从水上漂下来的村庄在满是星辰的夜色中消失了,一位骑着瘦马的男人从俄色花的花香中追着一群向北走的蚂蚁消失了,贡布像坠落在黄昏里的一只大鸟消失了…… 他站起身,不紧不慢地从怀中取出古铜色的驼铃,用额头虔诚地触碰手柄上的羊羔皮,接着举起驼铃,在风中有节奏地摇摆起来,哐当,哐当,哐当……他离我越来越远,远处的羊群看见他的离开,河流一样朝他涌去,那是一条可以流向任何地方的河流,那是一条柔软得如达乌里秦艽花瓣一样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