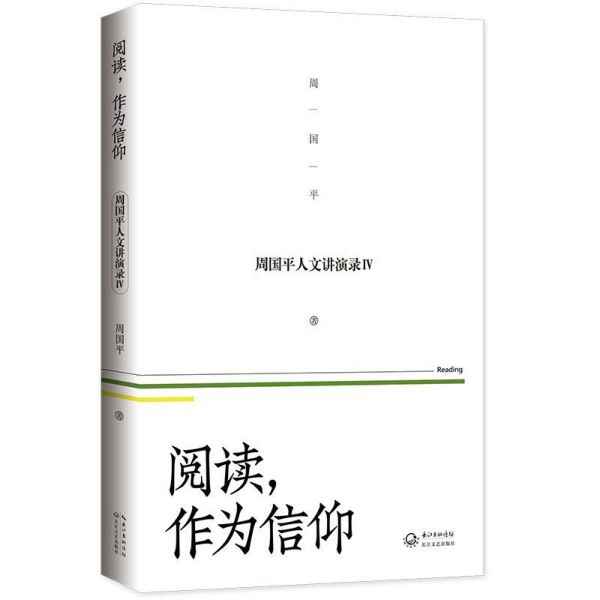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6.10
折扣购买: 阅读作为信仰/周国平人文讲演录
ISBN: 9787570212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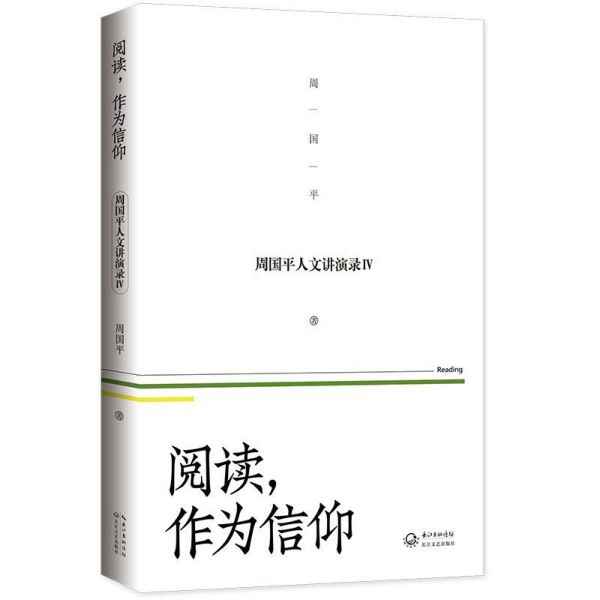
周国平,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生命的品质》;随笔:《人与永恒》《风中的纸屑》《内在的从容》《把心安顿好》;纪实文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学术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全新散文精选集《人生因孤独而丰盛》,等等。其作品以哲思和文采著称,寓哲理于常情中,深入浅出,平易之中多见理趣,多年来深受读者喜爱。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现场互动 问: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您对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者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因为有人说哲学是最高的科学,一些科学家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他们会成为一个宗教徒。您认为科学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宗教是否会消失? 答:问题非常好,每个问题都可以讲两小时。(笑声)你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哲学、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我非常欣赏罗素的说法。哲学和宗教,它们所追问的问题是相同的,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诸如世界的本质,灵魂的归宿,人生的意义。但是,哲学和宗教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哲学是通过理性,宗教是通过信仰,甚至是天启。宗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相反,哲学和科学所追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哲学思考的是超越经验的问题,科学讨论的是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然而,它们解决的方法却是一样的,都是要靠理性去解决。可以这样来打比方,从问的问题来说,哲学和宗教是一样的,都是灵魂在提问。从回答的方式来说,哲学和科学是一样的,都是头脑在回答。灵魂是一个疯子,尽问那些大问题,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头脑是一个呆子,按部就班,遵守逻辑。所以,哲学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疯子在那里问,呆子在那里回答。(掌声)至于科学发达了,宗教会不会消失?肯定不会,就因为它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宗教要解决的是终极问题,科学永远无法解决。所以,那些思考终极问题的大科学家往往有宗教情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问:我从您刚才的讲座里面感到,您所汲取的营养是西方哲学,您是否对中国哲学有一定的研究?您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样的呢? 答:我今天是没有谈中国哲学,我对中国哲学只能说略有涉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最主要的区别,我不认为在于中国哲学是综合的,西方哲学是分析的,中国哲学是混沌思维,西方哲学是逻辑思维。这些差别其实并不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会遮蔽主要问题。在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我更注意的是,我们是有古老的文明的,为什么发展到现在,在精神文明的程度上,我们不如西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哲学中有没有根源。我认为是有的,中国传统哲学缺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形而上学,就是对终极价值的关切,一个是个人主义,就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这正是我们应该向西方哲学学习的地方。 问:现在有些人文学者喜欢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成功。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认识和经历旁人是无法复制的,那您觉得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作为一个走在思考前沿的人,他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情怀,是应该好为人师,还是应该更多地为我们奉献发自灵魂的东西? 答:你好像在批评我。(笑声)的确,有些人文学者是好为人师的,觉得他们负有这样的使命,要启蒙人民,引领社会发展,我觉得这很可笑,我自己从来不觉得我有这样的使命。我只是碰巧做了人文这件事,成了一个作家,写了一些东西,这是碰巧的。首先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应该有一颗平常心。我写作时,我从来不认为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要去解决。我写得最好的东西都是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有一些困惑,我想开导自己,结果,我写出来以后,跟我有同样困惑的人与我发生了共鸣,这是我发生的所谓社会影响的原因所在,我自己很清楚。 问:您觉得中国文化中有没有尼采的酒神精神?中国是否需要这种精神? 答:得看你怎么理解酒神精神了,如果把尼采的酒神精神看成一种审美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说,庄子有一点像,但是他们的风格不一样,庄子偏于静,比较超脱,尼采偏于动,比较强势。 问:我读过的哲学书比较少,只看过一本《苏菲的世界》,请问这本算是哲学的经典吗? 答:肯定不是。 问:我记得您说过:“我将永远困惑,也将永远寻找。”现在距离您写的这一段话将近过去二十年的时间了,您现在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想问的是,在您现在这个人生阶段,您对人生价值有没有新的感悟?我们人类应该怎样为自身的存在寻找价值? 答:我实在没有什么可教给你的。你刚才提的那句话可能是二十年前写的:“我将永远困惑,也将永远寻找,困惑是我的真实,寻找是我的勇敢。”到现在为止,我的长进不大,在人生根本的问题上,彼岸的问题上,仍在困惑和寻找着。我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终极的信仰,但这不是想就能做到的事情。我这个人可能有内在的矛盾,喜欢思考,相信一个东西就必须有根据,这对宗教信仰是不利的。但是,终极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宗教,哲学永远是在解决的途中,永远是没有走到终点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比以前平和多了,大约是知道了终极问题不可解,就采取了一种和解的态度,也许和解就是一种解决吧,一种了犹未了的解决。 问:周老师,去年的时候,我也读过一本书,但是读过之后就忘了,我不知道我这种忘是永远忘记了还是吸收了?我想请问一下您的阅读方式,您是怎么读书的? 答:读书要是不忘的话,我觉得很可怕。(笑声)脑袋里堆满了东西,成了杂货铺。我觉得忘是正常的。我读书时,不在乎把书中的内容记住了多少,我是要把它转换为自己的东西。刚才我提出了读书的两条办法,第一是不求甚解,不要端着做学问的架子,正襟危坐,刻意求解,一个地方读不懂了就在那里死抠,那是学究们做的事,咱们别做。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你就是要不求甚解,因为读书是个熏陶的过程,也就是忘记的过程,这个东西你有了,但它是从哪里来的,你想不起来了。另外就是为我所用,你不要追究它的原意是什么,只要对你的精神生活有好处,变成你的营养,这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读书能够读到忘了,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祝贺你!(掌声) 问:看得出来,周老师您有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我想问一下,在生活中,您是如何保持平和的心态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周老师您在生活中是否也会发脾气? 答:其实我经常发脾气,而且都是为一些小事情,发完以后特别讨厌自己,人就容易在小事情上发脾气。后来我看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有一篇文章专门论愤怒,把愤怒分析得体无完肤,这是最渺小、最可笑的情绪。我读了以后深受触动,警觉了,一发脾气就觉得自己特可笑。总的来说,在生活中,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平和的。怎么做到平和呢?就是和生活拉开距离,你别太计较,你经常想一想,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当然你也别太悲观了。 问:我经常觉得做完业务的活之外,业务的活都是带着功利的心态的,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自己真正想读的书了,而我确实有很多书想读。我想问周老师,您是怎么样去协调功利的读书和精神生活的读书的。 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存在的,尽管我的专业决定了我能够把功利性阅读和精神性阅读较好地统一起来,但是,只要你看重利益,两者还是会发生冲突,你越看重,冲突就越大。我的办法是,自己选择研究的题目,基本不申请课题,我在哲学所这么多年,课题都不要。为什么呢?拿了那个钱,就会受到约束,可能必须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不主张你这样做,因为你需要生存,需要在专业领域内成功。我觉得你可以设法兼顾,把时间分配一下,比如说,白天用于功利性阅读,做你的课题,把晚上留给自己,用于享受性的、精神性的阅读。 问:我是一个中学生。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何时读的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从什么阶段开始读经典著作,是越早越好吗?第二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很多中学生包括我都比较忙,除了数理化之外,没有时间去读别的,怎么办? 答:当然是越早越好,有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经典著作,孩子可以读那些经典的童话作品呀。反正我觉得越早越好,越早就越能牢固地培养起好的阅读趣味。现在的教育真是没有办法,我都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了,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情况是最荒唐的。包括一些所谓的素质教育,修修补补的,弄一些课外阅读的范文、读物,其实也像课内一样地来进行,分析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一段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笑声)我的文章就常常被派这样的用场,有的孩子拿着这样的考卷来让我做,然后按照标准答案给我评分,勉强及格。(笑声)我自己都读不懂我的文章了,很可笑吧。这哪是培养阅读趣味的方法,哪是培养语文水平的方法!你真正要培养学生的阅读爱好,就应该给他们自由时间,可以推荐一些书目,让他们自己慢慢去品尝。 问:刚才您说到读童话,比如安徒生童话,我从小时候就开始读,现在有空偶尔也读一些英文的童话,但是好像没有以前读时的那种感觉了。我想知道读童话读出来的那个趣味到底在哪里? 答: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想,你在不同的年龄读同一篇作品,你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非常正常的。但你很难拿出一个标准来说,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的,真正有感受就都是对的。当然,无论读什么作品,你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是取决于你的整体水平的,不仅仅是文化程度的问题。 哲学家、青年人生导师周国平向万千男女讲述人生、婚姻、教育、幸福、阅读的秘诀。 全新修订,印制精美,值得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