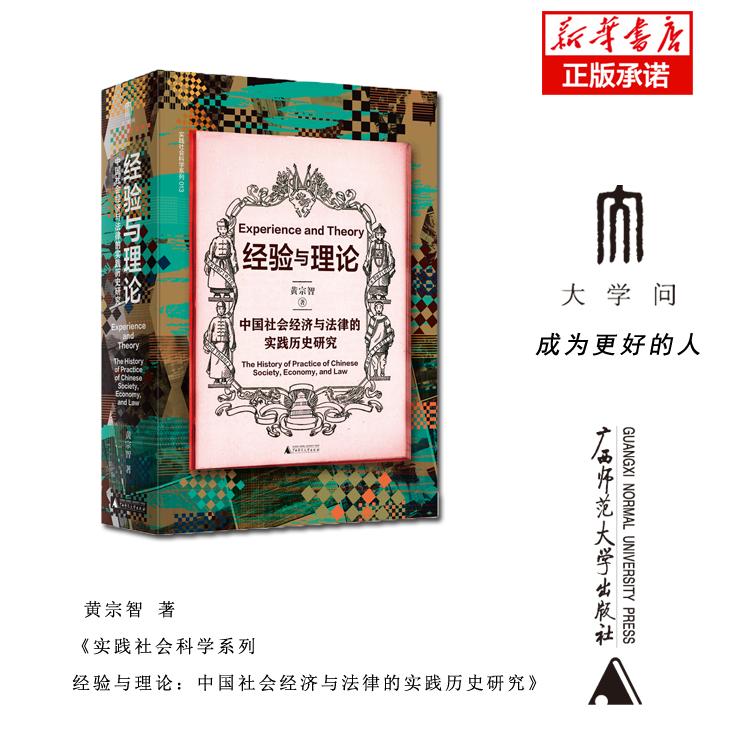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108.00
折扣价: 68.10
折扣购买: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 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ISBN: 9787559867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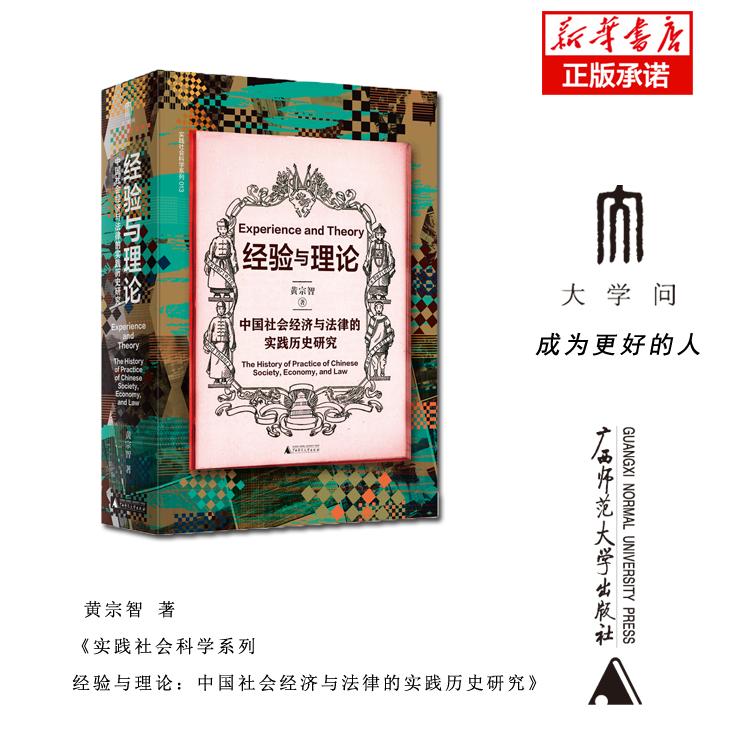
黄宗智,1940年生,曾任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代表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广西师大出版社)等。
连接经验与理论 ——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本章突出经验与理论联系问题,因为根据我自己四十多年学术生涯的经验,这是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共同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我近年来为国内研究生开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研修班便以此为主题。本章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国内的研究生,目的是把自己对这个问题多年来的一些想法为他们做一个简单的提要。另外,一些在美国的亲友们问我为什么巴巴地老远来为学生们开课,此文也许可以说同时是对他们的一个解释吧。 一 、只有特殊的学术模式,没有普适的理论 我在这里首先要突出的一点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结合当时的环境来理解。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研究的是有意志和感情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对没有意志和感情的物质世界的那种数学、物理似的科学方法的理解。即便是生物科学,也不可能具有今日许多经济学家自我宣称的那种类似于数学那样的科学性、精确性、绝对性。其实,物理学本身也早已超越了牛顿物理学那种绝对的时空观。 这里不妨用我自己的“内卷化”理论来说明“理论”的历史性。明清时期因为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核心地区人口已经基本饱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要么导致了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区的“内卷化”,即在按日报酬递减的情况下把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 这种内卷趋势在民国时期仍旧持续下去,在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其实应该说是帝国主义化)的趋势下,包括外来资本(尤其是日本在山东)所建立的纱、布工厂,棉花经济进一步扩充。花—纱—布的分离(手工种植棉花,工厂产纱,再由农村手工织布),大规模提高了农村的商品率,但内卷化逻辑基本一致。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随着现代科技因素(主要是机械化、化肥与科学选种)的投入,本来可以像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内卷化;但是,面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农业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复种指数大规模上升,结果是内卷化的持续。 进入80年代改革后的蓬勃农村工业化,在10年间吸收了1亿农村劳动力,尽管国家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农村工业的新就业也仅仅吸纳了其自然增长的劳动力,农业仍然内卷,农业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中。 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资本投入的推动下,1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连同乡村工业化,因此形成了历史性的2亿多农民的非农就业大趋势。进入新世纪,这个趋势正好与其他两大趋势交汇。一是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反映于新就业人数的下降。另外是伴随国民收入上升而来的食物消费转型,推动更高的劳动投入和成比例、超比例价值农产品的需求。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契机,可以走出长时期以来的农业内卷化困境,提高农村土地/劳力比例,提高务农人口收入,使农民逐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显然,我自己的“内卷”概念,自始便和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连。它是从历史实际提炼出来的分析概念,是一个与经验证据紧密结合的概念。从明清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是“内卷”的,但在近年“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下,未来的趋势很可能将是“去内卷化”。显然,我的“内卷化”理论自始并不具有超越特殊历史情况的普适野心,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它从来就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分析概念,不能超越时空。 二、历史学界的一个现象 目前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联合可以见于众多的学术领域,下面我们就以新近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重新阐释的学术为例来加以说明。这股潮流的出发点是从市场原教旨主义来重新认识清代前期:认为它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而根据市场主义理论,人们在那样的环境下的理性抉择必定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据此,得出的结论首先是,在人口史方面,中国的变迁并不是像过去的认识那样由死亡率(天灾人祸)推动,而是和西欧一样由人们的理性生育行为所主宰,人口压力程度其实不过与西方基本相似。同时,在市场机制和人们的理性抉择推动下,清代前期的经济实际上达到了与西欧同等的发展水平。 至于中国经济在其后19和20世纪的落后,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纯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认为帝国主义把西方文明带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落后国家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轨,便能得到西方似的经济发展;另一种观点同样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市场发展,但是承认帝国主义也许更多地为西方带来了发展,在落后国家则触发了20世纪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 上述这种论点同时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把坚持18世纪西、中基本相等表述为“去西方中心化”的论点,是否定西方现代主义目的先行的历史叙述的观点。不少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因此认同这种论点。在国内,不少学者这样理解:如果18世纪英国的发展程度只不过和中国基本相等,那么英国后来的发展只可能从外因,亦即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解释。显然,这样的理解在此论点上注入了民族感情内涵,但也完全忽略了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基本核心,无视它完全否定了中国自己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运动——起码从经济角度如此。 在经验证据层面上,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路也基本一致:认为任何史学论争最终取决于理论观点,经验证据并不重要。为此,我写于2002年的《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一文特别强调经验证据,总结了近二十多年西、中学术积累的翔实证据,说明像18世纪英国经历的五大社会经济“革命”那样程度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工场、消费、人口行为和城镇化革命)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其实一个都找不到。事实是,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不能仅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外因来理解,因为它确实具有一定的源自18世纪的内因,哪怕是偶然性的。18世纪英、中所面对的人口/资源压力十分不同,英国煤炭业的特早发展也和中国很不一样。我们需要的,不是中西哪一方更优越的感情性和意识形态性论争,因为那样只能再次陷入简单化的市场/革命、西方/中国的非此即彼选择。我们需要的,是基于中、西双方复杂历史实际的踏实研究和概念创新。 三、国内的学术环境 今天国内,也许部分出于过去革命传统造成的思维习惯,在处理思想和学术理论问题上,同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当然也与古代长期一贯具有正统地位的思想传统有关(虽然儒家的中庸精神自始便比较能够包容其他思想)。无论如何,年轻一代的研究生对待新接触到的理论,相当普遍地带有寻找绝对、普适真理的倾向。 法学和社会学也有类似的西化倾向。今日国内法学院所教所学多以西方形式主义传统法学、理论和法典为主。至于中国自身的法学传统则只有少数教员研究,不大吃香。虽然,法学院师生群体中,也有强烈的“本土资源”呼声和意识,但是真正系统地在中国自己的法律、法学历史中挖掘现代化资源的学术还比较少见。 至于今天的社会学院系,也基本都以西方文献为主。譬如,对研究生们“开题报告”的“文献”讨论部分的要求,主要是与当前西方学术研究“接轨”,而与之接轨的常常限于二、三流的复杂繁琐的当前学术著作,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基础性的经典源流。这样,学生们的视野难免陷于庸俗,提出的问题多是次级的问题,不能深入到根本性的层面。当然,也有“本土化”的呼声,这是可用的资源,并且可以走向费孝通先生那种创建新鲜概念于踏实的经验研究,并付之于实践检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方面的文献尚嫌单薄。 史学则多偏向纯经验研究。与日益理论化(要么是新古典经济学类的理论,要么是与其相反的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西方史学相比,今天的中国史学则更多地倾向于简单的经验主义。如果说西方史学越来越倾向于单一左手的使用,中国今天的史学则倾向于相反的单一右手的使用。在这样的偏向下,研究生们所得到的培训缺乏概念锻炼,结果等于使他们脑袋里的那块“肌肉”萎缩、退化,即使试图使用理论时,也多显得力不从心,不能精确有力地掌握、连接概念。客观地说,考证史学缺乏经验主义中用归纳方法的概念提升,更没有与演绎逻辑对话的概念创新,实质上等于是全盘拒绝现代科学的闭关自守。 考证史学的反面则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过去是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宰的史学,今天则是由其反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宰的史学。但我们需要的既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也不是简单的经验积累,而是经验与理论的双手并用,是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从新鲜的经验证据提升新鲜理论概念的历史学。 在今天的转型期间无所不在的浮躁之风下,真正心向学术的青年学生当然会感到十分困惑。什么是真的学问?怎样去做?什么是正确的理论?怎样使用?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面对社会的众多诱惑与压力,有的年轻人难免追求速成,不能安心去做踏实严谨的学术研究。不少最聪明的学生选择轻浮炒卖时髦理论的“捷径”,要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真理”(多见于经济系,也可见于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要么是后现代主义的自觉“反思”与“去西方中心化”(尤其多见于中文系,也可见于有的历史系)。另一种学生则完全依赖经验堆积,甚或自己的感性认识,自以为是,轻视任何外国的著作,对本国的研究又缺乏真正的好奇和独立思考。这样,西化与本土化两大倾向同样陷于轻浮。难见到的是结合理论与经验的严谨研究以及有分量的学术交流。在近年学术制度官僚化、形式化的大潮流下,只可能更加如此。 但是,我这里要指出,今天中国的青年研究生们同时具有很多优点,这也是我自己愿意大老远来为他们开课的原因。首先,优秀的学生之中,不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社会、文化责任感,其中包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救国救民于苦难的精神。这种意识在美国学生中是看不到的。伴随这种意识的是某种“本土化”的学术倾向,虽然今日这种倾向多出于感情用事,但它不失为一个可以用来纠正全盘西化趋势、建立独立自主学术的资源。再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感,哪怕是在西化的大潮流之下,许多研究生还是常常具有一种几乎是下意识的历史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就连偏重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生也是如此。这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生中也比较少见。另外,研究生们对本国的社会现实一般都 细读这本书,我不得不感动和佩服于黄教授的良苦用心——因为它确实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编排过的,有清晰完整的脉络,有扎扎实实的干货,更有助力青年学者的强烈关怀。通俗地讲,它就是黄教授的“经验之谈”;但从专业角度来说,它又不失为一本实用的学术研究指南。在我看来,整本书的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作者在业界已有相当影响力的几本学术著作开始谈起,先是经济史著作《华北》《长江》以及之后的进一步思考之作《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然后是法律史著作《表达与实践》。作者或摘取导论,或提出问题,旨在总结自己这25年的学术生涯以及集中探讨的学术问题。介绍经验。 第二部分则从社会、经济、法律三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历史现实与西方移植理论,甚至中国本土理论之间的背离之处,指出面对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简单在西方或中国两种表达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不合适的,它要求我们尽可能从实际的认识出发,创建新的概念,开拓新的研究路径。提出问题。 第三部分则通过一组文章,从自己遇到的学术陷阱以及如何突破,简单地说明自己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同时进一步澄清自己对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并基于前些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修班课程,讨论了今天影响最大的一些理论流派的局限,提出“连接经验与理论”的学术研究方法。解决问题。 当然,这三个部分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在书中甚至是穿插编排的,就跟上课一样,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跟我一样,从中提炼出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如此,黄教授的用心也算没有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