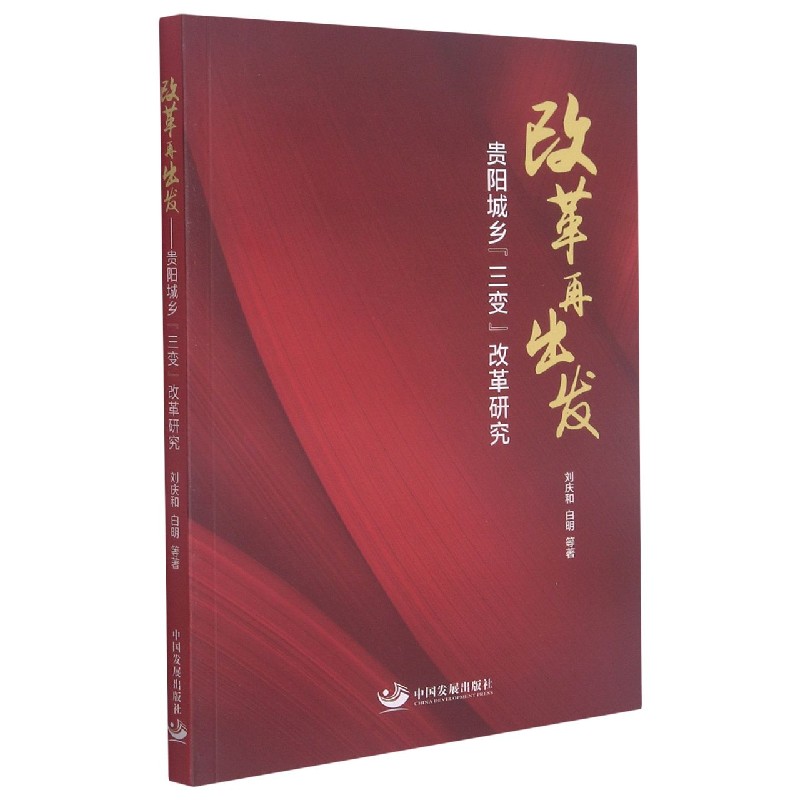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发展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29.40
折扣购买: 改革再出发——贵阳城乡“三变”改革研究
ISBN: 9787517711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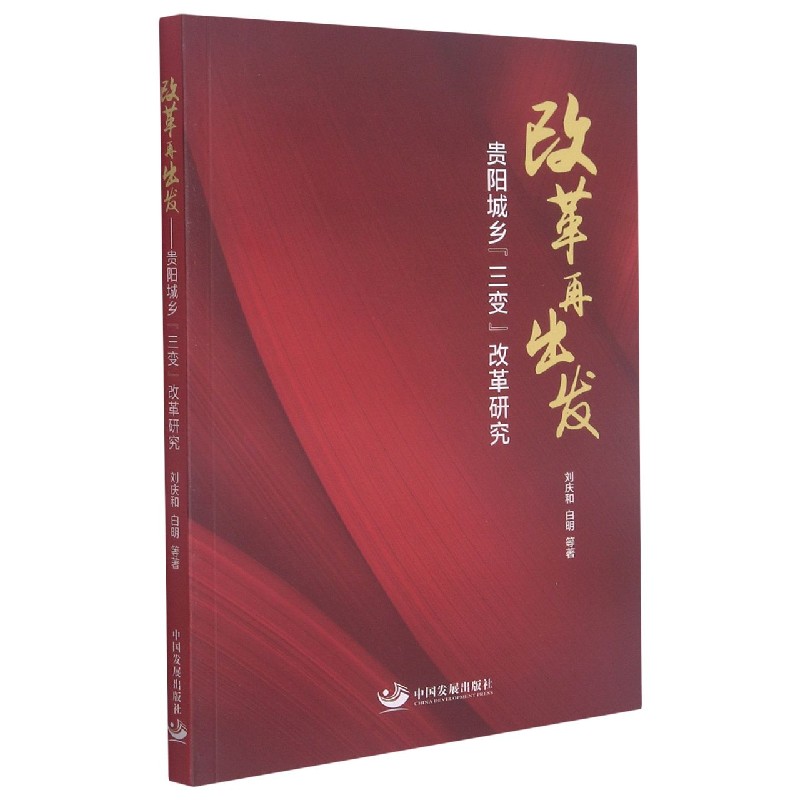
刘庆和,经济学博士,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委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国民经济、产业经济、经济增长与发展。著有《中国农业-宏观经济联系研究》《贵州经济年度模型与若干政策分析》等。 白明,经济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中国软科学》等刊物已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持各类课题20余项。
第一章?“顶云经验”:“阳关道”和“独木桥” 之争 贵州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民生活也很贫困。 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力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但部分地区仍然仅仅填饱肚子而已,一遇到灾年荒年,连吃饭都成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群众,自发地悄悄搞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际上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与小岗村的改革一样,顶云公社的改革是中国改革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实践。顶云的改革并非凭空出现,其产生和发展既有历史机遇,也有历史主体的主动选择。实际上,它根源于广大群众为了吃饱饭的基本需求和一场思想解放大潮的同频共振。在人心思变的大趋势下,许许多多干部群众敢于突破制度桎梏,在变革中求得命运的改变,实现了人民选择和政治承认的契合,体现了中国改革的大逻辑。 第一节?改革前夜的贵州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一、改革前夜的贵州 贵州地处祖国的大西南,资源丰富,其中许多资源储量排在全国前列;民族众多,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发展前景广阔。 1949年前,贵州长期处于交通闭塞、封闭落后的状态,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194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只有11.25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a。这是一个曾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省。 1949年后,贵州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中央对贵州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从1958年到1978年的21年间,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经过“三线”建设,贵州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为贵州打下了一定的技术物质基础。但总的来说,发展水平在全国还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1978年前的几年里,由于全省上下对省情认识不足,缺乏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的精神,照搬照套全国的一些口号和指标,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上,要求过急,超过了地方财力、物力的负担,使本来就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严重妨碍了投资效益的提高,致使贵州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建设、流通领域中效益差的状况十分严重,人民生活、城市公共事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农村贫困面继续扩大。在生产组织层面,“一大二公”的体制使得生产者缺乏必要的正向激励,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效率低下,并形成恶性循环。再加上各方面问题的长期积累,使社会生产力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压得贵州喘不过气来。 “穷则思变”。贵州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作出改变。于是,一场发端于农村的改革悄然提上了日程。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其中思想解放在改革发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76年,全国范围内人心思变,百业待举,社会各个领域都孕育着重新焕发生机的萌芽。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实际上,拨乱反正也面临着“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阻碍。这种持续状况越来越遭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反对,社会孕育着冲决罗网的爆发力。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 这个时候,党内外有了拨乱反正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1978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阐述,真理检验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没有实践检验,理论不能进行自证和自洽。经过国内重要媒体的转载,这篇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大多认可文章所提观点,但是也有一些人对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并进行了指责。 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顶云公社的改革就已经在当年的3月“悄悄地”展开了。1978年9—10月,中共贵州省委正在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为了参加中央会议,事先到黔西南等地农村进行了调研,希望掌握相关情况,通过调研把农村的问题向中央汇报。回贵阳途中,他在关岭县听取了县委汇报。县委试探性地汇报了该县顶云公社实行定产到组效果很好的情况,引起了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的关注。在关岭进行了初步调查了解后,他表示可以试验,并要求县委赶快整理材料送省委办公厅,作为参加中央会议的参考。他回贵阳后就召开了两天省委常委会,向常委会汇报了顶云公社情况。11月11日,《贵州日报》就对顶云公社的做法做了报道。这一报道在贵州历史上开启了顶云改革的大幕。但省委高层的某些领导同志,却不能理解这个改革的意义。其时,省委常委会也并未形成一个统一意见。据《贵州日报》的老编辑回忆,实际上,这篇报道未经请示省委就编发了。但是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会议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顶云搞“包干制”的做法,无疑给意见不一的各级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 很显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贵州各级干部带来的震动是非常巨大的。时任省委书记回忆道:“那个时候思想比较活跃,群众敢搞,我们也敢思考。这还是要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也就没有思想活跃,我们也不敢去调查研究包干到户。”a正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各级干部松了绑,解放了思想,才有后来省委对群众自发的“包干到户”给予承认,这再一次说明了我们改革的一个基本逻辑,即地方改革的经验化和改革经验的地方化。 第二节?顶云的改革探索 “顶云经验”虽然诞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实际上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紧密关联。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那么在全会之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是改革开放的序曲,“顶云经验”正是这场讨论在贵州唱响的最精彩的乐章。“顶云经验”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拨乱反正”和进行的重大转折是顺应民心、符合历史潮流的,反过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顶云经验”最有力的支持,使其最终得到承认和认可。 一、关岭等地的贫困 在1958年至1978年漫长的20年中,由于大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平均收入年增长只有1块钱!贵州低于全国水平,关岭更为滞后,1976年顶云公社农民人均收入、人均粮食配给分别只有56元、316斤a。顶云与全国各地一样,全乡28个生产队以“生产队大集体”的方式经营管理土地,生产落后,群众吃粮难的问题较为严重。 1978年前,“顶云经验”的发源地关岭县农村贫困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时任关岭县委书记李清泉对顶云改革前经济发展状况有一个总的认识。2008年12月,在顶云改革经验30年座谈会上,李清泉回忆道:“1978年,我在关岭担任县委书记,对关岭农村工作的现状是比较了解的。当时关岭全县有4个区、31个公社、2个街道办事处。顶云公社是全县最小的一个公社,只有2个大队28个生产队,859户4574人。有稻田3508亩,旱地1671亩。 距县城6公里,320国道贯穿全公社,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是全县自然条件较好的公社之一。粮食产量最高为1967年,总产270万斤,以后多年一直在250万斤左右徘徊。顶云公社尽管自然条件比较好,但由于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干和不干一个样,大家同吃大锅饭,因而顶云公社农民与全县大多数农民一样,解决不了自身的温饱问题。” 农民白天干、晚上干,但还是吃不饱饭。这种现象并非顶云公社独有。 由于体制机制的问题,特别是内部激励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吃不饱饭的情况比比皆是。据“富饶的贫困”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王小强的采访日志所描述,关岭等地的贫困现象在今天看起来,简直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 在关岭县考察了柏油路边安隆乡所在地——团园河村的胡家凹,群众的贫困程度令人震惊。该地距县城20公里,海拔1400米。当时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笔者身着毛衣毛裤加羽绒衣,尚感寒气袭人,而当地居民几乎全是两件单衣。十四五岁的姑娘有的连裤子都没有,赤裸裸的两腿冻得通红。走访的6户人家,家家都是透风漏雨的泥坯草房,人畜同居一室。锅里蒸的是玉米糊和白菜,粮食只够吃到来年三四月。孩子们瑟瑟发抖地缩在火堆旁。 杨开明一家9口,两床破被。杨和一个孩子躺在漆黑一团的床上,上吐下泻两天多了,没钱去看病。王德虎的爱人携大女儿三年前外出卖药,一去不返,杳无音信。家里没有床、没有被子,女儿睡在“阁楼”的草堆里,他身着一件三年前国家救济的烂棉袄,睡在距牛两米多远的草堆里。a 紫云县宗地公社中洞生产队15户63口人,祖祖辈辈住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山洞里,不洗澡,不洗衣服,吃洞里的水。亩产242斤,猪养得长毛细腿,疾驰如飞,最重不过90斤。民委知道后,拿出三万元盖房子,让他们搬出来住;并用大轿车把能动的人拉到贵阳去参观,使其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结果,居民们据此推断自己洞里肯定有宝,所以国家才费这么大劲动员他们搬家。于是,不搬了。b 二、顶云的改革历程 顶云公社是关岭县贫困程度较深的一个公社。早在1976年,为了解决吃饱饭的问题,秧井、八角岩、陶家寨等16个生产队就开始了土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在这些生产队当中,陶家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并带动着周边生产队的活动。 1976年,陶家寨有32户183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6元,人均粮食212斤。据回忆,一些家庭每年都有一半蔬菜一半粮的经历,甚至有的家庭在春节过后就断粮了,吃野菜加糠是常态,生活处于困难境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时任生产队队长的陈高忠等村干部一直在想办法。经过再三试验和讨论,陶家寨确定了下一步工作打算:一是定组和各组组长;二是定土地产量;三是定人口、劳动力;四是定耕牛和分农具;五是定副业人员;六是定各组送粮人员。与许多普通群众发起的改革一样,这时候的改革也确实有“坐班房”的危险。村委会对全寨定了几条规矩:一是全寨所有人,不论什么时候,对外(包括外寨亲戚、朋友)都不能说本寨“包产到组”的事;二是婚丧嫁娶不能大办酒席;三是不能把粮食借出去;四是不能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五是不管谁问,都只能说粮食不够吃。最后又定了规定:谁走漏风声,天打雷劈,大家撵他搬出陶家寨。 就这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偏远山区的贵州关岭拉开了序幕。许多年后,陈高忠等人或许没有想到,这场似乎要“坐班房”的冒险,却是中国改革史册的一记浓墨重彩。他们的做法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 秋天之后,这场改革的效应显现了。陶家寨的粮食产量横向比增加了200%以上。通过这场改革,人均粮食配给从212斤增加到504斤,从以往没有收入或收入比较少,增加到了200多元。这场改革说明:包产到组确实可增加粮食产量,让生产队的群众吃上饱饭。陶家寨的大胆尝试,让人信服。村委会认为,包产到组以后,社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还是不够高,能不能再彻底一点,直接把土地分到户,到了年终再算账,这样可能会把粮食产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想法又朝“资本主义道路”上迈了一步,风险更大,必然要求更加周密的安排和策划。 村委会带领大家召开了院坝会议。每家每户都选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推举陈高忠带领大家走“包产到户”的路子。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建立了风险共担机制,所有参加的家庭都必须签字画押:为了让陶家寨老幼能吃饱饭,经大家共同商量,将全生产队田地分到各家各户,若有哪个因此事被打板子坐牢,这家人的生产、生活由大家共同负担。这份合约也被称为“灯盏窝”合约。 “灯盏窝”合约签订后,陶家寨生产队的“包产到户”悄然进行。为了打一场静悄悄的战役,不让外人知晓,他们在田地两边埋下石头桩子当地界,用绳子拉好直线划分庄稼,并在口袋上作记号,等粮食收进仓之后,再趁晚上分别送回各自家里。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 顶云人冲破各种阻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精神被称之为“顶云经验”。 1978年4月10日至13日,顶云公社集中全社28个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及每队选派的贫下中农代表64人,参加农村经济政策骨干学习班。时任县委书记李清泉在学习班上,同意“包产到组”试搞一年,并改名为“定产到组”。到了秋收季节,“定产到组”的16个生产队全部实现增产。 1978年秋,中共贵州省委正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关岭县委向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汇报了顶云公社“定产到组”的情况,省委第一书记表示:可以试验,并要求县委赶快整理材料送交省委办公厅,作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参考。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的形式,旗帜鲜明地宣传顶云公社“定产到组”行之有效,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定产到组”的社会主义性质。1979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关岭全县范围内推广“顶云经验”,1000多个生产队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尽管如此,省委仍有人提出“三个不许”b,直到1980年6月,《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下发,才标志着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合法化。当时,除贵州省外,全国还没有一个省份,以省委文件的形式,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三、“阳关道”与“独木桥” 顶云改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在经过《贵州日报》1979年11月11日的报道后,经过短暂争论,贵州省委也认可了这一改革,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若干问题的讨论提纲》。实际上,省委组织的为期9天半的讨论,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a当时的贵州省省长回忆道:“由于这个提纲提出的政策与措施在一些方面比过去有较大的改进,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农村干部的拥护。”b相较全国其他地方,顶云改革得到了贵州省委的肯定,相关媒体也对此做了报道。但是贵州省委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一些保守省份的质疑。 1980年3月,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在国家农委召开。此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会议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反而争议很大,充满火药味。有些人在会上直接就提出:阶级斗争还搞不搞?学大寨还搞不搞?从争论的情况来看,其实质是指向路线问题。而1979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公开宣传的“顶云经验”在会上受到直接批判。作为农业发达地区的安徽认为,责任制能不能搞需要群众决定、选择。群众都说组不如户,可见包产到户实际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安徽的意见在会议上打开了问题的盖子,与会人员对责任制展开了深入探讨。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决定:应该把包产到户的口子再开大一点。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a 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同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展开了一场生动的辩论。前者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后者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会后,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阳关道与独木桥》b。文章以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重点阐述“包产到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全文。这篇文章引起极大轰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包产到户”的理论讨论。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仍然不少。 1980年12月底,中共贵州省委在写给中央《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报告了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的情况,并将包干到户定性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在报告上批示: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c这一表态对坚定贵州走包产到户之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贵州省委根据指示,大胆地在贵州进行探索。这是偏远地区为了实现吃饱饭的目标而进行的大胆探索。这反映了贵州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逻辑,部分折射了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本路线。 事实上,“包干到户”在贵州也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各方面围绕其合法性展开了诸多讨论。1982年春,新华社记者与《人民日报》记者在贵州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报道提出“包干到户”也不是什么“独木桥”,而是花了很大代价,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的“阳关道”,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究竟要走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还是应该根据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自己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显然在贵州,通过实践给出了答案和证明。它是贵州人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探索的结果。这个结论,是党与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创造,而不是哪一个人编出来的。 四、重要启示:在突破路径依赖中寻找制度创新空间 顶云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青史留名。顶云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个基层单位的改革,如果没有省、县各级党委政府敢于打破现行政策的条条框框,没有中央的最终“授权”,仅靠顶云不可能突破所谓的“路径依赖”。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解释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诺斯指出,由于在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个人在社会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信息时均存在着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而“人的这种心智能力与辨识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旨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则通过结构性(structuring)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a。诺斯解释,路径依赖一方面通过对经验和实践的总结和学习,形成了制度,为人们迅速认识客观事物、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一种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同时,它又固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路径依赖,使过去的选择决定未来的选择。为此,“理解制度以及制度变迁之困境(dilemma)的关键在于人们认识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些构成行事准则和规则的东西是在长时期中逐渐演化而成的……规则的变化要求规范、惯例和非正式准则的演进”b。用这一理论可以更为明确地认识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逻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经济长期以来遵循“一大二公”的原则和思路。一方面,这使得我国农村经历长期凋敝后,很快走向繁荣。但时间较长以后,形成了制度依赖,反映在政策界就是以生产资料的更高比例公有(“一大二公”)来解决农村生产力问题,结果却导致了农村生产力长期盘桓 不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后来才有了“顶云改革”“顶云经验”。今天,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时点上,我们应当思考:“顶云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第一,制度变革必须以实践为唯一的检验标准。一种生产关系是不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样要由实践来检验。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一重大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阶段,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正确的,符合我国国情,是必守的政策“底线”,不可以随便动摇。“顶云经验”的基本做法是包产到户,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宣传中回避了“包”和“户”两个字,可以说是贵州那个时代坚持实事求是的范例。省委领导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研,认定“顶云经验”是符合贵州实际的,并直接推向了全国,所以才有“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句名言。 第二,改革就是要通过政策的调整,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历史唯物主义不止一次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农民是一个充满着巨大创造力并且应该关注的群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乡镇企业是农民的创造,农民的一系列创造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就是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民意是改革的基础、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目的。以人为本是改革的出发点,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如果没有民意这个基础,无论什么样的改革,其结果都不可能成功! 第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要服从制度变革的逻辑。现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均”字。农村广大地区在改革初期基本上是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这种人人平分、户户承包的“均包制”,初期时对于解决温饱问题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这种土地制度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其历史局限性不断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土地平均承包的方式产生了土地规模过小、地块零碎等问题,并存在着继续被分割的可能,影响了农田基础设施和共同性农艺措施效益的发挥,不利于新技术的采用。经营规模细化和承包零散的问题比较突出。由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资源,且实施“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因此不少农户在家庭人口增加或者分家后重新在家庭内部分土地。这样就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本来细化的土地再次细碎化的倾向,而在细化过程中又造成土地浪费。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村的人财物不能自由流动,必然制约生产力发展。 总的来说,顶云改革给贵州农村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真正改变东西部的差距,对农村面貌的改变也非常有限。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场“发轫于贫困地区,滥觞于崩溃边缘的‘要素组合新规则’,在全国推广之后,运动出了新的更加剧烈的不平衡”。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对东西部带来的红利效应使两者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拉大。1978年贵州省国民生产总值为87.95亿元,同期江苏省为521.15亿元,两者相差480亿元;到1987年,贵州省国民生产总值为165.5亿元,江苏省为885.62亿元。b东西部省份之间呈现出一种“马太效应”。实际上,这种不平衡直接导致了东西部关于“梯度转移”的争论。这说明单纯的制度变更、要素组合并没有真正改变西部地区的面貌。 当沿海各省区市由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外部压力迫使内部产生的制度化变迁,带来生产力巨大变化的时候,对依然徘徊在温饱线上的贵州来说,改革能否再次让它登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呢?农村改革的彻底改变绝非仅靠一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能够达到。那么制度变革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改革一旦启动,便具有了自身的惯性。然而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在历史面前不能没有反思和能动性,改革必将沿着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回归生活常识的方向深化下去。 1.本书全面生动记述了贵阳城乡三变改革的始末,讲述了由包产到户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持续成长空间的城乡“三变”,理顺了改革与制度变迁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从城乡联动的视角做了初步探讨。2.城乡三变改革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系统性改革,其结果不仅可能撬动贵阳市的全面改革发展产生历史性“裂变”,还可为全国探路子并提供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