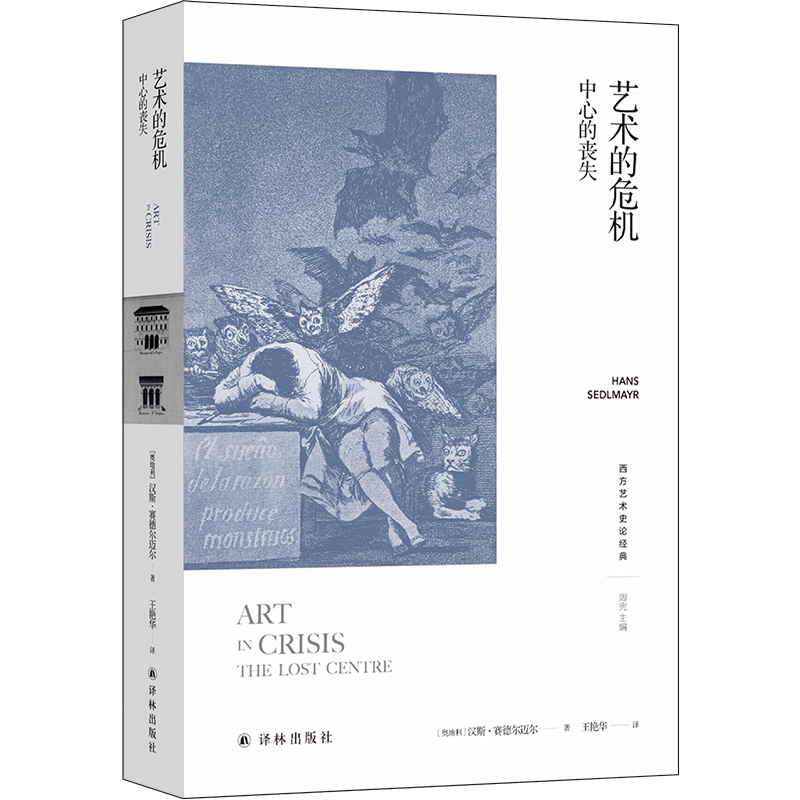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3.50
折扣购买: 艺术的危机:中心的丧失
ISBN: 9787544782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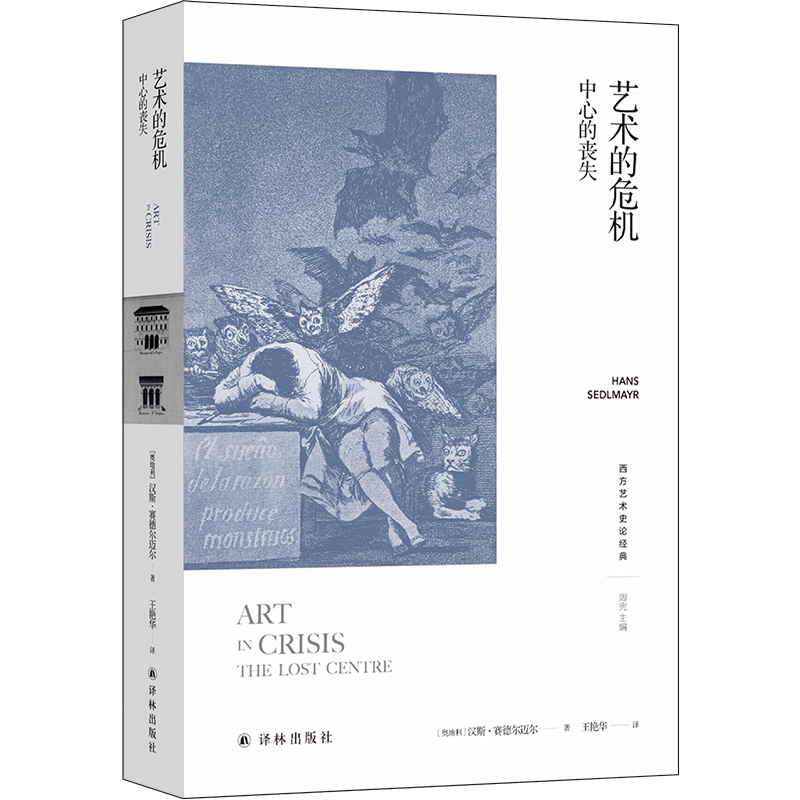
汉斯?赛德尔迈尔(1896—1984) 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新维也纳学派艺术史学创始人,曾执教于维也纳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加入纳粹党,不久退党,却因此被维也纳大学辞退,此后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并以“汉斯?施瓦茨”的笔名发表文章。1951年重返讲台,先后于慕尼黑大学和萨尔茨堡大学教授艺术史。主要著作有《艺术与真理》、《黄金时代》等,《艺术的危机》是其代表作。
第一章 新的主要形式问题 我们当前的任务一点不少于生活本身,因为一切都围绕着让具体的形式开口表达。 ——H.施拉德 自十八世纪末以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开始涵盖了一些全新的内容。它们可能是一些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或者,它们可能出现过却一直处于不重要的附属地位。 过去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教堂和宫殿,但是,现今这些事物被搁置一侧,一系列新的亟待解决的形式问题接踵而来,开始取代教堂和宫殿的地位。自1760年至今,我们能清楚地辨别出六七种不同的主要形式问题,每一个问题在它的时代都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大声疾呼,渴望得到解决方案。在此,我们所指的是风景花园、建筑纪念碑、博物馆、剧院、展览(馆)以及工厂。这些形式问题中没有哪一个能够在一代或至多两代人中占据主要地位。然而,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时代征兆,我们能够根据它们彼此交替的序列去认识某种特殊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这些新的主要形式呈现了一条艺术发展主线,这比其他任何艺术发展脉络都更加典型、更加清晰。不过,当受到一些外来的或者跨学科的流行风尚或潮流影响时,这条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会变得模糊而令人捉摸不定,然而究其根本,它们彼此在内在本质上是毫不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新的主要形式入手去理解艺术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会获得最好、最实用的导览线索,去破解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艺术谜径。 接下来,在入文前还有一点说明。虽然刚才我们一直提到某些主要的形式问题,但是,在此我们真正重点关注的是一些关键性的建筑形式。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对建筑形式的探讨才能将这些问题揭示出来。所以,只有建筑师以及伟大的园林设计师的思想,才与我们的研究密切相关—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必须得首先澄明: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只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绘画领域的不朽杰作,尽管伟大的画作在自己的领域里独领风骚,创造出非凡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与我的论题不十分相关。绘画领域自身地位十分独特,它与这些主要的形式问题所生成的土壤有一定距离,甚至相距较远。事实上,我所提到的这些形式问题,不是图画问题。绘画实践是自由的艺术形式创造,任何形式的“终结”对它都无甚影响,它不是那种服从于某种明确界定的、展现于公众视野的艺术实践。 然而,根据这种关联性我们可以肯定,新的主要形式问题与综合艺术作品(比如宫殿或教堂)是不直接相关的,后者为造型艺术提供了独特的创作场域和创作题材;新的主要形式或者与纯建筑形式相关,比如建筑纪念碑,或者与那种仅仅以建筑结构作为基础的建筑物相关,比如房屋或者博物馆等,在这些建筑形式之中,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趣味要求选择构建不同的自由艺术形式。只有在十九世纪中期所幸出现了剧院这一形式之时,才兴起了综合艺术作品的复兴,这时(唯有在这段历史时期),在处理与以上所提及的所有新的建筑形式相关的创作任务时,非凡的画家与雕刻家才在严格设定的创作原则和规定之下去完成他们的使命。 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来讨论这些主要的形式问题呢?在多样性的研究对象之中,我们选取了如上一些主要形式,这并非是武断、任意的,因为它们已经开始引起极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们的注意。而且,除了此处所遴选的这些形式问题之外,证券交易所也正在被建造,以及国会大厦、大学、酒店、医院、火车站等,也陆续出现。 所以,首先,我们是根据如下理由来确定“主要的形式问题”这一术语与具体作品的联系的: 1. 因为这些作品都具有一个共性,即能够激发创造性想象力; 2. 因为当考察这些形式问题时,我们可以运用一套共同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些问题可以遵循统一原则进行类型的划分; 3. 因为即使程度不一甚至在极小的程度上,在风格总体发展方面,这些主要的形式问题都能够施以创造性贡献,所以,它们可以为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参照的范本或可资借鉴的案例; 4. 因为不管是出自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目的,这些主要的形式问题都可以取代古代神圣、庄严的建筑形式。 此外,对于许多可以用“主要的形式问题”这一术语来表述的作品而言,它们对艺术的公共性价值和影响力的表征,它们所体现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所特有的、不可估量的个体主义倾向,将可能丧失。因为,尽管它们不具备伟大的、过去时代的综合艺术作品的影响力,它们实际上确实是那些综合艺术作品的合法继承者。 对于欧洲文明的早期阶段而言,主要形式问题是教堂建筑。那时综合艺术作品是最为杰出的艺术形式,它们凝聚并表征了所有艺术创作的上乘手法。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可以与之匹敌,综合艺术作品地位首屈一指,所有其他的艺术形式都要在风格和母题方面以之为借鉴。 自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开始,新的主要形式问题开始出现。出现在偏远或封闭、孤立地区的一些新的形式问题,比如市政厅等,它们在短期内取得了与教堂建筑地位平等的卓越成就,此后便接着开始推进自己独特的、新的图像世界的发展。它们在后来发展为两种不同的形式问题,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对同一形式的两种发展,是对同一问题作出的两种不同表达,这两种形式问题是城堡和宫殿。这些新的形式在十四世纪被创造出来,待及发展到十五世纪,它们已经获得与教堂建筑同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有时它们的影响力更大更为广泛。它们也成为神圣、庄严的建筑形式,成为偶像崇拜的核心表征性建筑,而且,它们还推进了自己的图像世界的发展,即它们自己的图像志。这时,与以教堂为代表的综合艺术形式相比照而言,在世俗的图像领域出现了与其比肩的建筑形式,而这两种新形式似乎更能表征伟大的文明地位和自我肯定。 古代综合艺术的没落 在十九世纪的发展中,古老的主要形式问题开始逐渐丧失它们的主导性。不仅城堡修建得越来越少,宫殿和教堂也逐渐无人问津。虽然许多古老建筑仍然矗立在各地,可是它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古老的文化自信和自我肯定已然褪色,可是,新的建筑体系还缺少独创性精神,新的独创性形式尚寥寥无几。 在新的教堂结构中,轮廓分明的建筑将难再出现了。人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空壳架构形式,然而举棋不定,因为传统的教堂结构仍然试图去全权掌控这种新形式,可是这只能是一种徒劳;新的教堂形式开始探索早期基督教建筑、拜占庭建筑、罗马式建筑、哥特式建筑以及文艺复兴建筑。有时,它甚至委身于希腊神庙的外观形式之上去寻求庇护和存在感。然而,这种形式体系整体上来讲是多么地流于肤浅和表面化,申克尔所设计的韦尔德大教堂地处柏林,它就是典型一例,它不遗余力地、清晰地呈现了这一特征。作为地基的立方体结构仍然保持原状没有改变,然而它也被乔装改造了一番,它戴上了面具以迎合新的、改变了的观者的奇想需求,有时它披覆上罗马式建筑的外衣,有时它隐藏在哥特式风格的表象之下,有时又伪装成为古风形式的象征之物。这种不甚高明的基底与附属部分之间的分离,以及将后者简单看作装饰部分的做法,昭示了欧洲艺术整体的未来命运,然而,作为教会建筑的特点再也无法辨别出来—当然这其中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事实上,整个关于教堂建筑的观念成为关于厚重的团块和赤裸的无装饰之物的总的观念,这不仅发生在新教国家,这种转变自身就说明了其中的原因。宗教元素不再显得神圣而神秘,它是诗意的,却不再是有机的整体而是成为一种外衣,一块意识形态帷帐,从过去和历史借鉴而来。只有在1760年至今的整个发展阶段,教会建筑形式才仿佛再一次迎来了复兴,成为时代的主要形式问题。那开始于神圣同盟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申克尔决定以哥特式风格来为德国设计一座国立教堂。1815年,一部篇幅较小的著作《新教堂》面世了,此后不久人们就开始构建科隆大教堂,并在同一时期竣工。在这一教堂的建设中,人们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可是,同样的,这一构建方案及其思想再一次披露了一种空洞性,甚至在那个纪元的后半期,当新兴的“新哥特式”教堂开始更加忠实并强调它们的历史传统范本时,新的教堂建筑的许多细部也同样反映了来自另一世界的、无实体的某些幽灵的征兆和特质。所以,“新哥特式”建筑只是教会建筑形式维系自身存在一致性、追求最长久持续生命力的一种表征,然而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它自身却转向崇尚另外一种更为广泛、多样的精神态度。直到我们当今的时代,教堂仍然继续依据“新哥特式”风格在陆续地被建造。 然而,与学院派哲学的复苏不同,哥特式教堂的复兴并未取得成功,因为它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内涵。事实是,在当时的文化语境看来,在复兴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的同时,绘画领域中并未发展出对应的形式,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一建筑形式在当时尚未取得成功。这时,建筑成就不再与当时的宗教艺术领域中所开展的呕心沥血的刻苦创作发生联系。十九世纪的教堂就其作为“图像志”的本质而言,已经走上了末路。当时的绘画领域大量产出神学题材的作品,却完全丧失了人类的想象力,它们的题材变得主观化,失去了真正清晰的思想表达。基督图像志创作方面的衰落与古代神话学的衰落属于同一过程,关于这一流变将来会有专门著述来详加描述。到那时,我们会真正十九世纪的教堂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从这时起,不再有真正的神学绘画作品出现,它们作为神学崇拜媒介的地位也难再维持。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人类无法再回归到过去的传统之中,因为宗教思想已经为纯粹的美学思想所取代。 把这种所谓“现代的”建筑学的发展趋势引向教会建筑领域并试图取得丰硕成果,那已经是后来的事情,而且,即使一些杰出的、卓越的艺术家可以创造出非凡的成果,然而总体看来,这种教会建筑再创造是失败的,这如同试图让工人们重返基督教的圣殿一样,是难以实现的。建筑工人们难再信仰基督教,新的技术架构也难再构建基督式建筑了。然而,那些新兴的钢筋玻璃架构的宏大建筑倒似乎内在地呈现了神圣化的内涵,人们不禁会联想到,这些建筑结构所体现的宏伟观念也许会预示一种新的教堂类型的出现,确切而言,与古代时期新兴的彰显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宏大建筑出现时的情形类似,这些基督教堂也可以通过相似的途径从那时的世俗建筑中脱颖而出。然而,这种新的教堂类型的发展机遇却并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或者即使有人已经意识到,却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城堡和宫殿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那个世纪中期的城堡建筑表现出更明显的保守倾向,比教堂还要保守,它的传统形式秉承了一种时间上的非关联性,这启发了后来博物馆的构造。然而,1830年前后,这个领域仍然受到了多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一种新的城堡类型出现了,真正明确的意义却消失殆尽,这成了它必然的命运。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时期的城堡建筑,似乎呈现了一种极端风格的一般性创作技法和原则;结果是整个城堡建筑仅凸显了戏剧性特征,这再糟糕不过了。海伦吉姆宫的凡尔赛系列作品是最能体现这一趋势的又一例证,许多人都试图去赋予它更为深刻的意义,可是它实在无法承载。海伦吉姆宫中有一些僧侣居住的房屋,供一位精神几近崩溃的僧人居住,这种设计几乎在呼应一种新的“太阳王”(Roi Soleil)风格,然而它的设计方案杂糅了其他各种流派手法,让人根本无法分辨出它的创作目的和特征。坦白地说,这组建筑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这组象征性案例表明了城堡与精神性之间的新的关系—城堡的各种山寨版图像志形式自身是空洞而苍白无力的。 在处理这些古代的主要形式问题时人们逐渐加强了对不确定性的强调,这源自对感官感受的过度讨巧;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尝试去构建一个全新的风格,应该源自对于某个全新主题的探索,源自人们努力去解决西方文化早期时代中尚未出现过的一些形式问题,或者世界历史有所记录的其他文明中同样尚未出现过的一些形式问题。 虽然如此,然而,在这场一般性的历史性回溯开启之初,我们还是从一种艺术形式入手吧,在过去的七十年间,它一直致力于将精神性与物质性的能量等同地注入大型建筑之中。所以,它完全称得上是“主要的形式问题”—尽管在它盛行的年代人们有时对于其他形式的研究和考察更为热心,而且,它的象征性意义对于本书的研究主题而言,意义非凡。下面我们将讨论这种主要形式,它是风景花园。 风景花园 在1972年前后的英格兰,作为对法国建筑花园的一种理性反叛,出现了风景花园这一形式。当时法式花园在外观设计方面采用了几何形式手法,后来人们批判这一做法在本质上违反了自然法则。所以,自1760年起,“英式花园”热潮迅速席卷欧洲大陆,人们的热情程度之高以及狂潮“席卷”的速度之快,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根据艺术家的日记记载,英式花园一经兴起,它早期的、尚待历史检验的创作探索就立即引发了兴建热潮,到处“大兴土木”,那种壮观景象真是前所未有。许多法式公园都开始纷纷转型,有时工程十分浩大,他们经改造后最终呈现为英式花园的格局。直到世纪末期,约略1830年前后,整个欧洲大陆都几乎遍布了自然的英式花园。这种对新艺术的狂热追求使当时的艺术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当我们提起世纪末期的阿尔明·冯·蒲克勒—姆斯考王子时—他因为两次试图将西里西安的广袤家园变成单一的风景园区而不得不面临破产,我们不由得将这一悲剧事件认定为“花园狂躁症”的盛行所致。 自从文艺复兴开始,对先前艺术形式的反叛开始成为艺术理论家反复讨论的主题。如今,风景花园在这一点上首屈一指。艺术理论界也对其进行了多方论证。首先,风景花园在折中、融合其他形式之后成为一种最具有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就空间而言,它融合了雕塑和建筑,甚至可以说,它作为建筑融合了雕塑、绘画和装饰等几种艺术形式。所以,风景花园成为一切想象性艺术作品中堪称最综合性的艺术,或者可称作“超综合艺术作品”。然而,当我们运用“综合性”一词去描述这种艺术时,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一方面,这种描述可说明风景花园确实是建筑的劲敌,首先它仅通过作品的规模就可以超越建筑;进一步而言,对于最壮观、宏伟的设计而言,它可以自由地利用空间,自由地进行空间创造。在构造方面,风景花园可以利用灌木丛和树林等有机团块来进行设计,可以布置小山的方位,并设计出池塘和小溪穿梭在其间,它还可以在这些树林之中蜿蜒、迂回地点缀一些装饰性元素,比如一些能盛开美丽花朵的植物丛。在这些大自然的组成要素之外,它可以构成一幅幅无与伦比的自然风景画,而画家如果依从它的风格进行创作,也只能在二维的框架里来完成作品;进一步与音乐艺术比照而言,风景花园可以构成一幅幅整体连续性的画面,这种与众不同的审美效果只有通过音乐艺术才能体现出来,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无法比拟的。在它所呈现的这些不同场景之中,它可以移步易景并唤起人们种种不同的感受,比如,人们会时而为壮观、宏伟的景物所震撼,或者时而陶醉于美景,享受一种宜人、宁静的氛围,又或者,人们会随着景、物的变幻而陷入沉思和忧郁,偶或心生苍凉之感。而最为重要的一方面是,这种艺术形式与自然自身关系最为紧密,它也在气质上与大自然最为相像,都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又极富于变化性。“没有哪一门模仿艺术能像风景花园艺术一样与自然那么水乳交融,也没有哪一门艺术能与大自然如此相像了。”可见,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风景花园具有明显的优势,有关于此的理论论证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风景花园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创作热情,这是当时其他艺术形式所望尘莫及的。人们随处可以看到,许多人真正热情地去构建样式新颖的风景花园,人们对兴建风景花园投注了极高的热情,就这一点而言,甚至堪比巴洛克建筑盛行时期引发的社会反响。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风景花园不仅是一种新的园林样式的出现。它暗示了一种对建筑霸权的反叛,暗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关系,一个一般的关于艺术的新的观念。 风景花园若要登上历史舞台,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人与自然原本的主动性关系必须由被动性关系来取代!这个新的、被动的对自然的从属关系的确立反映了一个伦理学的以及宗教方面的需求;事实上,“自然”一词本身如今拥有了一种宗教色彩,这个概念开始获得了泛神论意义。自然被赋予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她成为一种泛灵的力量,能够渗透到一切人与事物之中去。她不再以一种异化的身份与人类相对峙,人类已经被“同意”织入了她的存在。“在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皆可显露出相同的富于生气的实体存在,它是不可言喻的,它友好地靠近我们,将它自身注入一切。自然所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是完美的,她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的。人类最终的统治者存在于自然之中,用以感受美的理性和内在直觉等,一切都统统被赋予了自然之力。” 英国人阿什利·库珀是沙夫茨伯里第三代伯爵,他被歌德视为最富有才智的人,被视为整整影响一个时代并可以表征一个时代性格的思想家之一。正是这位阿什利·库珀成了这种新的泛神论自然崇拜的预言者,这一崇拜对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影响非常深远。斯凯尔以及莱内的作品最集中地体现了它的影响,他们是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很多成就至今仍尚未为人所知。 使园林设计师的艺术盛行的第一个条件得以满足之后,我们再来说明第二个决定性条件,后者几乎是神秘、不为人察觉的。自然的完善只能以理念的方式存在;这种理念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美(或极为抽象的美),它通过被创造之物散发耀眼的光辉,或者,它可以指向存在于世界起点的原始伊甸园,那也是人们不断努力寻求回归的地方。正是这第二种理念或构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性的精神力量。 自然在过去是一座原始的、完美的花园—关于这种观念的宗教起源说法不一,尚无法得到确切的考证—若以此为前提,那么艺术的任务,就是依据自然的这种最初的完善以及完美性去二次创造自然,在地球的某些地方,这种(完美)状态已然被保存完好。然而,通常来讲(此处的说法也尚待商榷),完美的自然图画只能在所谓的“史诗般的”风景画中被临摹。 就这最后一点而言,画家已然在不同类型的美之中做出了选择,并确定了创作的主题来统一他所选定的对象,他遵从某些特定的规则作画。他所选取的对象或多或少对应了园林设计师所努力实现的三维的再现。所以,他要经常、反复地思忖那些园林设计师在风格构造方面提供的技法和训谕,也就是说,他需要用伟大的风景画家的想法填充他的头脑,而且,只要有需要或者有的放矢,他自己就要尽可能地充当风景画家,如此一来,他才能使得他的模仿性作品与完美的原始图景相统一。因此,风景画家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要反复构想并设计上帝自己的创造场景并以此为依据,而且,风景画家只能凭借他们头脑中的构想,从而使上帝创造之物的完美之处得以显现。 这些画家们早先规定的技法和规则,后来随着时间的进程逐渐丧失了。当新艺术创作进入一种自觉的发展过程,并且开始强调并确立自身的独特个性和内在原则时,这些属于过去的种种规则和限定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即使在这时,人们仍感觉到,园林应该在观者的记忆之中激发起人们对于古老伊甸园的回忆,让人们忆起伊甸园、阿卡狄亚、弥尔顿的乐园、极乐之境,或者诗中的田园或仙境。 ? 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学家赛德尔迈尔集大成之作。 ? 以艺术作品的风格变化为基础,探讨社会更迭的现象与含义。 ? 这是一部探讨艺术作品的文艺之作,更是一部关于精神的批评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