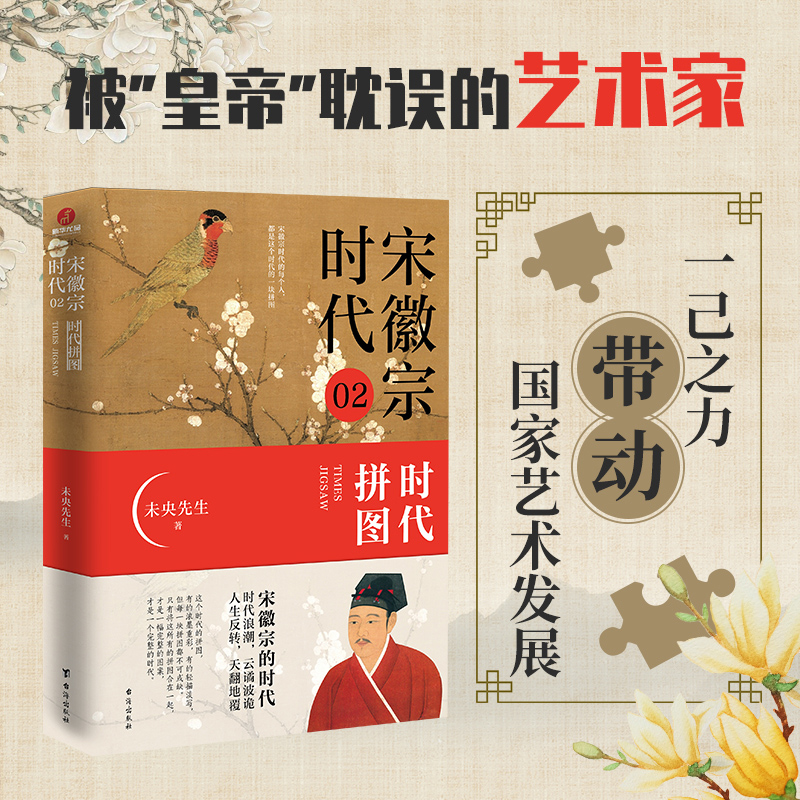
出版社: 台海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2.50
折扣购买: 宋徽宗时代.02时代拼图
ISBN: 9787516830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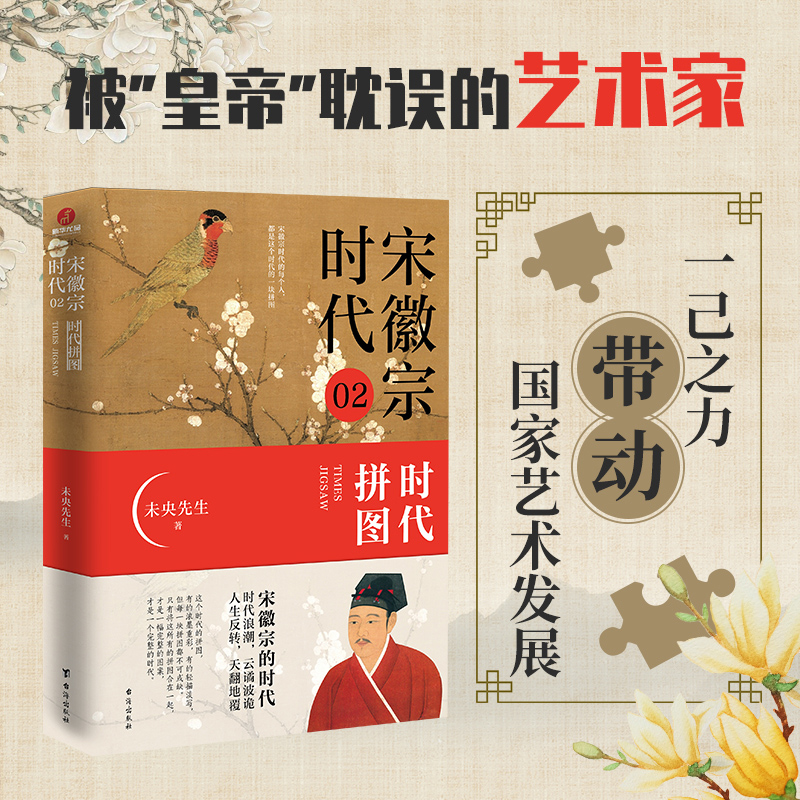
未央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人,政治学硕士,生在南方,长在北国,现客居香港。南北、北南,遍看九州山川大地,神游华夏历史千年。多年来,潜心读书,用心写史,尤爱两宋。致力于用文字鲜活文明,用人性丰满人物。期待与读者,共同走进历史,看见人生。
人生若只如初见 赵佶想起了一个女人,令他刻骨铭心的女人。 作为皇帝,他自幼长在深宫,见惯人间绝色。对于女人,他是有免疫力的。 可这个女人不同,不仅拓宽了他对女人的认识,也拔高了他对美的理解。她仿佛不是来自凡间,而是从天而降。 初次见面是在十多年前,他记忆深刻。 那是个暮夏的傍晚,落日余晖洒满皇宫大内,凉风习习,赵佶一身便服,坐上改装过的舆车,从左掖门悄悄出宫而去。这次出行,他期待已久。至于去见谁,他并不知道却也不想去问,这是一种情趣。 车穿过御街,再往南穿过东、西两座教坊,便是龙津桥。桥的两边都是民宅区,人气很旺,酒肆茶楼林立。进入晚间,更有夜市开张,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是东京城的一处热闹所在。 再往东去,过了麦秸巷、状元楼,嘈杂声渐渐平息,渐入一片幽静所在。这里有京城端的风月场所,多是些独门独院的小楼,乍一看和民宅无异,区别在于门楼下挂的灯笼。灯笼主要有两种,鱼头灯和兔头灯。鱼头灯挂起表示已有客人,不再接客,兔头灯点亮则表示空闲,可以接客。 这条路徽宗已走过多次,这些宅院他也进过多间。初来这里时,他还有心看看街边的风景。现在早已熟门熟路,坐在车里,甚至不用掀车帘,他仅凭着车的转向和外面的声响,就能大体判断出所在的方位。 只是到了那些记忆深刻的地方,他还是忍不住挑起帘子往外张望。看亮起的是鱼头灯,不免有些失落,看到亮的是兔头灯,内心就多了几分躁动。每次车速稍缓时,他都以为车会停下,可每次车都继续向前。他有些懊恼,但很快又重新燃起希望。几次三番,弄得他有些口干舌燥。 一番左转右转,车驶进一条小巷里。巷子很安静,有节奏的马蹄声和车轱辘在青石上滚动的声音,非常清晰。渐入巷子深处,车慢慢停了下来。 徽宗下了车,四下看了看,确信没来过这个地方。眼前的小院并没有挂任何灯笼,这让他有些疑惑。随行的宦官赶紧解释,这女子从不挂灯,只接待有缘人,无缘之人,纵使千金也难睹芳颜。今晚他们匿名而来,终能否如愿,也未可知。一席话让徽宗心痒痒,也更加好奇。 扣了门环不久,一位妇人开了门。这妇人四十岁左右,看上去很有些风韵,年轻时也定是个大美人。重要的是,她完全没有矫揉造作,言谈举止非常得体,既不是很热情,又绝不显得冷淡,让人亲近而舒服。简单寒暄后,她引着他们入了院。 徽宗走在后,仔细留意这小院。院落不大,收拾得非常利落,院子四周种了很多花木。虽看不清花的样子,但阵阵幽香令人心情愉悦。至少,有桂花无疑。 穿过两重院落,来到一座三层的小楼,那妇人领着进入客厅,请徽宗稍坐,便转身上楼。稍后,有使女过来奉茶,又悄悄地退了出去。四周一片寂静,院子里夏虫的鸣叫声清晰可闻。这般情境不似寻花问柳,倒像是到朋友家拜访。 徽宗开始打量这客厅。房间并不大,但布置得很雅致。屋子里的几件家具虽然说不上多么名贵,但也是精挑细选的无疑。客厅南面的墙上挂着一些字画,这让徽宗有了兴趣。 一幅秋水伊人图,吸引了徽宗的目光。画面上,秋水茫茫,水光接天,一舟自横,有位佳人立于船头,斜撑一把油伞,目光望向远方,脸上写满了惆怅和忧伤。画的右下角刻有一方印记,秋水堂主。 论起书画,徽宗是行家,也是大家,更是鉴赏家。秋水堂主,他未曾闻名。不过,这幅画的布局、意境和绘画的功底,即便算不上,亦在中上。 看着画,他开始琢磨起了题画诗,想了几句,不是很满意,又来回踱步开始重新构思。这时,身后的楼梯上,传来了一前一后、一重一轻的脚步声。 等的人来了。 他很好奇,虽略做矜持,但还是忍不住回头看,这一眼不禁让他倒抽一口凉气,还打了个激灵。作为皇帝,他阅尽人间美色,无论环肥燕瘦、软玉温香,还是艳若桃李、国色天香。可是,却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 楼梯上的佳人正值妙龄,一袭乳白色的纱衣,右手执团扇,左手扶楼梯。伴随着下楼的脚步,玲珑的身材如风摆杨柳,仪态万千。再近些看,高高盘起的发髻,白皙的面庞,精致的五官,如水的眼睛,一抹红唇,嘴边挂着浅浅的笑意。每一样,都如此地恰到好处,增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少,堪称完美。 他就这样看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忘记了身份,忘记了一切,一 脸的痴态。直到女子走到跟前行完礼,他也没有回过神来。旁边宦官见徽宗失态,只好从后面轻轻拉他衣袖。 徽宗这才反应过来,拱手向姑娘还了个礼,只是身体有些僵硬,动作略显滑稽。语言的功能也暂时失去了,喉咙似乎被堵上了,说不出话来,他有些窘迫。姑娘见他如此痴态,不禁掩面失笑。这一笑,千娇百媚生,更是令徽宗神魂颠倒、意乱情迷。 落座后,徽宗连喝了几口茶,才渐渐恢复了平静。他自称商人赵乙,来东京行商,仰慕姑娘许久,特地前来拜会,只是不知姑娘芳名?这句话,有着明显的逻辑错误。 女子听完,略带娇羞,又有些调皮地反问,既然不知名讳,又怎能仰慕?其实,行礼时她已说过名字,只是徽宗神游天外,完全没听到她说什么。 不错,女子正是李师师,东京城内风月场的头牌。 据说,师师是东京人,原本姓王,父亲叫王寅,在京城东二厢永庆坊经营染坊。虽是小本生意,挣点辛苦钱,一家人倒也衣食无忧、其乐融融。但天有不测风云,师师四岁时,父亲惹了官司,死在狱中,母亲不知所终。家散了,她无家可归。 可怜的小师师被寄养在寺庙里,这才有师师这个名字。其间的心酸,师师也从未与人提起过。一个被遗弃在世间的小女孩,还能有更好的归宿吗?果然,稍长后,她就辗转到了娼门。 风月场,就是名利场。这里世俗、功利,也真实。这里就信奉两样东西,色艺和钱财。有了任何一样,就能看到笑脸,千万张不同的笑脸。 师师就生活在笑脸中。她天生丽质,倾国倾城;她聪慧可人,才艺俱佳。尤其是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可谓天籁之音。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幸运?未及二八年华,师师已是人风流、歌婉转,在京城小有名气。 真正让她出大名的,是张先。张先,北宋著名词人,精通音律,一生做官、治学、填词,富贵风流且享有高寿,终年八十八岁。 张先与苏轼颇为交好,两人常觥筹交错、诗歌唱和。据说,张先八十岁时,新娶一房小妾,年方十八。大婚之日,张先看着红粉佳人,心潮澎湃,赋诗一首: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苏轼正在席上,即兴和诗一首: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要说东坡先生,才是真风流,调侃老友的段子诗,也能千古传颂。一树梨花压海棠,更是千古佳句。 不过,纵是小妾年轻貌美,还是没能留住张先的心。八十五岁的白发老翁,遇到了更为心动的人——正值妙龄的李师师。初见面,即惊为天人。 张先一生填词无数,是婉约派的杰出代表,青楼歌坊,多传唱着他的词作。 年轻的师师,让垂垂老矣的张先重新焕发了生命的光泽,才思如泉涌,他甚至专门为师师创作了新词牌《师师令》。在他生命的后几年,师师陪伴在他左右。而师师在张先的调教下,才艺也更上层楼。 据说,当年的东京城,高楼凭栏处,一个妙龄少女、一个白发老翁,红颜白发、白发红颜,一人歌唱、一人击节,人为天上人、曲为天上曲,引得无数人驻足观赏,为之喝彩。 有了张先的加持,李师师名满京华。 引得天下才子,趋之如鹜。 这其中,便有秦观,秦少游。 提到秦观,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苏小妹。 可惜,苏小妹查无此人。苏轼有三个姐姐,并无小妹。不过,秦观一生与苏轼结缘,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一。 秦观,江苏高邮人,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不过,他的仕途之路并不顺遂,两次科考,两次落榜,转眼已过而立之年,两鬓渐生白发。这时,恰逢苏轼到徐州为官,秦观仰慕他已久,便自家乡到徐州登门拜访。 彼时,苏轼早已名满天下,而秦观一事无成。不过,苏轼性格豪爽,礼贤下士,愉快地与秦观会面。两人促膝长谈,苏轼惊叹秦观之才,秦观仰慕苏轼之名,师生情分就此定下。在恩师的鼓励下,秦观三进京城,终于高中进士,时年三十六岁。由此,踏入了仕途。 公元 1085 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朝政发生巨变。太皇太后临朝听政,王安石新法俱废,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士陆续回京主政。秦观作为旧党领袖苏轼的学生,初入仕途,便赶上了好时候。 在秦观一生中,这段时光应是快意的日子。有了苏轼的力捧,再加上本人才情,秦观很快便名满天下。 人生得意,岂能无红颜相伴?李师师走进了秦观的生活。 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时间、怎样的场合初次相见。我们只知道,才子佳人从来都是相互吸引的。甚至,无须太多理由。或许,他们是在晏几道的引荐下相识的。 晏几道,前朝宰相晏殊的第七子。父子二人在文学上造诣都很高,后人称为“二晏”。与秦观不同,晏几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父亲是宰相,六个哥哥也都出仕为官。出身高贵,才情出挑,少年时,晏几道就是闻名京城的公子哥。 只是,后来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又被新旧党争所累,人生有了很多起伏,他尝尽世态炎凉。不过,正因为如此,他的词却作得越发精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皆是千古名句。 无疑,晏几道与李师师是老相识。关于师师的美,晏几道曾用一首词来形容: 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 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遍看颍川花,不似师师好。 如此绝妙佳人,秦观岂能不见? 据说,师师对秦观一往情深。虽然,在这东京城里,秦观除了才名,既非王侯将相、公子王孙,更无万贯家财。但他,就是入了师师的眼。爱一个人,理由千条万条。强悍的理由,永远只有三个字——我愿意。 对师师来说,她的笑从来都不属于自己,她的艺也从来都不属于自己。她用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成了京城的头牌,这才有了小小的自由。为了这小小的自由,她坚定而执着地坚守着。 如果说对张先,她是出于感激,那对秦观,便似是初恋。是的,青楼女子也有初恋。为了这个人,师师苦等了很多年。 郎有情,妾有意。两人耳鬓厮磨,如胶似漆,一对神仙眷属,似是天作之合。可惜,这两个都是命苦之人,他们的快乐时光,仿佛是跟命运借来的一般。 朝局的波折,打破了师师小楼的宁静。 随着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旧党全部被撵出京城。在送别老师苏轼不久,秦观也接到了贬谪的诏书。 在师师的小楼,两人后告别。 这晚,正是七夕,这原本是个重逢的日子。 师师坚持要跟秦观一起走,并要给自己赎身。这时,秦观早已过不惑之年,除了空有虚名,身无长物,师师此话更让他不堪。加之在朝中数年,他早已领教了仕途凶险。此去山高水长,何年何月是尽头,他根本不敢想。 他断然拒绝了师师。也只有如此。 几番梨花带雨、几番寸断肝肠。一夜无眠。 黎明,行前,他留下了一首词: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首词,他留给了师师,也留给了历史。 千百年来,这首词被无数人传唱。那些有缘的人、无缘的人,特别是有缘 无分的人,在心中默念千遍万遍,满含热泪。 李师师唱了一遍又一遍。 秦观向南而去。 自此,他们山水相隔,只有鸿雁传书。 在颠沛流离中,秦观度过了七年的时光。哲宗驾崩,徽宗继位,他和恩师都接到了回京的诏书。那一刻,他满心欢喜,偌大的东京城,他想见的只有一人。而东京城内的师师,也早已将小楼里外收拾一新。 眼见重逢在即。可惜,与东坡一样,秦观也没能再回到东京,路过广西藤州(今广西藤县)时,他驾鹤西去。自此,人间再无秦少游。 听闻秦观去世,苏轼感慨悲伤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一年后,苏轼也病故。 小楼一别,秦观和师师,人生再无相见。 不知七年相思路,即到重逢日的师师,听闻噩耗,是怎样的伤心欲绝,恨天不公、叹己命苦。 或许,唯有吟诵,唯有歌唱。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告别了张先,送走了秦少游,师师越来越孤独,名声却越来越大。求见的人络绎不绝于道,却都入不了她的眼。 朝廷新旧党争,让京城的官员走马灯般,又来了一拨新人,这其中就有周邦彦。 周邦彦,浙江杭州人,生得眉清目秀,是个美男子。 青年时,他在东京太学读书,人长得帅,文章也做得好,很是风流,渐渐也有了名气,就连神宗也有所耳闻,召其到宫中问话。周邦彦平时不拘小节、大大咧咧,见到皇帝也是如此。好在神宗并不在意,只是问起他近有无诗作。 周邦彦有备而来,献上了新作的《汴京赋》。洋洋洒洒数千言,用极尽铺张的华丽词语,将东京汴梁城描绘得美轮美奂。更重要的是,在赋中他坚定地表达了对神宗变法的支持。 这是个有智慧的年轻人,相比朝中那些附和新法之辈,同样是表态、表忠心,段位却高出许多。 神宗读之大喜,提拔其为太学正。进宫之前,他是太学的学生,见完天子,直接做官了。就好比现在的大学生,和校长谈了一次话,交了一篇作文,直接留校进了教务处。 如此,可见周邦彦的才华,也可见神宗的爱才之情。 不过,世间事祸福所依。你以为时来运转,从此前程似锦,却不知前方就是巨坑。 周邦彦献赋支持变法,天下闻名。世人皆知他是新党,后来卷入政治纷争、仕途坎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被撵出了东京城,在地方盘桓多年,多是做不入流的小官,大好的年华就这样悄悄溜走。直到哲宗亲政,秦观等旧党被贬,周邦彦这才重回东京城。 昔日美少年,归来已是不惑大叔。 诗穷而后工。与秦观一样,坎坷的人生经历,反倒让周邦彦在艺术造诣上更加精进。再回东京的周邦彦,早已是才学满天下。他在北宋婉约派大词人里后一个出场,是集大成者,被称为“词家之冠”或“词中老杜”。他不仅填词,还精通音律,是个全才。 一个是词家之冠,一个是京城头牌。 周邦彦和李师师的见面、相识,几乎是必然的。 或许是早年张先打下的底子,又或许是秦观留下的空白,师师对于这样的大才子,从来都没有抵抗力。她能视富家公子万金于不顾,却抵不住大才子的一首长短句。 师师和周邦彦,填词作曲、吟风弄月,日子过得安逸又宁静。 如果说秦观是师师的初恋,那周邦彦就更似她的婚姻。 初恋时,虽是真爱,却未必懂得爱情。只是任由情绪疯长,那是一种肆无忌惮,更是一种不管不顾的宣泄。虽然激烈,却未必长久。所以,师师当年愿意放下一切,跟着秦少游去天涯海角。如果不是秦观理性,断然拒绝,或许师师的人生已然凋零。 而婚姻在感情之上,更多的是彼此的依靠。这份依靠是对现实的妥协,也是对人生的妥协。流落风尘多年,师师累了,也倦了。她渴望有个肩膀能够依靠,周邦彦出现得恰逢其时。而周邦彦历经风雨、蹉跎半生,自然倍加珍惜,也更懂得如何去呵护这生命中难得的温暖。 虽然身在娼门,仍在人生的沼泽里,但有了周邦彦的陪伴,笑容又回到了师师的脸上,直到“赵乙”的来访。 内容考究,脉络清晰 以时间为叙事线索,以人物为时代经络,勾勒出王朝浮沉、帝国兴衰的浩荡画卷。文末附增多张大事年表,横向多元观照,纵向文化反思。 雅俗兼备,文风俊爽 从朝堂到江湖,从名士到布衣,从相依到倾轧,硬核史实与趣味故事相结合,古典气质与现代风尚相交融,文字明晰精巧,内容妙趣横生,堪比《明朝那些事儿》。 视角独特,笔法卓然 通过现代史家视角,用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讲历史,为您解读宋末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交流,窥入宋徽宗艺术天才与亡国之君的错位人生。全景式俯瞰北宋末年的盛世繁华与风云变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