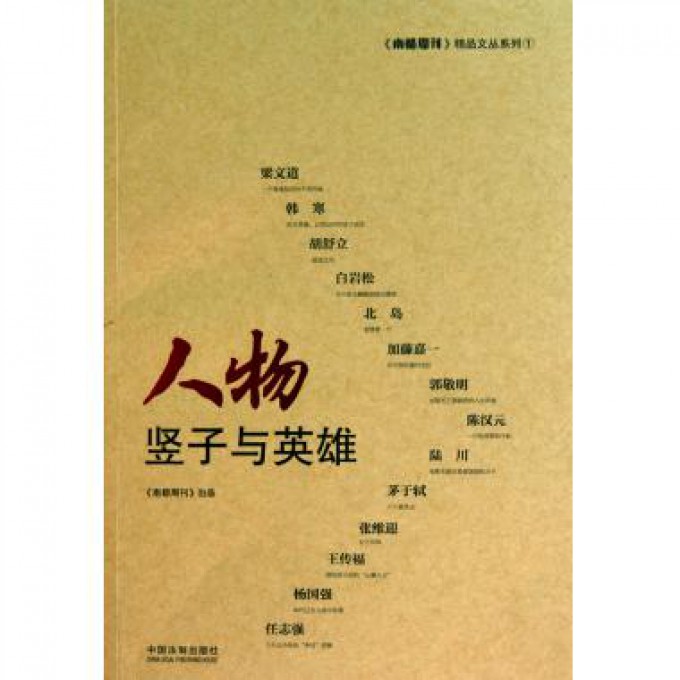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法制
原售价: 29.80
折扣价: 19.70
折扣购买: 人物(竖子与英雄)/南都周刊精品文丛系列
ISBN: 9787509328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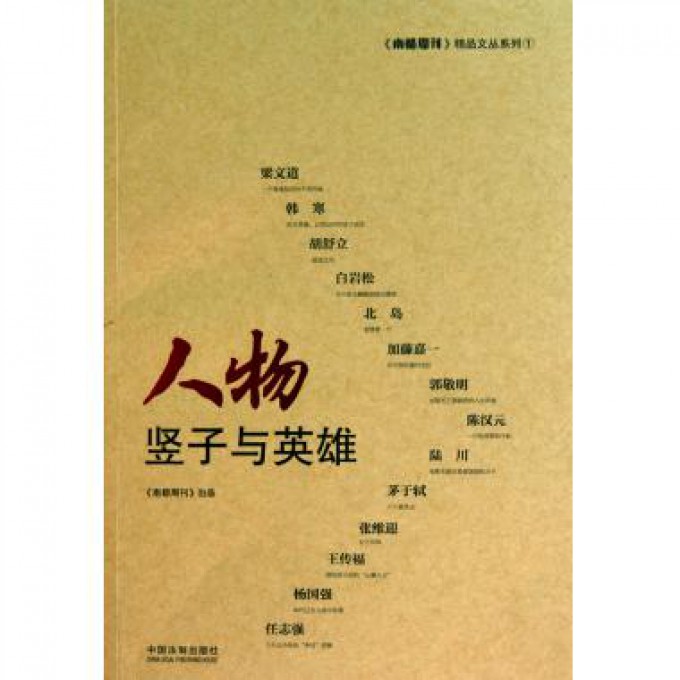
狂人蔡志忠 当初,谁也没想到搞了一辈子漫画的蔡志忠会去闭关十年研 究物理。十年后,他小心地交出了闭关作业——“宇宙四部曲”。 面对外人不解,他自比欧洲贵族,有钱有闲自然会去研究宇宙的 起源。他扬言千年后人们会记住他。他嬉笑怒骂,老夫聊发少年 狂;他随心所欲,天子呼来不上船。 邪 “我来北京四天,只吃了四碗面。”蔡志忠点上一根烟,微微 扬起下颌。深秋的北京已初露寒意,蔡志忠趿着一双布鞋,套了 件雪白衬衫便下了楼。 39年前,蔡志忠发现,吃完早餐后,“大脑便从天才变成猪 头”,从此每天只吃一顿饭。如今,节衣缩食于他是种享受。“口 中言少、心中事少、腹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快了。” 蔡志忠照着药王孙思邈的“四少养生诀”,保持饥饿和清醒。十年 闭关研究物理期间,他曾有120小时不进食的记录。 我问他,那是什么感觉?“72小时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是最聪 明的。”他说,“其实冷不冷、饿不饿,很多时候只是心理状态, 不是你真的很需要。” 62岁的蔡志忠觉得自己越老越聪明。年长让他更为温和敦 厚,他说已经十几年没有生过气;而数学的训练让他变得敏锐有 力,他绝少废话,反应敏捷,拿起鼠标摆弄电脑一点不比年轻人 慢。他给记者们表演,计算他们的生日是星期几,无一失算。他 有一套星期纪年公式,瞬间心算即能得出。 这只是客前表演的小把戏。他随身携带的黑皮小本上写满了 数学公式,致密而工整。十年来,他共推算出一万个数学公式。 1998年8月,50岁的蔡志忠到香港参加埠际杯桥牌赛,比赛结束 返台后即宣布:要闭关三年,专心研究物理。 他像个大孩子般兴奋地宣布: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阻 止我研究物理。外人多有不解,他自比欧洲贵族,有钱有闲自然 会去研究宇宙的起源。但出关的时间一再延迟,十年后,他小心 地交出了闭关作业——《东方宇宙四部曲》。 蔡志忠饶有兴趣地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谈起他的“东 方宇宙”发现,于殿利就会想起达·芬奇来。达·芬奇作为艺术 家尽人皆知,而他作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成就却不为常人所知。 “他们俩有非常重要的共同之处,”于殿利说,“那就是丰富的想象 力和对自然敏锐细微的感受力。” 艺术家颇似造谜者,科学家却是揭开谜底者。歌者朱哲琴在 给“四部曲”的序中这样写道,“这看似完全不同的两极,却有着 相同的起源,艺术和科学一样都是从想象开始的。” 想象之于少年蔡志忠,是件又爱又怕的事。 客厅窗户外,隔着庭院,正对几棵大树,太阳将树叶投影在 窗上。蔡志忠蜷缩在客厅太师椅中,随风摇晃的树影在他脑海里 幻化成各种奇怪模样:长长的叶影像香蕉,黑影像西瓜,还有的 像长发飘飘的女鬼……蔡志忠的想象力让自己感到莫名的恐惧, 乡野间的鬼怪传说都在窗上变幻的树影中上演。他感到新奇而刺 激,这是童年不多的乐趣之一。 五十岁之后,当他在凌晨走近窗边,聆听万象呢喃,思考从 原子到宇宙,从数学到物理诸多问题,想象力如脱缰之马奔驰在 无垠夜空,他视此欢愉为人间至乐。 蔡志忠一生斗志昂扬。小学时他的各科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 前茅。每天上学经过一座小桥,他过桥时都会将头探出桥栏,看 看河水中自己的倒影,然后告诉自己:“好高兴!今天又要去打败 别人啦!” 他喜欢当第一,出风头。在网络上,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是 Einstein(爱因斯坦),“既然都不要钱的,为什么取阿猫阿狗,就 取一个品牌,一看就非常显眼”。 绘画之余,他最爱桥牌。从1986年开始,蔡志忠拿过大大小 小100来个桥牌冠军。但他从不参加世界桥牌大赛,因为“老是 输,心里不爽”。 “我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个出色的动画导演。”蔡志忠29岁成 立卡通公司,8年内拍了4部电影,其中《老夫子》获得台湾金 马奖最佳卡通电影长片奖,曾多年保持台湾最高票房。1985年, 37岁的他当选“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蔡志忠清点了下自己的财产,他拥有相当于220万人民币的 存款和3幢“相当好”的房子。“220万不多,但我这辈子不赌钱, 不投资,不跟人家担保,到死的时候还有钱吃饭,应该够用了。” 蔡志忠觉得钱已赚够,接下来的时间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这一年他关掉公司,到了日本。旅行中他发现一双很喜欢的 布鞋,一口气买了14双,顺带买了30件白衬衫和20条卡其裤。 “我觉得可以穿一辈子了,没想到我活得比我的鞋子还要久。”蔡 志忠笑道。他说要过最大的精神自由的生活,就必须要过最节俭的 物质生活。“我—个馒头就可以打发一天,不必看人眼色过日子”。 钱对于蔡志忠从未成为问题。他腊月二十三的生日,人言他 赶上了猪年的尾巴,属猪有财运。37岁之后,他不在乎钱,却 也从不借人钱。他把积蓄用来买房子和佛像。最多的时候,他拥 有10套房子。如今在台北的家里,他用两间屋子来放3400多尊 铜佛。 “3400尊铜佛是什么概念?九年四个月,平均每天花一万人 民币买一尊,没有一天间断。”蔡志忠说,他一生画漫画赚到的钱, 只有收藏佛像后升值的十分之一。 香港作家蔡澜到他家玩,被满屋的佛像惊呆。他指着被佛像 包围的三张榻榻米:“遇到地震,佛像掉下,被压死了,也是一种 相当有趣的走法。” 痴 蔡志忠摆开电脑,掏出Itouch(他不用手机,所以没买 Iphone),得意地展示自己制作的动画。他让助理拿来啤酒和花生, 边喝酒边欣赏。他喜欢给大家造出其乐融融的气氛。 在上世纪40年代生人里,蔡志忠属于为数不多热烈拥抱新技 术的那拨人,在他看来电脑是人脑的延伸_o笔记本电脑和类似阅 读器的“掌中宝”是他始终不离手的两件东西。他曾对商务印书 馆总经理于殿利说,余下的人生就只想完成一件事,那就是实现 纸介质图书的数字化。 除却一头飘逸的长发几十年未变,蔡志忠身上并无世俗想象 中其他有关“艺术家”的特点。他饮酒却不酗酒,思维发散却逻 辑严谨,懒散与他无关。他不熬夜,天一黑就早早上床睡觉。但 凌晨一两点就醒来,不吃早饭,一直工作到下午一点。 蔡志忠早起的习惯来自幼时。当他还是台中彰化农家的一个 婴儿时,早上凌晨三点,母亲背起他起床煮猪食,喂鸡鸭。 他记事极早。他清晰地记得人生面临的第一次恐惧,那是他 不满一岁时,母亲与众人聊天,他倚在母亲腿边,伸手去抓母亲 的大腿。一只窘迫的大手坚决地制止了他,母亲的拒绝让他第一 次感受到惶恐。 他出身乡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乡民代表会的秘书,写 得一手好字,村里红白喜事都找他。蔡志忠从小享受父亲的荣光, 却没继承书法的家传。 这个家庭内部并无太多交流,家里无事便不讲话。蔡志忠多 次说到自己感情内敛,与幼时家庭生活很有关系。他跟哥哥睡同 一张床,三年没有说过话。“我小时候跟爸爸大概讲不到50句, 跟妹妹也讲不到50句。”至今,妹妹还不大敢过来找他。 但家里有一样好:父母对蔡志忠极少管束,他从小知道要自 己做主。“我们家每个人生而为主,从没有人问‘爸爸,我把我们 家这六个月饼全部吃光好吗?’——不用问的,你自己吃就好了。” 50年代的台湾农村清贫而宁静。读书于乡民,只是个识字工 具,学而优则仕的梦想远不及子承父业来得实际。“我们村庄里 每个3岁半的小孩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铁匠的孩子帮父亲打铁, 牧童都是5、6岁带着小孩子,但我什么都不会,所以我3岁半开 始思考,到了4岁半我发现我的专长跟喜好就是画画”,于是,他 决定只要不饿死,就要画上一辈子。 蔡志忠立志以画招牌画为终身事业,父亲并未阻拦。十年后 他把自己画的四张稿子寄给出版社,对方愿意请他当职业漫画家, 他决意休学北上。他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父亲捏着报纸哼了一 声:那就去吧。眼都没抬一下。 辍学是不是很痛苦?总有年轻人这样问他。蔡志忠感到好笑:、 “你爱一个女生,有天她说要嫁给你,难道这时候要说,等一下, 让我先念完初中、再念完高中、大学,再跟你结婚好不好么?” 因为家庭的关系,蔡志忠一出生便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刚满 一岁时,他已经跟着母亲到教堂听了100个基督教故事。他尚未 识字,只能以画面记住这些故事情境,由此培养起画面记忆和画 面思考。这些故事一直烂熟于心,成年之后搞创作,“杯子对筷子 说”、“香烟对火柴说”,这类故事他信手拈来。 他做过很多次智商测试,结果都是180。我问他是否见过比 他更聪明的人,他想了想,神秘一笑:我不好意思讲。 蔡志忠的内地助理刘继蕊说,他几乎没有娱乐,“我们平时没 事的时候总想看看电影电视休闲一下,但他不会。他永远都是在 工作”。 蔡志忠打开一个“中国美术史”的文件夹,里面有两万多个 子文件夹。这些资料都是他一点点从网络上搜集的。他在电脑上 建起一个惊人的数据库。“光这些文件名就得打上一个礼拜。”他 说,只要谁有一张画传世,这里都能找到。他计划把中西美术史 都拍成动画片。 喜欢亲历亲为的他觉得,自己做得比别人好。62岁,他依然 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他不喜欢别人说他勤奋。“我是疯狂,”他说, “不工作我会死的。” P4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