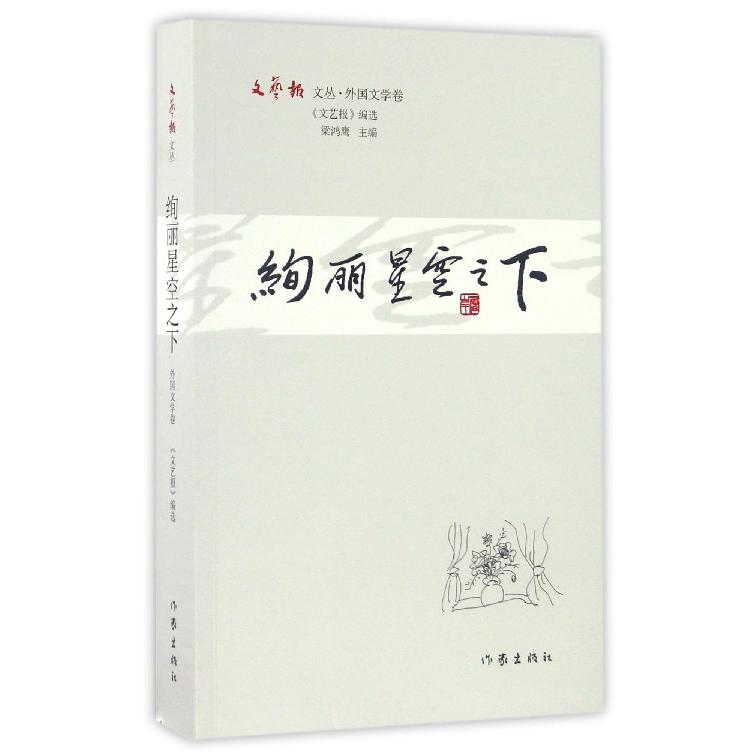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31.50
折扣购买: 绚丽星空之下/文艺报文丛
ISBN: 9787506392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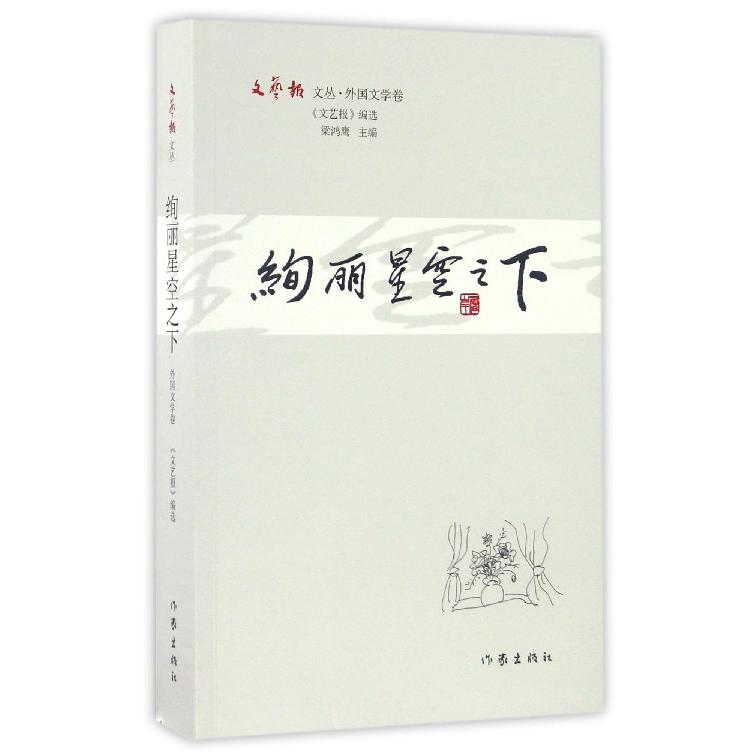
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创作于1979年, 至今走过了35年创作路程。以主题划分,他创作的第 一阶段可以说是“挖洞”的15年,第二阶段大致是“ 撞墙”的15年,第三阶段则是回归“挖洞”的5年。 2003年初,我趁作客东京大学之机初访村上,交 谈当中确认他在网上回答网友提问时说的一句话:“ 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够通过孤 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 ”进而问他如何看待或在小说中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 系。他回答:“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 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 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 同别人连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 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一言以蔽之,村 上认为,孤独是沟通的纽带,为此必须深深挖洞。如 《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等早期作品中,总体上倾向于 通过在自己心中“深深挖洞”来审视孤独、诗化孤独 ,并以此与人沟通。《1973年的弹子球》甚至通过主 人公执着地寻找弹子球机这类无谓之物而将孤独提升 为超越论式自我意识,从而确保自身的孤独对于热衷 于追求所谓正面意义和目标等世俗价值观的优越性。 不妨说,“挖洞”的目的大多限于“自我治疗”,即 “挖洞”是“自我治疗”的手段。《挪威的森林》和 《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继续“挖洞 ”主题,但逐步挖得深了,希求尽快“在某处同别人 连在一起”。这可能因为,木月死于孤独,直子的姐 姐和直子死于孤独,再不能让主人公处于“把自己围 起来”的自闭状态了。《舞!舞!舞!》中,喜喜死 了,咪咪死了,这使得“挖洞”的过程变得愈发艰难 ,愈发难以“同别人连在一起”。这意味着,村上用 “挖洞”进行“自我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于是村 上创作的第一阶段基本到此为止,而开始下一阶段的 “撞墙”13年。 “撞墙”源于村上2009年初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 时,为此发表的获奖感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 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同时表 明:“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 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 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 缠和贬损。”不过,村上针对体制这堵高墙的“撞墙 ”努力不是从2009年才开始的,而始于《奇鸟行状录 》(1994—1995)。可以认为,从那时起,村上明确意 识到仅靠“挖洞”这种开拓个体内心世界纵深度的做 法有其局限性。而要同更多的人连接,要进一步获取 灵魂的尊严与自由,势必同体制发生关联。但体制未 必总是保护作为“鸡蛋”的每一个人,于是有了撞墙 破碎的鸡蛋,为此村上表示“他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一立场较为充分地体现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 巨著《奇鸟行状录》中,而在其中揭露和批判日本战 前军国主义体制的运作方式即国家性暴力的源头及其 表现形式上达到顶点。《海边的卡夫卡》和《1Q84》 第1部、第2部持续推进这一“撞墙”主题,笔锋直指 日本黑暗的历史部位和“新兴宗教”(cult)这一现代 社会病灶,表现出追索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的社会架构 、同无所不在的体制之间的关联性的勇气。 令人意外的是,到了《1Q84》第3部,村上将笔 锋逐渐收回。及至《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 年》和最新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已彻底回 归“挖洞”作业——继续通过在个体内部“深深挖洞 ”而争取“同别人连在一起”,亦即回归追问个人生 命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治疗”的“挖洞”主题原点。 P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