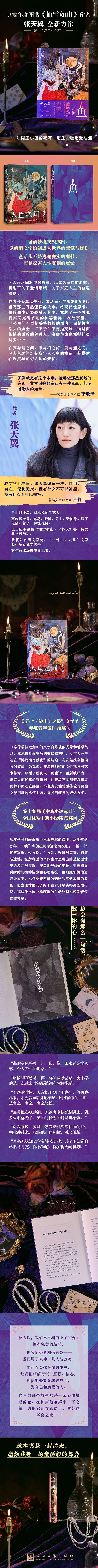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45.36
折扣购买: 人鱼之间
ISBN: 9787020189694

张天翼,自由职业者,写小说的手艺人。喜欢郁金香、海岛、游泳、芝士、恐怖片。膝下无猫。养了一棵桂花树。已出版小说集《如雪如山》《扑火》等、散文集《粉墨》,曾获朱自清文学奖、“《钟山》之星”文学奖、燧石文学奖等奖项,有作品改编成电影上映。
后记:童与真之间,幻与象之间 童话,是混沌与真实之间的一片林地,是最早照进幼儿之心的艺术的光,是一罐文明的开口奶。 我们这里的小孩子有童话读,是近百年才有的事。周大先生在《朝花夕拾》里讲了他那时代的儿童阅读——他当然也曾是个小孩子。所有威严的人,言语无味的人,挺着将军肚、双手虎口托腰的人,酒桌上逼实习生喝酒的人,泼汽油烧死妻子的人……都曾是小孩子。 一切小孩子爱的都是:动物、图画、故事。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绍兴小男孩樟寿,喜欢《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爱看有图的《花镜》,最渴望要一套插画绘本《山海经》。然而,他七岁开蒙,读的是《鉴略》,一种极无聊的韵文历史书。在家里,他被允许公开翻阅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 倒真有个亲戚,送来一本带画的图书。什么呢?《二十四孝图》。那里头讲:父母为了让老人不挨饿,应该把小孩抱去活埋。 很多年后他写道:“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 心灵干渴,与置身沙漠求一瓯水而不得,庶几相似。后来小孩们必读的《安徒生童话集》,一九二四年由赵景深首次选译成书,第一本《格林童话全集》则要等到一九三四年才正式在我国出版。 我记得我的第一套《安徒生童话全集》,是旧书,受赠于亲戚里某个不再是小孩子的人。一套很多册,叶君健译本,平装,暗绿封皮,那个宁静的绿,一看就想起放糖的绿豆沙,心头一阵清甜。书的纸张很薄,背面字的油墨透过影子来,跟正面的字叠在一起,仿佛句句有回声。他的每个故事都像一朵神异的花,每朵花散发不同的香气。 另外几本最心爱的:姜尼·罗大里《蓝箭》,米切尔·恩德《毛毛》,拿到诺贝尔奖的《丛林故事》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以及《吹小号的天鹅》。 还有《王尔德童话》,他的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心碎的吻,巨人亲吻男孩,燕子亲吻王子,矮人亲吻公主扔来的玫瑰,星孩吻他母亲的脚,渔夫吻着死人鱼的冷嘴唇。每个故事里,都有人把赴死的过程当一场舞会,擦亮生命别在衣襟上。 童话之影响,大矣哉。 有一则很可能不真实的著名“逸事”:人们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这一生里,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里获得的?”他答:“是在幼儿园里。” 我精神上很多最重要的东西,是在童话里获得的。现在,我一低头看看自己的胸脯,就能看到深爱的那些童话,像恒星在宇宙里稳定地燃烧,像长明灯在神殿里昼夜亮着。 有些故事,长大后不再喜欢,比如《彼得·潘》。我曾深爱彼得,他会飞,战斗起来冷静又聪明,我曾想象他一定有一对细长发亮的小腿,掠过云层时像鹤或鹳鸟。成年后重读,读到了童年时漏掉的、令人震惊痛苦的东西:“永无岛上孩子的数目经常变动,他们眼看要长大的时候,彼得就把他们饿瘦,直到饿死。” 还有些故事,小时就不那么喜欢。作为女孩,我读故事会把自己代入里面女性的角色。但说实话,代入进去,体验并不太好。比如《白雪公主》,一个女孩跟七个有老有少的陌生男的睡一屋,睡他们的床,这太可怕了。换衣服怎么办?洗澡怎么办?怎么保证这七个人都不偷窥?动画片里,矮人们出门工作前,到白雪公主面前排队,她逐个吻那七个秃脑门。他们洗头吗?肯定一股脑油臭吧?我只觉得恶心。 对《睡美人》《小红帽》等故事的不满,源于女主角的被动、愚笨。前者躺着睡一大觉,醒了就立刻跟眼前的人结婚,脑子不动一动吗?后者明明看到床上“人”的耳朵眼睛嘴巴都不对劲,居然还认不出那不是奶奶,我们小孩哪有那么蠢! 《彼得·潘》有个凄厉的结尾。彼得回来找温蒂,并不知道时间过去了二十年,“至死是少年”的他想不到时间流逝意味着什么。温蒂躲在阴影里,尴尬又难堪,因为她现在是个结了婚生了小孩的高大女人。终于发现真相,彼得恐惧地叫道:“别开灯!……”灯一亮,他们的关系就在灯光下终结了。 成年之后,我时常还想回到那些故事里,走在有人鱼的海边,跳上十二个公主的船,站在通往魔法之地的参天豆茎下。但我遇到了温蒂的问题:爱过的故事,没有跟我一起长大。跳进去,立即被拘得动弹不得。用成人的眼去看,那布景过于简陋,人物皮肤底下缺乏血液流动,更重要的是,很多情节已无法取信于人。 所以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我的一大乐趣是一次次回到老故事里,像修葺旧居一样,扩充空间,重新装饰,给花园种上新鲜的花草,把这些年我长出的血肉分给那些人偶,让他们有毛孔,有指纹,有…… 后来,它们变成了这本书里的样子。 这七篇里最早的是《辛德瑞拉之舞》,写于二〇一七年冬天。那段时间总失眠,每次在黑暗里辗转,都有一股想掀翻被子一走了之的冲动。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衾中人。但北京的冬夜实在冷,想出门,得穿秋衣绒衣毛背心,秋裤绒裤套牛仔裤……因此始终没走成。几个月后,我写了个故事,让那里的主角替我溜走。 主角有两位,一个活在当代的失眠人辛迪,一个活在解说词里的王妃辛德瑞拉。两人其实是一人。辛迪既是因一支舞开启恋爱婚姻的辛德瑞拉,也是硬要穿进不合脚鞋子的姐姐,也是带着两个女儿与离异有孩男子再婚的继母。老童话里所有女人,都在她身体里。 《普罗米修斯和鹰》写于二〇二〇年。身处封控之中,我想起被锁在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门上贴了封条,很多天里唯一能见到的陌生人,就是上门做检测的白衣工作者。没过几天,我开始盼着他来,甚至想跟他多聊几句。孤独的普罗米修斯与每天定时到访的鹰之间,是不是也有产生感情的可能性?……遂写了这一篇,探索故事里折叠起来的部分。 《人鱼之间》和《十二个变幻的母亲》写于二〇二一年。 除了《海的女儿》,《人鱼之间》里还放进另两个童话,一个“玫瑰与芸香”(《玫瑰与芸香》是王尔德一首诗的名字),另一个故事改写自《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海狮约书亚用这两个故事暗示、映射他的过去与未来。文中所提到海豚彼得爱上人类女研究员的故事真实存在,BBC曾制作一部纪录片,名为《与海豚对话的女孩》(The Girl WhoTalked to Dolphins)。 《十二个变幻的母亲》也是个“之间”的故事:母亲如何度过孩子熟睡到清晨重启之间的时光?当她短暂地从母职中卸任,会不会背对世界,跳起舞来?那几个小时她不再是妈妈,但也不再是从前的自己。 《红外婆》和《雕像》写于二〇二二年。 《雕像》的故事最早出现在脑中,是二〇一六年,拟的题目叫《阳具鉴定家》,主角是博物馆里的女研究员,她要为一箱从几十个雕像上锯下的阳具鉴定归属。当时跟编辑们说起这个故事,她们都让我不要写,“没有哪个杂志敢给你发的!” 又过了几年,我们去荷兰玩,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看到一幅画,整张画只画了一棵树。晚上回到旅店聊起来,两人都觉得那棵树好美,好迷人。拿手机翻看白天拍的图,想查一下作者,发现谁都没拍。我一向觉得拍展品有点傻,这次也忍不住懊悔。互相安慰说,回去找一张高清图,把那棵树打印了,配个框子挂起来。 然而,我们再也没找到它。 博物馆官网图,没有。花钱买了一套该馆藏品的高清电子图册,上千张图逐个看一遍,也没有。又在各旅行网站上翻别人拍的图,翻了几百个游客上传的几千张照片,还是没有。 又找到一个定居阿姆斯特丹的代购留学生,跟他买了几次郁金香冰箱贴,等他去皇家博物馆时,托他留意。他回来说,实在找不到那么一幅画。那棵画中的树,好像不曾存在过。 我决定写一个类似的“消失的雕像”的故事。雕像的名字叫伽拉,取自希腊神话里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爱上的雕像女子“伽拉泰亚”。“金”即国王。他们相遇,相失,重逢,再离散。最后他从海底回来,就像第一次见面那样,以一座残损雕像的身份。 《豆茎》是二〇二三年最后完成的。写完后有种奇异的感觉:这本书完整了。 亲爱的读者,感谢你走进这片童话与现实之间的林地,走进作者尽心莳育的花园。你一定看得出,这些故事里写了作者的很多不相信。 我不信在一支舞的时间里舞步和谐,就意味着后半生婚姻美满,“一直幸福生活下去”。我不信高居于豆茎顶端的富足世界里,那金子是靠魔法母鸡生下来的。我也不信善良天真、会跟动物说话,就能在矮人之家快乐地过活,最后等来完美的王子。 但还有一些东西,是第一次被童话的光照亮心灵时,我就始终坚信的。如今我仍然相信。我相信爱同属于天神、凡人与万物,能让石头化为血肉生灵。我也相信勇气、坚强、信心,相信要攥紧双拳去战斗,为自己和亲爱的人。 每个故事是一朵心血染成的花。谢谢你把它别在襟上,与作者共度这舞会之夜。 天翼谨白 2024年3月于北京 柳眼才青,花结未解 春是讲了一千遍的童话 永远古老,永远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