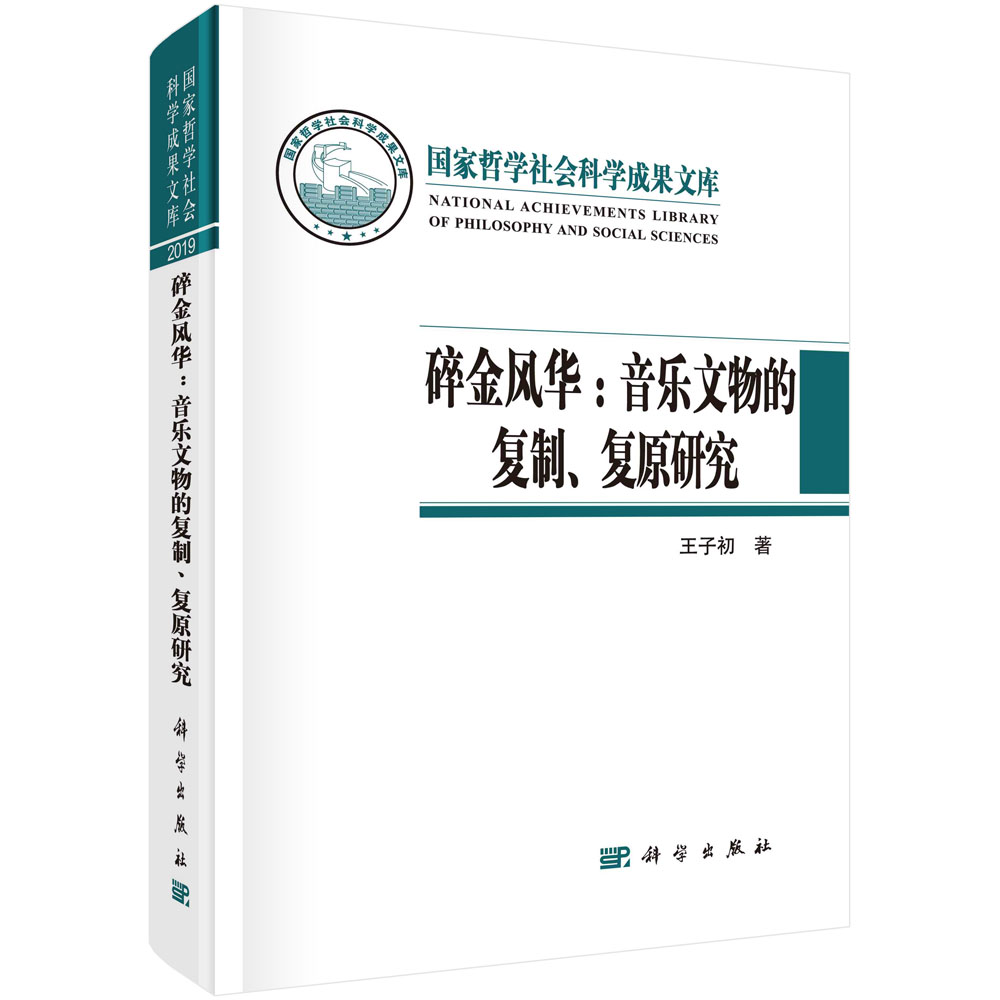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398.00
折扣价: 314.50
折扣购买: 碎金风华--音乐文物的复制复原研究
ISBN: 9787030681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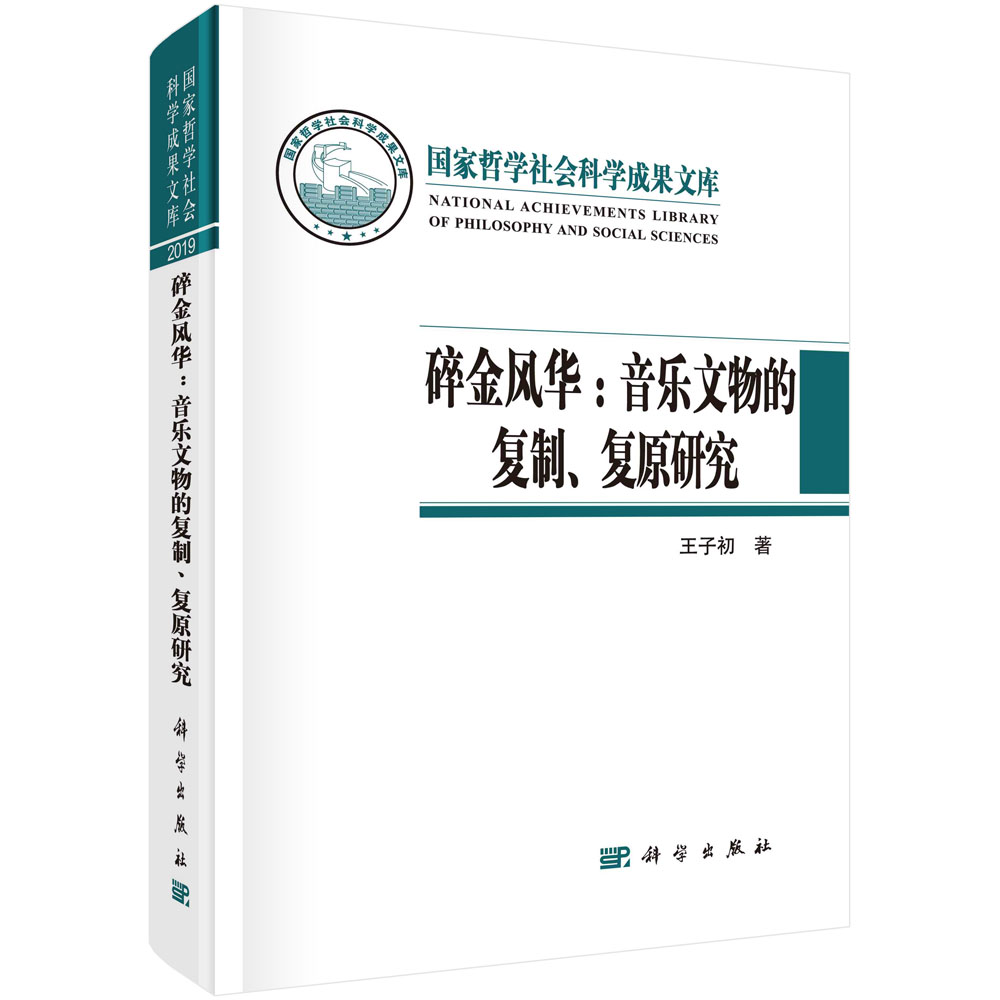
绪论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故《辞海》在对“考古学”进行定义时,增加了“广义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义。以此可以确定,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定义应该是根据古代人类音乐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一门科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考古发现的音乐文物,正是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们历经岁月沧桑,锈迹斑斑,却如碎金,虽残缺却不改其珍贵!
古代中国长期盛行重葬之风,所以地下埋藏的大量宝物留存至今。随着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至,稀世珍宝屡见不鲜,其中的音乐文物也是琳玻满目。就目前所见,中国考古发现的音乐文物,主要包含乐器类实物(包括乐器的零配件和舞具等)与音乐图像类文物。乐器类实物与古代人的音乐活动的联系较为直接,其所反映的往往与音乐本体相关的微观信息较多;音乐图像类文物的成分较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岩画、墓葬壁画、洞窟壁画、汉画像(石、砖)、乐舞俑、艺术绘画、建筑雕刻、器皿装饰(包括编织图案)、音乐书谱(包括铭文)等9种。它们以写实或写意的方式较为间接地表现了古人的音乐艺术概况,侧重于社会音乐生活场景的描摹,其在古代社会音乐生活方面反映出的宏观信息量往往要大于乐器类文物。至于音乐书谱和铭文,则是人类为了表达特定的音乐概念创造出来的特殊符号,如文字、谱字等,它们间接地记录了古人音乐生活的内容。
研究音乐文物的复制和复原,对数千年来出现的大量音乐文物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势在必行,通过掌握其数量、形式、种类、保存现状和分布等,可以全面展开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图像类音乐文物的分类学研究,评判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这是本书首先要做的一项基本工作。
本书要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对当前高等院校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教材中关于音乐文物史学意义的认识和史料的应用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特别是对杨荫浏、李纯一等史学大家的学术成果,应加倍关注;在对前人学术成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方可进一步探讨那些音乐文物的史学意义,并考虑相关文物如何作为一种新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艺术是人类发挥想象表现思想和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音乐艺术是其中的重要门关。音乐是音响的艺术,其以声波为传播媒介;表演停止,声波即刻停息,音乐也不复存在。音乐又是时间的艺术,音乐作品存在于表演的瞬间。从本质上说,音乐文物不能表现音乐本身。音乐学家既难以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某种特定的声波为研究对象,也无法将早己逝去的历史上的音响作为直接研究对象,但音乐文物作为古代社会音乐生活的物质遗存,却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留存至今。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各个时代社会音乐生活的历史信息,并由此成为今人认识古代社会音乐的直接信息源。通过它们对音乐的历史和理论进行探索,是我们认识古代文化生活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研究渠道。故音乐文物具有一种历史实证的史学意义,不同于传统作为治史史料来源的历代文献,更不同于现代民族民俗学研究获得的人文信息对古代音乐的推论;其对于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意义,是其他材料不可替代的。
本书中所记录的大量音乐文物的复制与复原案例,既是音乐考古学涉及的应用性项目,实质上也是当今考古学界方兴未艾的“实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对于音乐史学的意义,并非仅是提供了一些音乐史料而已,而是以音乐文物的复制、复原为研究手段,开展以探宄文物所代表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音乐生活面貌为直接目标的一种另辟蹊径的微观研究。由之,我们可以以小见大,深入考察历史的真实面貌,总结音乐艺术发展的规律。故本项研究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学术意义,同样是其他学科、其他方法所不能取代的。
本书为笔者数十年间对出土音乐文物的复制和复原经历及实验音乐考古所做研究之大成。
珍贵音乐文物的出土,无疑是研究、认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故常成为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象征、地方文化的骄傲而被当地各级文博机构看作不可或缺的常设展品;珍贵文物往往都是孤品,却又有着引人注目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罕见的音乐文物,也是国家和民族音乐历史研究的重要物证,各个专业机构及文博馆所因教学、科研和艺术实践所及,也常有因展陈而复制文物的需要。诸如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刘非墓中,出土了罕见的大型仿玉玻璃制品——22件编磬(图0-1)。这不仅是中国乐器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西汉标本,因其形制之大、数量之多,也是中国自然科学史、玻璃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物证!不单是南京博物院,江苏辖地的淮阴区博物馆、盱眙县及墓葬遗址博物馆,乃至如中国陶瓷博物馆等相关的博物馆,都想得到收藏、展陈这套编磬的机会。当然出土的原件仅此一套,作为发掘者的南京博物院不可能放弃出土原件的收藏权,严格和精确地复制出土文物,就成为满足多地展陈需求的重要途径。
同样,如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原件已由湖北省博物馆馆藏,作为当地历史文化的象征和骄傲,其出土地随州无论如何也要复制一套,陈列于当地博物馆,这对当地的文化考察、社会教育、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均是显著的。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音乐艺术院校因教学、科研的需要正拟建或在建音乐博物馆、乐器陈列馆等设施,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是其不可或缺的展品。如大量调集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原件来展览,显然不大现实。由此而来的面广量大的音乐文物的复制或复原就势在必行。当然,这里所说的“文物复制”,与文物贩子为牟取暴利制作可以乱真的假文物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现实中音乐文物复制需要的不同,常见到“仿制”“复制”“复原”等不同的概念。
“复制”与“仿制”二者联系较为密切。一般认为,所谓的“复制”,应严格以出土文物的原件为蓝本,即复制件的形制、大小、色泽乃至材质,尽可能做到与原件保持一致,甚至做到做旧如旧、有残不修,与原件放在一起难辨真假,这应该是“复制”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至于“仿制”,则没有如此严格,要求相对宽松一些。一般来说,只要能够体现文物原件的主要特征,让人能由之联想到文物原件者,均可以算是“仿制”。所以,放大或缩小,甚至改变色泽与材质等,在文物仿制中均屡见不鲜。当然,仿制也有“高仿”一说,即要求仿制件与被仿原件之间的相似程度较高。由此而论,仿制件与被仿原件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仿制”也就越接近于“复制”。反之,“复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相似程度较高的“仿制”。故人们常将“仿制”“复制”相提并论,甚至合称为“复仿制”。
对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刘非墓中出土的钟磬乐悬的模仿制作,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范畴,主要体现在出土的青铜铸件上(图0-2),如编钟的钟体、钟磬龔篇的青铜透雕架饰及兽形簾座等。这些有形有体、保存相对完整的器件,虽已残破,但可以通过修复对出土原件直接进行翻模,利用现代发达的金属精密铸造工艺,仿旧如旧、做旧如旧,制成可以乱真的复制件。
一些古代的工艺,如青铜透雕架饰上的鎏金这种含有剧毒、具有重污染性的工艺,今天已难以实施。又如编钟表面的氧化层,即体现编钟外观色泽的所谓的“包浆”,由经2000余年复杂的化学物理变化所致,若再加上其他细微之处,要做到完全一致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通过一些其他的替代工艺和方法,让编钟的外观效果做到基本相近,还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复制”的内涵。
总之,复制是立足于把今天所见到的文物面貌模仿出来,不仅要做旧如旧,甚至还要“见残仿残”。无论是仿制还是复制,其模仿的都是文物的现时状态;对于出土文物来说,也就是模仿它从地下挖出来时或之后人们所能见到的状态。如果说这件古乐器的产生时代是距今2000余年的西汉,那么仿制、复制所要模仿的显然不是其2000余年前的面貌。
一般被复仿制的出土对象,基本上都是在地下保存相对完好,或者虽然破碎,但还可以修复完整的文物;而经不住地下漫长岁月的侵蚀,已经残腐不堪的文物,特别是一些难以成形的竹木类文物,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成为复仿制的对象的。这就涉及另一个概念——复原。
复原,也是一种对出土古代文物的模仿制作,不同于仿制、复制。前述的复仿制,其模仿的是模仿对象的现时状态。复原,则是要求恢复出土文物在其被岁月侵蚀之前的面貌。如在盱眙刘非墓钟磬乐悬的复制工作中,有些内容应属于“复原”的范畴。刘非墓中出土青铜编钟,完全可以进行翻模复仿制,而同墓出土的“玉”编磐,则有所不同。“玉”编磬实为中国2000余年前的一种琉璃制品,其材质亦即中国独有的高铅钡古玻璃。出土时“玉”编磬破碎较为严重,并在磬体表面伴有程度较深的腐蚀风化的痕迹,少数磬块因有所缺失已难以完整拼复。因此,对盱眙刘非墓编磬的模仿制作,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案。一是完全仿照编磬出土以后的外观形象,包括其残损缺失、腐蚀风化等,较为细致地进行模仿制作。这应该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这样制成的复制件,可以作为博物馆中用于展陈的出土原件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