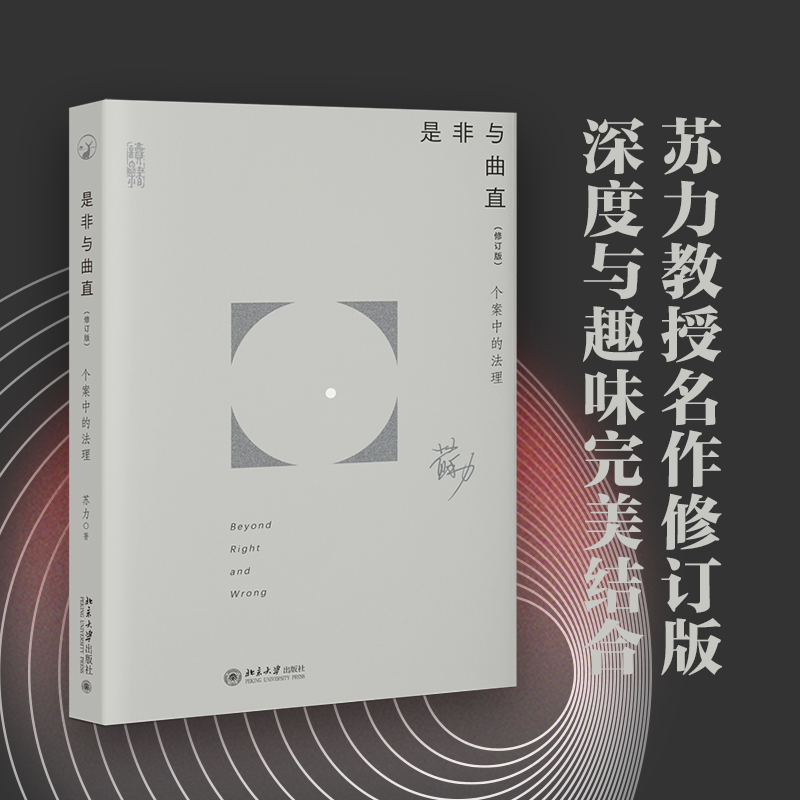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76.00
折扣价: 51.70
折扣购买: 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法理(修订版)
ISBN: 9787301339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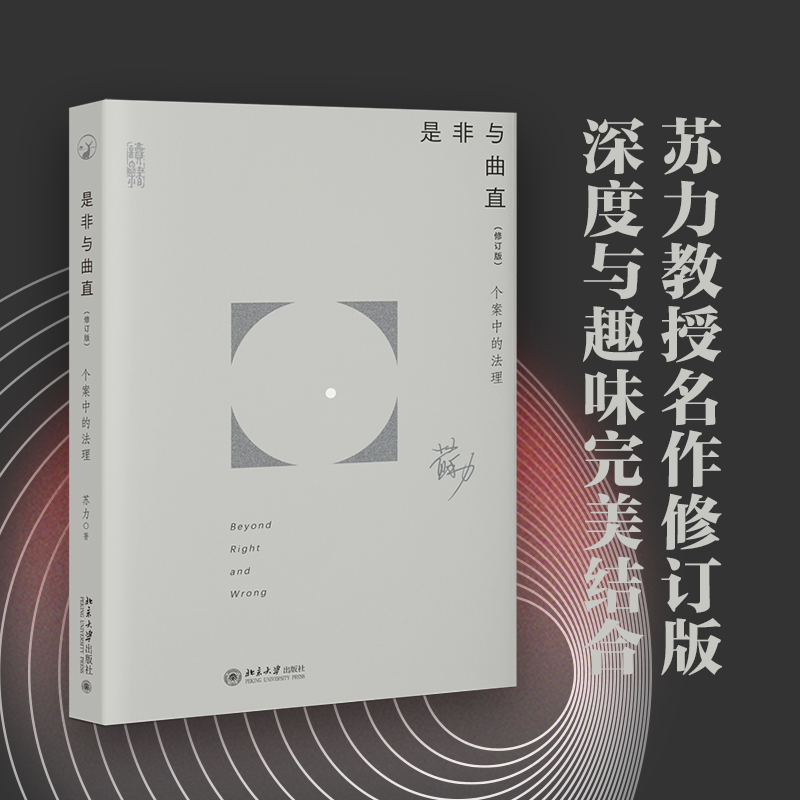
苏力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 祖籍江苏,1955年愚人节出生于安徽合肥。 少年(1970年)从军,再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员军人进了北大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1992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至今。 独立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个人独著、文集以及译著多种。包括北大社出版的:《并非自杀契约》《波斯纳法官反思录》《波斯纳及其他》《大国宪制》《法官如何思考》《法制及其本土资源》《批评与自恋》《是非与曲直》《送法下乡》《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走不出的风景》等。
3 何为“紧急情况”? 很多质疑者认为医方不强行手术是担心引发医疗事故,怕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指出,医方可以诉诸《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1款强行救治。这一款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言外之意,李的情况理所当然属于紧急情况,医方担心医疗事故是多余的。 其实,若仅仅就减轻医方的担心而言,医方完全可以诉诸该条第5款,“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不属于医疗事故。但问题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未细致界定何谓“紧急情况”。即使当时已经构成了紧急情况,不顾患方“签拒”的强行治疗是否属于法律许可的“紧急救治措施”? 许多法律都有紧急情况的规定,尽管中文的具体表达不同。它在外文中是一个词(英语emergency;法语urgence; 德语Notstand)。它大致指向这样一种抽象状态,即必须采取与相应法律之常规相当不同的应对措施,以较小损失防止正在或即刻发生的对国家、公共利益和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的更大伤害。由于各法律指涉的具体事态非常不同,各法律间的紧急情况不能相互搬用或套用。 但有一点很明确,也很关键,“紧急情况”并非一个不要法律可以恣意妄为的状态,不是一张随便填写数额事后都能获得批准的“空白支票”。允许背离常规的法律要求,它却仍然是一种由法律界定的状态;它不仅不允许毫无限制地中止或剥夺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不允许诉诸这一条款的人把法律拿在自己手中任意解释。在各部门法中,除了事先界定外,往往会通过具体法律实践逐渐明确“紧急情况”的边界;当受到挑战时,还可能得接受司法的审查。司法的判断标准也不是某个抽象定义,无论是否是法学界的通说,而总是要具体考虑紧急措施造成损失之大小,所保护收益之大小,危机的实在性和急迫程度,有无可替代性应急措施及其成本如何等因素。在经验层面,特别当涉及专业问题时,司法往往会尊重专业或职业标准,有时甚至会尊重当地的职业标准。 因此,争点不在于李的病情是否需要紧急救治——医方已开始急救;也不在于医方对紧急情况下的救治引发的不良后果是否要承担医疗事故责任。争点在于,紧急情况下是否还必须遵守某些法律,是否还要接受某些法定制约?是否因紧急情况,手术就无须执行患方同意签字的法律规定,甚或可以直接对抗患方明确表示的反对意愿?或医方可以——在字面的中性含义上——“为所欲为”?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手术治疗中患方的知情同意权,如前所述,不仅为法律明文规定,是强制性规定;而且是各国医疗职业长期遵循的核心伦理和惯例之一。因为(下一节详细论证)即使在紧急情况下,这仍然是对患方权利最有效的制度性保护措施。 但允许例外。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医疗实践来看,确有无须获得患方知情同意就手术治疗的紧急情况。查阅英美等国的法律和判例之后,概括起来,仅限于以下几种情况: (1) 患者需急救但不省人事,且无法及时获得有权同意者(亲属、监护人或其他有法定授权的人)的同意签字; (2) 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年龄可低于选举年龄,一般还会考虑患者对医方建议的治疗手术有多少理解),需急救但因其酗酒或吸毒或其他原因没有医学上的行为能力,且无法及时获得有权同意者的同意签字; (3) 年幼患者且需急救,却无法获得其父母的同意(包括因其拒绝)或其他有权同意者的签字;以及 (4) 患者有生命危险,患者和/或有权同意者均拒绝同意签字,但患者的存活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其死亡极有可能危及至少一位无辜第三人的生命和安全。 这一条看起来颇为奇怪,违反了个人自由原则。其实这类情况也不少:(1) 如烈性传染病患者,他若拒绝治疗可能引发疾病流行;(2) 如受了致命伤的恐怖分子有可能拒绝治疗,想以死来保守恐怖组织的秘密;以及,(3) 临盆孕妇基于宗教信仰拒绝输血,可能危及胎儿生命。由此可见,个人自由仅限于不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至少同样重要值得保护的自由。 李某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李当时清醒、有行为能力,她可以明确同意治疗并要求肖某签字或自己签字,但她授权肖处理;肖在场,有能力签字,相关法律还规定手术必须有他的同意签字,但肖令常人不解地(其实有解,第四节分析)签字拒绝了手术。也许这也是一种“紧急情况”?许多人认为是,认为应当是;我不反对。但这没用。因为这不是法律规定和医疗实践确认的紧急情况。问题因此成了,是否应当将此视为一种新的紧急情况? 涉及应然,涉及制度安排,涉及立法,涉及公共政策,因此留待下一节讨论。但这里仍有一个实证法必须关注的问题,即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解读法律概念,不会有任何实在的法律后果,反而在心理上会有良好的自我感受,觉得自己很高尚,很道德,甚至很勇敢。但医方当时必须直面的却是,它能否认定肖的签拒就是法律规定的紧急情况,或至少它确信包括法官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会接受它的认定?我们在此讨论的都是“事后诸葛亮”——李已死亡。这一死亡就让这个问题变了,我们是事后考虑,是否应当对紧急情况扩大解释。这个应当就表明它曾经不是或我们没法确定地认为这就是紧急情况。这个事先事后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转变,对人的行为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我认为,从相关法律看,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中,医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从合乎情理的常人标准和医疗职业规范来看,都无可挑剔。如果医院不是在20分钟内就做好了手术准备;如果不是一直劝说肖;如果肖不是签了字拒绝,而只是拒不签字;如果卫生局批准了医院的请示;只要最后是现在这个结果,医方都会受到更多更严厉的谴责和指控。 (31-34页,注释省略) 1.作者对具体事物的观点是扎根在一个很深厚的思想传统里的。 2.作者非常强调,法律应该是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广大普通人的日常实践的,这样才是有价值的。在个案分析中也秉持这样的价值观。作者会思考每个具有普通常识和通情达理的中国人,对这些法律的实践怎么想,怎么看的。 3.这本书虽然是从个案入手,但实际上关于如何认识法律、运用法律,体现了整个法学研究的一个理论流派的发展。 4.本书的分析具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思辨的力量和持续的学术魅力,不是局限在法律的领域。 5.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字魅力和诗性敏感,阅读体验非常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