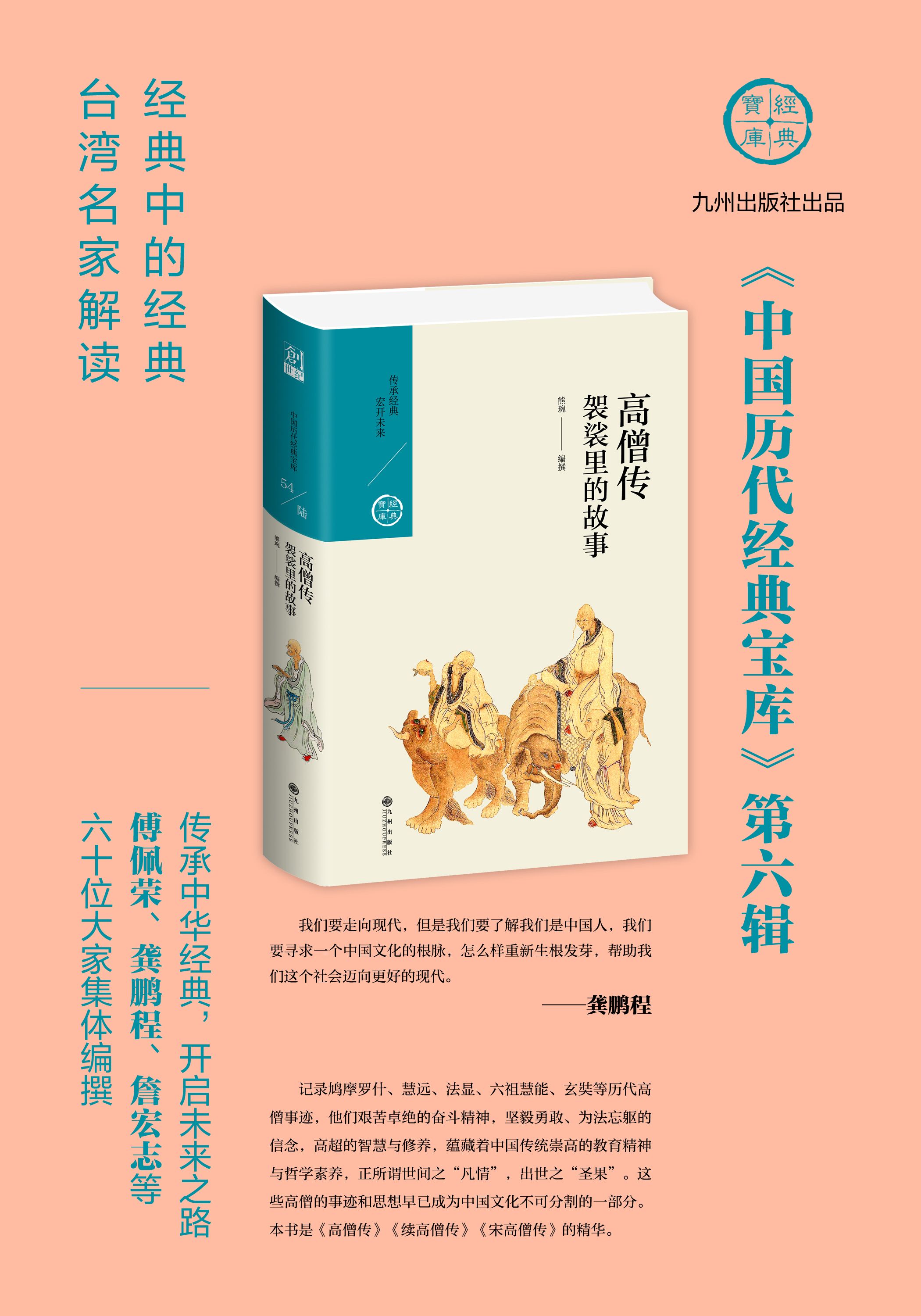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高僧传:袈裟里的故事/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第六辑
ISBN: 9787510878909

熊琬:1947年生,台湾大学学士、辅仁大学硕士,政治大学博士。现任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作有《宋代理学与佛学之探讨》《管子研究》《高僧传:袈裟里的故事》等。
摩腾法兰,白马驮经 摩腾二人不辞长途的疲困劳苦,冒着风霜雨露,跋涉流沙。一路上,他们以白马负驮佛经,历经了千山万水终于在明帝永平十年抵达中国。他们先住在洛阳城内,明帝对这两位远自西域来的尊者不辞艰险、以法自任的精神非常钦敬,特颁圣旨给他们以最优厚的招待,并且特别为他们在洛阳城西门外,建立一所精舍(就是佛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学舍)以安顿之,这是中国最早有出家修行人的开始。腾师住处,就是现在洛阳城西门外的鸿胪寺,后来改名为“白马寺”。这也就是我国最早有僧寺的开始。本来“寺”是官府的意思,鸿胪寺是招待与迎送外宾时的官府, 约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自从改为白马寺,住了出家僧侣,“寺”便成为出家人僧舍的专称,乃是佛、法、僧三宝的象征。“寺” 字既成专有名词以后,就一直沿用到现在。至于“白马”一词, 也有由来。传说,从前外国有个国王,曾经破坏许多佛寺,最后只剩招提寺尚未被波及。某天晚上,忽然有一匹白色的骏马围绕着寺塔发出悲鸣,似乎在为众生请命。国王闻知大受感动,即刻下令停止破坏佛寺,并改“招提寺”为“白马寺”。从此,许多佛寺都喜欢以“白马”命名。 同时,蔡愔自西域所携回来的佛像,也分别供置于南宫的清凉台及显节寿陵上。这些旧像虽然今天已不复存在了,但这是我国有佛像的开始。 生公说法,顽石点头 生公钻研佛法日久,已能彻悟言外之旨,乃喟然叹息道:“言辞文字只是一种工具,本不过是用以表达佛理的,佛理若真通达了,便不会死在文字下。自佛典东入中国,由于辗转地翻译,人多拘泥经文,不知变通,所以就不能圆融佛理。果能得鱼忘筌(只要得到了鱼──文义,就不必拘执捕鱼的筌──文句),才能深契佛理。如此才可语于道了!”于是校阅真俗书籍,研思因果关系。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的理论。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等,都能廓清旧说,妙发渊旨,因而引起拘守文义之徒的嫉妒。 初《涅槃经后品》未至,生公熟读久之,剖析道理,深入隐微,乃说“一阐提”人(断善根极难成佛的人)皆得成佛。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谓闻所未闻,全系创见。旧学之徒,都以为有违佛法原旨,必是邪说惑众,在戒律上应当加以摒弃。生公乃在大众前正容宣誓道:“如我所说,不合经义,愿此身得恶报。如果实契佛心,愿在舍寿时,高据狮子宝座。”说完,便径自离去。生公后游吴之虎丘山,不数日即有学徒数十人向师求法。 传说,道生尝竖立石头为听众开讲《涅槃经》,讲到“阐提也有佛性”处,就问众石头说:“如我所说,契佛心否?”群石皆为之点头首肯。意味其能阐发经中幽微之义理,妙合佛心,赖此至诚,感动顽石。这就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后来昙无谶译《涅槃经》后品,果然称“阐提悉有佛性”,与生公从前所说正若合符契。生公慰喜不能自胜。生公既获新经,不久即讲说《涅槃经》。 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生公在庐山精舍说法,升狮子座,神色开朗,德音俊发,反复论议,穷理尽妙,观听之众,莫不怡悦叹未曾有。传说,生正在法席将毕之时,忽见麈尾(魏晋清谈者喜执麈尾为拂尘以助言谈,后讲法指授之时亦习用之)纷纷坠下。听法大众骇然,趋前探视,只见生公端坐正容,凭几而卒, 颜色如生,好似入定一般。正应前言舍寿时,据狮子座之预言。于是四众道俗无不惊骇叹服,远近徒众皆相悲泣。至此,京师诸僧方觉愧疚,追念生公前语,无不信服其阐提佛性之卓见。后其徒众将师礼葬于庐山之阜。 卜居庐山,结白莲社 慧远祖师自卜居庐山,结白莲社,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专志净土,澄心观想,三次见到圣相,而沉厚不言。传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七月晦夕,于般若台之东龛,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日光之中,有诸化佛,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左右侍立。佛告远祖说:“汝七天后,当生我国。”又见莲社中先往生者如慧永、刘遗民等,皆在佛侧,向前作揖说:“大师早先发心,何来之晚?”远祖道:“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圣相。今天又得再见圣相,吾将必生净土。”到八月六日端坐入寂,年八十三。门徒号恸,如丧考妣,道俗奔赴,接踵而来。远祖以娑婆情重,恐难割舍,故早制定七日展哀之期,遗命使露骸于松下, 既而弟子收葬。浔阳太守阮侃于山之西岭凿圹开冢。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南阳宗炳又立碑于寺门。 远祖一生,善作文章,辞气清畅文雅,每登讲席,谈吐精简而扼要。再加以容仪端整,风采洒落。门人画其像于寺中,借供远近瞻仰。所著论序铭赞诗书收集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远师以僧节令人钦仰,其风范可谓善继道安。 净土宗历代祖师:晋初祖庐山慧远大师──莲社第一位创始人;唐二祖长安善导大师──疏论净土三论;唐三祖南岳承远大师──曾居衡山设教,从化者以万计;唐四祖五台法照大师── 在五台山建竹林寺,代宗尊为国师;唐五祖新定少康大师──在睦州开念佛道场,在新定散钱于市,使小儿辈随之念佛;宋六祖杭州延寿大师──即智觉禅师,本是法眼宗第三代祖,日课佛号数万,作四料简,提倡禅净双修,著有《宗镜录》百卷;宋七祖杭州省常大师──住杭州南昭寺,结社领众念佛,度化缁素颇众;明八祖杭州袾宏──号莲池,因居云栖寺,故亦名云栖大师,融合禅净二宗,以禅理疏成《弥陀疏钞》,一生著作悉收在《云栖法汇》中;清九祖灵峰智旭──字蕅益,自号八不道人,融会性相,扶持戒律,倡修净土,著有《蕅益大师全集》;清十祖虞山行策大师──字截流,虞山普仁院,倡兴莲社,学者翕然宗之; 清十一祖杭州实贤──号省庵,因参念佛是谁得悟,后专修净业, 著有《劝发菩提心文》;清十二祖红螺际醒──字彻悟,号梦东,亦由禅入净,著有《彻悟禅师语录》,阐净土法门;清十三祖苏州圣量──字印光,深通经藏,力倡念佛为不二法门,著有《印光大师全集》。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某日,达摩大师突然向门人宣布说:“我即将西返天竺,你们何不各言所得,以见悟道的境界呢?”当时就有门人道副答道: “文字在阐明佛法真谛,不可执着文字,也不可舍离文字,始能得道之受用。”达摩祖师说:“你只得到我的皮毛而已!”门人尼总持答道:“就我所知的道,正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佛说东方另一 佛之国土),一见之后,便了悟实相,豁然开朗,更不需再见了。”达摩说:“你只得到我的肉而已。”门人道育说道:“四大本空,故称人体为四大假合。五阴非有,而我所见之处无一法可得。” 达摩说:“你也只不过得到我的骨而已!”最后轮到慧可,只见慧 可起身礼拜祖师后,始终立于原位,不发一言。祖师会意,就说: “汝乃真得我‘神髓’。从前如来(佛十号之一,因佛乘真如之道, 而成正觉,来三界垂化,故名如来)以正法眼藏(朗照一切事物谓之‘眼’,包含万德谓之‘藏’,唯佛陀正法具此眼藏)交付迦 叶大士(运心广大能建佛事,故称大士,多为佛菩萨之称号),如是辗转相传而至于我,今又付托给你,并且也把我的袈裟(僧衣)一件作为传法的征信。”接着又说:“内在传授诸佛法印,以确实证明心地的法门;外则传授法衣,以明示建立禅宗的宗旨。这是因为后代的人们,心地渐狭,多疑多虑。或因我是异国僧人, 如何能传法予中国之人?口说无凭,多疑兴谤,易滋纷争,届时只要出示此衣与传法偈语,以资证明。对于将来的教化,便无多大妨碍了。在我逝后两百年,此法衣就停止不传了。那时,禅宗的法门,周遍各地。不过明道的人虽多,但真正行道的人很少。而隐身在千万人中,潜修密行,由此而得证道果的人也会有的。切记!你应当努力护持并发扬此道,万不可轻视未开悟的人,任何人只要一念之间,回转其向外驰求的放逸心,便同已得证道果的境界。现在听我说法偈如下: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曲女盛会,威震五印 正当奘师准备回国的时候,东印度鸠摩罗王遣使奉书与戒贤法师,说想见支那国大德。奘师本不欲往,但经鸠摩罗王坚请之下,只好辞别戒师等,随使前往彼国。鸠摩罗王亲率群臣迎拜, 延请入宫,每日奏音乐、奉饮食,并有香花等上好的供养,如是经过一个多月。戒日王闻说奘师竟往彼处,心中不免大怒,谓我先前一再恭请不来,现在何以却先赴彼处呢?于是威胁鸠摩罗王即刻遣送师来。鸠王因惧怕戒日王的势力,不敢不从,就暂将奘师送往戒日王处。其时正值夜晚一更许,戒日王慕师已久,不顾深夜,前往迎师。只见河中有数千火炬并一步一鼓,火光映彻, 声势浩大,煞是好看。既至,王顶礼师足,散花瞻仰赞礼毕,心头感到无限欢喜,因值夜深,与奘师亲切晤谈一会儿,王即告辞, 临行告以明晨即来迎师。 次日,奘师与鸠王同往戒日王宫,王与门师二十余人出迎入坐,盛设各种珍膳(珍异的食物),并奏音乐,散鲜花,以为供养。戒日王对师说:“听说法师曾作《破恶见论》,愿能拜读。”奘师即呈递与王。王取观后,非常欣悦地说:“弟子闻日光既出,则荧光烛火之明俱皆被夺;天雷之声震动,则铁锤斧凿即便绝响。” 王便回首对门师说:“师等上座提婆羼那自己称说他的理解力冠于群伦,学问则兼该众哲,并且时常毁谤大乘。可是一听说有远奘师)来,就即刻避往吠舍,托名瞻观圣迹,借以逃避, 所以我知道你们(指门师)并没多大本事。”戒日王非常赞叹奘师的《破恶见论》,就对奘师说:“法师的大作价值非常,弟子与此间诸师,无不深生信服。但恐其他各国小乘外道,仍然笃守固陋,执迷不悟。故希望在曲女城为师作一公开的辩论会。遍请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都来集会,借此开示大乘微妙法门,杜绝他们毁谤之心,亦可因此显示出法师盛德之高,摧伏彼等我慢之心。” 戒日王于是日发出通告,邀约诸方大德与会,便与奘师出发赴会,先期到曲女城。这次集会可谓盛况空前。赴会的人员,在五印度中有十八国王到会,精通大小乘的僧人有三千参加,婆罗门及其他外道有二千人与会。那烂陀寺亦有千余僧人到场。这些高贤都是极一时之选,他们无不博通经论,具足辩才,并想前来聆闻法音,所以皆来聚会。而且有的随身带来侍从,或驾象,或乘舆,或悬幢,或挂幡,各自围绕簇拥而来,好像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浩浩荡荡,盛况空前。 戒日王先行整饬装潢会所,营造二座临时宫殿,拟安置佛像及徒众。殿堂广峻,各可容坐千余人。戒日王行宫则建在距会场西边五里之处。是日,将金铸佛像一尊,安装在一头大象上,上悬宝帐。戒日王本人作帝释形,手执白拂随侍佛之右侧;鸠摩罗王作梵王形,手执宝盖随侍佛之左侧;二人都身着天冠华鬘,垂挂璎珞佩玉,又以两头大象装戴宝华,追随佛后,随行随散。并请奘师及门师等各乘大象,依次排列二王之后。另外再以三百头大象,由诸国王、大臣、大德等乘坐。如是前后罗列,前拥后遮,从清晨自行宫出发,一路向会所行去。来到会场门口,戒日王命大众下乘,首先捧佛像入殿,置于宝座上。然后命十八位国王入座,再请诸国高僧、博通经论者千余人入座。次请婆罗门外道有名行者五百人入座。又请诸国大臣二百余人入座。此外道俗都在院门外安置。俟内外坐定,王使人施食供养毕,特别设置宝座,请奘师登座为此会论主。奘师称扬大乘,说明作论之意,并请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法师宣读全论内容,令大众闻知。并另行抄写一份(本),悬示会场门外,普令大众无不俱知。并宣告于众:其中若有一字无理,但凭指摘;若能难倒,或摧破其立论,就请立斩己首以相谢。如是自晨至晚,竟无人能发一言。戒日王欢喜赞叹,于是罢会还宫,诸王及诸僧退席,还归止息之所。第二天,又再聚会,迎像送引如前。这样经过五日,小乘外道见毁其宗派,心中结恨,阴图谋害。戒日王得悉后,立即宣示道:“邪道乱真,其来已久,埋隐正教,误惑众生,不有上贤,何以鉴伪?支那法师,显扬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惭悔,反起害心, 谋为不轨。此而可容,孰不可恕。如有任何人伤触法师者,立斩其首;毁谤辱骂者,截其舌。但为申辩义理,攻难驳正者不在此限。”自是邪妄之徒销声匿迹。如是经十八日,仍无一人发论。 将散会的前夕,奘师更称扬大乘,赞叹佛之无量功德,令无数人当下返邪入正,弃小归大。戒日王益发增其崇重之心,供养奘师金钱一万、银钱三万等,十八国王亦各施珍宝。奘师却一切不受。戒日王又命侍臣庄严一头大象,施一宝幢,请师乘坐;并 有贵臣陪侍巡众,同时一面唱言于众,表示大义得立无人可屈, 这是印度礼俗凡立论得胜的表示。奘师谦让不行,戒日王说:“自古印度习俗如此,事不可违。”于是就将法师袈裟遍倡于众,说: “中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经十八日,无人敢加以论难, 宜让大众个个悉知。”大众欢喜,竞相为法师立义名,大乘众叫作“摩诃耶那提婆”,译为“大乘天”;小乘众立名“木叉提婆”,译为“解脱天”。大众乃烧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奘师的盛德美名,就愈益高扬了。 了凡入圣,自求多福 袁了凡先生,名黄,江苏吴江人。自幼好读书,通古今之务, 学问无所不通。举凡象数、律吕(古正乐律之器)、水利、兵政、堪舆、星命之学,均能精密研求,富有心得。著有《历法新书》《皇都水利》《评注八代文宗》《手批纲鉴》等书行世。 传说先生于童子时,有孔先生为之卜终身吉凶休咎,其后他的一生科考名数先后,皆一一不出孔先生所悬定(预先卜度)者。了凡由此深信凡人之一生,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淡然而无所求。于是,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中,二人对坐一室,经过三昼夜不思不虑,也不瞑目。 云谷禅师感到非常诧异地问道:“凡人之所以不得超凡入圣只为妄念相缠所致,你现在静默坐此三日,并不见起一妄念,是何缘故呢?”了凡就老老实实地说:“因为我一生的数命,已为孔先生所算定。故知每人的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即使想要妄想, 亦无可妄想。”云谷师笑着说:“我只以为你是个豪杰,原来还不过是一个凡夫。” 了凡就请师慈悲开示,云师说道:“凡称之为人的,不能无心,有心即为阴阳数命所缚,丝毫无法改变。但是唯有凡人才有数命可言,极善的人,气数固拘束他不得;极恶的人,气数也拘束他不得。你在这二十年来,被别人算定,不曾转动分毫,岂不是十足的凡夫吗?” 了凡问道:“难道定数可逃吗?”师说:“命本是由我作主的,福也是由自己求致的。诗书所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确实为古圣昔贤的明训呀!佛法教典中所说,欲求富贵得富贵,欲求男女得男女,欲求长寿得长寿。夫妄语者,本是佛教之大戒,诸佛菩萨又岂会随意造些诳语欺人呢?” 了凡大感怀疑地说:“孟子所言‘求则得之’,是求固在我也。然而,道德仁义,固可信其可以力求;至于功名富贵,又如何可信其可以力求呢?”师说:“孟子的话本自不错,你自错解了。你不见六祖慧能在《坛经》中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指心),从心而宽,感无不通。’若果能求其在我,则不独可得道德仁义, 亦可得功名富贵。如此内外双得,是知求固有益于得也。如果不知反躬内省,而徒然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了。如此是内外双失,所以无益矣!如今应平心自检,将过去过恶一一寻出,一一加以改刷。悭贪者,转之以施舍;愤激者,转之以和平;虚夸者,转之以切实;浮嚣者,转之以沉定;骄慢者,转之以谦恭;惰逸者,转之以勤奋;残忍者,转之以仁慈;怯退者, 转之以勇进。务要积功德、累德行,以基厚福。勿以才智盖人, 勿轻言妄谈,忌纵情任性,忌褊急量狭。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包含荒秽,比喻度量宽大),务要和爱,务要爱惜精神。总需针对自己病症,一一发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一一积习,悉皆扫除;一一病根,悉皆拔去。时时处处,常自警觉,严自克治,保管天真,如保赤子。改造命运,全权在己,不属造化。果能如此,始为义理再生之身也。要知彼血肉之身,尚然有定数,此义理之身,岂不能感格于天呢?《诗》云:‘永言(恒言)配命(上合天心),自求多福。’这是千古不磨的金言。譬如孔先生算定你不登科第,不生儿子,这是所谓‘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现在你当尽力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这是自己所作之福,怎会不受享呢?《易经》为中国第一部高深的哲理书,其中论及君子处世当如何趋吉避凶。若说天命有常,然则吉何能趋,凶何可避呢?可见吉凶本无常,要当视人是否知趋避之道了!又须知:为善而心不着善(并作善之念, 获福之念而无之,曰不着),则随所成就,皆是无量,皆得圆满。否则,心中若着于善,则虽终身勤励,只不过是半善而已!譬如以财来救济他人,必当内不见有己,外不见有人,中亦不见有施之物,是谓‘三轮体空’。佛家所谓‘无相布施’,就是指此而言,否则,不足以称为菩萨了。” 了凡听闻云谷禅师这番立命之说,深信其言,心中感激,拜而受教。从此精勤奉行,终生不渝。并即改号(初号学海)叫“了凡”,盖取了脱凡情、优入圣域的意思。其后,追记其事因作《了凡四训》以垂训子孙,昭示后人。 1.历代高僧事迹,按时间次第,又依佛教八宗分门别类,一部佛学的起源和发展史。 2.历代佛家弟子的修行必读书,佛学爱好者的入门读物。 3.阅读高僧传记,学习做人做事做学问,享受悟道人生。 4.弘一大师说:比如我们想做一位清净的高僧吧,就拿《高僧传》来读,看他们怎样行,我也怎样行,所谓“彼既丈夫我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