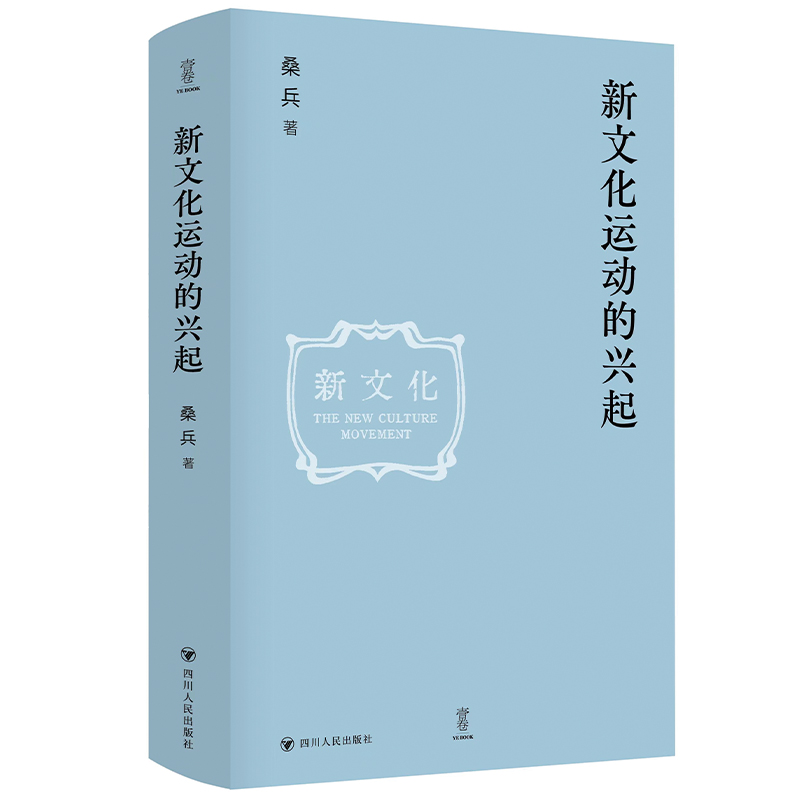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55.90
折扣购买: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壹卷
ISBN: 9787220138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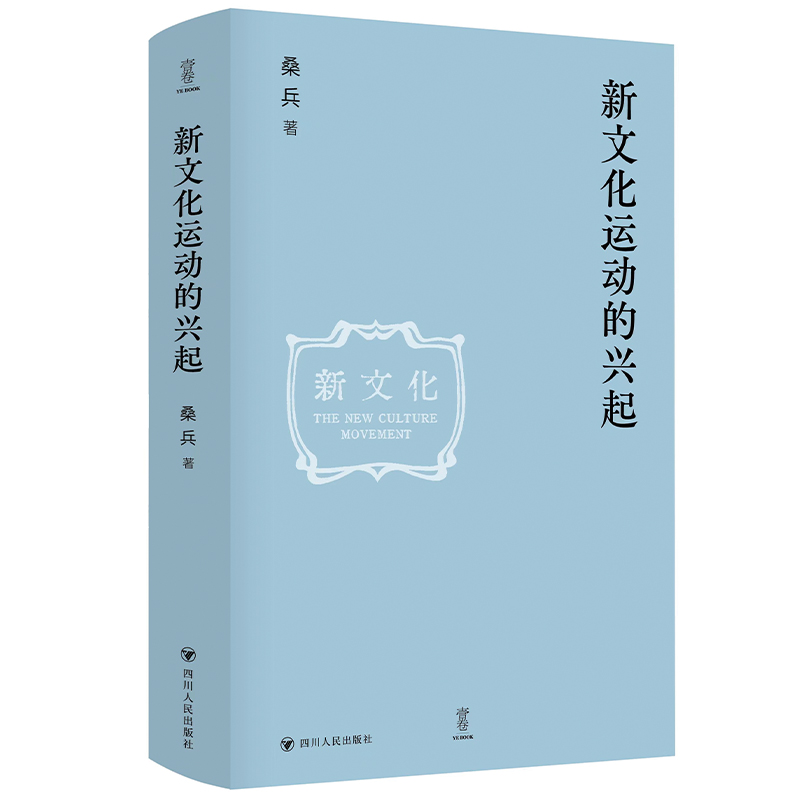
桑兵,河北威县人,原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首位历史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清代以来的学术、大学与近代中国、近代中日关系史、大学与近代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国学与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抗日战争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治学的门径与取法》《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等十几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绪论? 新文化运动史的逼真与如实 第一节? 重写大历史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重写大历史计划“五四与新文化 运动系列”中的一部,因为篇幅过大,分为两本,这一本叙述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演进,下一本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反省、下 限、后续以及历史叙述的形成。两本书包括了新文化运动自身 的发生发展、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阶段演进、历来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指认及纪念、各方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叙述 的形成以及逐渐约定俗成为教科书和一般历史的演化进程。依 照原有的时空顺序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 合为一体,构成比较完整的新文化运动史。 重写大历史的动因之一,是鉴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在 一些过去用力较多的领域,似乎呈现出无由精进的局面,新进 者误解偏信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之说,一味寻找前人未见的新材料,试图填补自己视而不见的所谓空白,或是以为历 史真相大都仍然深藏于尘封已久的秘籍密档之中,必须解封揭 秘才能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结果不断以刀耕火种的粗放方 式垦荒拓殖,却无力考究深耕细作,以至于研究的水准始终不 能精细化。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又长时间重心取向 偏重于学术以外,而各类史料极大丰富,相应地历史事实的繁 复程度也大为增加,如果依照现有状况就已经可以束之高阁, 则古代史的研究早就没有继续进行的空间及必要。如此一来, 中国近现代史很难摆脱较为粗疏的状态,进入更高一级的发展 阶段。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自我反省明显不足, 反而对相关质疑不以为然。例如原来以1919年为下限的中国近 代史有三次革命高潮之说,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 在以革命史为导向的时代,三次高潮的研究投入的人力物力自 然较多,成效也较大。随着现实中革命热潮的退去,革命史观 逐渐淡出,即使研究革命问题,也不再循着革命史观的理路, 甚至重大的革命事件,已少有专门研究之人。如今接续前人在 这些领域的工作并且努力更上层楼的来者,犹如凤毛麟角。 然而,已有的成就固然可观,相较于所面对的历史问题的 繁复,至多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相当 漫长。这不仅是激励,也是实情。虽然不是全外行却并非专家 如我,在诸如此类的领域随手可以列举数十乃至上百项能够形成专书的课题,整体而言说是仅仅过了开头难的阶段,应该 不是故作大言高论。即使在未必以革命史为导向的域外或海 峡对岸,类似情形也普遍存在。辛亥百年之际的民国肇建研讨 会上,曾经提示时间虽已过去一个世纪,但是民国究竟如何开 国,可以说还是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五四与新文化运 动同样如此,历经百年沧桑,几乎年年纪念,可是时过境迁,随 着语境的变化,每年各方纪念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看似大同, 其实差异也不可小觑。而且由于各自阐述的重点有别,久而久 之,后来的学术性纪念非但不一定逐渐接近历史本相,反而不 断增添各式各样的后见,以至于历史叙述与其本事渐行渐远。 类似的意见引起一些质疑,言下之意是未免夸大其词。 专家们觉得自己耕耘过的领地已经剩义无多,毋庸置喙,必须 拓展创新,或转移阵地以另谋生路,或扩张材料以填补空白, 否则困守原地,只能日趋萎缩,鲜有生机。于是乎人人都想预 流,反而导致无流可预。要消除种种疑虑,窃以为最好的回应 是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在相关领域做出几个案例,以示所言 不虚,绝非故标高的。 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由虚向实的同时,似乎有 意识地避开历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一方面,选题往往相 当偏门,有意回避过往研究较为成熟的部分,如三次革命高潮 之类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即使涉及一些重大问题,也尽可 能避而不谈,以免陷入难以厘清的纠葛。这样的取向,一定程度是对以往的各种论战看似热闹非凡,却对具体历史的研究未 能实际推进的反弹,有些内行外行都能畅所欲言的论题大而无 当,而且多为后设,并非从历史事实之中得出,彼此相争不 已,往往陷入意气之争,结果各执一词,无益于实效。新进不 知来龙去脉,觉得无谓,于是敬而远之,连带导致历史上实在 的大事件大问题也被弃置不顾。尽管治史到精深处不嫌琐碎, 可是如果一味枝枝节节,不识大体,就不仅是一堆散钱不能成 串,更容易陷入支离破碎、东扯西拉的坊间闲谈。 概言之,目前的研究普遍而言存在显而易见的偏向,一则 历史研究理应整体之下研究具体,不知具体所在的本来位置及 其前后左右的联系,看似深入的具体,很可能导致整体偏差而 不自知。二则被忽视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往往具有枢纽性, 不能把握得当,势必影响各种具体历史的认识。三则分科治学 的架构之下,加上门类过于狭窄的专业训练,形成小圈子的竖 井化眼界,研治相同的历史问题,不同的学术背景非但未能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反而彼此抵牾,形成相异相悖的判断,似 乎所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事实。革命史、基层社会研究和 科举停罢对于近代乡村权势的影响看法大相径庭,即为典型案 例。尽管学术背景有别,各有侧重情有可原,各自的论述看似 也能够自洽,可是对象相同,问题相近,总不至于差若天渊, 全然不能沟通。类似的情形并非个别,只是分门别类的小圈子 学术生态之下,身处其中者习以为常,对于相左的材料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难以察觉而已。 所谓重写大历史,并非组织大型化的通史或专史系列,通 史未必通,专史或许偏,是清季以来史学撰述中始终未能妥善 解决的弊病之一。即使时空两面看似覆盖完整,相较于材料与 史事,仍然是先验地选择部分,并且或多或少脱离了原有的时 空联系,依据后出外来的观念方法重新加以连缀组装。由于先 有预设,又不能贯通,无论通史专史,都不免与史事本相若即 若离,流于表面肤浅。 所谓大问题,也不是以往聚讼纷纭的争论焦点,如分期、主 线、阶段,等等,这些主要是历史认识的范畴,而不是历史事实 的认定。另外有的问题确系历史事实,却仅仅被当作历史认识 来对待,如帝国主义。今人用现行的帝国主义概念理论分析研究 近代史上的相关事实,和近代不同时期中国人使用意涵有别的 帝国主义概念进行言说,是两个相互关联同时又分别显然的问 题。现有论著,几乎都是将帝国主义作为既定概念来指认和看待 所有相关的历史事实,并以此为据进行叙述,以至于模糊了二者 的分别,也就无从考究彼此的联系。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类似,如 果无视汉族的概念受域外观念的影响形成于清季的事实,理所 当然地将名实相符的汉族历史上溯到汉代甚至先秦,势必使得 看似条理清晰的汉族历史与历史上汉与非汉关系的史事相去甚 远,从而可能会严重妨碍汉族形成史的梳理和探究。 研究大历史,理应着重关注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尤其是重大事件当中的重大问题。这些事件和问题,往往具有贯通、 重现和解读历史整体的枢纽性作用。按理说,尽管中国近现代 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又较长时间受学术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制约 影响,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毕竟是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应 该认识较为深入,把握较为妥帖,否则难以进行相关研究和表 述。然而实情似乎并不令人乐观。许多基本观念和关键概念, 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而研究者又缺乏足够的自觉,不能察觉 事实与认识的差异,甚至造成背反,即运用与史事不合的观念 概念,才能进入研究和表述的舒适区,否则就会陷入失语失忆 状态,无法理解文本和表述事实,由此造成历史事实与历史认 识、历史叙述之间严重脱节,使得认识与叙述变得似是而非。 或者担心大历史已成固化式结论,不宜甚至不能重新审 视。此说看似有所依据,实则于理不合,于事不符。治史首要 实事求是,与中国古今思想文化的理路高度一致;比较一个世 纪以来各种类型的文本,不难发现即使在教科书和特定通史读 本的层面,随着历史研究的进展,相关史事的认定与论述始终 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由此可见基本的轨则仍具决定性作 用,固定的结论必须以事实为基准和依据。除了别有用心的影 射史学,或等而下之的翻案钩沉,严谨的学术研究只会增进历 史认知而不是造成紊乱。至于宣称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因 而怀疑其中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大概率是居心叵测者心术不 正,不相信历史发展总要顺天应人。如果胜利都由阴谋而来,人类进步如何实现?政治军事外交,当然包含谋略,关乎成 败,可是历史上鲜有单靠权术可以成就大业的范例。见不得人 的密谋不可能成为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天下大势,才是把握大 历史脉动的关键所在。 收起全部>>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研究也长期是近现代史领域中的“显学”,百年以来,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许多论述似乎已成所谓固化共识。但有心者若深耕史料,细究其中,不难发现通行的诸多相关叙述,与历史实情仍有相当的抵牾,各种具体史实的叙述和认识存在不少误读错解。近现代史去今未远,但后来研究者或避重就轻视而不见,或不求甚解一笔带过,遂至于百年之后,事实反而愈发不明。本书旨在重审熟知历史,还原细节及其联系,不仅纠正偏蔽,亦可指示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