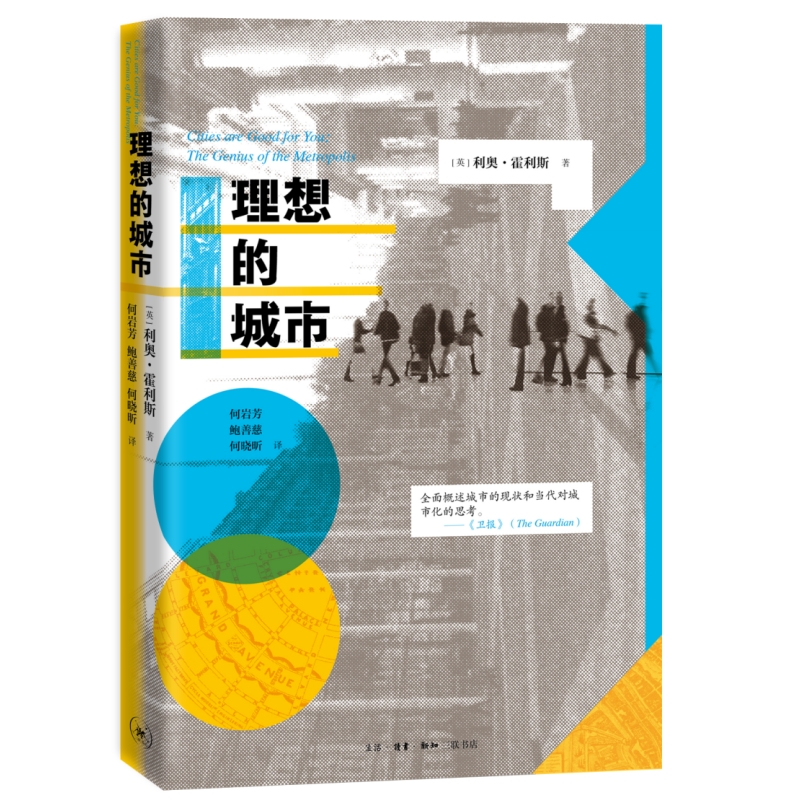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55.25
折扣购买: 理想的城市
ISBN: 9787108077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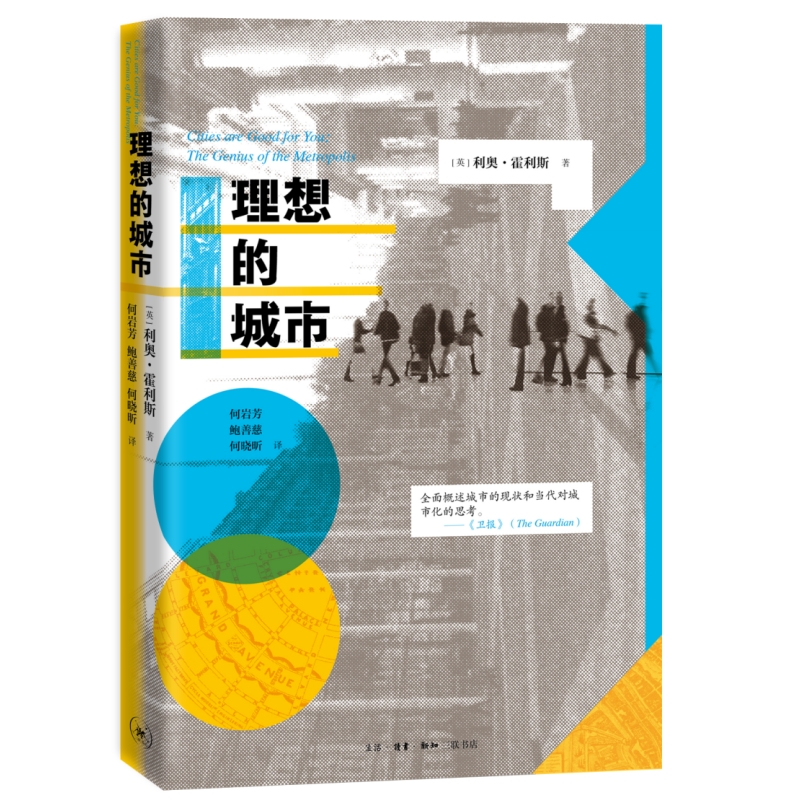
利奥·霍利斯(Leo Hollis),1972年生于伦敦,曾就读斯托尼赫斯特学院(Stonyhurst College),后进入东英格利亚大学学习历史。著有《伦敦的崛起》《伦敦的石头》《理想的城市》等,并定期为英国《新政治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每日电讯报》等撰写文章。
社区复兴 随着世界人口日益城市化,重新定义社区成为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如今,涌入城市的个人、家庭以及团体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来到的地方如此庞大且多样化,以至于不能简单地用一个身份来进行定义。社区可能包含许多元素,一处共享的空间、一种行事方式以及人本身,然而,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则不限于任何单一元素,而是一个综合过程。它是一种将地方、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结合于一体的生态。 但是,聚集而居似乎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太多的人挤在狭小的空间,让城市变成一颗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对比巴黎沙龙之夜与上下九千年的都市发展史,某些地方表明,社区问题已然成为棘手的危机。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危机? 人是群居动物,天生就爱挤在一起。尽管我们常常被教导说,作为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然而,适者生存是游戏的唯一规则。人们寻找彼此并组建社区的行为刻在了基因里。人是社会性动物,因此,城市是最适宜的地方。我们的个性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塑造的。我们分享共同的语言。与他人的联系让我们更快乐、更聪明、更有创意。正是彼此合作的能力使人类得以生存至今。共同协作助力解决复杂难题,让人与人彼此联系,强化社会纽带。正如进化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Martin Novak)所言:“合作是进化的总建筑师。” 人类的相互协作和聚集而居到底能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常常令我们难以置信。下面仅以“一群人”为例。2011 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想看看能否科学地计算出一大群人在街上行走的集体行为。拟考察的议题包括:人们是否遵守某些特定的交通规则?繁忙的人行道是否一片混乱,因为人们相互碰撞,像随机乱滚的桌球?通过使用跟踪设备,迈赫迪·穆萨伊德(Medhi Moussaid)的发现出人意料:在测试的所有情况下,拥挤的行人都会迅速成为一个复杂系统,并开始自我组织。几乎从一开始,他们就会分成两条通道,允许与自己反方向行进的人通行。遇到堵塞时,各自又会遵从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尽量靠边走以保持道路通畅。 虽然这种调节纯属随机,然而有趣的是,行人的原居地会对其选择产生影响。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人们本能地选择向右移动。而在亚洲很多地区,人们却是习惯向左移动。通常情况下,这不会带来无法应对的局面,但如果世界各地的游客大批同时聚集到同一空间,譬如奥运会或宗教朝觐,很可能就会导致混乱。 这种混乱的另一个困境是,这些行人大多都不是单独行动:通常有70% 的人分属于某个较小的次群体。当三人或更多人一起行走时,他们会根据步行的速度形成队形。如果行走节奏很快,他们通常采用冲锋式的Λ 形,即一个领头人冲在前面,两个小队跟在后面。如果行走节奏稍慢,小组的队形经常会形成一个U 或V 形, 此时,中心人物会走在最后面。 此外,正如奥斯卡·王尔德形容所有的伦敦人看起来都像要赶不上火车了一样,不同国籍的人行走的速度也会不同。在一项开创性的实验中,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对31座城市的平均步行速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前十名(都柏林、阿姆斯特丹、伯尔尼、苏黎世、伦敦、法兰克福、纽约、东京、巴黎、内罗毕、罗马)中有九名是富裕城市。显然,赚钱能力、生活成本以及时间精度等经济因素是决定速度快慢的关键。当时间就是金钱时,我们往往会加快步伐。 基于生物学需求,人与人需要团结在一起。但是,如何把握人类抱团的紧密程度,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与人能够团结在一起,通常需要遵从一定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也因地而异。社区的问题常常源于对规则的理解不同。 要融入已经成熟的社区,常会面临人与人之间过分亲近的问题。让-保罗·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不过,这位烟不离手的存在主义者此说谬矣。我们最好还是回到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哈德逊街社区。从人与人的随机聚集到形成一个社区,需要综合长期积累的日常活动和人际关系,并与当下发生的各种联系交织在一起。社区不是一个有着强韧纽带和义务约束的家庭,而是一个由弱联系、熟悉的面孔以及约定俗成的礼仪共同组成的网络,动荡不定,不断在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密度(人与人共享空间的必要条件)的作用举足轻重。从简·雅各布斯居住的格林威治村,我们发现: 人决意要拥有最起码的隐私,与此同时,又希望与周围的他人有着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一个好的城市街区,便是能够在这两大需求之间获得奇妙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对诸多敏感细节的妥善经营。实施的一方与接受的一方都是如此随意,以至于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人口密度定义了社区,也定义了城市。关键问题是,人满为患时,疾病可以通过社区这个网络摧毁整个街区。一旦拥挤的程度超过临界点,城市中的老城区就容易变成“贫民窟”。这样的社区就像一辆超载的公共汽车,让人不得不等待下一班。它也好比一份超长的社会性福利住房轮候名单,让许许多多的儿童陷入贫困(纵然离伦敦的富人区只有几百码远)。随着未来三十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密度很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世界上那些基础设施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地区而言。与印度孟买贫民窟水龙头前等着接水的长队等量齐观的,是尼日利亚拉各斯堵塞长达十小时的车辆长龙。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密集居住的优点。在抨击城市过度拥挤带来的问题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住在一起的好处。我们现在知道,大型的、密集的城市更有创造性,通过弱联系构建的网络、人口的多样性以及更激烈的竞争促进了创新。城市的高密度也会影响生育率,降低平均每个家庭拥有的子女数量。它也降低了人均消耗的能源,提高了日常生活的效率和生产力。也许最出人意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交往可能让人表现得更好。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身份不明的一大群人聚到一起容易变成具有攻击性的暴民,事实上人口的密集促进了文明。 城市化是21世纪的主旋律。目前,全球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一比例将继续上升。但城市的未来并不一定“一地鸡毛”。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可能更环保,虽有些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