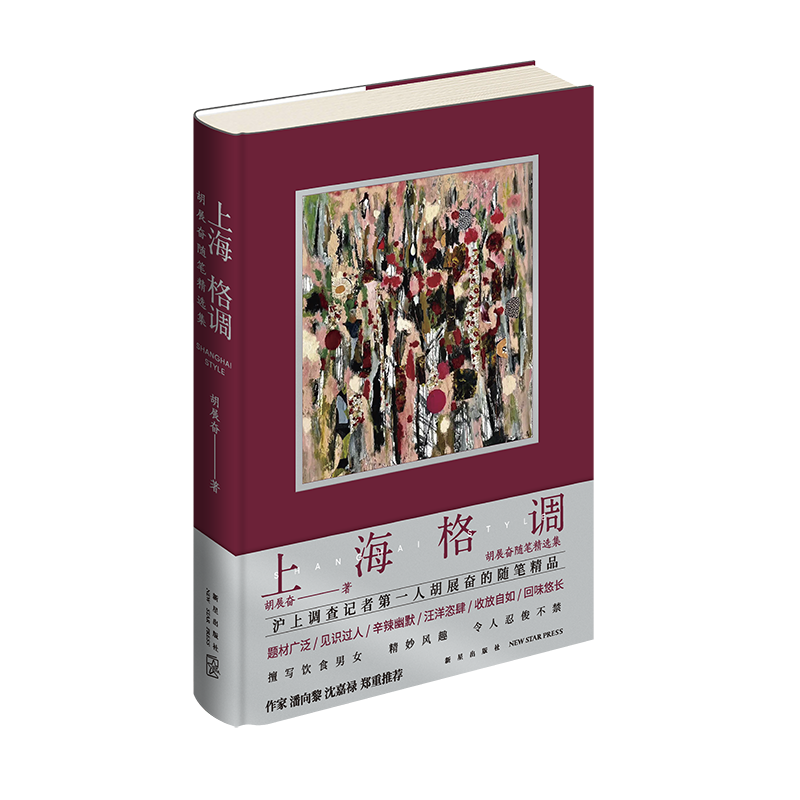
出版社: 新星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上海格调:胡展奋随笔精选集
ISBN: 9787513353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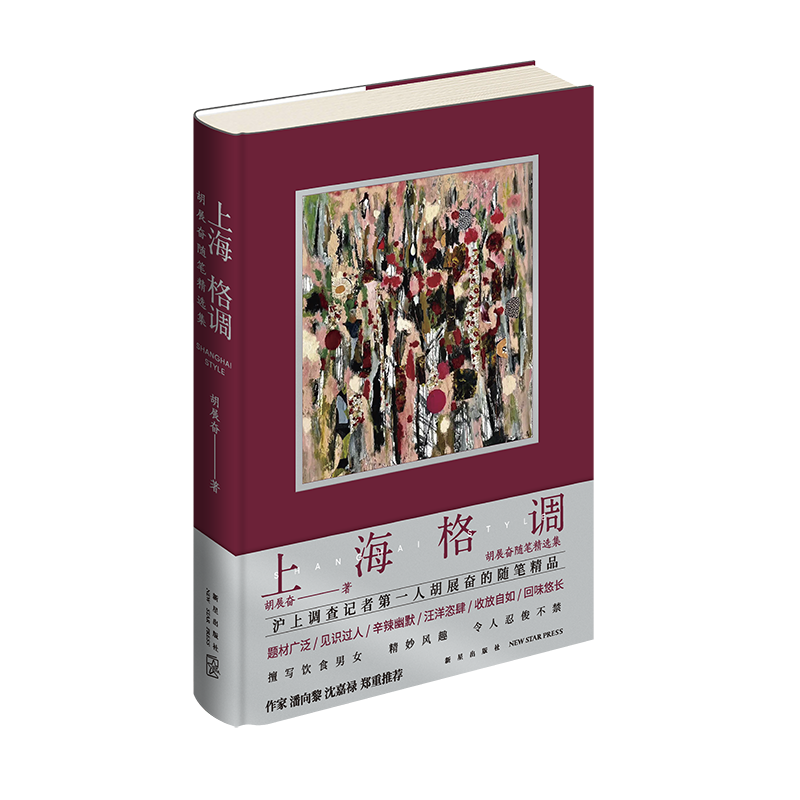
胡展奋,1955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中国作协会员。1986年起历任《康复》杂志编辑部主任,《劳动报》特稿部主任,《新民周刊》编委、特稿部主任、主笔,还是华东师大兼职教授。他也是南方周末、文汇报、新民周刊等媒体的专栏作家,著有《黄金的挽歌》《我的最后一张底牌》《等鱼断气》等。
自序 “沪上第一调查记者”胡展奋写随笔,从第一篇算起的话,也三十五年了。新星出版社要给他出一本随笔精选集,他知道了既欣喜又惶恐。 从文的最忌被称“第一”,这道理他明白。但“第一调查记者”乃百度强加给他的标签,多次投诉无效,不知道的都以为是他自己操弄的,还装傻,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又要出“精品”,国内随笔名家多多,精品多多,他怕他的“精”徒有其名而贻笑大方。这是实话。 高兴的是,他的随笔总算有出版社以“精品”的名头出版了。花谁不争艳,人谁没虚荣。于是就像旧时的深闺怨妇,既想幽会又要牌坊,七十岁之前想给自己树一个旌表,不亦人之常情乎! 但他对自己非常不满。天下文章比他好的为什么恁多!尤其写随笔的,笔绽莲花、才高八斗的多到爆棚。鼠标一点,无非人生华妙,绣口一开,即见世相纷披。歌颂天地造物的,挥毫立就万类之瑰丽;索赜心灵微观的,遣笔尽显神明之深邃。或严父慈母的懿言嘉行,或乡党闾里的古井微澜,或市廛百态的荣枯盛衰,但凡人间悲欢离合、灵肉升降、业界传奇、衣冠优孟,那些妙笔无所不窥,无所不及,他因此常想,含英咀华的本事都传了他该多好! 虽然是实话,也符合人性,但他是个真小人无疑。 事实上,此人最先什么也不是。矿山附近爬出来,突然做了记者,并且在南京东路的《康复》杂志上班,左“文汇”,右“解放”,南边还有“大壶春”。从天天鸡鸣狗盗、荒原野壑,到天天德大牛排、外滩钟声,他不能不信主宰人之一生的是命运。 因此,他做新闻非常投入,上手就是调查记者。多年后一直做到案惊中央,文惊“纽时”,两度获评“萌芽文学奖”,先后获评“腾讯”“南周”年度人物。故,尽管其言行时有放诞,但有的事毕竟不能胡扯,不是说啥都有记忆的吗? 兀那展奋本以为可以一直风光“调查”下去的,不料世事无常,他那个行当渐渐被手机新闻废了,惆怅之余便重新去寻随笔。 不是说人生除了生死就都是擦伤吗,但随笔也不是容易写的。说“重新”,是因为当年他第一篇见报的文字就是随笔。第一篇随笔《快乐的逗号》,据称是1987年的秋天写的,之所以记得真切,是因为那年9月他母亲离世,此文就是悼母的。 随笔大抵是散文的一种,之所以叫“随笔”,有人以为可以“随便写写”或“谁都能写”,展奋以为大谬不然。须知随笔真正写到“随便写写”而羚羊挂角、踏雪无痕,乃是随笔的天花板,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看起来“随意”而已,其实,正如王羲之的无上书法,貌似天心直达的背后,焉知不是日日苦练而把一泓池塘妥妥写黑的旷世奇功? 如此的见解是否暗示胡展奋的随笔写得很好呢?当然不是。他一个原生新闻的,写随笔本来就是抢别人生意,半路出家,应该识相。但其人习惯大言不惭,就姑妄让他再来几句。 随笔无非考校发现力、整合力、表达力,展奋认为发现力最重要:内在的发现,外在的发现;在场的发现,不在场的发现。没有敏锐、独具的发现,“整合”就是洗稿,“表达”就是炫技。发现,还得有格调,在他,随笔应该就是带上海视角、上海格调的“一个上海人”的发现。 本书入选篇目顾及各个时期,自1987年至今,前十年少些,中间十年稍多些,最后十七年最密集。基本出自“南周”“笔会”“夜光杯”以及《新民周刊》的专栏,恰好印证了他调查新闻越做越少、随笔越写越多的曲线。只是没有标注发表时间,有点遗憾。 书分五辑,他最看重的是那辑“人间世”,里面尽是他的情感宣泄。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搞调查的要那么丰富的情感干什么?按他们的“生意经”,一,不和调查对象为友;二,调查结束立刻脱离现场;三,不和当地发生任何经济往来——他应该是个寡情的人。 也许这也属于“上海格调” ——无情生意经,有情始做人。 “上海格调”,乃东西方文化的优化结晶,具有极丰的内涵和极高的段位。本书只是努力向往着“上海格调”,而后者更像真理,你永远只能接近再接近,却无法包养它,更无法穷尽它。 他应该感谢著名摄影家雍和,大师提供的作品让他离“上海格调”又近了一步。 向往着可望而不可即的“上海格调”,展奋时显尴尬。我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头搨:有谁在乎你的尴尬呢?没看到每个人都急着说话,每个人都没把话说完吗! 没听说人生忽如寄,莫负茶、汤、好天气吗?都快古稀了。歇阁来! 胡展奋2023年秋于田林大风楼 等鱼断气 清明时节有微雨。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父亲。他这辈子对我们三个孩子不怎么样,但对母亲是没说的。 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当时求诊于龙华医院的老中医,老中医开出了一剂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他认为,患者急需补充优质蛋白,既是优质蛋白,又能消肿利水的首推鲜活鲫鱼。且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那个时候,物质高度匮乏,菜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的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他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 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黑市买来鲫鱼马上操作,第一步是为她“退黄”,剖二百克鲜鱼熬约三十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成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翳即消退,服用了一个月,黄疸全部退去,便去老中医处报捷,老中医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老爸一听,傻了,老中医这可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啊,时值冬令,鲫鱼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早把家里掏空了,而且老中医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和人在鱼摊前拗作一团。 老爸听了不响。老中医继续说,今天开始,二十天内不能碰酱油和盐。“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老中医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快去看看!” 天已擦黑。路灯下,远远地看到他蹲着,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儿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两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西北风像伤风的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身子冻得簌簌发抖。但,仍然坚定地蹲着。 这是1969年的冬天。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伊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要等其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规矩,鱼一死,就卖半价,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翕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地叫了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侬!蹲了两个钟头伊港!”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掣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了鱼肠,那鱼鳃还在一翕一翕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老爸就成了“老蹲”,只要有耐心,不怕等不到刚断气的鱼。因为刚死的鱼或弥留之鱼,尽管半价,价格还是高于久死之鱼,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 日子久了,他还蹲出了经验,并授我心法:“背脊黑黑的鲫鱼,不要去蹲守,有得拖辰光了。只有濒死之鱼,身上鳞片才会越来越黄、越来越白,及时一蹲,可以少吃多少西北风!” 但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的蹲守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水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高烧发到四十度。 眼见得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篑,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也不忍,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不收钱,后来读书,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褪去。 这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的暖气吹。 蒲扇缘 “惨了”!当旧金山海关把我那猥琐的蒲扇从行李箱里揪出来的一刹那,我已接近半昏迷。 我的英语属“永不开口”级。太太只会蹦几个单词,和海关的对白便当场呈“二战蛙跳”状。最后他们擎着猪头大小的蒲扇,如同逮住了违禁偷运的黑科技,高视阔步地把我俩直送“小黑屋”。 一路上把肠子悔青。性躁,怕热。赴美前,于杂沓行李中,临行还不忘塞进了这把蒲扇。 当下完了。听口气好像涉嫌什么“境外不明植物入侵”。 有顷,远远地来了一位亚裔签证官。刀条脸,竖纹布满两颊。类似的脸型一看就不好说话。我现在只祈求把蒲扇没收了事,别坏人。 她先检查我们的证件。没问题。接着,注目肇事者。不料一看到蒲扇,本来硬痂似的她立刻蓬松了,眼神柔和了,用华语招呼说,别紧张,只是例行程序。然后拿起蒲扇,掂了掂,转了转,侧着脸,略带调侃地扇几下,手势之熟如视己物,边扇边对同事解释,只是驱暑用具,木质干制品,不存在“异类植物入侵”的可能。 她微笑地把蒲扇还给我,只说了半句话:“我们小时候……” 一把蒲扇,居然摆平了签证官,我很意外。“我们小时候……”她仅仅想说她小时候的事吗?我特别注意到了这个“我们”。 没几天就是旧金山大伯九十五岁的生日盛宴。参加聚会的大都是他“南模校友会”的同学,都生活美国多年,但一见我手中的蒲扇都呆萌了,那意思大抵是,咦?格地方,会有这个宝贝?! 一老男头若雄狮,比大伯小十五岁,后来知道他是钢琴家,原先故作贝多芬状,现在突然放下了矜持,客气地向我要过蒲扇,细细打量,反复摩挲。 “小时候,蒲扇是弄堂的夏天之王”。雄狮老人的回忆像他刚才的钢琴演奏一样,沉稳中饱含柔情:上海那种热,是呛人的湿热。那时,电扇只是少数邻居的奢侈品,所以一出梅,就是满弄堂的蒲扇声,很多人家“咵哧,咵哧”地摇着,响到天亮。 看一家主妇是否会持家,夏天看蒲扇。乘凉时亮扇。好人家的蒲扇都是布条绲边的,摇起来无声无息。“烂潦人家”的蒲扇直接就是凤爪,摇起来,前楼、客堂都听见。但无论“好人家”还是“烂人家”,小时候的风景,就是一早满弄堂的生煤炉,满弄堂的烟。 那时的上海还没流行煤饼,煤球炉很少能捂过夜的。我们弄堂我是生煤炉大王,诀窍是煤炉先摆下风口,人站上风头,否则会被烟熏死,其次燃料要分层级,依次是报纸、细柴梗、柴爿、煤球——煤球或后来的煤饼,架在柴爿上应该镂空,不能捂实,初始应该轻轻地扇让报纸和细柴充分引燃粗柴爿,一旦柴爿红了,就猛扇,给大火,让柴爿更旺,烧着煤球后,再继以小火,火头稍蓝,就短促、小幅度地扇,扇面自下而上地斜着刮,若有铁皮小烟囱,则觑见煤球与柴爿的接触点发红了,就把烟囱戴上去,让它慢慢拔风自燃。 当时最大的误区,就是生煤炉习惯用破扇。殊不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破扇漏风,有啥用。我煤炉生得好,就是家里舍得用好扇,镶了绲边的蒲扇照样生煤炉,效率是别人的二倍甚至三倍。 他悠悠地摇了几下,把扇子递给了座右的校友。那位老人细瘦,衣着华贵,大企业家,原先下唇微翘,睥睨四周,待到接过蒲扇,就谦卑了不少。“弄堂里,赶苍蝇,拍蚊子,责备孩子做功课,甚至摇着扇子吵相骂——‘啪啪啪’地,都是蒲扇。”他回忆说,“我的蒲扇记忆最深的是乘风凉”。 当年最大的聊天平台就是乘风凉。我家亲戚多,我从小喜欢串门。淮海坊和步高里的乘风凉,爱讲旧社会大亨故事,后来不时兴讲了,就聊“杨乃武小白菜”或“梁山伯祝英台”,再后来聊“绿色的尸体”或《参考消息》里的趣闻,比较文;虹镇老街和蓬莱路的亲戚就喜欢摇着蒲扇讲鬼故事了,什么鬼都有,讲到紧张处,扇子都没人摇了,收摊后大家不敢回家,挤作一堆,这时往往有人大叫一声:鬼来喽!便头皮绷紧,尖叫着一哄而散。一次奔逃中,我的蒲扇掉井里了…… 坐我左手的是一对南模夫妇,男的是直升机专家,女的叫柳信美,拿过蒲扇却哭了,弄得众人很没劲。“我从小爱生痱子,”她回忆说,“每到夏天,浑身都是,还有脓头,又痒又热地睡不着,我爸爸每个晚上都非常耐心地摇着蒲扇为我驱热,直到我睡着,他有时累极,也趴在床边睡着。1982年的夏天,肺癌晚期的他已经弥留,家里没有电扇,我也不停地为他摇蒲扇,直到他咽气……” 盛大的生日酒会,记不清多少南模老人向我要去蒲扇,边嗫嚅着“我们小时候”,边上下翻转着欣赏,那些举止怎么都近亲繁殖,会一模一样,草草的一把蒲扇,忽然成了旧金山社交公约数,哪怕素昧平生的人摇扇互颔之际,突然都像熟人,纷纷交换名片,互刷微信,已记不清和多少人合影,但每次合影蒲扇必居中心。 临回国,大伯要我把蒲扇留下。他将献给旧金山“南模校友会”永志纪念。 介子推那坨肉 清明前偶读《东周列国志》,觉得最精彩的桥段应该就是重耳(晋文公)出亡流浪十九年,最后“老来红”,一举被尊为天下霸主,堪称“中国的奥德赛传奇”。 不过,如果没有介子推,故事就没了。 公子重耳被父亲晋献公和“小娘”骊姬迫害,匆匆离开晋国流亡,有十几位臣子追随他,介子推是其中之一。一次重耳断炊多日,饿晕了,介子推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熬汤喝。后来重耳得到秦国的帮助,返回晋国继承君位,群臣纷纷表功争宠。介子推不屑与此辈为伍,躲进绵山隐居。重耳找他,遍寻不见,乃放火烧山,想把他赶出来。没想介子推坚持不出,与老母一起被烧死。重耳感念介子推的高节,命令在其死难日禁火,后延续成寒食节,又渐渐演变为清明节。 这里有个问题不容回避:经历长期的饥饿颠沛后,介子推割股救主是否可信?重创之余何以能继续逃亡? 让我们回到历史。考其流亡图,介子推“割股”大约发生在逃离翟国之后。这是相当狼狈的一次遭遇,此前重耳在蒲国已经遇刺,被他侥幸逃过,此次杀手又来突袭,重耳君臣闻讯再次仓皇出逃,只带金帛,未带干粮,长途跋涉之后,负责管钱(金帛)的亲信又携款叛逃,丢了盘缠,重耳一行山穷水尽地投奔卫国,须知重耳出奔的翟国在今天的陕西省耀县、富平一带,而卫国在今日河南与山东的交界处,两地相距近千里,逃亡者几乎一路行乞,经数十日的挣扎,满望能在卫国吃口饱饭,没想饥寒交加地到达卫国,却遭卫君鄙视而拒之城外,只得枵腹就途,再度跋涉,勉强挣扎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一棵大树下集体躺平,重耳已饿得虚脱,忽闻肉香,介子推捧肉汤一盂以进,重耳一口气喝了才问介子推哪来的美食,后者回禀是自己的大腿肉,重耳听了悲愤欲绝。 笔者曾就此组织过课堂讨论,长期的饥饿流亡,随从已经形同饿殍,受群臣“特供”的重耳尚且饿成这样,他人可想而知,我们从小看到的连环画,都把介子推画得枯槁不堪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虽然现代解剖常识告诉我们,再枯槁,大腿内侧总是肉质略丰的,但万万动不得,因为有大动脉,断之立马失血而死;大腿正面与外侧也有动脉,但是众多的小动脉,偏偏此处肌肉贫瘠,挖浅了无所得,于重耳无补。深剜则危。也就是比大腿内侧剜挖得更深,方能有所获,但如此深剜,小动脉几乎全部切断,失血的危险并不逊于前者,结果至少不逊于战场重创,动弹尚且困难,何况继续逃亡还有致命的感染。有学生说,可以立即结扎止血呀——很遗憾,解剖常识再次告诉我们,股动脉无论大小都隐藏很深,结扎止血基本无效。笔者多年前有个安徽的同事进深山打猎而误扣扳机,股外侧小动脉齐齐被打断,他是复员军人,懂点自救知识,赶紧用随身的绳索以绞盘原理紧扎止血,但仍止不住而大量失血死去。 也有人大胆推断介子推切割的是自己的臀部组织。可惜,角度忒刁,拗身运刀,殊难自圆,我当场请同学比拟了一下,结果如同提着自己头发离地,难。又曰,介子推可以请他人动手啊!问题是,以介子推的狷介孤傲,割股尚且不欲人知,如此张扬岂不更有违其初衷? 读古书,常会发现类似的疑点。好比项羽临败曾对他的死忠粉小范围地说,“是老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这话,谁听到的?因为乌江边,项王与亲兵最后都战死了呀! 瘸腿“丁克勒” 上海市的南部,有个已经取消了行政建制的老城区叫“南市区”,它和黄浦区合并多年,但习惯上那些地方我们还是叫“南市”。 我和南市区的缘分不浅,小时候我的养父养母就住南市局门路,我在那里生活过多年,1991年我所供职的《康复》杂志分房,我分到了蒙自路的一套“一室半”公房,觉得很幸福。蒙自路的隔壁就是局门路,局门路的隔壁就是制造局路,三条路紧挨着,当然制造局路是老大,制造局路因著名的“江南制造局”而命名,辛亥革命期间,新军沪督陈其美曾率军“三打制造局”。战事打得非常激烈,制造局路与局门路附近血流遍地,但如今制造局路却因“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而出名,这家医院以整容外科、口腔颌面外科之成就卓越而驰誉全国,而我和丁克勒的相识却是很“小儿科”的。 1995年的暑天,儿子刚读小学,入学不久就感冒发烧,进儿科急诊室挂盐水,旁边一个女孩也在挂盐水,看她和儿子聊得热乎,一问才知道居然是同班同学,家住制造局路,陪她的胖老头,是她外公,年近七旬,腿瘸,医院里的人头很熟,大家都叫他“丁克勒”。往后三天,两个小孩约好了同样的时间来挂盐水,我也就和丁克勒聊了三天,从此很熟了。 上海人习惯把生活方式洋派、仪表举止西化、人情世故通达的人叫作“老克勒”,上迄晚清,上海十里洋场就流行“克勒”这个洋泾浜名词,就是英文Color的谐音。Color 的原意是颜色、色彩、特色、个性、漂亮……在英文里就有 Color Man 这个词汇,意思就是弹眼而有个性特色的男人。这已经接近我们上海人说的“老克勒”意思了,老,不是说年纪大,而是形容纯度高、级别高,传说首饰店就把三克拉以上的钻石称作“老克拉”,后来的延伸义,变得非常丰富,大抵行事老到,功夫老到,凡事深通窍坎而带点洋绅风度的,都被叫作“老克勒”。 因此丁克勒能被医院上下如此认可“克勒”,当非泛泛之辈。 他大了我三十多岁,那种胖,比较油腻,因为瘸,就拄了根黑漆“斯迪克”(拐杖),反倒像拜伦爵士一样,瘸得饶有风度。不知何故,聊着聊着,又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央商场”——四十多年前,丁克勒靠着中央商场发了不少财。 坐落在南京东路的中央商场源于抗战胜利后,1945年,有人以高价引入了沙市二路16号底层大楼,开设“新康联合商场”,内设九十多个柜台,再加上外面中央弄、沙市一路、沙市二路的马路摊贩,这一带成了倾销美军剩余物资的福地,统称为中央商场。据记载,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每只柜台的租金要五两黄金,美国大兵在上海登陆,善于经营的上海人,用各种方式从他们手里获取剩余物资,除了大量的医疗器械与餐厨杂具外,办公用品、克宁奶粉、牛肉罐头、旅行刀具、望远镜、呢大衣、皮靴、玻璃丝袜等美国货大受欢迎,也形成了“老上海人”普遍爱用美国货的风气,但长期以来的一个疑问是:当年的上海人,具体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拿货的呢? 丁克勒听了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当年的拿货人之一,而且大家都拿不过我!中央商场“美国货”柜台的朋友都要看我的眼色行事。 我听了不断地打量他,快七十的人了,还是油头粉面的大背头,那套老旧西装虽然过气了,但穿在他身上反而很“克勒”,因为“合时令”。 但凡老克勒的西装,冬有冬装,夏有夏装,决不能混淆。冬天的西装之用料,因为要御寒,不是哔叽就是麦尔登、羊绒;夏天的则不是凡立丁就是派力司或毛麻,讲究一个透气挺括。 眼下的丁克勒就是一身浅灰的“派力司”,与人交谈“接口令”很快,属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那一种,问题是,这一类头子活络的生意人,大上海比比皆是,他丁克勒并非特别出挑,而且还瘸了一条腿;那么是不是丁克勒的英语格外好呢?丁克勒的英语的确好,可问题仍然是,当年上海英语出挑的多了去,为什么就偏偏他最拿得到美国货呢? 且听丁克勒慢慢道来。首先,很多生意人虽然英语好,但不去了解美国人,不知道美国水手的心态,他说,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要货要东西,很让美国兵看不起,你急什么呢?其实他有大量的剩余物资要脱手,猴急的应该是他。问题是,一旦你比他还急,他就发飙放刁了,上海老话所谓的“发翘头”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战争一结束,美国兵最想的是什么?赌博?嫖娼?强奸?不!这恰恰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认识误区,当时过度的舆论渲染使大家相信美国兵都喜欢性暴力,其实美国兵最想的是回家!众所周知,美国是个新教徒占其国民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多数的美国人私生活都很保守,循规蹈矩。尤其是在性问题上,美国人的保守态度可能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 在美国,政治人物竞选时都渲染自己对家庭的爱,包括对自己宠物的爱,强调自身私生活的严谨,做出一副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如果政治人物包养情妇,无论是在议会还是政府,必然会丧失支持,甚至身败名裂。此外,许多非政界的公众人物为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也保持私生活的严谨。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很多城市,夜生活并不丰富,晚上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灯红酒绿。在一些宗教影响较强烈的地区,夜晚简直死气沉沉。 因此,美国兵并非都是喝得烂醉而滥嫖滥赌或开着吉普乱撞人的形象。他说:“我当时所接触的美国兵,大都是停在高雄路码头、公平路码头、高阳路码头或军工路码头的军舰上的水兵,他们只能在规定的时间上岸,并非随时可以离舰,我当年小本本做过一些记录,当时先后来上海的巡洋舰为巴尔的摩级的圣保罗号(CA-73)、海伦娜号(CA-75)、洛杉矶号(CA-135)和芝加哥号(CA-136),还有轻巡洋舰克里夫兰级的斯普林菲尔德/春田号(CL-66)、阿斯托里亚号(CL-90)和亚特拉大号(CL-104),都曾经到过上海。” “远离家庭的水兵当然很寂寞,也性饥渴,但一般都很胆小,军舰上到处是色情画报和照片,他们就拿那些东西解闷。所以,我的诀窍是,一上船就给他们讲故事,讲东方色彩的家庭故事和言情故事,故事的来源你可能想不到,大都是从鸳鸯蝴蝶派小说比如张恨水的小说里搬来的,后来发现水手们仍嫌传奇性不够,我就直接从‘三言二拍’里搬,什么‘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啦,‘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啦,我大肆篡改,加入很多原先没有的色情细节甚至直接就是黄段子,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堪入目的淫书坏书,比如《绣榻野史》《灯草和尚》,我把它们剪辑了塞进去,听得他们抓耳搔腮,狂吹口哨,而且上了瘾,你说,我会不受欢迎吗?每次去,很远他们就叫了:‘看!瘸子来了!瘸子来了!’” 说到这里,丁克勒不断发出猥琐而带点歉疚的笑声,说:“说实话,我这么做,不太道德,利用美国人的精神空虚做他的生意,但那时也是为了生计,那些美国大兵一旦高兴起来,只收我很少钱,什么派克金笔,司照相机,有的甚至不要钱,特别是美国靴子和大量的罐头食品、棉被、羊毛毯,统统低价卖给我,只要航次结束,回到基地,这些物资都要被当作生活垃圾处理,现在碰到我这样的‘知音’,何不大做人情呢?” “我一旦在高雄路码头、公平路码头、高阳路码头或军工路码头拿到了货,就雇车直接运到家,整理分类后,送到中央商场上柜。” “我发了几年财,结了婚,可惜我这样的坏分子一到1949年以后就没有好日子了,里弄里揭发我和美国人接触密切,我被判劳教,后又改判徒刑……” “我原来是个坏人……现在只是个退了休的老家伙,”他说着不断地擦着汗,“人民政府给我出路,我就过过太平日子,当然,对我来说,最幸福的日子还是1945年到1949年初的日子,在美国军舰,在中央商场,我被大家追捧着,那些日子虽然不很长,也算是难忘的啦!” 五十年前的美国货,他现在只剩了一支派克金笔与一条军用皮带了。他得意地掀起派力司西装给我看,那皮带扣子是黄铜的,相当厚实,皮带更结实,用了五十年了,居然还在用。 当然,他还带着一只卡地亚山度士金表,那可不是美国货,而是为了“老克勒”的腔调而淘来的二手货,因为罩着“Color Man”的光环,谁都会觉得那表,丁克勒至少戴了四十多年了吧! 我们在儿子快进中学时搬离了蒙自路,从此和丁克勒断了联系。 前些年听说他去世了,享年九十岁。 一个人的遭遇 写下这样的标题,一点也没有和俄国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抬杠的意思。我的比方其实很渺小:一个人的遭遇其实和一条虫的遭遇差不多。 “小雪”那一天,几个同龄的朋友邀我观赏蟋蟀恶斗。 事情很平常。但气氛不平常,几个水泥厂的朋友都提前退休了,当年都是和我一样的“文学青年”,现在叫“文青”,三十年过去了,都已退隐,只有我还在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但彼此有多少斤两,都明白得很,隐隐地,都很感慨:“我们的才学何尝输给你?只是机遇不如你啊!” 俗话说,“小雪到,虫恶咬”——眼下小雪节气正是蟋蟀竞斗最惨烈的当口,是骡子是马,都是拉出来“遛”的时候,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伤嫩”和“败老”的结果都出来了。 蟋蟀(沪语“财积”)和人一样,有早熟型、中熟型和晚熟型,不得其时则不得其志,一条虫的命运和一个人的遭遇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小时候蓄过一头名将“黑黄”,就是这样的遭遇。 我们那时候喜欢下午捉蟋蟀,河堤旁一站,水没到胯部,然后舀水浇堤,无数的蟋蟀会跳出来,树洞下尤多,记得“黑黄”刚出土时我们都很激动:“这么大的‘黑财积’!” 那时哪懂什么“黑黄”,只看它“黑铁魄落”的一个,配一副黑牙,体魄大而且柜台型,就由它去斗,一天可斗二十余场,“黑铁魄落”只要黑牙一张,最多两口,对手一定别头就走或者被咬得倒地抽风,一时间弄堂里称起了大王,但不久就碰上了“顶头虎”。 那是一只真正的黄“财积”,浑身披一件黄战袍,六足蜜蜡一样的黄,配一对“钨钢牙”,大家叫它“油纸黄”。说来也怪,牛气冲天的“黑铁魄落”一见“油纸黄”就如同见了鬼魅一样,连连后退,双方合钳,抱夹一滚,“黑铁魄落”居然跳盆逃跑了,捉回来怎么也不开牙了,而且口水淌了一地。大家见状一起哄笑:“大王败鬼(鬼,沪语音‘举’)!大王败鬼!” 我正思想斗争,是否摔死它以挽回自己的面子,弄堂里的“老爷叔”发话了:虫废了,给我吧! 这事很快忘了,大约一个月后,“老爷叔”把我叫去,说请看“一场白戏”,进门才知道是一场恶斗。 对方赫然就是冤家“油纸黄”,但是油色好像褪去一些,“老爷叔”的“黑财积”看上去似曾相识,浑身黑气笼罩,但是“金斗丝、银抹额、乌金翅”,揭盖后撑高缓行,双须矜持地扫动着,一派大将军风度。两虫都是黑钳,见面更不打话,老相识一样,“油纸黄”故技重施,用无敌的钨钢牙夹住“乌金翅”单钳,猛力合钳,但是“乌金翅”却“吃夹还夹”,搭桥以后,用凶猛的“抱夹”还击,跌开后两虫再次合钳,“乌金翅”突发绝命夹,竟然用罕见的“举夹”(霸王举鼎)把“油纸黄”高高举起,猛摔盆壁。可怜的“油纸黄”当场昏死过去。 见我们发呆,“老爷叔”笑了:“认识吗?这就是你的败鬼(举)!”它的品名叫“黑黄”,属于晚熟大将,你早秋就逼它上阵,就叫“伤嫩”,而“油纸黄”呢,是早熟名将,一个月之前正是它当令,“黑黄”怎能是它的对手呢?现在不同了,“油纸黄”的时代结束了,它的主人却还逼它上阵,这叫“败老”;“黑黄”当道的时节来了,你如果让它退休,就叫“失斗”,一条虫的遭遇就是这样。 一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这样。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不该上场的时候,上了场,也叫“伤嫩”;该上场的时候,不让上场,亦叫“失斗”;而该谢幕的时候呢,主人却还逼它上阵,不也叫“败老”?命也运也,天何言哉! 我退休的朋友们,品茶品虫,借虫喻人,胸中颇有郁勃之气,他们哪里知道,我何尝没有尝到“伤嫩”“失斗”和“败老”呢,不说也罢。 回家偶翻班固的《汉武故事》,再次深深感叹命运的无常——汉武帝到郎署见一老翁,白发苍苍,衣衫不整,就问他:“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今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 遇和不遇。一条虫的命运,何尝不是这样。 遇和不遇。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沪上调查记者第一人”胡展奋散文随笔精品